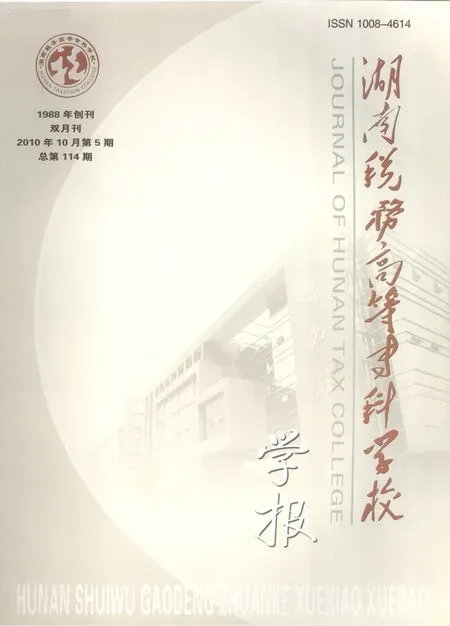莎士比亚之“名”与莎士比亚之“实”——从莎士比亚剧作的著作权争议说开去*
□ 全凤霞
(北京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37)
莎士比亚之“名”与莎士比亚之“实”
——从莎士比亚剧作的著作权争议说开去*
□ 全凤霞
(北京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37)
西方文化界和学术界曾大打莎士比亚著作权争议之战,莎士比亚一度被炒作为一个难解的历史文化之谜,中国也深受其影响。笔者认为,在莎士比亚著作权争议中,最大的偏激之处在于争论者过于关注莎士比亚之“实”。区分莎士比亚之“名”与莎士比亚之“实”有着特殊的意义,应更多地关注莎士比亚之“名”,而少纠缠于莎士比亚之“实”。
作者观;莎士比亚之“名”;莎士比亚之“实”
在人类文明史上,镌刻着一长串闪光的名字,何马,达芬奇,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孔子,庄子……。他们或是思想家,或是艺术家,或是文学家。这些巨匠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给人类带来了无比丰富的精神财富,从而被人们当作神一样供奉在心灵的圣坛上。然而在这些巨匠当中,谁也没有象堪称文学“巨匠之最”的莎士比亚那样曾经引起过一波又一波的“争议之浪”。已故著名学者余虹先生在借鉴国外一些思想家的作者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区分作者之名与作者之实的观点。受其启发,笔者认为,区分莎士比亚之名与莎士比亚之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有助于平息几百年来围绕莎士比亚著作权的种种争议。
一 莎士比亚剧作著作权争议
根据多方考证,莎士比亚出身贫寒卑微,学历学位让人难以启齿,婚姻和家庭生活也堪称不幸,而且似乎也有中途辍学、偷猎贵族园林等不光彩的历史。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幸而又令人头痛的人,却写出了不朽之作。这个极大的“矛盾”便产生出了纷繁多样的疑点。一个中途辍学者有可能写出如此不朽的作品吗?莎氏其人是否存在?他的故乡是不是斯特拉特福?出生在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亚是不是《莎士比亚全集》的作者?“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伊丽莎白时代那位诗人、演员剧作家的真实姓名还是如某些人所断言的“是个笔名或化名”?甚至有人还怀疑莎翁的国籍问题。总之,莎士比亚一度被炒成一个难解的历史文化之谜:到底“谁是真正的莎士比亚”?
据裘国安先生介绍,最早提出怀疑的是一个名叫詹姆斯·威尔莫特的英国人,这发生在莎士比亚逝世 170年的 1785年。此后,各种怀疑论此起彼伏。比如,1857年美国怪僻的老处女迪莉亚·培根写书提出莎剧原是弗朗西斯·培根爵土所著。这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所谓“培根派”。一切口舌之战毫无结果后,终有美国物理学家托马斯·门登霍尔用科学方法,即通过不同长度的词的使用频率来确认不同的作家,证明了培根的写作风格与莎士比亚的完全不像。其他否定莎士比亚剧系他本人所著的理论从 19世纪下半叶以来陆续出现,所指称的捉刀人有几十个,简直无奇不有。历史进入到了 21世纪,西方学术界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兴趣丝毫不逊前辈。更是以作品风格学①为指南,运用先进的电脑技术对海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分析几个世纪前的各个可能的“真莎士比亚”的作品,再结合模式识别技术,以图得出有关莎士比亚生涯新观点的做法。不过,研究结果让否认莎士比亚的那些人深感失望。
关于莎士比亚的剧作是否出自莎翁之手,在中国学界向来也有争议。其中裘克安、方平、辜正坤等莎学专家都曾发出较为有力的声音,以各种理由对莎剧著作权或提出质疑,或进行辩护。
在“莎士比亚是某人的笔名”之争论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某人”;另一个是“笔名”。就“某人”而言,多年来,人们推测出了 50多名可能是“真”莎士比亚的人,其中包括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才华横溢而又高深莫测的克里斯托弗·马洛。关于“笔名”,这将是下文要重点阐述的内容。
二 作者之“名”与作者之“实”
我国当代著名学者余虹在《文学知识学》里,结合前人的思想,提出了要区分作者之“名”与作者之“实”的观点。笔者认为这种作者观有助于熄灭关于莎剧著作权的争议烽烟。
余虹在《文学知识学》一书关于作者的专章中问道,“如果没有作品还存在作者吗?”②因为,就我们日常经验来说,作者仿佛是全部文学活动的起点,没有作者的创作就没有作品,没有作品就没有作者对世界的言说,没有作者对世界的言说就没有读者在世界中对此言说的聆听(阅读)。
传统的作者观是,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这个创作者在作品未出现之前存在着,在作品出现之后也存在着。换句话说,作者是可以与作品分离的实体。然而,自 19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史上出现了反思批判传统作者观的新作者观,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家有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和福柯。罗兰·巴特在《作者的死亡》一文中将作者现象纳入一个新的视野中来观察。在此视野中,传统视野中的作者死了,即那个出现在作品前后、操纵作品来表达自我的人死了。在此视野中的作者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不是一个可以与作品分离的先于和后于作品的存在实体,而是与作品共时存在的存在者。
余虹顺着罗兰·巴特的思路指出,对作品的存在与读者的阅读而言,作品所署之“名”才是真正的作者。作品所署之名可以是作者的笔名也可以是作者的本名。笔名的基本功能是要将作品的作者与写这个作品的真实个人即那个“实体”区分开来,并介入作品的构成。对读者来说,作者就是作品上署名的那个人;只有署名与被署名的作品同在,这个名字是作品的有机部分,它活在阅读的历史中。比如,说《家》的真正作者是巴金而不是李尧棠似乎更为准确。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者只是一个“名”,这个名所指称的“实”与现实生活中那个写作的人所具有的“实”并不统一,但却与作品一体相关,是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是作品的产物。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就提出了作者生产了作品,但作品也生产了作者的思想,艺术家与作品互为本源。没有《阿Q正传》就没有鲁迅,但可以有周树人;没有《子夜》就没有茅盾,但可以有沈德鸿。同样,没有《汉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仲夏夜之梦》和福斯塔夫,就没有我们所崇拜的莎士比亚,但可以有一个作为制鞋匠的儿子的莎士比亚。
区分莎士比亚之“实”与莎士比亚之“名”十分重要。这对我们理解关联到读者的莎士比亚作者现象很有帮助。首先,作者的实体是一种短暂的生命现象,他与读者无关;作者的形象却可以永恒,只要其读者不死,他就永在。其次,作者的实体是一,只有一个可以查证落实的莎士比亚;而作者的形象却是多,有多少个莎士比亚的读者就有多少个莎士比亚的形象。所以,莎士比亚就是《汉姆雷特》、《仲夏夜之梦》上面署名的那个莎士比亚,就是“闪光的不都是金子”的言说者。莎士比亚是《汉姆雷特》所生产的那个莎士比亚,培根是《论读书》所生产的培根,克里斯托弗·马洛是《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所生产的那个克里斯托弗·马洛。
三 莎士比亚之“名”与莎士比亚之“实”
今天,我们很多人对莎士比亚卑微的出身和一地鸡毛的生活都不清楚。关于他的生平,有确凿记载的史料并不多,更多的是众说纷纭的推侧和传说。也就是说,莎士比亚之“实”的形象在读者的心目中是模胡的,而且,实际上,这个早已故去的作为血肉之躯的莎士比亚之“实”与读者无关;但莎士比亚之“名”却如雷贯耳,我们分明感到他还活着,他具有一种伟大而高不可攀的形象。那迄今还活着的莎士比亚显然是作者的形象,即活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作者形象是永恒的,他永远活在他的作品里。比如,在悲剧《麦克白》里,莎士比亚通过他独特的语言让读者通过自己的感官想象力编织出了一个图像世界。莎士比亚就像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绘画大师,运笔洒脱,以激情的语言、奔放的笔触和奇特的想象将麦克白夫妇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麦克白和麦克白夫人的一幅幅肖像呼之欲出,恰似浪漫主义风格绘画。阅读《麦克白》时就像在进行一次紧张的视觉旅行,似乎在欣赏一幅幅笔触浪漫的“黑绘”③。《麦克白》读者想象出来的人物肖像中,那大块的黑色让人紧张激奋难以忘怀,这些形象永远印刻在了读者的脑海里,莎士比亚的名字也永远留在了读者的心里。在历史剧《亨利五世》里,福斯塔夫生活在国王身边,可我们又分明觉得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和他很亲近。人们阅读着《哈姆莱特》,欣赏着《仲夏夜之梦》,或感叹于剧中人物的命运多舛,或沉醉于绿色原野的魔幻神奇。读者情不自禁地赞叹着莎士比亚,崇拜着他,内心亲近着他。
在其辉煌的作品中,莎士比亚充分显示了他人道主义的崇高与深刻。他赞颂母爱、仁慈、同情等人性之美,批判神性和神权统治,提倡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他建构的是丰富、复杂和深刻的人性,它让人们在认识自己的同时,理解他人、理解社会、理解时代。歌德在谈到读者心中的莎士比亚时说:“莎士比亚多么无限丰富和伟大呀!他把人类生活中的一切动机都画出来和说出来了!而且显得多么容易,多么自由!”④。所以,对文学史和文学实践来说,尤其对读者或创作者来讲,莎士比亚之“名”远比莎士比亚之实重要,因为只有莎士比亚之名对读者有着实质性的影响,正如歌德说的那样,“一研究他,就会意识到莎士比亚已把全部人形的各种倾向,无论在高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描写得竭尽无余了……”⑤。在《哈姆莱特》里,莎士比亚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⑥。我们从中获得了多少鼓励和做人的尊严;莎士比亚还教我们要慧眼看世界,他说“发光的不都是金子”⑦,更重要的是,他在教我们怎样热爱和欣赏大自然,怎样热爱生活和发现生活中的美。他说“我要在这里访寻几滴露水,给每朵花挂上珍珠的耳坠”⑧。原来,生活中处处有情趣,每滴小小的露水都是美丽的珍珠,生活中的美就在这小小的点滴里。莎士比亚真的离我们很近,在大自然清新鲜亮的气息里,我们仿佛看见莎士比亚站在青青的草地、清清的河边,召唤着:“快来吧!这儿是大自然,你们的家!”。
正如人们所赞美的那样,莎士比亚是个天才。裘克安在《千年之交话莎士比亚》一文的开篇即写道,“回顾过去千年,世界上有三位大天才。了解物(自然界)和解释物的大天才是爱因斯坦,了界人和描写人的大天才是莎士比亚,了界社会和说明社会的大天才是马克思”⑨。朱生豪在其莎士比亚全集译者序里写道,“于世界文学史中,足以笼罩一世,凌越千古,卓然为词坛之宗匠,诗人之冠冕者,其唯希腊之何马,意大利之但丁,英之莎士比亚,德之歌德乎,此四子者,各于其不同之时代及环境中,发为不朽之歌声……。但以超脱时空限制一点而论,则莎士比亚之成就,实远在三子之上”;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文学巨人本·琼生对莎士比亚也是赞叹有加,称他“不仅属于这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时代!”当这些大师因为被作品深深感动而发出各自的肺俯之言时,他们内心的崇拜一定是直指莎士比亚之“名”所生产的那个天才,而非关于其身世人们纠缠不清的那个凡夫俗子。
四 结尾
当然,作者总是在世界中创作,这不仅意味着在语言、文化、文学传统中创作,还意味着在特定的社会中创作。现实生活中的作者之实,他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性情癖好、才学思想、社会立场会影响他的创作。对莎士比亚也一样。不过,笔者认为,关于莎士比亚之“实”的过多争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用在乎他的国籍,他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不要犯狭隘民族主义,不用在乎英国人是否因为有了莎士比亚就有了文化优越感,莎士比亚是我们全人类的骄傲。我深感庆幸,在初次接触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我是“到底谁是真正的莎士比亚”这种争议的无知论者,所以我对莎士比亚一直挥之不去的牵挂和发自内心的敬仰是如此地纯粹;我也为“到底谁是真正的莎士比亚?”的深究者感到一丝悲哀,因为他们的心里会无端地多一分纠缠。所以,本人发此拙文,以期让莎学界少一些困惑和猜疑,更多地沉浸于丰富漫妙的莎剧世界里。生活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现实世界的人们,应该拂去蒙在心灵上的浮尘,淌洋于美丽的作品世界,为自己的心灵营造一方净土,更多地关注莎士比亚之“名”,而少纠缠于莎士比亚“实”。
注释
①作品风格学在此特指一种文学作品分析方法,即根据作品的风格来推断作品的作者.
②参见《文学知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1月出版)第 51页.
③“黑绘”一词是对古希腊艺术中的一种独特的绘画形式既瓶画的其中一种风格的形象的描述和概括。“黑绘”即在有色的泥胎上,用一种特殊的黑漆描绘人物和装饰纹样。在欧洲绘画史上有一种绘画方法既“黑绘法”曾风靡一时,其主要代表人物主要有 17世纪意大利的绘画大师卡拉瓦乔(1573-1610)等。“黑绘法”实际上是对这类绘画作品的光色效果的形象描述,其具体处理方法是,把物体完全沉于黑暗中,然后用集中的光把主要部分突出出来。这类画其画面色调浓重而又单一,构图显得简洁单纯,画面的重点在深色或黑色的单一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突出和显眼.
④见《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91页.
⑤见《歌德谈话录》第 15页.
⑥见朱生豪译《哈姆莱特》第二幕第二场.
⑦见朱生豪译《威尼斯商人》.
⑧见朱生豪译《仲夏夜之梦》第二幕第一场.
⑨见裘克安著《莎士比亚评介文集》第 1页.
[1]余虹.文学知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裘克安.莎士比亚评介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周骏章.莎士比亚散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4][德]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
[5]桂杨清.埃文河畔的巨人莎士比亚[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6]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朱生豪译)[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
[7]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朱生豪译).[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
[8]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 (朱生豪译)[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
I06
A
1008-4614-(2010)05-0037-03
2010-09-27
全凤霞 (1966-),女,湖南张家界人,北京工商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