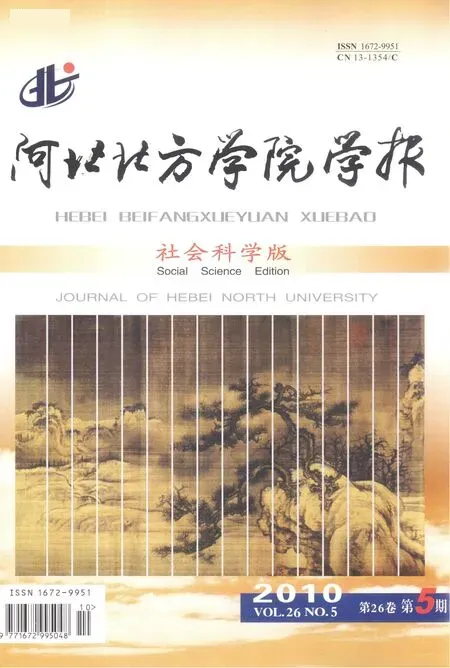试探田猎赋的奠基历程
——从《七发》到《子虚上林赋》
袁世刚
(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河北张家口075000)
试探田猎赋的奠基历程
——从《七发》到《子虚上林赋》
袁世刚
(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河北张家口075000)
在对先于汉赋的经史子集作品中田猎题材的发展状况有所概述的基础上,认为田猎题材在汉赋中发展到鼎盛,从枚乘《七发》到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所呈现出的奠基历程功不可没。《七发》作为田猎赋的先声之作,其所开启的程式化创作思路、铺陈的艺术、极致的美学追求和欲抑先扬的讽刺艺术,在被《子虚上林赋》继承发展的过程中趋于定形和成熟,以其模板式影响奠定了后世田猎赋的基本走向。
田猎赋;奠基历程;《七发》;《子虚上林赋》;模板式影响
伴随着狩猎这一人类最古老、最有魅力的活动,田猎成为文学创作的对象,并逐步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学题材,进入文学描写领域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学现象。先秦的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这一题材,到了汉代,其标志性体裁——赋,更是促使田猎题材得到长足发展,竟至成为表现这一题材最有力的文学载体。梁萧统编纂《文选》,按题材将赋分为15类,田猎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类,被排在第4类。第1类“京都赋”虽然卷帙较多,共6卷,但其作品实际上只有4篇,即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南都赋》和左思的《三都赋》;“田猎赋”虽然卷帙少于“京都赋”,不到3卷(第7卷中另有“郊祀赋”和“耕籍赋”各1篇),但其作品却也是4篇(是将《子虚赋》与《上林赋》合为1篇的结论①),而且京都大赋中也有大量描写田猎的内容,几乎形成了“无赋不猎”的局面②,或独立成篇,或文中穿插,蔚为大观;质量上,不管是思想内容,还是审美意蕴,都较先秦田猎题材有了质的飞越,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汉赋尤其是其中的大赋,凭借自身“骋辞云构”的体制优势,成了田猎题材发展到鼎盛的助产婆,“田猎赋”的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奠基阶段应该追溯枚乘的《七发》和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
有学者认为,田猎赋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即肇始于《诗经》,鼎盛于两汉,汉以后仍绵延不绝[1](P31)。笔者有不同意见。从语义上讲,“田猎赋”一词是指“赋”这种文体的题材分类,而《诗经》从文体上说,是“诗”不是“赋”,因此,把《诗经》中的田猎题材诗纳入“田猎赋”的发展阶段,是混淆了两种文体的界限,不宜将田猎题材在诗歌发展史中的某一阶段视为在赋体发展史的某一阶段。但毋庸怀疑的是,“田猎赋”的发展确曾受到《诗经》田猎题材诗的影响,因此,这位学者的论证对笔者颇有启示,启发笔者思考田猎题材在“赋”这种文体之前是如何发展的。
一、早于汉赋的文学作品中田猎题材发展状况概述
早在中国传说时期的远古歌谣和神话中,就有了描述人类狩猎活动的口头文学。今存最古老的猎歌当属保存在《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远古神话中“后羿射日”的故事,很明显是人类早期狩猎生活的反映。类似的文化遗存一定远远多于今天所能看到的这些,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学田猎题材的起点可以提前到远古文学时期。
田猎题材在先秦经、史、子、集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今存田猎题材作品数量较多的当属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有学者统计,《诗经》中的田猎诗作共有8篇[2](P99)。与其它题材相比,田猎题材的作品虽然在数量上还不是很多,但这在它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却不容忽视。《诗经》中的这些田猎诗,对田猎时猎人的射箭技术、驾驭技术、猎具等都做了一定描述。特别是《车攻》和《吉日》两篇作品,对猎前准备、狩猎场所之阔大、扈从人员之盛、车马弓矢用具之盛等作了较为详尽的描写,对后代的田猎赋创作不无影响。除此两篇之外,其它作品只是对田猎某个部分的描写,或写猎具,或写猎人,或写田猎时的某个片段。从总体上看,《诗经》中尽管《车攻》和《吉日》两篇作品对田猎活动有较为细腻的描述,但不管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还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突破。
中国先秦时期的史、子散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但也是表现田猎的载体。《老子》、《孟子》、《左传》、《战国策》等作品都对田猎有所涉及。但笔者注意到,诸子作品并没有直接把田猎作为描写对象,只是借它来阐述己见。由此可见田猎题材在诸子作品中的从属地位。如《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3](P19)又如《孟子·梁惠王下》云:“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4](P26)
田猎题材处于从属地位,其独立性尚未确立的局面,在楚辞中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楚辞中的田猎描写,或仍作为表现作品主旨的例证,或仅是事件描述中的一部分,或为片段,或一语带过。如《招魂》中有这样的笔墨:“懸火延起兮,诱骋先。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与王趋梦兮,课後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5](P1550)
总之,先于汉赋的经、史、子、集作品,虽有个别作品对田猎的描述较为详尽,但从整体上看,田猎题材始终处于附属性地位,即使有了《高唐赋》中的田猎描写——“于是乃纵猎者,基趾如星。传言羽猎,衔枚无声,弓弩不发……”[5](P881),也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直到出现汉赋这种文体,这种状况才逐渐有了改观。
二、枚乘《七发》:田猎题材之独立的转捩
在汉赋中,枚乘《七发》有着独特的地位,“传一代文风,定一体风格”[6](P41)。它赋写音乐、饮食、车马、游观、田猎、江海、要言妙道七事,“六过一是”;艺术上“腴辞云构,夸丽风骇”[7](P147),在多方面具有开创意义。单就题材而言,枚乘《七发》中各“发”分解出来的各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大有发展的余地[8](P177)。如音乐、田猎、江海等题材,在汉赋中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而《七发》中令楚太子“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③的“田猎之发”,可谓对田猎赋具有“范本”意义的先声之作:
将为太子驯骐骥之马,驾飞軨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之劲箭,左乌号之雕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蘋,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于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逐马鸣镳,鱼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践麖鹿,汗流沫坠,冤伏陵窘。无创而死者,固足充后乘矣。
这段对校猎之至壮的描写,从田猎所用的马、车、箭、弓,到田猎的具体过程,无一不是非常精细的描绘,并且写猎后“收获掌功,赏赐金帛”,“旨酒嘉肴,羞炰脍炙,以御宾客”,乃至“高歌陈唱,万岁无斁”。
较之先秦经、史、子、集作品对田猎的表现,枚乘《七发》对田猎的描述有了很大变化。尽管它是服务于“六过一是”之主题的,但是,其描写规模已经远远超出先秦经、史、子、集作品,其有声有色的田猎描绘远非先秦经、史、子、集作品所能比,更重要的是,作者写作田猎之顺序——猎前准备(马、车、箭、弓)、开赴猎场、猎杀、宴乐,已经呈现出一定的创作程式,这种创作程式给予后世田猎赋的创作以极大的启迪,基本上为后世田猎赋所继承,并逐步发展为具有独立性地位的题材。由此可见,视枚乘《七发》的“田猎之发”为田猎赋之先声并不为过,它绘声绘色的描写手法和程式化创作思路,直接影响了田猎赋的奠基之作——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产生。
三、田猎赋的奠基之作——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
笔者把《子虚上林赋》视为田猎赋的奠基之作,是因为看到了它对《七发》的继承与发展,在后世田猎赋创作中发挥着“模版”作用。可以说,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前承枚乘的《七发》,后启扬雄的四大赋,不仅堪称田猎赋创作的典范,更是汉大赋创作的扛鼎之作。
(一)枚乘《七发》的程式化创作思路在《子虚上林赋》中趋于定型和成熟
1.猎前准备之描绘在继承中发展、定型
描写猎前准备是枚乘《七发》写作程序的重要构成,但文字比较简要,仅各用一二句赋文依次描写车、马、弓、箭的准备,而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则较为详尽地描述这一程序。首先,它对准备车、马、弓、箭的描写,决不仅仅是一二句赋文了。如子虚对云梦猎之“车”的描绘已经扩展到四句赋文了:“驾驯駮之驷,乘彫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显然是要对“车”进行全方位描绘。除了详尽描写车、马、弓、箭的准备之外,作者更注重田猎场地的描绘。先看齐王海滨之猎前的准备:“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气势盛大,无与伦比。再看楚王的云梦之猎:田猎场地是楚七泽之一的云梦,其面积竟有“方九百里”,物产丰富,地形复杂,不愧为一个田猎的好地方。而天子上林之猎的场地描写就更壮观了——上林苑“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霸产,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鹜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不同凡响,无可比拟。此外,还有对扈从人员的描绘:“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行横行,出乎四校之中。”相如身后的扬雄在他的田猎赋中将田猎前的准备描述得更为具体而全面:从田猎场地、修筑道路到布置警卫巡逻、沿途悬挂旗帜,再到田猎人员的到达指定位置,无不周密而有序。
2.开赴猎场之描绘在继承中发展、定型
这一环节在田猎赋叙述中也时常出现。它既是猎前准备的继续,又是正式田猎的开始,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此内容是枚乘《七发》写作程序的重要构成:“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浔。掩青蘋,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将这一环节描述得更为全面:齐王开赴海滨之猎——“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菟辚鹿,射麋格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楚王开赴云梦之猎——“楚王乃驾驯駮之驷,乘彫玉之舆;靡鱼须之桡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将之雄戟,左乌号之彫弓,右夏服之劲箭。阳子骖乘,孅阿为御”,还有“郑女曼姬”侍候左右;天子开赴上林之猎不仅有车驾扈从——“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还有鼓乐仪仗——“鼓严簿,纵猎者,江河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靁起,殷天动地”,天子更是殷勤出动——“乘舆弭节徘徊,翱翔往来,睨部曲之进退,览将帅之变态”。
3.猎杀之描绘在继承中发展、定型
猎杀手段、效果、氛围的描绘是《七发》和《子虚上林赋》写作程序的又一重要构成,它们几乎将猎杀的所有手段都描写到了:射猎、刃杀、围猎、网猎、借用鹰犬、焚猎、追击等,其场面非勇气过人、胆大如虎之士不能为也。如枚乘《七发》中“逐狡兽,集轻禽”、“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徼墨广博,观望之有圻”、“白刃硙硙,矛戟交错”,就包括了追击、射猎、借用犬马、焚猎、刃杀等猎杀方式;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中齐王的网猎是“罘罔弥山、掩菟辚鹿”,射猎、格斗如“射麋格麟”;天子田猎时还有场面宏大的围猎:“于是乎背冬涉秋,天子校猎。”车驾是“乘镂象,六玉虬;拖蜺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游”,扈从有“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乐仪仗为之壮威:“鼓严簿,纵猎者,江河为阹,泰山为橹,车骑靁起,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于是将士们勇猛猎杀:“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壄羊,蒙鶡苏,绔白虎,被斑文,跨壄马,陵三嵕之危,下碛历之坻,径峻赴险,越壑厉水,推蛮廉,弄解廌,格瑕蛤,鋋猛氏,羂要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脑;弓不虚发,应声而倒。”还有天子亲自上阵的惊心动魄:“流离轻禽,蹵履狡兽,轊白鹿,捷狡菟,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弯蕃弱,满白羽,射游枭,栎蛮遽。”这都为扬雄《羽猎赋》描绘围猎和刃杀提供了范本——“移围促阵,移围徙陈,浸淫蹴部,曲队坚重,各按行伍”彰显的是围猎的壮观;“若夫壮士慷慨,殊乡别趣,东西南北,骋耆奔欲。拕苍豨,跋犀牦,蹶浮麋,斫巨狿,博玄蝯,腾空虚,岠连卷。踔夭蛟,娭涧门。莫莫纷纷,山谷为之风猋,树丛为之生尘”,则洋溢着狩猎者慷慨任气、所向无敌的刃杀之威。
4.宴乐之描绘在继承中发展、定型
猎后描绘是《七发》和《子虚上林赋》写作程序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只是在描绘什么上同中有异。如果说《七发》重在描绘猎后的宴飨、犒赏:“收获掌功,赏赐金帛。掩蘋肆若,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脍炙,以御宾客。”《子虚上林赋》除此之外,更注重描绘猎后的歌舞助兴,给宴飨、犒赏注入了文化意蕴:“于是乎游戏懈怠,置酒乎颢天之台,张乐乎胶葛之宇,撞千石之鐘,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金鼓迭起,铿枪闛鞈,洞心骇耳。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那么,在宴饮过程中,常有文学侍从献辞,以娱耳目,则是扬雄《羽猎赋》对《子虚上林赋》注重表现宴乐之文化品位的另辟蹊径:“鸿生钜儒,俄轩冕,杂衣裳。修唐典,匡《雅》《颂》。揖让于前,昭光振耀,蚃曶如神”。
5.反思之描绘在继承中发展、定型及其独特意义
枚乘《七发》写道,楚太子听了吴客的前六“发”,仍说“仆病,未能也”,而听了第七“发”——“论天下之释微,理万物之是非”的“要言妙道”后,“涊然汗出,霍然病已”。这是一种“六非一是”式的反思,反思主体并非单纯的猎者,反思内容也不是纯粹由“田猎”引出的,而是由耽于享乐引出的。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对反思的描绘则从主体到内容都呈现出了与猎者、与田猎生活的密切关系,其独特意义在于从一个方面确立了田猎题材的独立性。赋文结尾写道:“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览听预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恐后世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乎解酒罢猎。”这一段反思之语,显然是对《七发》创作程式的继承与发展,并为后世田猎赋所采用,定型为赋文末尾“一条光明的尾巴”。这一定型在扬雄四大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一般都要在赋文结尾描写天子反思之后并有所悔过的作为。如《羽猎赋》中云:“奢云梦,侈孟诸。非章华,是灵台。罕徂离宫而辍观游,土事不饰,木功不雕。承民乎农桑,劝之以弗迨。侪男女使莫违。恐贫穷者不遍被洋溢之饶,开禁苑,散公储,创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驰弋乎神明之囿,览观乎群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罝罘,麋鹿刍荛与百姓共之,盖所以臻兹也,于是醇洪鬯之德,丰茂世之规。加劳三皇,勖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庄雍穆之徒,立君臣之节,崇贤圣之业,未皇苑囿之丽,游猎之靡也。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
综上可知,田猎赋的内容程式发端于枚乘《七发》,定型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影响于后世田猎赋。值得注意的是,《子虚上林赋》对《七发》田猎题材表现程式的继承和发展,是伴随着对《七发》田猎题材绘声绘色之描写手法的继承
《子虚上林赋》在内容上有一定的创作程式,在艺术上也有着非常鲜明的特点,即在多采用铺陈手法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极致的美学倾向,进而达到一种欲抑先扬的讽刺效果。
1《.七发》的铺陈艺术手法在《子虚上林赋》中的继承和发展
汉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最突出的特点是铺陈。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7](P80)刘熙载云“: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9](P121)正是有了铺陈这一手法,汉赋才会给人留下“千态万状”“汪洋恣肆”的印象。铺陈之所以有如此的渲染效果,是因为它主要凭借了描写、虚构、夸张等手法。
描写。枚乘《七发》写田猎基本上都是叙事描写的笔触。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中描写的手法更是无处不在。刘勰曾以“写物图貌,蔚似雕画”[7](P81)来形容汉赋中“描写”这一手法的运用。《子虚上林赋》天子田猎场地上林苑中的鱼鸟玉石的描写便是刘勰这一品评的最好体现:
这段描写细致生动,既有鱼龙水族的水中嬉戏,又有鸟儿奋翼追逐,就连玉石似乎也有了生命的色彩。再如上林苑的河流:
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异态。东西南北,驰鹜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州淤之浦,径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彭湃……
这段描写纵横捭阖,错落有致,给人以清新、振奋之感。
“以类相缀”是田猎赋描写最突出的特点,即把属于同类的事物联缀在一起加以描绘。同类事物联缀,从数量上有利于铺陈。《子虚上林赋》对天子田猎之地上林苑的各色景物进行铺陈时,就非常巧妙地使用了这种描绘方法,正如刘勰所说“:繁类以成艳。”[7](P81)上林苑中依次出现的是水族、飞禽、花草、走兽,将这些景物分别缀于一类进行铺陈,面面俱到,气势宏大。
田猎场面的描绘还遵循着时空顺序。先写楚、齐两个诸侯王的田猎,然后重点铺叙天子的游猎。而在描写上林苑的时候,又按照东南西北的顺序展示各方景观,显得有条不紊。
虚构。赋体文学的虚构手法主要运用在人物设置上。《七发》假立楚太子与吴客两个人物,并通过的他们的对答引和发展同步进行的。
(二)枚乘《七发》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子虚上林赋》中的继承和发展
出“七发”,各“发”虽是并列,但在气势上层层推进,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将这种手法的运用提升到一个人人仰视,唯恐模拟不及的高度。篇中人物设置增加至三人,均为虚构,并附有一定的身份和使命:“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10](P3002)正是有了这样独具匠心的设置,赋文的情节安排才显得合情合理,引人入胜。作者首先安排楚使子虚参加齐王的田猎,紧接着让子虚夸耀楚王云梦之猎,齐国乌有不满其夸耀,以齐王的海滨之猎的壮观与之辩驳。由于作者以“亡是公在焉”一句在前文埋下了伏笔,所以,当子虚、乌有争辩得不可开交之际,适时推出亡是公代表作者否定子虚、乌有所象征的诸侯之争,寄托“大一统”的赋旨。亡是公盛言上林苑的巨丽和天子出猎的至壮,并以天子的幡然悔悟表示出对诸侯逾制及耽于游乐的不满,最后以子虚、乌有“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的描写,暗示诸侯臣服于天子的“大一统”的赋旨。这样的设置,既缜密无失,又跌宕起伏。在扬雄的《长杨赋》里也虚构了翰林主人和子墨客卿,借以言天子得失。正是这种虚构手法的运用,才会在赋予田猎赋故事性,引人入胜的同时,巧妙传达赋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虚构主客关系的手法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转换的,后世赋体作家并没有因为《子虚上林赋》对《七发》的创造性继承而止步不前。
夸张。这一手法往往与描写、虚构联系在一起,形成“夸饰”。《七发》中“田猎之发”的场面宏大且形象逼真,给人以紧张急促的观感,就是因为这种手法的运用才达到的效果。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极力描绘齐、楚、天子苑囿的广大,游猎阵容的壮盛,宫殿楼阁建筑的雄伟,也无不融汇着夸饰的表现手法。上文提到的田猎中猎杀的描写,就是对猎者动用各种手段捕捉猎物极尽夸饰,常常一开篇就直接进入到对田猎壮观场面的描述,而猎前准备则靠追叙形式完成,因而田猎的描写往往先声夺人,气势磅礴至极,声色之壮已非《七发》所能比。
2.《七发》极致的艺术美学追求在《子虚上林赋》中的继承和发展
汉赋向来以体制宏大、内容丰富著称。赋家作赋时务求面面俱到,穷形尽相,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因此,汉大赋所表现的内容大多事无巨细。司马相如曾言“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11](P12)。这种内容上的极致追求,折射出别具一格的审美追求。正如《子虚上林赋》中亡是公所言“君未睹夫巨丽也”,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巨丽”是当时赋家极力追求的一种美。司马相如和扬雄赋中所写景物的巨大和繁富,构形的奇特和多姿,无一不是将“巨”和“丽”结合在一起的。这一点在田猎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赋家写田猎,必写田猎苑囿之广袤,其间山川林薮之形胜,水陆物产之丰饶;田猎后必附以歌舞宴乐之淫逸;写物必穷形尽相,土石的色彩之杂:“丹青赭垩,雌黄白坿,锡碧金银。”美玉的种类之多:“赤玉玫瑰,琳珉昆吴,瑊玏玄厉,碝石武夫。”香草的繁盛:绿蕙、江离、留夷、揭车、衡兰、若孙。禽兽的林林总总:白虎、玄豹、大象、骆驼、牦牛、凤凰、孔雀。林木的珍贵:豫章、女贞、栌、葡萄。鱼类的目不暇接:鱏、鲸、比目、鲨[12]。赋家力图通过遣词造句营造出一种趋于极致的艺术效果。而这种艺术效果,则彰显出赋家别具一格的审美倾向——极致。这样的审美倾向,在枚乘《七发》中已经彰显出来。赋文极力铺陈至悲之音乐、至美之饮食、至骏之车马、靡丽皓侈广博之游观、至壮之校猎、天下怪异诡观之江海。萌芽于《七发》的这种艺术美学追求,经《子虚上林赋》的继承,使其“极致”的倾向逐渐定型成熟,一方面是时代使然,另一方面也与汉大赋独特的体制有莫大的关联。汉朝是继秦而立的大一统朝代,并且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盛世繁荣的局面,给了赋家以极大的信心,他们面对着汉大帝国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局面,自然要大力赞叹了。他们借助汉大赋的体制优势,将自己迫切建功立业的雄心蕴于其中。而田猎作为最富时代特征的题材之一,正契合了赋家借这种极致的审美追求抒发雄心壮志的意愿。
3.《七发》欲抑先扬的讽刺艺术在《子虚上林赋》中的继承和发展
《两都赋·序》云:“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13](P123)汉赋是有一定的讽谏意义的,其中的田猎赋更是将讽刺艺术发挥到极致。所谓“曲终奏雅”“劝百讽一”,正说明这一点,这也暗示出它讽刺艺术的独特,即采取“欲抑先扬”方式。田猎赋这种讽刺艺术,既与它的内容创作程式相关联,又与它极致的审美追求密不可分。
田猎赋内容上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将田猎的整个过程都描述得具体且详尽,这显然需要一定的艺术技巧相配合,因此,它采取铺陈的手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铺陈的手法一方面将赋家想要描述的田猎场面尽情展示出来,另一方面也服务于它独特的讽刺艺术。由此可知,田猎赋所呈现的铺陈手法、极致的美学追求和欲抑先扬的讽刺艺术三者是相辅相成的,这与田猎赋内容上推而隆之的手法相配合,一表一里,内外结合。
枚乘《七发》极力铺陈至悲之音乐、至美之饮食、至骏之车马、靡丽皓侈广博之游观、至壮之校猎、天下怪异诡观之江海,而最后以“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的“要言妙道”称是。前六“发”为铺垫,最后一“发”为旨归,出人意料,令人警醒。正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所言:“作者在赋中花费大量笔墨去精心描绘的内容,正是作者最终所要超越和否定的东西。”[14](P159)“田猎之发”等被作者极力夸饰,而最终却都予以否定,这明显的体现出欲抑先扬的讽刺特色。后世田猎赋也大多沿袭了这一手法。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将这种手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作者先将诸侯之猎极力铺叙一番,子虚乌有两先生的争论也达到了白热化,就在这时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且二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一语就将二人加以否定,并批评他们的过失,指出诸侯的逾制之罪。紧接着,又让亡是公极力夸饰上林苑的水族、飞禽、花草、走兽,盛言天子之猎的声势之浩大,既为亡是公批评子虚、乌有提供佐证,又极力称颂了天子的声威。在田猎之后还大力渲染宴乐、游玩,而文末却笔锋一转,写到:“于是酒中乐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一语也将天子的田猎活动加以否定,最后,“解酒罢猎”,并让天子提出一定的补救措施。扬雄的《羽猎赋》与此类似,先将天子的游猎场面极力夸饰一番,最终也以天子的反思结束。
田猎赋这种欲抑先扬的讽刺艺术,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独特心态,更折射出特定的文化内涵。
四、从田猎赋的文化内涵看田猎赋的奠基历程
极力宣扬大一统意识,是田猎赋文化蕴涵之根。表现在赋的艺术手法中,就是对田猎内容的极尽铺陈,塑造了一个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国势强盛的帝国形象,字里行间所蕴涵的极致的审美倾向,也正适应了这帝国形象的塑造的要求,赋文最后的“曲终奏雅”则更加明显地表现了维护国家大一统的意识。
宣扬大一统意识的表现之一是规讽帝王的得失。历代赋作对帝王过失的规讽常表现为批评其荒于游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等都对帝王纵情游猎,不顾民众的活动提出了批评。其中,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借亡是公之口代表天子,对齐楚二国之君的“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而贪雉菟之获”的行为,表示了“仆恐百姓被其尤”的担忧,至于扬雄的《长杨赋》,则更对发民入山围捕野兽,送至长杨馆令胡人手搏,天子亲往观看一事提出非议,认为勤政爱民乃立国之本,校猎亦御敌大务,“岂徒淫览泛观,驰骋稉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践刍荛,夸诩众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获哉!”还有对诸侯逾制的批评,《子虚上林赋》中亡是公以“楚则失矣,而齐亦未为得也”否定诸侯之争,批评其“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警告他们应该“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抑藩必当尊君,《子虚上林赋》大事渲染天子田猎的浩大与盛况,便是对尊君抑藩思想最形象、最含蓄的阐释,实质就是对大一统意识最佳的艺术阐释。总之,不管是规讽帝王得失,还是尊君抑藩,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归根结底还是宣扬和维护大一统意识。汉代是继秦而立的又一个大一统朝代,她正处于中华民族的上升时期。汉赋作为有汉一代的文学标志,同样蕴含这个时代的大一统精神。田猎是最富时代特征的文学题材之一,大一统精神蕴含其间亦不难想见。从枚乘《七发》的谏止诸侯到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的尊君抑藩,再到扬雄《羽猎赋》、《长杨赋》的劝谏天子,大一统精神始终贯穿于田猎赋的创作中。《子虚上林赋》的作者司马相如以“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气魄塑造了大一统的帝国形象,“在这个国度里,奇花异草,珍禽异兽,美酒佳肴,巧夺天工的池苑亭台,气象万千的崇楼峻宇,应有尽有;可以搏虎的勇士,曼妙赛仙的佳人,贤良方正的大臣,无不聚于仁政爱民的帝王周围;诸侯宾服,四海宴然,君民同乐,富庶无边”[14](P162)。这样一个大帝国形象的塑造,实际上也是大一统意识精神的表现。这种意识的表现在扬雄的《羽猎赋》、《长杨赋》中更进了一步,赋文在对天子游猎有所批评的基础上,
从天子的自身修养到与民休息的措施,一一地艺术再现,从而更有力而含蓄地传达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大一统统治的赋旨。总之,笔者在对先于汉赋的文史哲作品中田猎题材的发展状况有所概述的基础上,认为田猎题材在汉赋中发展到鼎盛,从枚乘《七发》到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赋》所呈现出的奠基历程功不可没。《七发》作为田猎赋的先声之作,其所开启的程式化创作思路、铺陈的艺术、极致的美学追求、欲抑先扬的讽刺艺术,和大一统文化意蕴,在被《子虚上林赋》继承发展的过程中,趋于定形和成熟,以其模板式影响奠定了后世田猎赋的基本走向。
注 释:
① 学术界关于《子虚上林赋》的篇名有《子虚赋》、《上林赋》《天子游猎赋》等多种说法,参见刘南平、班秀萍著《司马相如考释》第三章第一节。笔者取其“《子虚上林赋》”说。
② 本文对“无赋不猎”说的理解和阐释,既在适当的语境中指汉大赋名篇——《七发》、《子虚上林赋》、扬雄四大赋、“两都”、“二京”赋,又在适当的语境中泛指汉大赋。
③ 此论文所引述的汉赋作品原文皆出自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校注的《全汉赋校注》(广东教育出版2005年版),其中《七发》见第32页至37页,《子虚上林赋》见第69页至72页和第87页至92页,《羽猎赋》见第253页至257页,《长杨赋》见第273页至275页。
[1] 刘贵华.古代狩猎赋论略[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31-34.
[2] 陈鹏程.《诗经》田猎诗的文化内涵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99-102.
[3] 沙少海,徐子宏.老子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
[4]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 梁·萧统.文选(李善注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 赵燕平.传一代文风定一体风格——枚乘《七发》赏析[J].职大学报,2000,(1):41-42.
[7] 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 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9] 清·刘熙载.刘熙载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0] 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晋·葛洪.西京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 钟继彬.论汉赋山川景物描写的美学形态[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8,(6):78-80,128.
[13] 费振刚,仇仲谦,刘南平.全汉赋校注[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
[1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5] 曹明纲.赋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16] 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
[17] 曹胜高.汉赋与汉代制度——以都城、校猎、礼仪为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Abstract:Having overview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of hunting theme which is before Han f u,the study considers that the subject of hunting developed to its peak in Hanf u,owing to the great contribution made for its foundation course by from Meicheng'sQif ato Sima Xiangru'sZixushanglin Fu.Qif a,as the harbinger of huntingf u,carries the following features:programmable creation thoughts,laying out the art,the ultimate pursuit of the aesthetic,and the irony art of“raise in order to restrain”.In the course of being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yZixushanglin Fu,Qif a's features tended to be stereotyped and mature,whose template-style laid its impact on the main trend of later huntingf u.
Key words:huntingf u;foundation course;Qif a;Zixushanglin Fu;template-type impact
(责任编辑 刘小平)
The Foundation Course of HuntingFu——FromQif atoZixushanglin Fu
YUAN Shi-gang
(School of Chinese,Hebei North University,Zhangjiakou,Hebei 075000,China)
I 209
A
1672-9951(2010)05-0006-06
2010-03-20
袁世刚(1984-),男,河北故城人,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09届毕业生,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