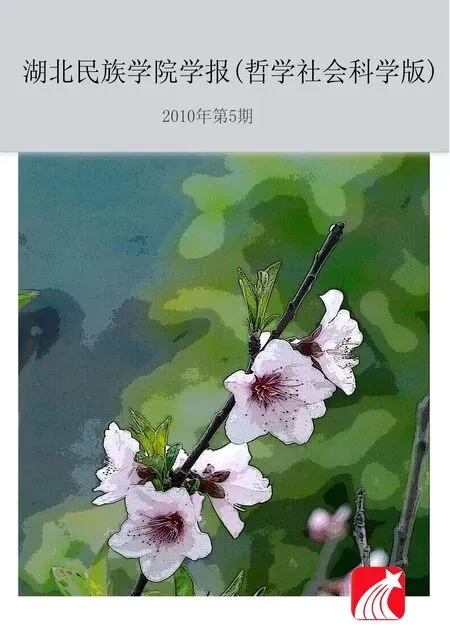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曾小月
(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中国古代白话文论在文学理论教学实践中的价值
曾小月
(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相对于用文言文书写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因其语言的通俗性而更便于人们的理解与应用。然而,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包含了古代白话文论在内的传统文论的批评功能持否定态度,且纳入到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中,使得中国传统文论失去了应有的现实价值。本文以古代白话文论的梳理、学术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以及古代白话文论在教学中的意义为线索,深入分析以古代白话文论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当下意义,并由此揭示古代白话文论于文学理论教学的价值。
古代白话文论;文学理论教学
一、古代白话文论的内涵
古代白话文论是指,中国古代所形成的用白话文书写的文学理论。相对于用文言文的形式所写就的传统文学理论,古代白话文论处于一个较为边缘的位置。但是,在面对近十年的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转型,以及高校文学理论教学中传统与现代的抉择等问题时,重新认识与审视古代白话文论的特征、意义便成为了必要。
为更清晰地把握古代白话文论,我们应先对其具体内容做一个宏观地了解。先秦两汉时期,王充的《论衡》,便多用时言口语,读来通俗显豁,清晰易懂。该书虽是一部哲学著作,但其中也大量论及了文学。那些论及文学的章节和段落,完全可作为白话文论的萌芽。并且对于如何在文学作品中运用口语,王充就已达到一种自觉的高度。王氏在《论衡·自纪》中论及了文学写作的四个问题,在谈到行文走笔时,他主张口头语可登文学的殿堂,只是作者要善于把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和谐地统一起来。他认为,“文犹语也”,语言的目的在于“明志”“言恐减遗,故著之文字”。又语言贵在通俗易懂,“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因此必须“文字与言同趋”[1]。
在王充时代,针对白话入文这一现象,有所谓“高雅之士”明确表示反对:“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与俗不通之文字,才是贤圣之手笔。王充以为此观点极为荒谬,他批斥道:“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1]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古代文论发展的高峰。钟嵘的《诗品》是产生于这一时代的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杰作。《诗品》的语言风格与同一时代的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一批骈文论著相比,使人感受到钟荣笔下已经轻扬起一脉略显通俗的语言清风。钟嵘反对雕琢刻镂与使事用典,提倡自然直率的诗风。这一文学时期,刘义庆《世说新语》也值得一提。该书虽是一部笔记小说集,但其中涉及文学的部分里,有许多地方可视作一种文学批评。而他这种独特的文学批评,在语言运用上,也都呈现一种生动活泼的口语风格。此外,《颜氏家训》中谈诗论文的片断,同样驻留了用当时口语评论文学的印痕。
时至唐代,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他们继承王充用语通俗的精神,大量采用白话来谈诗论艺。在宋代则出现了专门品评作家作品、记载文坛掌故的文论著作。在当时的诸种文体写作中,通俗化、口语化蔚成风气。于是,许多文论著作便也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白话化特色。这些著作堪称典型的白话文论。
宋代的白话文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诗话词论,一类是各种文学选本的点评。在宋代诗话中,作者于论诗谈艺及记事析辞之际,常采用浅易明白的语言来表明自己的观点,使读者易于领会。诗话与笔记的文体渊源十分密切:“历代诗话的文体源头是六朝笔记小说,故诗话这一批评文体的‘血缘’是文学的而非理论的。”[2]一看便知,笔记小说的白话化用语影响了当时的诗话创作。此后,在诗话这一领域又出现了侧重于理论模式的著作体式,如《沧浪诗话》之类。此类诗学著作,专注于诗学理论探讨,倡导并实践着理论的系统性。然而,就是这种理论著作其行文也显示着浅近化。如“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3]这几句话正是源琅琅上口的白话,所以几百年来一直为大家熟知和流传。
元明清的白话文论,主要集中在以金人瑞为代表的小说戏曲批评和李渔的戏曲批评。金氏的文学思想体现在他对“六才子书”的评点上,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水浒传》与《西厢记》的批评。其评点多用通俗的白话,议论风发,见解深刻,笔端饱含感情。且看金氏小说评点的浅易和明畅:“《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读第五才子书法》)金氏用以讨论小说作法的文字极为口语化,就连当今的读者也能毫不费力地理解其意。
此外,李渔《闲情偶寄》以强调体系建构著称,是今人拿来与西方文论之体系论相比较的文论佳作。通读全文,我们不仅钦佩作者把握当时戏剧创作动态的敏锐眼光,而且也欣赏他在遣词造句时能极尽通俗之能事。李渔在该著作中不仅论述了戏剧剧本的结构、演员的培养作育与临场表演等,还用许多篇幅论述了戏剧的语言问题。他对语言总的要求是,浅显通俗、机趣尖新、戒浮泛求肖似及注重音乐美。从清一代到后来的梁启超等人之文论中已明确显现,其用语风格愈加趋向通俗显豁,或者说是越来越白话化。可见,用白话谈诗论艺,立言著论,不但古已有之,而且一线相承,成了中国古代白话学术的重要内容。
二、当今学界对古代白话文论的认识
就目前情况而言,学术界对于古代白话文论基本上构成两种截然对立的认识。其一,认为古代白话文论纯属中国传统文论范畴,其性质属性决定了在现代文学批评当中的无效性与落后性。其二,以为古代白话文论由于其白话文特征,仍然适合于以白话文书写的当下文学作品的分析与阐发。在此,笔者认可第二种观点。
持第一种论断的学者主要是针对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观点[4],并由此否定所有与古代相关联的中国文论于现代意义上的有效性。之所以对“失语症”观点持否定的态度,这些学者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和依据:他们认为,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话语形式的转变,文言文让位于白话文,于是以文言文为语言载体的传统文论也自然地随之成为明日黄花。因而,传统文论不适应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便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当然理论。而那种要将传统文论激活起来的想法,便被视为一种唐吉柯德式的痴梦,一种民族主义末路英雄般的妄想。[5]这种观点是偏颇的,其失误处在于:他们笼统、轻率地将古代文学批评的语言形式和文言文划了等号。
其实,当年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并非凭空造屋。白话文运动,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继承。因为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学之语言形式的洪涛大波中,书面语言(文言文)的确是其主流,然而口头语言(白话文)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之语言大潮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源流。白话文现象自古以来便有之,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成巍巍大观之势,才出现那种“罢拙文言,独尊白话”的霸气局面。应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园地里,既有大量的文言文论,也有为数不少的白话文论。因此,简单地认为“由于时代前进,所以要废止文言;由于中国古代文论是属于文言范畴,所以便属于要废止之列”这一逻辑,是行之不通的。
我们在面对中国古代文论时,那些以古代口头语言撰文的白话文论便能为今人所了解与把握,而这一点也正好说明了中国古代文论并非由于语言的晦涩而终身陷入失效的泥潭。如果我们敢于尝试一下,将那些以口头语言撰文的古代白话文论从以文言文为语体的经典古代文论中挑选出来,放置到当今的文学作品批评,或者是把它纳入进课堂教学实践当中,会发现其批评与鉴赏功能丝毫不会逊色于西方文学理论。
三、重新认识古代白话文论的意义与价值
1.古代白话文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能解决文学理论教学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杨乃乔先生在《西方的后民族主义与东方的民族性》一文中这样讲道,中国古典文论只是被研究的对象,而不再是研究艺术文本的武器。[6]笔者对此的理解是:中国古代文论已丧失其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指导意义,仅是被现代西方文论视为参照或比较的对象,因此古代文论早已没了生命力。而钱中文先生却以更为公正的眼光表示:中国古代文论的复苏与生存最重要,至于是否“不朽”,这问题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东西。[7]笔者赞同钱先生的意见,认为文学实践是检验文论的标准。我们不要囿于中西文论谁是主脑地位的争论,要着重于做实事,看谁能真正解释当下的文学创作。
文学理论教学最忌理论的说教,将抽象的文学创作观点纳入到具体文学作品的解析当中,是易于为学生理解与接受的。比如,谈及小说创作方法时,我们经常用到的是西方文论之人物、典型、时代、性格等范畴。然而,作为面对中国材料的作者,以及面对中国作品的读者(学生),在熟悉西方文论之余,启用本国文论作为解释文学作品的方法将显得更为贴切与直接。由此,我们将以具体的例子作为证明。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归纳出数十种“文法”。所谓“文法”,就是对作家创作经验、艺术表现手法、作品创造的艺术规律的理论总结。这些“文法”包括:关于小说人物语言的“夹叙法”、“不完句法”;对比不同性格人物,借次要人物反衬主要人物的“背面铺粉法”、“染叶衬花法”;对人物进行反讽描写的“绵针泥刺法”;把握叙事缓急的“弄引法”、“獭尾法”;安排小说结构的“倒插法”、“横云断山法”、“移云接月之笔”、“顺风斜渡之法”,等。
首先来说这“草蛇灰线法”。金圣叹是这么说的:“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8]也就是说,在看似不经意间,设计一条贯穿整个故事情节发展过程的非故事性线索。它在故事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为读者提供一个能将零碎情节、细节贯穿的内视角,循此线索,读者就能把握复杂情节的递进过程,这过程具有提携作品形散神聚的整体艺术效果。在小说中,作者的叙述重点和作品的核心事件往往不是存在于“草蛇灰线”之本身,但“草蛇灰线”却造成了一个结构的“空筐”。由于有了这一恰如其分的“空筐”,便顺顺当当地把叙述重点和核心事件全装进了这一空筐之中。与“草蛇灰线”相对应的便是那条有形有迹的“实蛇实线”。
我们可用此法分析当代作家唐浩明的长篇小说《张之洞》。小说主要描写了张之洞为富国强兵,全力以赴投入洋务运动的事件。为达此目的,张之洞奋力排除腐朽官场中的干扰。一次次波澜是作品的有形事件,即作品的“实蛇实线”。但作者又设计了另一个人物:桑治平。张之洞去山西赴任,要一个文案帮手。家住北京郊外古北口的桑治平便进入了读者眼帘。通过朋友介绍,桑来到张的身边。桑为肃顺家的西席,但在镇压的当晚他侥幸逃脱。这一切他自然向张之洞隐瞒。桑是一个有大志大德的人,他钦佩张的为国为民之嘉行,为张奔走办事。乍一看来,作者对这桑治平的设计,似乎只是写了一个张的陪衬人物,甚至可有可无。小说中桑只是偶尔露峥嵘,在那里出一下,在这里点一下。然而,只要是懂得“草蛇灰线”法的作家或评论家便会意识到,作者设计出桑这样一个人物,是设计出了一条可以盛载许多事件的极有价值的结构虚线。这正如金圣叹所言:“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
再来看“背面敷粉法”。这是用一此样性格之人,来衬托另一彼样性格之人的方法。可拿白先勇的短篇《岁除》为例。大年三十夜,台北军人刘营长家里过除夕,请来老友赖鸣升。赖鸣升边喝酒边谈他的风云史和风流史。赖是一个粗人,他嘻笑怒骂颇有点粗野,但言谈有趣,满肚子铁哥们义气。为了刻画赖这一个近乎于黑李逵的豪爽形象,作者设计了另一人物:青年军人俞欣,他带着未婚妻一块来刘家喝除夕酒。作者一边写赖的豪放粗野,一边写俞欣的拘谨和腼腆。越写出俞的窘态,便越显出赖的粗野豪气的有趣个性。白先勇正是运用了“背面敷粉法”。恰如金圣叹所言:“如要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8]
从以上列出的几个文学作品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论并不只是视为研究对象的古董,而确实是可用以对当代创作进行指导和研究的一把利器。当然,当代文坛和剧坛早已呈现出新气象。许多先锋派、现代派的作品的确不能简单地用传统文论来衡量,因而引进西方文艺批评的新方法完全必要和应该。然而,缘此就把本民族的批评方法一概予以丢弃,那实在是一个不理智的行为。笔者以为,中国文论界应适当调整工作重心,把对“失语症”存在与否的外围探讨,转移到切实的传统文论价值重现的内部工作中来。因为,唯有实践才能经得起考验。
2.借用古代白话文论,能提升学生对传统文论,乃至传统文化的认识,改变现代文学理论等同于西方文论的现象
曹顺庆先生曾如此总结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9]同时,他还无不痛心地之指出:“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9]面对这样一种严峻的局面,中国文艺理论工作者应该引起重视,这其中还包括我们的文科高校教学。
在高校文学理论的教学实践中,全面介绍与充分利用古代白话文论,能提高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水平。譬如,面对文学结构论此一命题,大多数学生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西方古希腊时期由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结构理论。然而,如若教之以李渔的戏曲结构论,便能在课堂上展现一副中西结构论比较的图景。西方结构说自有其科学性与普适性,然而中国之结构论也有异于他者的特点。于此,我们暂不赘述西方结构说,且来看看李渔之结构论。李渔戏剧理论中最为人所注目的是关于结构的论说。不仅首卷词曲部最前面七款直接命题为“结构”,而且以后各卷各部各款,仍总与结构问题相联系。在李渔的结构论中,“立主脑”最为重要。“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止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俱属衍文,原其初心,又止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而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矣。”[10]此段文字言简意赅,且表述自然,使得读者在阅读之余能直接体会到李渔之“主脑”于一部戏曲的地位与作用。
如此一来,中西方之文学结构论鲜活地展现在学生面前。面对西方文论长期统治现代文论的现状,中国文论界视之为平常。然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寻求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特点已成为跨文明异质性对比和互补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总结本国文化与文学理论的特质显得尤为重要。古代白话文论隶属于中国传统文论,是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另一精英文化。因此,将古代白话文论的传授与习得,作为中国传统文论、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良好继承,这不仅是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界的重要任务,更是高校文学理论教学工作中的头等大事。此外,将古代白话文论纳入到当下文学概论教学之中,并以之与整个西方文艺理论形成一种知识的对比与互补,这样,既能增添课堂学习的活跃气氛,又能在中西方比较的模式中形成一种良性学习方法,起到加深记忆、巩固知识的学习目的。
[1] 王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80.
[2] 李建中.辨体明性:关于古代文论诗性特质的现代思考[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2).
[3]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24.
[4] 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J].东方丛刊,1995(3).
[5] 陶东风.全球化、后殖民批评与文化认同[M]//全球化与后殖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 杨乃乔.西方的后殖民主义与东方的民族性——关于世纪之交艺术话语权力的争夺[J].民族艺术,1998(1).
[7] 钱中文.文学理论: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J].中国社会科学,2001(1).
[8] 金人瑞.金圣叹全集.第一册[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22.
[9]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M].跨文化比较诗学论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79-181.
[10] 李渔.闲情偶寄[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7,8.
责任编辑:王飞霞
Value of Ancient Chinese Vernacular Critical Theory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Literary Theory
ZENG Xiao-yu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angsha 410004,China)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eory in classical Chinese,the ancient Chinese vernacular literary theories is easier to understand and apply.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of ancient Chinese vernacular,academic circle′s cognition of ancient vernacular Chinese critical theory,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ncient vernacular Chinese critical theory in the teaching,this paper toughly investigates into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with ancient Chinese vernacular critical theory as a representative,in the literary criticism,and thus revealing Chinese vernacular critical theory′s value in teaching the literary theory.
ancient vernacular critical theory;teaching of literary theory
I045
A
1004-941(2010)05-0105-04
2010-08-16
曾小月(1978-),女,湖南益阳人,博士,现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