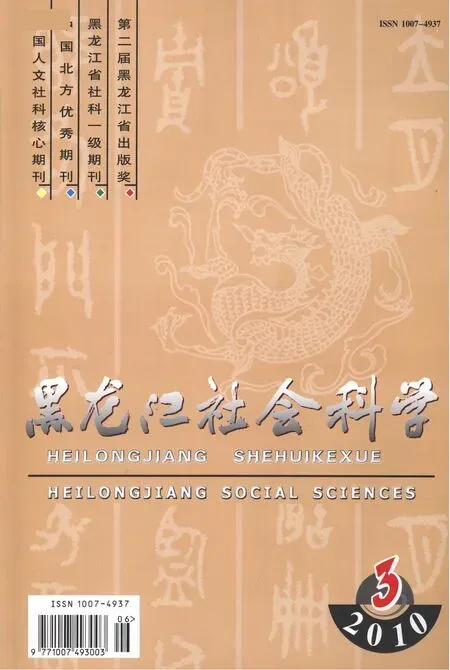关于日本战后赔偿分期问题的思考
田 野
(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 130012)
关于日本战后赔偿分期问题的思考
田 野
(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 130012)
对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分期的划分差异,反映了研究者不同的历史认识与视角。学界对日本战后赔偿史分期的争议,透视出日本战争赔偿问题的复杂性。对日本赔偿外交时期的深入研究,能够辨明日本战争善后赔偿问题的本来面目。
日本;战后赔偿;赔偿外交;经济外交
历史研究是非常重视分期问题的,对于历史事物发展演变过程分期的划分差异,反映出研究者不同的历史认识与视角。日本的战争善后赔偿源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的巨大损害。受害各国从其遭受入侵时起就开始酝酿战争结束后的日本索赔问题。所以,在学界的多数著述中对该问题的研究也大多是从战时的损失调查和对日索赔计划开始,直到 20世纪 70年代后期日本结束对东南亚相关国家的赔偿止。关于这三十多年的日本战争善后赔偿历史的演变过程,国内外学者对该问题的认识是见仁见智的。本文试图对此进一步探讨,从中明确一些模糊的认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日本战后赔偿史的分歧
日本于 1945年 8月 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国主导下,战败的日本开始陆续对曾遭受其发动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伤害或者饱受其殖民统治的亚洲诸多国家进行战争善后赔偿与补偿。这个善后赔偿一直持续到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历时三十余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与战后补偿是对战后日本的主要处置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战争赔偿复杂、富有变化。一方面,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对正义与责任的进一步理性思考;另一方面,它的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 1947年冷战的爆发与演进,使得日本的战争善后赔偿过程充满变数。随着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索赔国以及日本方面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而,国内外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由于研究视界的不同,中外学者将日本战争善后赔偿过程作了以下划分。
1.二分法 日本的战争善后赔偿以冷战爆发为界,分为拆迁赔偿期 (1945年 9月—1949年 5月)和协议赔偿期(1951年 9月—1976年)。还有学者以 1951年 9月签署“旧金山和约”(1952年 4月生效)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1945年 8月—1951年 9月),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直接左右着日本的赔偿问题;第二阶段(1952年 9月—1977年 4月),日本与东南亚各国进行赔偿交涉与支付赔偿。
2.三分法 以冈野鉴记为代表,将日本战败投降到《旧金山和约》缔结的六年间分为三个时期,即非军事化强行时期(1945年 8月—1946年末)、自立经济促进时期 (1947年 1月—1949年 5月)、和平条约缔结时期(1949年 5月—1951年 9月 8日)。同时,他也指出和平条约签订后日本与缅甸、菲律宾、印尼、南越个别交涉的完成,相当于第四个时期。冈野鉴记提出的分期法,主要是宥于其于 1958年发表的《日本赔偿论》,不能够完成对整个赔偿过程的划分。另外,伊藤信哉提出将 1945年 8月至 1952年 4月这一历史时期划分为“赔偿政策的形成 (1945年 8月—1947年 4月)、赔偿政策转换 (1947年 4月—1949年 5月)和对日媾和条约的缔结 (1949年 5月—1952年 4月)”三个阶段。
3.四分法 以孟国祥为代表的研究中国索赔问题的学者认为,从日本战败投降到 1972年 9月中日建交,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准备酝酿阶段(1945年 9月—1946年 3月),讨论、磋商与部分实施阶段(1946年 3月—1949年 5月),索赔终止与相继放弃阶段 (1949年 5月—1952年 4月),对日索赔的个别处理阶段(1952年 4月—1972年 9月)。
4.五分法 原朗在其《昭和财政史 (第 1卷)总论·赔偿·终战处理》一书中,把日本战争赔偿分为“初期赔偿基本原则的确立”(战时—1945年 11月)、“先期拆迁赔偿计划的实施”(1945年 12月—1947年 4月)、“美国对日政策的转换与先期赔偿的终止”(1947年 4月—1949年 5月)、“美国对无赔偿原则修正与劳务赔偿政策的确立”(1949年 5月—1951年 9月)、“旧金山和会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于赔偿事务的交涉”(1951年 9月以后)[1]149-150。学者们的观点,主要着眼于日本战后赔偿政策的制定与演变,比较多地强调了在美国操纵下的拆迁赔偿实施进程,而忽视了日本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对亚洲各国开展赔偿外交交涉的过程。
笔者认为,日本的战争善后赔偿以 1951年 9月签署、翌年 4月生效的《对日和平条约》(通称《旧金山对日和约》)为分界线,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即美国主导的“强制赔偿期”和日本操作的“赔偿交涉期”。前者是从 1945年 8月日本战败投降,到 1952年 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旧金山体制确立。在长达七年的美军占领下,美军占领当局实行的是“间接统治”,日本丧失了单独对外交涉的权利,也不能独立地进行政策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美国的旨意。美国掌握了日本的战争善后赔偿等战后问题处理的主导权。摆在日本面前的唯有争取尽量减轻强制性的战争赔偿负担。所以,这个时期的日本战后赔偿体现出美国的亚洲战略构想和自身利益,经历了惩罚性的“拆迁赔偿”和不断减缓的赔偿过程。1949年 5月“麦考伊声明”的发表标志着强制拆迁赔偿终止。1951年 9月召开的旧金山媾和会议,最终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其中规定:“兹承认,日本应对其在战争中所引起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自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义务。因此:日本愿尽速与那些愿意谈判而其现有领土曾被日军占领并曾遭受日本损害的盟国进行谈判,以求将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在其他工作上的服务,供各该盟国利用,作为协助赔偿各该国修复其所受损害之费用,此项办法应避免以增加的负担加诸其他盟国。当需要制造原料时,应由各该盟国供给,借免以任何外汇上的负担加诸日本。”[2]这实际上反映出美国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又一个重要变化,即从原则上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但允许个别国家在签订和约后以双边交涉的方式获得日本的象征性“劳务赔偿”。
日本操作的“赔偿交涉期”是从 1952年 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国家主权之后,直到 1977年4月完成向缅甸支付 1.4亿美元的准赔偿止。这一时期,日本战后的东南亚外交是从赔偿交涉开始的。1952年日本经济已逐渐恢复,但日本与东南亚许多国家没有实现邦交正常化。这无疑是日本发展对外贸易的一大障碍。而消除这一障碍,必须解决战争赔偿问题。于是日本的赔偿外交交涉应运而生。日本开始巧妙利用国际形势以及索赔国的困境,以赔偿名义积极主动地开展对东南亚各国的赔偿外交,并在外交谈判中掌握了赔偿主动权,在上世纪 50年代先后与缅甸 (1954年 11月)、菲律宾 (1956年 5月)、印尼(1958年 1月)、越南(1959年 5月)四国缔结和平条约、赔偿协定和经济合作协定。赔偿与经济合作、投资开发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赔偿新模式。随之,日本陆续与老挝、柬埔寨、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蒙古等国相继签订了被日本称为“准赔偿”的经济合作协定或者“赠与”协定,进一步扩大了经济援助和经济开发规模。这不仅解决了悬停在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之间持久的、复杂的战争善后赔偿问题,结束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战争状态,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日本摆脱了“亚洲孤儿”的困境,同时也巩固了美国构建起来的东亚“防共反共”阵线。诚然,日本也以此为契机,以赔偿为旗号,以经济合作、经济援助为着眼点,开辟了对东南亚的出口市场,确保了天然原料资源的供应渠道。日本从 1955年开始支付赔偿直到 1977年终结,形成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突出经济外交色彩的战后日本外交新模式,日本重新活跃在亚洲的政治舞台上。
二、日本“赔偿交涉时期”的界定
“赔偿外交”(賠償外交)一词经常出现在日本学界、舆论界的文章、著述中,尤其在分析日本战后经济、外交以及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著述中屡屡提及。但是,在政府官员的相关正式发言中则多使用“经济外交”一词。笔者查阅了日本平凡社的《世界大百科事典》(2007)、小学馆的《日本大百科全书》(1994)、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日本外交史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新版日本外交史辞典》(1992)、《广辞苑 (第六版)》(2008)等辞书,都没有与之相应的条目解释。
赔偿 (Reparations),本文中所论及概念适用的范围是指战争赔偿。战争赔偿 (W ar Reparation),日语常用“戦争賠償”或“戦時賠償”来表意,是指由于战争行为,交战国 (战败国向战胜国)提供金钱、役务、生产品等作为损害、损失的赔偿,通常是指在媾和条约中规定的战败国对战胜国支付的赔偿金。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放弃了货币赔偿和产品赔偿,更多地改以实物赔偿方式,包括没收海外资产、拆迁过剩工业设备、提取当年工业产品与劳务补偿等。旧金山和约中又引入劳务赔偿的方式 (日语译为“役務賠償”)。“赔偿外交”词语,是“赔偿”与“外交”结合而生成的说法。所谓日本的“赔偿外交”,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为了与被侵略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而开展赔偿战争损害交涉的一种外交政策和行为。战后日本在美国冷战政策的指导下,以保护自身利益为目标,以落实《旧金山对日和约》中所规定的战争善后赔偿为旗号,以东南亚地区为重点,通过双方外交谈判,灵活主动地开展经济赔偿活动。截至 1977年,共支付赔偿 10.12亿美元,无偿经济合作 4.9576亿美元,合计折合 15.0786亿美元[1]536。“赔偿外交不仅是战后日本重建与东南亚关系的起始点,也是战后日本外交和经济外交的出发点”[3]。日本学者吉川洋子在《日菲赔偿外交交涉研究:1949—1956》中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模式(Pattern)被谓之经济突出型的经济外交,如果是因为赔偿交涉关系到经济财政问题,就简单地认定为经济外交的看法则是过于轻率武断,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了解整个赔偿交涉的过程,以及当事国的历史、心理、意识形态、决策方式、政治文化差异,就会明白这是一种显著而又历史价值很高的政治外交。”[4]
日本学界在审视日本从 20世纪 5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中期对东亚各国开展的赔偿外交交涉进程时,大多认为属于经济外交的范畴。但是,日本学界对“经济外交”的概念及其内涵存在较大歧义的。日本平凡社《大百科事典·2》(1984年)将“经济外交”定义为“把重视扩大贸易和市场,确保资源这种经济价值作为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5]。山本武彦认为:“如果对经济外交进行广义的定义,则可称为在对外政策上,为实现一国的各种利益,该国政府动员本国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实行对外交涉的一种模式……战后的日本外交,确实向实现‘贸易立国’的国家目标集中投入了人力、物力资源,以至获得了成为发达国家的成功果实。”[6]增田弘、佐藤进编著的《新版日本外交史手册》(2007年)中认为“经济外交”是围绕贸易、通商、交换、金融、投资等经济性利益的扩大而完成的外交,也是对战前军事外交的反省以适应战后新的国际社会经济秩序为目标,积极重视国家利益的外交理念。而据田所昌幸近年来的研究结果,他对“经济外交”下的定义是以“国际地位的重建”为目标,以“经济立国”为志向的外交。高濑弘文认为“经济外交”是包含为了达到某种经济目的的外交和利用经济性手段的外交两个方面,这是由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微妙,形式上能够相互转换。一个概念的产生并不仅仅取决该概念或观念所涉及的现象本身,而是能否准确地反映其事物的本质。在“赔偿外交”概念产生之前,以其他名称或语义来表达后来我们所称谓“赔偿外交”的现象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将赔偿外交纳入经济外交范围内是否妥当还有待商榷。
实际上,“经济外交”最先是由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在战后提出来的,就其目的而言无疑是区别于二战前的军事外交、武力外交、威吓外交,试图向世人表明其专心致志于经济活动、和平活动的政治“低姿态”。1952年 11月 24日,吉田茂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使用了“经济外交”的概念。他说:“扩大生产规模,加强流通机构,以增加生产,是我国经济的重要问题。为此,政府准备首先进行一系列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等,以发展贸易;同时增加远洋船舶,加强出口产业和运用持有的外汇,以促进进口,开辟出口市场,扩大贸易规模,特别是促进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7]181-1821955年,岸信介提出经济外交的构想时说:“重建国家的基本路线是:一、制定自主宪法和确立防卫体制;二、加强与自由主义国家的合作,推进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外交;三、纠正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建立有计划的自主经济;四、通过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革,提高道德水平。”[8]1957年 9月,日本外务省发表的战后第一本日本外交蓝皮书——《我国外交的近况》,明确提出“善邻友好、经济外交、调整对美关系”为日本外交“当前三大重要课题”,对“经济外交”进一步解释为“对信奉和平主义的我国来说,要提高充满四个小岛上九千万国民的生活,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唯一办法在于经济力量和平地向外发展,从而适合于国民经济要求的对外经济发展作为目的的经济外交是向我国外交提出的第二个重要课题”[9]。这是日本正式将“经济外交”作为国家大政方针而公布于众。
三、结论
笔者认为,使用“赔偿交涉时期”概念来概括日本战后对曾遭受其侵略的亚洲各国及其他地区实施赔偿的这个历史进程,能够准确地反映战后日本善后赔偿问题解决的本来面目。
首先,从日本战争善后赔偿产生的历史背景看,这个赔偿源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同盟国对日本进行应有的战后处理的主要内容之一,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已经规定日本必须向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蹂躏的亚洲各相关国家支付战争善后赔偿。这是日本必须面对和无法逃避的法律与道义问题。所以,一些国家将日本履行赔偿与建立外交关系联系在一起。日本唯有支付赔偿,才能获得索赔国的原谅,从而摆脱孤立的国际地位,重返国际社会。
其次,从日本实施赔偿的目标和内容看,日本政府为了开辟东南亚市场,获得充足的原材料供应,将赔偿与经济合作、市场开发三位一体联结在一起。日本参与了索赔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大量社会基础工程建设,例如缅甸的巴鲁河水电站、菲律宾的马里基纳河域开发工程、印尼的布兰塔斯河域开发、越南的达尼姆水电站等都在赔偿总额中占较大比例,其他方面如港口、铁路、通讯网、运输船舶等也成为赔偿的主要项目。
最后,赔偿外交的结果是日本与缅甸、菲律宾、印尼、越南四国先后分别签订了“和平条约”和“赔偿协定”,与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越南、蒙古等国分别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贷款或赠款协议。日本向这些国家支付赔偿及准赔偿合计总额约 15亿美元。这与索赔国所提出的数百亿美元的索赔要求相差甚远。尽管赔偿行为属于财经领域,包含大量经济援助、市场开发的内容,但以此断定属于经济外交则忽视了战争赔偿的本义。
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明确指出:“外交必须根据实际和潜在可用于追求目标的实力来决定自己的目标。”[10]1952年 10月,吉田茂内阁的冈崎胜男外相在战后首次发表的外交演说中强调说:“赔偿,应该作为政治问题来解决。”[11]力求以赔偿促外交,尽早与东南亚各国普遍实现邦交正常化,改善日本经济发展的地区政治环境,为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打下政治基础。这反映出日本决策层在对待赔偿问题解决上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吉田茂说:“我国由于《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在原则上负担了对战争时期日军曾经予以损害的东南亚各国支付赔偿的义务。当然,在原则上这是对战时损害的赔偿,不过在我国来说,必须把它视为加深彼此友好关系,建立经济密切合作的机会。我们在丧失了领土,丧失了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今天,当然希望援助东南亚地区的开发,确保粮食和工业原料的供给,并且使这个地区成为有力的市场。”[7]26由此不难看出,粮食安全、工业原料的安全已经成为战后日本赖以生存的根本,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其决定日本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实施赔偿外交是吉田内阁的一项重要对外政策。
作为日本政府政策性阐述,在吉田茂、鸠山一郎、岸信介等内阁的施政方针中多次提及经济外交,但仅是相对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文化外交而言的。之所以产生以“经济外交”代替“赔偿外交”的提法,无外乎在于日本的执政者从现实的利己主义立场出发,竭力模糊战争罪责及战争赔偿,内心深处不愿对日本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进行深刻的反省所致。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政府没有向世人做出过真诚的道歉。事实也证明日本没有丝毫对受害国赔偿的诚意,也不愿提及“赔偿”一词。“许多日本人对于赔偿问题感到好恶参半,日本民众也对赔偿问题大体上持否定的态度,赔偿谈判一结束,各报刊就很少再讨论这个题目”[12]。日本在赔偿问题上不仅态度消极,而且即便是在实施赔偿的过程中,日本人也不忘讨价还价。实施赔偿完全被日本人看成是做成一笔最大生意的机会,而完全不顾索赔国家民众的感情。因此,如果我们过多地强调赔偿外交的经济属性而将其划入经济外交范畴,就模糊了人们对日本赔偿外交的本质认识,也忽视了日本战后政治家们的政治野心,而且给大众造成仅从经济视角来看待战后日本历史责任的错觉,影响我们对日本应当承担的战争善后赔偿责任的辨析。
[1] 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財政史(第 1卷)終戦から講和まで[M].东洋经济新报社,1984.
[2] 国际条约集 (1950-1952)[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340-341.
[3] 周杰.战后初期日本对东南亚“赔偿外交”的策略变化分析[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70.
[4] 吉川洋子.日比賠償外交交涉の研究:1949-1956[M].东京:劲草书房,1991:344.
[5] 田中邦彦.大百科事典 (2)[M].东京:平凡社,1984:1317.
[6] 有贺贞,宇野重昭.国際政治講座 (4)日本の外交[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157.
[7]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 4卷[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8] 田尻育三.岸信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133.
[9] 外务省,編.わが外交の近況[M].东京:大蔵省印刷局,1957:9.
[10]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利斗争与和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39.
[11] 永野信利.日本外务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40.
[12] 劳伦斯·奥尔森.日本在战后亚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6-28.
〔责任编辑:时 妍〕
K1
A
1007-4937(2010)03-0120-04
2010-03-25
田野 (1963-),男,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
- 黑龙江社会科学的其它文章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路及实践坐标
- 从历史角度看科学划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