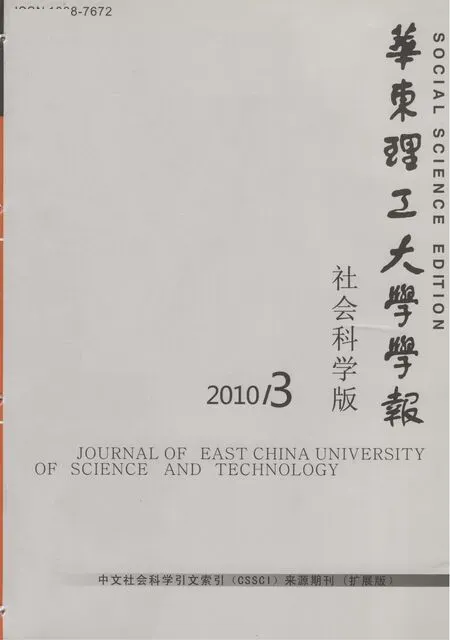偏差青少年同伴圈的形成研究及对社会工作的启示
费梅苹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上海 200237)
社会学与社会工作
偏差青少年同伴圈的形成研究及对社会工作的启示
费梅苹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上海 200237)
本研究通过深入访谈,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边缘化初期的生活形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同伴圈是其街头生活的基本形态。偏差青少年同伴圈由玩、结成玩伴、因利益形成同伴圈、建立认同感等阶段逐步形成。同伴圈的形成反映了青少年自主性发展的内在需求,且其自主性发展具有很强的群体性、相互影响和制约性特征。以上发现,对社会工作者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有重要启发。
偏差青少年 同伴圈 社会工作
一、有关青少年同伴圈的文献回顾
同伴关系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的观点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在现有文献中没有就青少年同伴圈的开展的相关研究。与此相近的是关于青少年团伙或者帮派的研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学者对于青少年团伙或青少年帮派的发展与贡献皆有其独特之处,有的强调团伙或帮派的描述,有的强调团伙或帮派的社会原因,有的则提出团伙或帮派的理论,或理论的整合。
从已有文献来看,青少年团伙或帮派研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一是青少年团伙或者帮派的特性界定。所有的关于青少年团伙或帮派特性的描述有比较一致的共识,如青少年团伙或帮派成员以青少年为主,他们有比较一致的背景;有严格的帮规;成员之间有高度的凝聚力;帮派的活动经常是反社会的、不法的、暴力及犯罪的;个人在帮派中的目标、角色及责任明确;命令是等级式;帮派有强烈的地盘意识;帮派持续不断地吸收成员,尤其以在校园内最为积极等等。①蔡德辉、杨士隆:《青少年暴力行为原因、类型与对策》,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309页。国内学者考察某个青少年团伙或帮派组织通常以我国九届人大二十七次会议关于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立法解释为标准来判断是否属于黑社会组织:第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人数较多;第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它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第三,以暴力、威胁或其它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百姓;第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容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①我国九届人大二十七次会议关于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立法解释。
二是青少年团伙或帮派活动的现状或成因分析。相关学者以调查数据和案例分析的方式呈现了青少年团伙或帮派活动的规模和内容②周心捷:《中国大陆地区青少年帮派活动的现状与原因分析》,《犯罪研究》2003年第3期;侯田田:《浅析青少年团伙犯罪》,《科教文汇》2006年第9期;杜文俊、李雅璇:《青少年帮派犯罪之预防与矫正》,《青少年犯罪问题》2009年第11期。,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青少年帮派组织不能完全等同于黑社会组织。有些学者就青少年的生理、心理、社会性特点对青少年团伙形成的原因进行分析。如关于青少年团伙犯罪行为模式基础的分析、关于青少年团伙形成的心理原因的分析等③王宏亮:《社会学视域下的青少年团伙犯罪》,《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刘翠花:《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特点、心理成因及预防》,《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闻静、张连华《关于青少年团伙犯罪的思考》2003年第7期。,提出了青少年的共同需要、模仿、逆反、冒险、团伙优势等是青少年团伙形成的主要心理基础。
三是对青少年团伙或帮派的预防、矫正研究。从立法、预防和惩治措施等诸方面开展了研讨。④刘翠花:《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特点、心理成因及预防》,《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杜文俊、李雅璇:《青少年帮派犯罪之预防与矫正》,《青少年犯罪问题》2009年第11期。
总结现有关于青少年团伙或帮派的相关研究,关于青少年团伙或帮派特性、青少年团伙或帮派形成的心理基础等的研究结论,为笔者开展青少年同伴圈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学术基础。但笔者认为,已有的相关研究,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第一,现有的研究主要针对青少年团伙或帮派而开展,并以团伙、帮派或黑社会组织的属性特征为判断标准对青少年群体性活动组织开展研究,尚没有以处于边缘化初期的偏差青少年街头生活的基本单位——同伴圈开展相关研究。而笔者认为同伴圈还没有衍化为青少年团伙或帮派组织,处于同学、朋友集聚期,或者说团伙或帮派的前属期。但作为青少年街头生活的基本形态,具有很大的普遍性,且有着其自身的特征和衍化方式,对其关注和研究可以丰富研究者对偏差或边缘青少年的理解和认识。第二,现有文献更多侧重于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注重青少年团伙或帮派这一现象存在的现状及原因分析,缺乏对于青少年团伙或帮派现象的产生过程,以及青少年团伙或帮派行为对青少年成长性需要满足或自主性实现的关系研究。而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了解和理解一个群体的生命轨迹,理解其行为和生活形态背后的生命意义,对于更好地协助青少年群体实现人生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笔者以某社区青少年矫正对象为研究对象,聚焦于从学校游离至街头,开始街头生活之后的基本生活方式开展质性研究。通过对22名研究对象的深入访谈,发现了同伴圈是青少年街头生活的基本单元或生活形态。笔者通过资料分析,形成了对青少年同伴圈的形成过程、青少年同伴圈对于青少年自主性发展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基于研究发现,笔者对青少年矫正社会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一些想法。
二、青少年同伴圈的形成过程研究
根据受访者访谈资料的分析归纳,笔者发现青少年同伴圈是伴随着玩而产生的;他们因玩的需要,在玩的过程中形成联盟,结成玩伴;玩伴们在追求共同利益,特别是在应对冲突纠纷时,逐渐形成同伴圈;同伴圈的成员彼此有一种认同感。
(一)玩
本文中所指的“玩”,主要是指受访者脱离学校后以网吧和游戏机房等为主要活动场所、以网络游戏等为主要手段的娱乐生活;同时也包括少数受访者在娱乐过程中与其他青少年之间发生的冲突和纠纷、打架,这些行为作为“玩”的衍生产物,与网络游戏和网吧活动一起构成青少年的“玩”的生活内容,他们对这些“玩”的形式或内容津津乐道。
1.玩的起始时间与玩的类型
大部分受访者从初二开始受同学影响而接触网络游戏。也有一些受访者一开始并不直接进入网吧,他们与同学或朋友在课外一起玩,如打篮球、踢足球、溜冰等等。他们在玩的过程中慢慢建立了交往圈,随着交往圈的扩大,他们接触人群多了,也跟随结交的朋友开始尝试不同的玩法,最终网吧都是他们娱乐生活的主要场所,网络游戏活动是他们普遍参与的娱乐活动,甚至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
归纳研究对象的访谈资料,青少年们认为玩有两种类型,一是进入网吧或者游乐场所的游玩方式,二是把街头闲逛、惹是生非作为玩的方式。
青少年认为进入网吧或者游戏场所游玩,主要受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与父母和学校的对抗。当发现青少年沉迷网络时,父母往往加倍地管教,学校也会以强硬态度予以规劝、批评或者处分。但这一切都会加剧青少年与家庭和学校的对立冲突关系。离家离校出走成为青少年反抗的主要方式。二是流行文化给青少年带来的影响。如蛊惑仔,是很多受访者都提到的影响他们对“酷”的定义和行为追求的香港影视片。他们的玩以及玩的方式及追求的感觉很多方面是缘于对这些影视剧情节的模仿性。
把在街头闲逛、惹是生非作为玩的形式和内容,虽然这个过程发生很多纠纷和冲突,但青少年们的感觉是“好玩”,觉得打人、欺负人本身也是很好玩的。究竟什么原因使这些青少年有如此行为和偏好呢?进一步的访谈发现,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从小被欺凌的经历让他们产生了一种报复和玩弄的心理。通常被欺凌的经历最早发生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二是会为了朋友,或者在女生面前示强而发生打架纠纷事件。按照受访者的说法,打就是为了争口气、为了帮朋友、为了面子。所以街头的打架并不一定是因为具体事件而引起,而受访者也常常把街头的打架纠纷视为是一种游戏,一种玩,但这种所谓的游戏和玩的背后,则是他们探索自我、实现自我、学习与同伴交往、处理冲突的一种社会化实践。
2.玩与青少年角色与行为规范的习得
当“玩”成为受访青少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时,玩的过程中慢慢出现的角色分工,玩的内容和玩的方式对他们行为规范的习得就发生了影响作用。当网络游戏成为青少年“玩”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时,网络对青少年角色型塑及行为规范的习得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受访者几乎都把玩网络游戏视为他们走出课堂、走入街头社会的主要生活内容。他们玩的游戏如魔兽世界、传奇、劲舞团、梦幻西游等让他们在沉迷的同时,在价值观、性格、行为等方面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网络游戏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虚拟版的现实社会,在里面可以释放所有的人的本性,也演化着成人世界诸多不良要素,如暴力、血腥、价值、欺骗、权利等等。在游戏中那种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拼杀,视对方为怪兽而不再有任何人的感觉的长期浸染,使青少年的暴力血腥倾向日益膨胀,现实生活中的打架和暴力冲突事件的频繁发生,也与这种网络游戏行为有直接的关系。
受访者在学校或家庭生活中受挫后,他们能在网游中得到满足,找到归属感。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实现了对青少年现实生活的替代和迁移,为处于发展和冲突之中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可以完全没有烦恼的新天地。而网络游戏的游玩过程,是青少年共同建构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角色地位、行为特征、价值取向等都有明确的规定。青少年根据游戏互动中的规则参与的同时,就是建立自我认同以及根据“网上的社会期待”塑造角色和角色行为的过程。青少年在游戏过程与网络环境中进行“角色换位”,把自己“假定成”不同的角色,体会不同角色的需求和情感并按照自己理解的角色规范进行角色实践,并通过游戏信息的反馈验证自己的角色行为。在多次的实践和验证下形成自己在现实社会中扮演各种角色的尺度。游戏过程中的“网络环境”为青少年理解角色、扮演角色、形成角色定位提供了反复实践的机会。网络游戏中所弥漫的价值取向、人际关系、行为方式,给正处于自我认同探索的青少年以非常大的影响。网络游戏的角色实践,使他们形成了相同的话语内容、生活方式,构成了共同的行为模式和处事原则,并逐渐形成了圈内生活。这个圈内的生活与主流社会的青少年有不一样的学习内容、不同的交往方式、他们逐渐具备了自己的同伴圈,以及同伴圈内的文化认同。
(二)玩伴
玩伴是受访者在街头生活的主要社交关系。对于一些曾经离开居住社区到外区上学的青少年来说,他们辍学或退学后回到居住社区所交往的玩伴,基本上是那些从小就很要好的小朋友,从小的伙伴是玩伴的核心群和同伴圈的雏形。
一些学校处于居住社区的青少年,或者还在学校读书的青少年,他们因同学而成为玩伴,在玩的过程中又结识新的玩伴,玩伴圈越来越大。一些受访对象是在网络游戏的过程中结识玩伴并结成同伴圈的。受访者普遍反映,他们喜欢和习惯于一帮人在一起玩,觉得只要在一起就是很开心的。尤其是初中一、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小,一个人总是很寂寞的,总希望有一帮人一起玩,大家在一起很开心的。他们在网络中玩在一起,大家都在QQ中聊天。即使现在很多人上班了,没有时间玩在一起了,下班回家,就上网QQ,看是否在,如果在,就聊聊天,然后睡觉了。感觉大家还是都呆在一起的。
青少年们在玩的过程中结识朋友,就像滚雪球一样,一个滚两个,两个滚四个,越滚越大。他们崇尚和痴迷蛊惑仔的样子,片中主角如何被人家打,大家如何出来玩,如何打,如何一点一点地获得圈里的位置,感觉与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一样的。他们认为自己的生活也是这样,也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所以就也想试试看。抱着这种想法,一帮人先是打篮球、踢足球,后来打游戏机、玩电脑等,还有小花园聊聊天,要么大家一起去唱歌。开始几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慢慢的象滚雪球一样的,如出去打架,认识几个人,出去踢球,认识一些人等,就这样一滚二,二滚四,越滚越大,最大的时候可以滚到20-30人的规模。
(三)冲突
游戏机房与网吧的不同是它的对打和对机游戏方式。一些受访对象在游戏机房因玩游戏而遭遇冲突。在一个充满竞争和冲突的游戏环境中,解决冲突以及为解决冲突而形成的同伴交往关系,不断建构着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并使他们的社会化过程具有了冲突性和群体联盟性特征。
通常来说衅事者是知道对方的底细的,如在什么学校、住在那个社区等。他们会候在校门外,或者候在街头,纠着一帮人过来找事。其实他们就是想要钱。所以游戏机房或者网吧游玩的时候发生的冲突,往往会衍生到游戏场所之外街头社会的群体之争、帮派之争。前一种冲突往往是受欺者遭受皮肉之苦及金钱损失落荒而逃,后一种冲突就会引发帮派之间的纠纷和持续的争斗。为了不被欺负,一些玩伴也会投身于某帮派门下求得保护,在免遭别人欺负的同时也可能成为了帮派的打手。
发生冲突时,如果是因为个人之间,或者一个人与对方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另一个人会劝的,但如果劝不住,他们打起来了,旁边人也会帮忙的。尤其是当朋友与他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即使本来不参与的,或拉住的,但看到朋友吃亏了,就会上去帮忙的。可能因为是男孩,正处于血气方刚的时候,觉得解决的方式就是以暴制暴。但有时候即使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就是一群人走在大街上,冲突也会惹上来的。在回击冲突、或者主动出击的时候,打架是这些青少年的主要表达和解决方式,或者说同道相处的主要方式。
玩和因玩而产生的冲突,成了受访者街头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交往形式。在玩中产生冲突,为对付纠纷结成联盟,或者从小的玩伴在进入街头社会后自然组成的同伴联盟。这个同伴联盟就是一个同伴圈,即由玩和玩中产生的关系建构而成的,有角色分工、有规则、有认同和归属感的同伴关系圈。
(四)彼此认同
大多数的受访者都认为在玩的过程中能够结成同伴圈的主要原因是觉得彼此都是同一种人。
有的受访对象说,他们一帮人,家境都很特殊,有的是有个后爸,有的是父母离异的,父母不管他们,随他们做什么的;有的是父母忙,只顾自己,也对他们不管的,只是在桌上扔点钱,也不问他们在外面认识了什么朋友。他们这些在外面玩的人的家庭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所以,当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在聊天和喝酒的时候都会说起自己的家庭的。大家喜欢在一起,就是因为觉得大家都很像,思想等都很像,家庭情况、喜欢的事情、喜欢的游戏、思维方式、冲动等不理智、觉得好玩就行等等这些都很像。因为这个“像”,使大家对彼此有一个认同,对大家的同伴圈有一种归属感。大家愿意聚在一起,吃住玩在一起,互相帮助互相支持。
我们发现,受访者的同伴圈是在他们的玩及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大家首先觉得是一个相同的群体,彼此接纳和认同,开始交往和聚集在一起。在交往的过程中有些同伴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形成彼此的支持和认同。当面对外力欺负时,他们共同抗争一致对外,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这个有彼此认同和接纳、结成联盟共同抗争外界、共同行动的小团体,就是一个同伴圈。
自从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后,受访者在玩的过程中接受的游戏训练,以及他们与玩伴发生冲突时的交往行为,从本质上遵循的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相互竞争的自然界法则,同伴圈是他们生存中的重要资源和生存的意义所在。当他们受到欺压时,同伴圈帮助他们抗击外界及维护自身的利益,当同伴圈的朋友遭到欺负时,他们义不容辞鼎力相助。他们的生活离不开同伴圈,他们也为了同伴圈的朋友而每天完成各种活动。他们在同伴圈内获得角色、地位和归属,也在参与同伴圈行动的过程中获得承认、尊重和满足。
同伴圈的成员可以分为两种,核心圈和随从者。核心圈是同伴圈的起源和关键组成力量。但随着青少年交往活动频率和规模的扩大,也有一些追随者加入同伴圈,他们参与活动,听从安排,享受与大家在一起的时光,也成为同伴圈的固定成员。当受访者讲起他们的关系和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凝聚力的时候,他们常常用“好朋友”三个字来概括和表达。好朋友之间也有他们认同的相处原则。比如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为了面子不愿辜负朋友的期待、在乎、友情等等。
三、对青少年同伴圈的理论思考
笔者提出同伴圈的概念是因为青少年不仅是组成玩伴的集合,而很大程度上结成了真正的同伴联盟。他们是基于规则发生互动;有一种归属感;形成群体自己的规范,包括游戏、穿着,如何思考和如何行动。一些关系紧密,并开始在网吧之外的街头社会有黑道交易的同伴圈,还会形成成员为共同目标而努力的结构或等级组织(如领导者或其他角色)。生活在同伴圈中的青少年会发现合作的价值,形成共同目标的责任感和忠诚感,学习社会组织如何实现目标等很多经验。
皮亚杰等一些理论家认为,同伴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起到了与父母同样重要的作用。①Harris,J.R.The Nurture Assumption:Why Children Turn Out the Way They Do.New York:Free Press,1998.Harris,J.R.“Socialization,Personality Development,and the Childs Environments:Comment on Vandell.”Developmenal Psychology.vol.36,2000,pp.711-823.韦伯斯特新大学词典把同伴定义为“相互之间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发展学家也认为同伴是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或者是至少在某些时候行为复杂程度相似的个体。②Lewis,M.and Rosenblum,M.A.Friendship and Peer Relation.New York:Wiley1975.同伴的典型特点是有同等地位和权力,如果他们希望友好相处或者实现共同目标,就必须学会理解彼此的观点,互相协商、妥协、合作。因此,同龄、同等地位同伴的交往有助于青少年获得在不平衡氛围的家庭中难以获得的社会能力的发展。
根据劳伦茨·斯坦伯格(Lawrence Steinberg)和苏珊·西尔弗伯格(Susan Silverberg)的观点,青春早期对同伴的强烈顺从是自主发展的必要步骤。①Steinberg,L.and Silverberg,S.B.“The Vicissitudes of Autonomy in Early Adolescence.”Child Development.vol.57,1986,pp.84-851.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对父母依赖逐渐减少,但是他们还没有自信坚持己见,因此需要同伴接纳提供一种安全感,并且依附他们。如果他们常常完全顺从成人的规定和价值观而没有机会与同伴在一起,就不可能得到这种接纳。
上述各类论述,为笔者理解受访者的同伴圈现象提供了理论指引。同伴圈对青少年自主性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社会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需要进一步反思的是,这种对青少年的社会化产生极大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同伴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呢?
一般来说,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主体与客体、客体之间、客体构成要素之间相互沟通、由此达彼的“通路”。②沙莲香:《“己”的结构位置——对“己”的一种释义》,《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关系可分为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在本质上是心理的、人格的。人际关系的一个特点是它是在人际沟通中形成的,通过接触,形成印象和判断,产生某种好恶亲疏之感等等,由此,又可以将人际关系理解为心理关系。由于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因此,各个生活领域都充斥着心理距离不等的亲疏远近。人际关系,它就像个横断面一样,插入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这种交错,就成为社会资源之配置、分配和转移等,提供了一种“人工”之路。
“关系”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特殊功用:
梁漱溟在谈到中国社会的“本位”问题时提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也是关系本位,“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也就是说,在社会与个人相互关系上,中国社会既不是把重点放在个人,也不是把重点放在社会,而是放在“关系上了”;中国伦理看重的是“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而忽视社会与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由此,梁氏说,伦理社会所贵者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对方”。③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明路书店1949年版,第101页。
许烺光提出“情境中心”概念,用以说明中国人的相互依赖性特点。“情境中心”态度取向是“以一种持久的、把近亲连结在家庭和宗族之中的纽带为特征。在这种基本的人类集团中,个人受制于寻求相互间的依赖”。④许烺光:《宗族、种族、俱乐部》,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60页。“情境中心”概念,提示出个人的依存性和依存关系的多重性。
费孝通使用“差序格局”概念来说明中国人的关系特点。他说,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遇到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⑤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29页。“差序格局”这一描述性概念,蕴含着一个重要观点,即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大圈套小圈的“关系圈”。
金耀基使用关系性和个体自主性来说明中国人人际关系特点。他认为,儒家的关系视角为中国人提供了一条途径,使他们能够创造一个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个体乃是一个关系的存在,被赋予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主性,并置身于一个复杂的、富于人情的关系网络中”。中国人以个体同其它个体或群体共有的“归属性特征”来与之发生“多元的”认同关系;“个体拥有的归属性特征越多,就越能拉关系”。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拉关系”这一人际装置中,使人类固有的“关系”变成能够起到社会资源“调动”作用的东西,这是金耀基说的“把关系的建构作为一种文化策略来调动社会资源,藉以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达到目标”。①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9-71页。金耀基的这种“文化——关系”思路,给人们提供了宽泛的思考空间。
从四位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是中国社会的“关系本位”,其义在于把社会生活重点“放在关系上了”(其重点不是社会,也不是个人);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个人,是依赖于他人的“关系者”。二是成为社会本位的这个“关系”,是以人伦为准则的“圈子”、“关系网”,其社会实质是个人对个人的私人关系。三是“圈子”中的这个个人,是关系的中心,有自主性。
分析受访者的同伴关系,笔者发现在同伴关系建立之初,青少年更在乎一种关系带来的感觉与反应,一种平等、自由、尊重、接纳、认同、归属感的获得。当同伴关系衍变成为同伴圈时,这时候的关系对青少年的影响更体现在青少年同伴关系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这种相互依存性和依存关系的多重性在青少年身上凸显,有的是相互平等的;有的是呈层级分布的;有的是合作的;有的是命令和服从的;但彼此依存、彼此依赖。在这个关系中,他们彼此认同。一旦发生与圈外的纠纷和冲突,他们会团结一致,一致对外,他们也会争取更多的其他伙伴圈前来相助。关系对于青少年获得社会认同和获得生存空间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从同伴圈的研究中发现了青少年对于关系的依赖。这种依赖关系丰富了笔者对青少年自主性发展的理解和认识。这种自主性是依附于关系之中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关系可能会促进青少年自主性的萌发,如一些同伴圈中的核心领袖,他们承担了促进关系的维持和发展的领导功能,在承担领袖角色的同时,培养了其自主性的发展。但有一些青少年也因对关系的依附而推迟了其自主性的发展,如同伴圈内的一些随从者,他们会满足于服从和依附,不思考、不主动,一切随大流,安于同伴关系的玩乐中被动地接受任何安排,自主性发展受到制约。因此,青少年的自主性发展是具有很强的群体性和相互影响和制约性特征的。
四、青少年同伴圈研究对社会工作的启发
笔者通过对青少年同伴圈的研究发现,进入社区矫正体系接受刑法执行的青少年罪犯,他们的很多行为处于帮派行为的边缘,或者是接受帮派委派而发生的。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帮派组织的一员。只有很少的1至2名受访对象陷入帮派组织中,并成为该组织体系中的骨干成员。但受访者自身结成的同伴圈,他们之间却已经形成了比较高的凝聚力,有初步的自然形成的角色分工,有一定的地盘意识,要遵循内部的团体规则,所以这些同伴圈已经超出了一般松散型的同伴或伙伴关系,具备了帮派组织的某些要素,虽然他们以玩为主,但常受到帮派组织拉拢,个别青少年已经成为帮派组织的帮手。同伴圈内的青少年失败的学校经验、紧张的家庭关系、渴望寻找新的经验、追求获得被尊重的内在需求,这些构成他们对于群体关系的追求和认同的内在逻辑,而帮派组织中大哥的“关照”、“帮忙”、“支持”、“温暖问候”、“撑腰”、“罩着”等等,成为吸引青少年接受或者加入帮派组织的重要因素,也成为青少年加入帮派组织或者参与帮派活动的内在动因。因此处于帮派组织萌芽状态的同伴圈现象,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应成为社会工作者关注的重点。
以同伴圈为主要形态的协同性群体行为,为青少年寻找自我和实现自我提供了支持,并创造了获得自我认同和价值的机会和场域。青少年在寻找自我、追求价值的过程中参与群体性活动,获得了同伴群体认同,实现了自我价值,由此更强化他们的行为和交往,逐渐形成以同伴圈为依托的自衍行为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相互刺激和产生结果的发展过程,青少年自身的寻求自我和价值追寻是核心动力。或者说,同伴圈成为青少年主体性不断萌发的支撑载体,满足了青少年实现自主发展的根本需要。这是需要引起社会工作者高度认识和关注的。
由此的结论是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的开展,只有把握了青少年追求自主性发展的内在需求,以符合青少年同伴相互支持的形式开展服务,不断提升和引导青少年对生活和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认识,内化及优化其自主发展的方式和途径,才能真正符合青少年的发展要求。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of Delinquent Adolescents’Partner Circle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Social Work Studies
FEI Meiping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with adolescents under community corrections,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Partner Circle is a key component in the adolescents’street life.The formation of such Partner Circle undergoes stages of“playing together”,“becoming playing buddies”,“forming fixed Partner Circle based on interest”and finally “developing mutual recognition”.The formation of such Partner Circle reflects the adolescent’s need of self-motivated development,and such development is social,mutually influential and mutually restrictive.The above knowledge provide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on social work studies.
delinquent adolescents,Partner Circle,social work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偏差青少年社会关系干预研究》(课题编号:08 B S H024)资助 。
费梅苹,女,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青少年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
C916
A
1008-7672(2010)03-0018-08
徐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