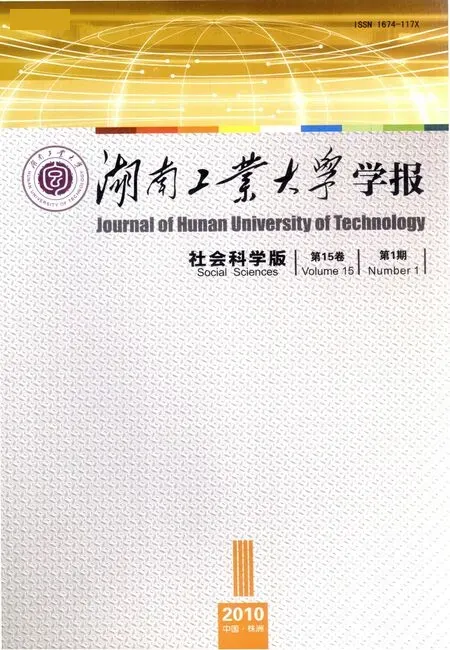从《〈希望〉编后记》看胡风编辑刊物的倾向
赵双花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从《〈希望〉编后记》看胡风编辑刊物的倾向
赵双花①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200241)
从《〈希望〉编后记》看胡风编辑刊物的倾向是:严肃的文学观,继承与发展鲁迅精神以及主观战斗的现实主义。胡风所编《希望》比《七月》更进一步地实践了自己的文艺理想和编辑理念,而每期的“编后记”则鲜明地揭示了这种倾向。
《希望》;胡风;鲁迅精神
文学史上的“七月派”是以胡风1937年9月11日在上海创刊的《七月》而得名。《七月》之所以在连绵的炮火中,在四处流落中不致湮没无迹,能够死中复生,是在“许多作家的协力和读者的参加下而产生,成长的”,而这恰恰又证明了七月社编辑部“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结合点的存在的尊重,对于各派作家的创作方面的重视,对于作为友军的许多文艺堡垒的尊敬,而且表示了我们对于文艺将在民族战争里而得到万花灿烂的发展的预想”。[1]从这方面看,《七月》明显的是为抗战服务,为团结更多的进步作家服务的。当然,《七月》不仅仅满足于这些,在胡风的理解里,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不仅意味着政治倾向的一致,同时还是创作方法上的趋近。后因《七月》被查封,刊物改名为《希望》。《希望》从1945年1月到1946年10月共出版了2集,每集4期。在每一集的第一页目录的下方,都有一个“致读者”的说明,其中一点是:“愿意广收同好者的来稿,凡文艺创作与文化批评不论哪一类(暂不收纯学术性的文章)也不论长短,由几百字到两三万字,除了我们认为不好,或者实际是好的但我们不能理解的以外,都愿发表。”[2]那么,胡风们对所认为的“好”是怎样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倾向性表现在什么地方?而且他们对保持这些倾向所做出的努力在文学史上又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不妨结合《希望》的“编后记”来思考一下。每期必有的《编后记》可以说是刊物的眼睛,最直接地体现了胡风的编辑审美标准、用稿原则,最直接地的向读者呈现了刊物的质量。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分析:
首先,胡风在编辑《希望》时不断申明文学的严肃性。在每一期的“编后记”里,胡风都会郑重其事地简要分析他所选文章的理由,而每一条理由都与文艺界发展的不良倾向有关,与努力把握整个民族的文艺走向有关,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与文艺理论工作者的态度、眼光。他在第1集第4期“编后记”明确申明文艺的战斗性,反对以游戏的态度进行文学创作,这对当时沉浸在胜利氛围中的人们是一个必要的告诫。
这种严肃文学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重视文学的批判功能。批判,在胡风看来,实是文艺创作的应有之义。细读《希望》每一期的杂文专栏,这些杂文从历史、政治、文化等角度入手,直击现实社会的各样弊病,显示出追求社会正义的勇气与力量。如何取得斗争的全面胜利,在胡风看来,人格的健全,精神的胜利是更为重要的事情,批判的锋芒更是对准民族痼疾。在第一集第一期“编后记”中,胡风在评价路翎中篇小说《罗大斗的一生》时说到:“《罗大斗的一生》就是色彩浓郁的油画的大幅。在这大幅上面,有色底渗透和线的纠结,人民的苦恼,负担,和希求,在活的生命形象上使纸面化成了一个世界。在作品里看不到‘结论’就惊慌失措的批评家们也许要用显微镜来寻找‘主题’罢,但我不妨冒昧地说一句:我们所要求的人民的英雄主义是能够从这里呼之即出的。而且还不妨再加一句:在文艺思想上,无论对于客观主义或教条主义,这都能成为有效的一击。”[3]其中所说的“人民的苦恼,负担”不正是千百年来农民所受的精神奴役创伤的体现么?而这又无不是承续了五四时期鲁迅开创的“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题。
在提到舒芜的《论主观》时,胡风说:“但《论主观》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求新生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这问题所涉甚广,当然也就非常吃力。作者是尽了他的能力的,希望读者也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3]对于文艺批评,他的态度是:“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追索到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的联系,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揭开而且解剖一切病态倾向的真相保卫而且培养一切健康力量的生机。但批评要实现这样的任务,就非处在能够个人直说真话的民主政治的条件下面不可,因为批评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民主性的行为。只有在民主政治下面的民主的批评,才能够反映时代,教育读者,把创作实践以及批评实践本身推进真理的门。”[4]胡风是真诚地想得到批评的,也是真诚地想通过批评来追寻真理,促使文艺走向健康之路的。单单从随后几期陆续刊出的舒芜的《论中庸》(1集2期)、《思想建设与思想斗争的途径》(1集3期)、《个人、历史与人民》(2集1期)等进一步阐释《论主观》的文章就可以看出。
其次,是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胡风是很看重精神榜样的力量的:“精神巨人所给予我们的力量,犹如他在他的那个时代苦斗了过来一样,是要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时代也坚强地苦斗下去的罢。”[5]虽然他不是每篇《编后记》都提及鲁迅,但他从鲁迅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则是毫无疑问的。在第二集第四期的《编后记》中,胡风似乎显得特别的疲乏与无奈,由于出版公司的经营出了问题,刊物不得不脱期,而且能否继续,心中还没有底。但是这个月恰逢鲁迅逝世10周年,胡风还是打起精神将这期几乎做成了纪念鲁迅的专刊。封底是胡风作词的歌曲“鲁迅先生颂歌”《由于你,新中国在成长》,封面内里引了鲁迅先生的三条语录,283页的填白处也引用了鲁迅的话。除此之外,刊登了鲁迅写给胡风的六封信,发表了胡风自己1937年10月写过的专论鲁迅精神的《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指出鲁迅不是新思想的介绍者或解说者,却是运用新思想同旧势力做彻底斗争的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斗士。鲁迅战斗的一个伟大特点是“把‘心’、‘力’完全结合在一起”。至于鲁迅精神的现实意义,胡风在文尾指出:“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期的今天,鲁迅的信念是明白地证实了:他所攻击的黑暗与愚昧是怎样浪费了民族力量,怎样地阻碍了抗战怒潮的更广大的发展。为了胜利,我们有努力地向他学习的必要。”[6]同时,还发表了舒芜的《鲁迅的中国与鲁迅的道路》,这篇长文以雄辩的气势论证了目前的中国还是鲁迅当时所面对的中国——“在这个国家里,‘旧社会的根底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在这个国家里,充满了‘做戏的虚无党’……”。[7]我们所要走的道路还是鲁迅所选择的道路——“不断铲除着这样的‘光明’,显现出‘黑暗与虚无’之为‘实有’的道路”。[7]我认为这篇文章是对8期《希望》中的文学创作在追求、体现鲁迅精神时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其它很多创作也是接着鲁迅所开创的话题继续说的。试拣举两例:耿庸《说到“民主”》历数了野史记载的豪绅为竞为赌而吃人的令人发指的行为,不仅指出这是鲁迅“吃人历史”观的具体例证,而且指出“吃人历史”的有可能再续,且是以“民主”的名义。署名“一筒”的杂文《关于“发抖”》,借史指出发抖实是奴隶心理病态的体现,而这又体现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中,哪怕是揭竿而起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陈胜吴广也不过是农奴。奴隶实是我们民族的最基层,是支撑金字塔的庞大底座,这与鲁迅提出的民族劣根性不是一致的吗?
最后,与以上两点紧密联系的是胡风旗帜鲜明地提倡主观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在第二集第一期的“编后记”中,胡风重申了在抗战结束后,关于抗战主题的写作必要性。对于表现抗战时期的人民的生活变革与精神状态的作品,胡风说“历史总是由过去走向将来,更何况抗战时期的社会性格现在还并没有成为过去?”[8]所刊登的三个诗集正是表现了战斗的理想与战斗的情绪。在第二集第二期的“编后记”中,胡风指出“在现在的中国,一切都现出激烈的变动,一切都现出鲜明的对照。”[5]他还指出:“知识分子,无论他从现实人生中取得什么,怎样取得,向现实战斗给予什么,怎样给予,总是要通过他的思想武装,也就是精神发展的过程的。”[6]
胡风强调知识分子的精神改造,但这种改造与解放区《讲话》中提到的“改造”却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改造”意思也是他发表在《希望》第一集第一期首篇位置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中所提到的“自我斗争”。在这篇文章里,胡风以一种流畅、富含激情的雄辩气势论证了要取得民主的彻底胜利,在文艺领域里就必须坚持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从感性的对象来看,是血肉的现实人生,它“是思想内容的最尖锐的最活泼的表现。”[3]他认为“只有从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开始,在文艺创作里面才有可能得到创作力的充沛和思想力的坚固。”[3]如何体现这种现实人生呢?“在对象的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把握它的社会意义,在对象的具体的活的感性表现里面溶注着作家的同感的肯定精神或反感的肯定精神。”[3]这对创作主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仅要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且“主观力量”要“坚强”,“坚强到能够和血肉的对象搏斗,能够对血肉的对象进行批判,由此,创造出包含有比个别对象更高的真实性的艺术世界。”[3]同时,作家要向“感性的对象深入,深入到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3]对于作家来讲,这种批判、表现的过程也意味着“自我斗争”,因为既然对象是充满感性的,那作家的思维活动就不能逾越感性的机能;同时现实生活是紊乱、繁杂的,人们身上沉淀着几千年累积而成的“精神奴役创伤”,如何不被它所淹没、所同化而保持着批判的锐度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除了站在“和人民共命运的实践立场”外,还应具备“坚强的生活意志”,即人格力量。胡风认为,只有“通过了这样的自我斗争,一方面,对象才能够在血肉的感性里面涌进作家的艺术世界,把市侩的‘抒情主义’或‘公式主义’驱逐出境;另一方面,作家的思想要求才能和对象的感性表现结为一体,使市侩的‘现实主义’或‘客观主义’只好在读者面前现出枯萎的原形。”[3]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斗争。这是胡风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所发表的对于文艺创作的见解,我们可以明确地领会到,胡风对于新文艺“启蒙主义精神”的继承,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的走向应该如何的设计与解答。只有这样的现实主义才能抗击法西斯主义以及封建主义的精神压制,才能取得最彻底的解放。而备受争议的舒芜的《论主观》则从哲学的角度具体阐释了何为主观,主观作用自身的发展是怎样的情形以及为什么说发挥主观作用是今天战斗的武器。《在疯狂的时代里面》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压迫尤其是精神压迫依然存在,旧的势力做着最后的挣扎、叫嚣,甚为疯狂,而新生力量“被冤屈所啃嚼,被痛苦所燃烧,被失望所窒息”,也就陷入了另一种疯狂里面。如何才能从这疯狂的泥淖里走出来,获得坚强与健康呢?胡风剖析到:“这坚强,这健康,从客观上说,是产生自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需要的结合里面,从主观上说,是产生自巨大的热情和远大的认识的结合里面。”[5]前者提供了运用战略的基础,后者提供了相应的能力,而道路则在于客观情势里斗争的过程。在这里,胡风强调了主观、客观结合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之上,主观的努力是关键的环节。这依然是其在重庆时期“主观战斗精神”的重申。
每期的“编后记”提纲挈领般地点出了胡风在编辑《希望》时所持定的原则,足以代表胡风的文艺理想,也反映出当时文艺界的创作状况。他所说的严肃的文学观侧重于对黑暗的批判,他所承继的鲁迅精神是对鲁迅的战斗性的强调。
[1]王大明,等.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G].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54.
[2]胡 风.编后记[J].希望,1945(1).
[3]胡 风.编后记[J].希望,1945(1).
[4]胡 风.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G]//胡风评论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5.
[5]胡 风.编后记[J].希望,1946(4).
[6]胡 风.编后记[J].希望,1946(1).
[7]舒 芜.鲁迅的中国与鲁迅人道路[J].希望,1946(1).
[8]胡 风.编后记[J].希望,1946(2).
The Journal’s Tendency Seen from Its Editor Hu Feng’s Post-editorial Remarks of Hope
ZHAO Shuanghua
(Chinese Department,East China Normal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
From"Post-editorial Remarks"of Hope,one can see the editor Hu Feng’s or the journal’s serious literary view,the spirit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from Lu Xun,and the subjective fighting realis m.Having in mind a clear editing idea,Hu Feng carried for ward his literary ideals further now than when he was editing July.Editorial remarks of each issue best express his tendencies.
Hope;HU Feng;Lu Xun’s spirit
G237.5
A
1674-117X(2010)01-0079-03
200-11-04
赵双花(1980-),女,河南南乐人,山东省济宁学院中文系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李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