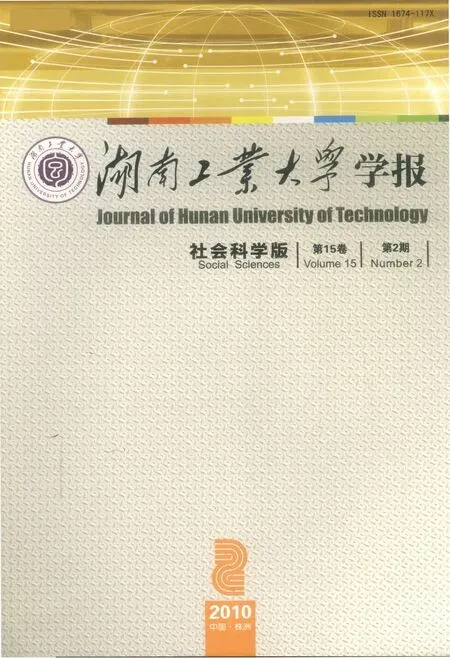米兰·昆德拉流亡书写下的身份认同模式*
李 维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米兰·昆德拉流亡书写下的身份认同模式*
李 维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流亡状态下的个体把追寻自我的认同作为生命的本能,但认同的过程必然有其复杂性,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就呈现出个人核心的单向认同、价值核心的双向认同和双重身份的去核心认同三种身份认同模式,这些认同模式象征性地反映出米兰·昆德拉对现代性社会下的时代和个人身份的认知状态。
米兰·昆德拉;流亡书写;身份认同模式
法国捷克裔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特殊流亡经历和流亡生活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危机、自我价值的缺失以及人类情感的无所依托,使得其给予了流亡情境下的自我生存状态和个人身份认同以热切关注和深刻思考。流亡下的个人身份认同是流亡者永恒的追诉,也成了昆德拉流亡书写的重要主题之一。其移民后的创作:从《笑忘录》到《无知》,无一不是用各种变奏述说着这一主题。昆德拉说:“人与世界连在一起,就像蜗牛与它的壳;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状态。”[1]45那么自我的认同也就不是个人对自由、独立等主体性的绝对追求,它必须被放到历史、社会、民族等概念中来论述和被承认。而本文在探讨昆德拉流亡书写下的身份认同模式中所强调、所追寻的身份认同,其实就是期望自我“与……一样”,把自己变得“与……相同”。这个期望和转变的过程它不能完全依靠个人意识活动来完成,而需要自我与心灵、与他人、与社会、与历史文化相互交流、相互选择。正是这个交流和选择的过程产生出认同的复杂性和艰难性,使人们在追寻自我认同的途中呈现出不同的身份认同模式和自我认知状态。以下本文就从个人主体的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生命追寻及其与他人、社会、文化等外部世界的不同关系来具体探讨昆德拉流亡书写中所表现出来的三种身份认同模式。
一、个人核心的单向认同
个人核心的单向认同模式指的是个人的身份定位、自我解读、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在与他人、社会、文化等的碰撞、交流过程中得不到认可,而成为一种纯粹的个人化理念追寻,最终只能淹没在社会主流意识的大潮中。
《笑忘录》里的塔米娜是一个一心活在过去的流亡者,所以她想要拿回留在国内的记载自己和丈夫11年波希米亚生活的信和记事本,但她同时又是一个在普遍遗忘中试图保存自我记忆却最终陷入绝境的悲剧性人物。她付出巨大代价想找回过去记忆的失败正是其个人追寻得不到他人认同的确证。塔米娜和丈夫的关系,其对爱情、婚姻的忠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她对自我生命的捍卫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婆婆不仅不为塔米娜对儿子的深情所动,反而跟她算起了过去的旧账;父亲坚持给塔米娜送皮大衣,认为那比信包更重要,但这并不是父亲在意女儿的健康,而是父亲一直不喜欢女婿,向他发动了无休止的战争;而丈夫的政治问题更是让弟弟唯恐避之不及。他们对塔米娜要拿回信和记事本的请求是冷漠,推托,甚至拒绝。而在外人雨果那里,这个请求变成了交易。觊觎塔米娜已久的雨果一直以信誓旦旦地要去布拉格来诱惑塔米娜,然而他的满腹激情在塔米娜那里遭遇了性冷淡,变成了不得不屈从的将就和交换,他想要的世界——他要在里面捕获塔米娜并融合着他的血液和思想的世界——破灭了,[2]178意想不到的失望和报复欲望使他丧失了为人的道德和信誉,他决定不去布拉格了。这样一来,塔米娜的希望落空,她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与祖国亲人的相互隔绝、彼此陌生,与流亡的朋友的相互不信任、彼此不理解的桎梏之中。她成了这个世上孤立的个体,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也不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之中。作为一个现代社会中失去家园,找不到归宿的象征性人物,塔米娜没有了“客我”,也就没有了某一意义上的“主我”,她丧失了获得自我认同的基本条件——“个体只有在与他的社会群体的其他成员的关系中才拥有一个自我”,成了尘世间一个虚无的存在。[3]129
再如《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弗兰茨的追寻始终没有得到萨宾娜的认同,包括他们的情人关系。正像昆德拉在小说中所展现的那样:弗兰茨喜欢音乐,认为那是使灵魂得以释放的救星,而音乐在萨宾娜那里却是一群放出来扑向她的猎犬;弗兰茨坚信忠诚使我们的生命完整统一,而萨宾娜却被背叛吸引——“再没有比投向未知更美妙的了”;[4]110弗兰茨想要消除私人生活和公众之间的阻隔,“活在真实里”,而萨宾娜却认为“失去私密的人失去了一切”,[4]133活在“真实”里的惟一方式就是保留私密。弗兰茨和萨宾娜在生活观念与个人信仰上的巨大差异导源于他们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背景:弗兰茨是欧洲民主社会中渴望理想、革命和激情的知识分子化身,而萨宾娜来自高度极权社会——一个革命梦想早已破灭的国家,[4]123是一个对革命、理想、进军与个性自由的冲突有着深刻体验并勇于追求自我的知识女性。艾晓明就曾说:“弗兰茨要进入境界恰恰是萨宾娜要逃出的,弗兰茨正在寻求和建构的象征意义又恰恰是萨宾娜不断消解和取缔的虚假意义。”[5]331其实,弗兰茨对萨宾娜的追求,对其祖国的向往都是建立在一厢情愿式的幻想中,因为他并不真正了解萨宾娜、萨宾娜的祖国以及在那发生的一切,更不可能理解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思想、情感和需求。所以弗兰茨一直陶醉于其中的,认为能帮助他找到真实的生活,找到自我,满足其对萨宾娜的渴望的伟大进军不过是一场荒唐的闹剧和一个荒唐的梦,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根本得不到萨宾娜的响应,也不可能实现他要的爱情和理想生活。而萨宾娜否认了弗兰茨,也就背叛了爱情,她一生的背叛,背叛父亲,背叛婚姻,背叛大街游行,最终让她流落异乡,陷入了无所背叛的虚空。
弗兰茨的死,是他以个人价值认同为核心实现自我及其向往的真实生活在现实的检验中破产的悲剧性结局。临死之际的弗兰茨终于知道了自己惟一真实的生活,不是列队游行,也不是萨宾娜,而是一直深爱着自己的女大学生。而萨宾娜的背叛和反媚俗,是她对真实自我的追寻和对绝对服从的抗争,但这种抗争却让她成为了昆德拉笔下勇气惊人但命运悲惨的形象化身。因此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乔治·H·米德说:“只有当他人的自我存在并进入我们的经验时,我们自己的自我才能存在并进入我们的经验。”[3]128也即个体只有在与他人达成共识、与外部环境相适应时,他才能够使他自己成为一个自我。而弗兰茨和萨宾娜正是不能在他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承认他人,也就失去了获得自我实现条件。这种以个人为核心的单向认同模式正是在个体间交流与对话的隔阂与不可能中摧毁着自我身份的建构与认同。
二、价值核心的双向认同
价值核心的双向认同模式指个人主体在自我身份、自我解读、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的定位上与其所追寻的社会大环境的主流价值因素相一致,在此,个体的需求也是他者的渴望,能够与他者互动,得到其中大多数成员的共鸣。个体企图获得的大众认同的意愿也就在这个有着共同价值取向的磁场里得以实现。
其实,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四处存在的都是迷失自我、渴望找到身份定位的流亡者,但真正能够实现自我,得到大众认可的人并不多。在其流亡书写中笔者仅从《不朽》和《慢》中窥见了一些找到“价值归宿”的心灵。
《不朽》展现的是一群十分渴望在人类历史和记忆里留下足迹的人们,他们稀罕“不朽”的名声,并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其中的贝蒂娜和洛拉就是把感情上升为价值的人,她们利用感情的价值进行自我扩张,控制他人的思考,来达到自己“不朽”的人生追求。贝蒂娜一心想与歌德建立起暧昧的情人关系,好在歌德仙逝后紧握他的手,把自己领入光荣的殿堂。为此她不停地给歌德写表达爱慕之情的信,接近歌德的母亲,给歌德设计雕像草图,还在歌德死后花了3年时间修改、重写、补充他们之间的通信并出版。为自己在人类历史上创作了一部名不副实的罗曼史。而洛拉则通过做加法,不断地在她的“我”上面加上新的属性来培植她的独特性。所以我们会看到怀抱着暹罗猫的洛拉、有着优雅手势的洛拉、戴着墨镜的忧郁的洛拉、在地铁筹集募捐的洛拉……最终她赢得了自己想占有的一切,包括姐夫保罗。
而在小说《慢》中昆德拉刻画的是一群寻找“自我价值”的人:他们在公众中乞讨荣耀以获取自身存在的意义,在他人身上寻找爱慕的眼光以获得自我存在的证明。在书中他们被戏称为“舞者”。舞者追求的是荣耀,是道德的嘉许,恐怖的是得不到公众目光的注视和青睐,登不上表演的舞台放射自我的光芒。所以才有了一见到摄像机就做秀的议员杜贝尔克和知识分子贝尔克之间展开的道德柔道竞赛;才有了参加昆虫学术会议还在游泳池旁旁若无人“模拟交媾”的文森特、朱丽,以及只顾对着话筒自我吹嘘,陶醉在众人的欢呼声中而忘了演讲的捷克学者。
其实,昆德拉在《不朽》和《慢》中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现代的自我世界。其中的“不朽者”和“舞者”从某个层面上讲都是现代个人主义的认同者,也是现代性社会中涌现出来的新型的个人价值的追求者。他们这种自我实现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性社会的产物,也是昆德拉在小说中明确指出的现代性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意象学”艺术显现,“它影响了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政治观点、我们的审美趣味,甚至影响了我们所喜爱的地毯的颜色和书的选择;这种影响力和从前思想体系是一样的。”[6]132所以他们(这些意象学家们)对身份的表达不再满足于独守自我的那份宁静,而是更具向外侵略性;他们“念念不忘把自己的生活看作一件艺术品的材质”[7]22,渴望在众人的颂赞喧哗中开创自己的“艺术人生”。在这里,人类的自我实现已不仅仅是“我”的单向度的表达,更是在人类历史和个人记忆中的“我”的显现。自我肯定就是投身人群,在众人的目光中实现和完成。“在这点上,它不仅需要别人,而且在竭力——正如革命一样——将所有人控制在自己的掌中。”[6]404
从昆德拉的小说书写上我们不难看出他对这个现代自我的世界没有好感,对这群现代个人主义者的价值观也并不称道。在这个世界里自我是在别人身上映射出的我的形象;自我必须回到集市上,陈列在所有的目光中;自我不能忍受不被爱,不能忍受不作为惟一的存在而存在。这个现代自我的世界仍然是一个极权的世界,[6]405而这些现代个人主义者把“不朽”、“被看”当作了一种价值追寻,一种获得自我的方式。他们都是在对这一价值的认知上达成共识,由这一个价值核心凝聚在一起,从而在无形中结成了一个具有某种固定特性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中,因作为团体的一员,他们彼此间才能相互认同,才能在同一价值诉求的双向互动中实现自我的追寻。而不同于前文谈到的塔米娜、萨宾娜和弗兰茨,他们找不到容纳自己的团体,也不知道自己归属于那个团体,所以追求自我的认同也就成了单向的纯个人的理念图示,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依托。但这种自我完全在他者中建立,也深刻地反映出他们真正自我的丧失与对大众自我的追逐,也源于一个快速运转的社会中人类自我价值的迷失。
三、双重身份的去核心认同
双重身份的去核心认同模式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后殖民主义的身份认同理论。后殖民理论家们否定和摒弃了本质主义的身份认同观,认为身份不但是被建构的,而且是依赖某种“他者”被建构起来的一套或者一系列的身份。如霍米·巴巴就表示“今日文化的定位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而在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处和疆界处。在那里,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的’、或混杂的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8]307同时,他还提出了“双重身份”。作为一种身份建构策略,“双重身份”并不是简单地说有两个身份,而是要指出身份协商的重复性,及其连续的重复、修订、重新定位,没有哪次重复与前面的是一样的。[8]310后殖民主义的这些认识的潜在进步意义就在于否定身份的固定性,而认为它是一个可以协商、变动、有多重因素相互混杂,需要不断重新定位的过程,这样去中心自然就成为身份认同的本质特征。所以,简单说来,双重去中心身份认同模式就是指个人不再拥有恒定不变的身份认同感,身份成了一个混杂的、不断协商、不断修订、不断重新定位的循环过程。
昆德拉的小说《身份》的主人公尚塔尔就是一个在不断地身份转变中追寻自我的人。现实生活中的尚塔尔一直戴着面具跳舞,在不同面具的映射下变换着自己的身份,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承受着不能同时拥有的痛苦和害怕失去的痛苦。尚塔尔一直在追寻一个“玫瑰香”的神话,渴望一次艳遇,像玫瑰香一样四处扩散,穿透所有的男人,并通过男人去拥抱世界。所以她一边做着让·马克忠诚的情人,一边小心翼翼地掩盖着自己追求爱,渴望被更多人爱,进而得到了爱的心灵出轨的小女人的欣喜和不安。流走于忠诚的小情人和追求虚幻爱情的男性征服者的身份之中,但这些其实都不影响尚塔尔拥有自我的身份,因为这些都是尚塔尔的个人追求,是她在不同的生活情境和人生需求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个人特点,同时是她对自身存在的更多可能性的追寻,也是后殖民主义所强调的一个主体的双重性、矛盾性和冲突性的显现。正如霍米·巴巴所辩解的:“因为本质主义的身份模式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了:身份更多的是演现性的,是你自己建构起来的一种认同感。”[8]298
同样,在昆德拉的近作《无知》中也存在着这样一些去核心的双重身份的拥有者,他们就是被迫离开家园多年的流亡者伊莱娜和约瑟夫。他们在流亡地都有着自己的生活:新的工作、新的家庭、新的亲人和朋友,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活就在这里了。尽管如此,但每当提起回归、提起自己的祖国他们还是满怀眷念、心驰神往的。他们是努力融入移民地的生活,却又无法摆脱故园之根的移民者,始终处于本国文化和移居地文化的纠结中;处在历史和现实的冲突中;处在过去和现在、记忆和遗忘的对抗中;处在自我身份定位的焦虑与矛盾中,找不到自身的归属和认同。
离开祖国的移民者们不可能真正归属于移民国,而只是移民地人民眼中的流亡者,他们始终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与祖国同命运、共荣辱,肩负起自己公民的使命和责任。正如伊莱娜的朋友茜尔薇所表示的,伊莱娜应该回国,那才是她的家,她的祖国正大事当前,不得逃避;也如约瑟夫的妻子所说的,他“应该来这……不回去,是不正常的,没有理由的,甚至是卑鄙的。”[9]74在移民地人民眼中,流亡国外是一个悲剧,流亡者是痛苦的。而同时,回到祖国的流亡者也无法与祖国人民融为一体,他们在祖国亲人的眼中已成了一个逝去的人。正如回国后的约瑟夫,他觉得自己的回归“就像一个死人在二十年后起死回生,走出坟墓”。[9]73曾经属于他的房子、他的表、他的画都已被哥哥、嫂子占据;曾经熟悉的母语已成了一门音调陌生的语言;甚至连亲人的过世也没有人给他发过讣告。他对祖国及其人民来说“根本就不存在”,[9]54为此,他也就无法再在过去的社会关系中定位自我的身份。
可见,移民者不论身处自己的祖国,还是流亡国都不能得到完全的认同,他们处在两种文化身份的交织中,却又无法真正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所以他们对自我身份的找寻就成了一个矛盾性、协商性的探索过程,“一种引用、引证、重新定位、重复和修订文化风格、传统和身份的能力”。[8]187-188移民者或许应如欣赏“混杂文化”和“世界主义”的霍米·巴巴一样拒绝一种始源的、稳固的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而宁肯选择一种矛盾的、协商的和演现式的双重身份,永远据守自己那不确定的移民身份。这或许就是主体在现代性社会的影响下的身份认同取向,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身份从未被视为完整的,而应将其看作一幕场景,或者一个意义、价值和立场的循环,看作一种整体性的幻觉。[8]301
流亡情景下的个体身份认同是流亡者永恒的心灵叩问和自我追寻,昆德拉流亡书写下的不同身份认同模式正是流亡者们相异的自我价值取向、个人追寻和自我认知状态的展现,但也是他们关注个人的“生命世界”,在生活——这种永远沉重的努力中,努力使自己在原位中永远坚定地存在的展现。
[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 米兰·昆德拉.笑忘录[M].王东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约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 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 李风亮,李 艳.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1986-1996)[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
[6] 米兰·昆德拉.不朽[M].王振孙,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7] 米兰·昆德拉.慢[M].马振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8] 王 宁.文学理论前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9] 米兰·昆德拉.无知[M].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IdentityM odes in M ilan Kundera’sW ritings on Exile
L IWei
(College ofLiberalArts,Hunan Norm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Individuals in exile regard pursuing self-identity as an instinct.However,the process of identification is complicated.There appear inMilan Kundera’s novels three identitymodes:one-way individual-oriented identitymode,value-oriented dual identity mode and de-centered identity mode,which symbolically reflectMilan Kundera’s state of perception of the modern society aswell as his personal status.
Milan Kundera;writings on exile;identitymodes
I106.4
A
1674-117X(2010)02-0078-04
2010-02-05
李 维(1984-),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