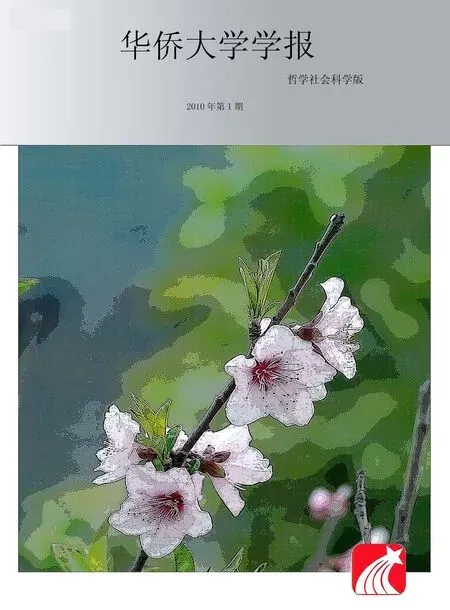看得真与真的看
——试论“可见性”的内涵及其层次
○姚 波
(华侨大学 建筑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可见性”与“可见者”是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以下简称梅氏)的现象学常用的一对概念,用以探究“看”这一行为的实质内容及其在艺术表现中的贯穿和作用。“可见者”尚可被明确地理解为被知觉并意识到的事物,但“可见性”的内涵在日常知觉的表现中就不那么简易明了——看见“可见者”似乎就意味着对其“可见性”的确实把握,然而梅氏又断言常人眼中的“可见者”总是忘记其“可见性”——个中究竟就必须藉对“看”这一寻常活动的逐步剖析加以认识。以下讨论无疑要涉及怎样“看”才是纯真的,是什么阻隔和遮蔽了我们的“看”,以及艺术靠什么来说话等问题。弄清这些问题,会使我们在当下艺术嘈局中保持应有的明辨力;更将有助于我们的艺术教育在时尚与经济的大潮中增强定力,把稳舵盘。
一 “看”的本真状态
在笔者的认识中,人初始之“看”的方式是已然被理式设定了的,其第一要义就是适于生存。这样“看”在生活中的首要(最基本的)任务就恰恰不是为了看(真的看),而是为了求真,遂瞬息转向对可见者的识辨和确认(看得真)。这里的“转向”意味着“看”在一般的观看过程中总要经历的一种难以察觉的被替代程序,而这一切都表现出毋庸置疑的与生俱来性,说明尽管“看”可以从零开始,但其最基本的观视方式却是已然被先验地赋予了:初生的视觉或日常之看恰恰不是无目的或盲目的,它生就由理式的法则约束和操纵,执行着通过“看”进行归纳、抽象、记忆储存、对照、识辨等直接关乎其生存的指令。也就是说,本能的“看”的方式及其过程所体现的恰恰不是感性而是理式预设的规定性。
可见本能或日常之看是功能性的,目的不在自身而在于身外事物。这就让我们意识到,由于生存的第一性要求,“看”必须先完成规定任务,而后才有可能自由活动。这也意味着“看”在本能或日常性运作中总是处于被“非看”消化和处理的状态,所谓归纳、抽象、记忆储存、对照、识辨等程序必须是在“看”的直观性退席的前提下方可展开,亦即“看得真”必须由阻断“真的看”来实现,从而使得日常性的看与其说是观看,毋宁说是经由理智来得出判断的反思,从而使常人认为看到的事物与其真正看见的事物有着质的视觉差异。针对这种真正的“看”总是终结于理智介入的日常性观看,梅氏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常人眼中的可见者忘记了它的各种前提,它依赖于一种有待重新创造的、将摆脱囚禁在它身上的那些幽灵的完整可见性(的反思[注]括弧内的三个字“的反思”非译文原有,为笔者所加。笔者认为没有这三个字,译文的意思无法通解。因为梅洛—庞蒂一贯认为知觉先于反思,先于知识,而常人的视觉是以反思、知识来代替知觉,从而使其认为看到的事物脱离了它们被知觉的前提——“光线、明亮、阴影、映像、颜色等。因此“反思”才是导致常人眼中的可见者忘记其前提的“罪魁”。译文显然是将被遗忘的东西与造成遗忘的原因错译为一谈。)。”[1]45的确,按照一般唯物论认识,直观到的东西往往流于肤浅,要抵达“真相”当然需要一种再造——人的理性反思对可见事物的“去伪存真”的处理。这个“真”就是“常人眼中的可见者”,因为它已被去“伪”——“摆脱了囚禁在它身上的那些幽灵的完整可见性”,也就是被“常人眼中的可见者”遗忘了的“它的各种前提”。这正是人的“为了看见事物,我们没有必要看见阴影”[1]45的日常之看的逻辑:阴影善变(如幽灵)而事物本身不变,故而忽略阴影而直逼“真相”,以至于忘记了“真相”首先出自其阴影对它的描述——由于要看得真,故而在意识上必须忽略真的看。如此一来,常人眼中的“可见者”实际是一种“非可见者”,它已祛除了事物能够被看见的感性前提,所以它毋宁是一种其形式经反思而被概念化了的“已知者”的呈现,而非由直观直接触及到的“可见者”。
日常之看虽说具有无意识的本能性,但其功能性的视觉逻辑或内在模式却在人类的长期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中得到了有意识的肯定和强化,它的那种“去伪存真”的探索与征服的信念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和理性的高度发展而变得愈加坚不可摧,使得“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发变得难以挣脱科学和功利的操纵:总是急于与事物拉开距离,以便将其控制为清晰的客体。在它冷峻、肃静的“注视”下,事物无不经历剥茧似的剖析、解构和重构,成为一种绝对功能化的对象。正如梅氏所说:“科学操纵事物,并且拒绝栖息其中。它赋予事物以各种内在模式,依据这些模式的指标或变量对事物进行其定义所容许的各种变形,它只不过渐行渐远地与现实世界形成对照。”[1]30由于这种对照之形成的超强稳定性和排他性,“看”作为一种单纯的知觉,在日常的活动中就极易被干扰和阻断进而被导入知性判断的思维轨道,这不仅导致生动而富于变化的知觉现象难以得到理智的圆满的解释,更令人的知觉感受力变得愈发贫弱而几乎沦为理智主义的附庸。
“看”(感觉)因已知的介入而退席。也就是说,当人不再对照,不再分析、不再自以为是地面对事物时,“看”才能真正地亲近乃至栖息于事物活生生的呈现之中。所以“生活”才是“看”的恰当姿态,它意味着被看的事物都处在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之中,互为前提、互为存在、相依为命,任何变动都会导致生活的改变。而真正的看就是视知觉对某一生活的融入。相反,理智主义则执着于事物的纯粹性,势必无视和排斥外界影响。故而梅氏有言:“理智主义看不到被感知物体的存在和共存方式,看不到贯穿视觉场、暗暗地将视觉场各个部分联系在一起的生活。”[2]62因此,当一种事物的模样与理智主义所理解的模式相合时,“看”就不再继续而被立即代之以已有的概念形态;反之则被称为“错觉”,意思是错误的感觉。殊不知太多的感觉的“错误”都属于理智参照下得出的莫须有。
譬如“泽尔纳错觉”[注]泽尔纳错觉是指,在一组平行线中的每一条线上,分别画上方向不同的同一种排列的短线,这组平行线就会显示出不平行的感觉。。加上了辅助线之后的主平行线在感觉上不再平行,辅助线在图样的结构中显然是注入一种奇特的视觉力量:横向排线均使主线产生向上弧的感觉;竖向排线均使主线产生向下弧的感觉,从而将主平行线原有的生活改换为另一种生活。这无疑为原图形引入了一种崭新的、至此与该图形不再分离的意义。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知觉作为视觉场的整体把握,场中各部分的当下关联性决定其意义的形成,部分的变动导致其关联性的变异,从而构成新的生活-意义。“生活”就是事物在某种环境中与其他事物磨合共生的生存状态,是十分具体的场氛围呈现,绝不可能是事物的孤立描述。也正是在这意义上,美国心理学家埃德温·波林才断言:“严格地说,在心理学中不存在错觉这个概念,因为实际上任何经验都不能完全摹写现实。”[3]287因此,“错觉”这个概念对知觉而言是武断的,它是以已然确立了的绝对事实为依据,对具体感知到的现象施加的独断,在其判断中,那个事实实际上是空洞的、失去了其特定生活环境的概念性存在。所以“错觉”又是一个悖论,因为作为“觉”来说,它是只针对来自现象的直接刺激获取的直观感受,无所谓对或错;而那个“错”却恰恰在实际上不能被“觉”察,它不是来源于感知而是得自于判断——严格地讲,没有错觉,只有误判。这就证明了梅氏的论断:“判断是采取的立场,旨在认识在我的生命的每时每刻对我来说和对存在着的和可能存在的其他人来说有价值的某物;相反,感知则致力于显现,而不试图占有显现和了解显现的真实。”[2]60
再譬如对色彩的感知。如果说理智主义的“看”特别注意事物的命名(如那是个“苹果”),并以其名称所导引出的事物的概念图形来结束看的过程的话,那么他对色彩的把握亦是如此(如那是个“红”苹果),只不过他会在事物的统称之前再加上一个色彩的统称——固有色的名称(色相)。至于颜色的具体纯度和明度它并不关心,而这在画家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英国艺术理论家罗斯金就曾经说过:“形状是绝对的,因此你就能说在此时你画了一根正确的或错误的线,颜色则完全是相对的。遍及你作品的每一块颜色都是由你在其它地方添加的每一个笔触得以改变的,这样,一分钟前的暖调子,当你在另一个地方摆上一块更暖的色彩时它就变冷了,一块和谐的画面,当你在旁边放上其它颜色时,就变得不和谐了,这样,每一个笔触都不是为了当时的效果,而是为了它未来的效果摆上去的,它的所有后来的结果,都是先前考虑到的。”[3]287-288所以对知觉而言,任何已有的经验和知识都是无益的,必须避让给单纯的“看”。
这样看来,单纯的“看”由于其性质的单纯固然常被画家和艺术理论家称之为“童真之看”或“天真之眼”,却在实际上并非随意能够做到。对比人的初始之看或常人之看,单纯的“看”的有意识的实现在常人那里往往相当困难,即便有时就身处其中也无意识;而真正的童真之眼亦如前面所说过的,由于本受限于理式天赋的规定,其“看”也确不单纯,只是幼稚罢了。儿童画的形态所普遍具有的圆形性可以充分证明,童真之眼恰恰是高度简化和概念化的,与单纯的“看”的思维方式大相径庭。可见单纯不等于幼稚:幼稚体现为经验的稀缺与思维的简单化;单纯则意味着对一种思维方式的坚守和执著。所以单纯亦可谓纯粹。
基于这个角度我们将不难发现,无论童真之眼或常人之看,他们都包含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思维——感性的和理性的——方式的迅即转换:感性的用作搜集信息,理性的用作处理信息并得出结论;而艺术家、画家所追求的“天真之眼”,其实质就是单纯或纯粹的“看”——一种始终处于感知(或无知)的状态:注视各种存在呈现于感官面前的具体生活,欣奇于各种造物之可见的万千变化,沉浸于种种外在现象所营造的可见的精神氛围;不分析,不辨识,不判断,无须功用亦不作结论,只以对事物之可见性的纯粹体验来缔造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活,供视觉-心灵栖息。
二 “可见性”——“看”的核心内容
如果要为“看”找出其在传统上可对应的词汇,那毋宁是日常语汇中的“欣赏”,以及艺术理论或美学中的“审美”。然而众所周知,“欣赏”或“审美”活动有着明确的价值取向,那就是美。“赏”与“审美”的对象在今天一般都是被认为具有了美的必然性的一些事物,譬如绘画、雕塑、建筑、工艺品、戏剧、音乐等,再如日出日落、海景、雪景、山水等自然风景,“看”已然被规定为一种赏识,其对象已被预先告知为美的事物。然而,纯粹的“看”是不被规定的,它没有预设的前提,是一种放松的甚至是无目的的观视生活,是眼睛与显现的投入和忘我的对视、浏览、私语;真正的“看”在于对意义的发现,既包含对美的发现,也包括牛顿看到苹果坠落时对引力形式的感悟。因此,对“看”而言,包括美在内的所有感知意义都是或然的,期待每一个个体的视觉体验、感悟和发现。既然是视觉体验,事物的“可见性”就必然是“看”的核心内容,而“美”的知觉作为一种价值的取向就是对某种“可见性”的知觉诠释。由于“美”这样一种价值在人类的发展史上被积淀了太多的人伦的、道德的等社会价值判断的内容,常常使审美越离“看”的范畴(即把善,甚至把真视作为美)。有鉴于此,用“可见性”的概念来对应、解释和讨论“看”,无疑比用“美”在实际上来得更单纯、直观和通俗。要弄清这一点,就必须了解所谓“可见性”的具体内涵和层次。
梅氏在其《眼与心》中论及“何者为画家之所求”时这样写道:“光线、明亮、阴影、映像、颜色,画家所求的这些客体并非全都是一些真实的存在:就像那些幽灵一样,它们只有视觉上的实存。它们甚至只处在常人视觉的阈限之上,它们不能够被普遍地看到。画家的注视向这些客体询问它们如何被捕捉到……以便让我们看见可见者。”[1]44这段话明白道出了“可见性”之所指——它不是物质实体,也不描述存在的真实性,它的静默的出场只为了显现自身;当然,它可以用来见证存在,但这与纯粹的“看”无关。纯粹的“看”只关心显现,并因此只关注那些直接导致显现的知觉因素及其构成的现象。这些与“看”直接交流的可见因素及其整体促成的视觉-心理现象、景象或情境,就是事物的“可见性”。也就是说,恰恰不是说我们看到了事物就等于看见了它的“可见性”,否则就不会有梅氏“常人眼中的可见者忘记了它的各种前提”的断言,而是说“可见性”是既作为让事物被看见的前提条件被真正地意识到的,同时又被作为“看”的直接对象的那些东西。 如此一来,所谓“可见性”就必然首先就指向光线、形状、线条、明暗、体块、质地、颜色等使事物可见的前提要素。
但是很显然,“看”并不止于此。这些形式要素只是“可见性”内涵的最基层的内容,“看”必须由此展开才能进入实质性的空间。正如梅氏所言:“由于万物和我的身体是由相同的材料做成的,身体的视觉就必定以某种方式在万物中形成,或者事物的公开可见性就必定在身体中产生一种秘密的可见性。”[1]39此处的“公开可见性”,其实就是指光线、形状、线条、明暗、体块、质地、颜色等使事物可见的前提要素,它们毫无偏向地对所有的视觉开放;但由于知觉个体的差异性,每一个“身体的视觉”在万物中看到或投射的对应性情形是不尽相同的,或者说事物的“公开可见性”就必定会酿成不同的视觉-心理图景(感受)。这正是“秘密可见性”的秘密所指,它构成了事物“可见性”的第二层含义,让“看”由对基层的形式要素及其关系的审视和把握跃上赏读或审美的实质性层面并浸淫其中。举例来说,我们都看到了草地上的一朵小花,可只有某人在凝视后怅然道:“多么孤弱的美丽呵!”看到了草地上的一朵小花是对一个物理事实的确认,而某人在这之外不仅感到了小花的美丽,还进一步体验到其存在的孤弱。这样,“孤弱的美丽”就成为“草地上的一朵小花”这一自然景象的人性化的抽象诠释,就成为“草地上的一朵小花”所呈现的一种深层次“可见性”的发现。是它,作为一种精神空间,一种价值取向,让某人情不自禁地哪怕只有片刻地浸淫其中。
可见单纯停留于形色的“看”在生活中很少发生,事物的形色作为一种“可见性”通常是一种引子,它有可能引发诗意的情怀并与之亲近、互动进而继续释放出较深层次的“可见性”,以激发物我的通灵和共鸣;而对于常人的现实性眼光,它通常就戛然而止于被看到而不再有任何交流。有鉴于此,笔者才认为梅氏的上述论断只适用于纯粹的“看”而与常人之看无缘,只有纯粹的“看”才会创造物我交融的契机,才会在我“身体的视觉”看到事物的同时,也看到事物中清晰展现出的我的相应情感的“可见性”。
值得注意的是,梅氏的这一段话还传达出与西方主流哲学认知非常不同的宇宙观,带有明显的“天人合一”的东方色彩。“由于万物和我的身体是由相同的材料做成的,身体的视觉就必定以某种方式在万物中形成”明确表达了人与万物皆为自然意志与物质的产物,二者乃同质一体的存在的观念。所以他能够深刻地认识到,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人的一切就可以在自然中找到其对应,人之所看也就必定会在某种契机下转化为万物之眼,进而达成人之所感与自然之所显的一种不谋而合,或者说事物的物理外显就必然会因与人之所看所感的碰撞产生某种奇妙的同构性、相似性的呈现,正所谓“身体的视觉就必定以某种方式在万物中形成”。从而使人之看不仅是对事物的观照,亦是人通过事物对自身的观照——人与自然的精神的共生共通;从而看与被看的转换与交织会令人的身心产生出一种既不同于看者亦不同于被看者的两者兼而有之的互拥惬意的景象。诚如“当一种交织在看与可见之间、在触摸和被触摸之间、在一只眼睛和另一只眼睛之间、在手与手之间形成时,当感觉者-可感者的火花擦亮时,当这一不会停止燃烧的火着起来,直至身体的如此偶然瓦解了任何偶然都不足以瓦解的东西时,人的身体就出现在那里了……”[3]287这个“人的身体”不就是人在对自然事物的关照中看到的自身,不就是人与事物互拥惬意的景象,不就是所谓的“秘密的可见性”——一种人性化了的景象的浮现吗?!
由此可知,“可见性”的公开与秘密的关键差异在于,前者意味着事物之呈现所必须具备的客观视觉条件,后者则表现为由事物呈现之现象引发的与看者有某种心理对应或同构关系的主观反映。由于这种反映带有浓烈的心理-情感取向,客观的自然景象在人的眼中就有了如“萧瑟”或“悠然”一般的人情色彩。因此,“可见性”的公开与秘密两个层次实际对应的就是人的眼与心:“眼”是一种直观层次上的看;“心”则是经由直观上升或转化为直觉层面的感知意识,是一种不经由理智而直接把握景象情感实质的看。直观与直觉都主张视觉对事物不假任何先入之见的零距离接触,但直观倾向于对事物客观外显形态的整体感知和把握,直觉则更强调人在直观事物时所获得的内心体验。这一点也清晰反映在美术教育的阶段上,譬如专业院校的基础写生课所侧重解决的是如何观察和准确表现事物客观呈现在那里的形、色及其整体关系——肉眼层次的“公开可见性”的捕捉与传达;而高年段的写生无论是静物、风景、人物,均特别强调在肉眼层次基础之上的对事物呈现的“情调”、“氛围”、“意境”这些具有浓厚内心体验色彩的内容的把握和强调表现——心眼层次的“秘密可见性”的捕捉与表现。肉眼与心眼——公开可见性与秘密可见性——的不谋而合才能构成艺术表达或创造的真正缘起。
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在梅氏给我们分析的两种“可见性”中,“看”显然都还只是停留于转瞬即逝的知觉过程,而且这种发现“可见性”的知觉越是强烈,它消失的速度可能就越迅速,因为任何感受的震撼力都会在持续的感受中削弱乃至消亡,人的知觉神经不可能总处于亢奋和激越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需要艺术,用它来留驻令人感动知觉景象,让本只属于个体的“秘密可见性”以某种独特的方式转化为具有“公开可见性”性质的“纯粹可见性”,以期让别的视觉都能看到其所看到的“可见者”。换句话说,在艺术表现中,第一层次的“公开可见性”和第二层次的“秘密可见性”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被转现为最高层次的“纯粹可见性”。所谓艺术作品就是为纯粹的“看”而创造的集三个层次的“可见性”于一体的“纯粹可见者”。
在艺术中,亦即在“纯粹可见者”中,公开与秘密的“可见性”要成为纯粹的,就必须与某种绘画材料结盟,并依附在它由其物质特性与作者个性的相互作用所呈现出来的诸如特有的形色、笔触、刀痕、色渍、构成等手法之上,这样一种由特定绘画材料、作者个性在绘画运作中创造出来的纯粹诉诸于知觉的技巧呈现,笔者称其为“绘画可见性”。换言之,公开与秘密的“可见性”的表现必须依赖于具体的“绘画可见性”才能实现其具体的传达。
绘画在西方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是以模仿为目标的,而模仿恰恰是以尽量消除或抑制“绘画可见性”来换取公开与秘密的“可见性”的表现的。“绘画可见性”的真正解放是在18世纪,尤其是印象主义绘画以后的事。后来的超级写实主义绘画则是例外,但它与其说是以极力消除“绘画可见性”为手段,毋宁说是极力消除“绘画可见性”本身就是其重要目的,也可以说:消除“绘画可见性”本身就是其所追求的“绘画可见性”或“纯粹可见者”。然而绘画在照相机诞生之后的反思告诉我们,见诸于材料的视觉特性、绘画个性和绘画自由之上的表现,才是绘画在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标志和价值所在。由于绘画个性和绘画自由的发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绘画材料物理与视觉特性的认识、理解及其熟练的掌控与施展,故而“绘画可见性”的个性化表现就成为绘画艺术之价值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可以这样讲,有了好的构思、构图,表现意图亦即公开与秘密的“可见性”的传达也很清晰,但如果在“绘画可见性”的表现上乏善可陈,也就是说,前两个层次的“可见性”传达缺少第三个层次“可见性”(绘画材料特性与作者个性)表现的物化融合与展现,那么作品的艺术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正是绘画及其画种能够并将永远存在下去的根由所在。
三 结 语
因此,只有在艺术中,“可见性”与“可见者”才可能升华为纯粹的并合而为一,这也是艺术之为艺术的基本规定:它源于生活但被抽离了原本的物质实体,只借用物质的形式及其构成因素间的关系的呈现来默示生活于其中的“可见性”寓意。因而它的形式即内容,它只有呈现,并只在呈现中实现一切。亦即,艺术无需自身以外的释义方式,它自成一体,它就在那里默默地自圆其说着;任何其自身以外解读方式的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就是它静默的呈现,它应当也必须活在呈现中并在“看”中得到确认。所以艺术的表现要特别警惕文字语言的阐释,“阐释”将鲜活的直观感受转述为反思的形式,使得转述的过程必然成为以“看”或感受为思维对象(客体)的另一种语言形式的再组织与传达。这种传达通常是基于个体视角的描述,带有较强的个人风格及其认识与判断的确定性,在不同程度上就会形成对他人之“看”的下意识的控制与催眠,因为“知觉是感知的思维。它的体现不呈现出任何要解释的确定特征,它的亲在只不过是一种对自己的无知。反省分析成了一种纯粹倒退的学说,在它看来,一切知觉都是一种含糊的理解活动,一切规定都是一种否定。这样,反省分析取消了所有的问题,除了一个问题:它自己的起源的问题。”[2]65这一点表现在阐释者以职业批评家、理论家的身份出现时尤其如此:常使一人之眼取代众人之“看”,为了阐释的圆通,结合其自身语言组织的另一种想象力和组织力就必须活跃起来以求自身的通达,受其影响的“看”就往往被异化为迎合、趋附(看得真),从而失去知觉(真的看),一切听命于文字的武断。国内外的一些被热捧的当代艺术尤其前卫艺术样式及其作品不正是在文字的阐释中得以流行、喧嚣的吗!这些作品的共同特征在于极端蔑视对表现内容之“可见性”的挖掘与传达,亦即轻视对内容表现的直观性形式与技术的研究,故而让要表达的“可见性”失去与“可见者”合而为一的可能,或者说他们要表达的东西根本就不具有或者尚未捕获其“可见性”,这就逼使观众的“看”离开文字的阐释便无的放矢、莫名其妙,终而在根本上架空了“看”。
“可见性”既是艺术表现冲动之缘起,又是其核心内容的体现:“可见性”愈强,其“可见者”就愈具感染力,“可见性”弱则其“可见者”乏味或牵强,未具“可见性”者则其“可见者”不成其为可见者,或者说是一种空洞的可见者。艺术的“皇帝新衣”往往就是以不尊重“看”,不重视事物的“可见性”研究与传达,最终不得不用概念、观念遮蔽并凌驾于直观感受的强权方式编织出来的。尊重“可见性”就是主张感性思维,主张不设任何前提地去看——真的看而非看得真,主张艺术的创造与表达从形式的观察、研究和探索出发终而又回归为呈现着的形式。
参考文献:
[1]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眼与心[M].杨大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 [英]贡布里奇.艺术与幻觉——绘画再现的心理研究[M].周 彦,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