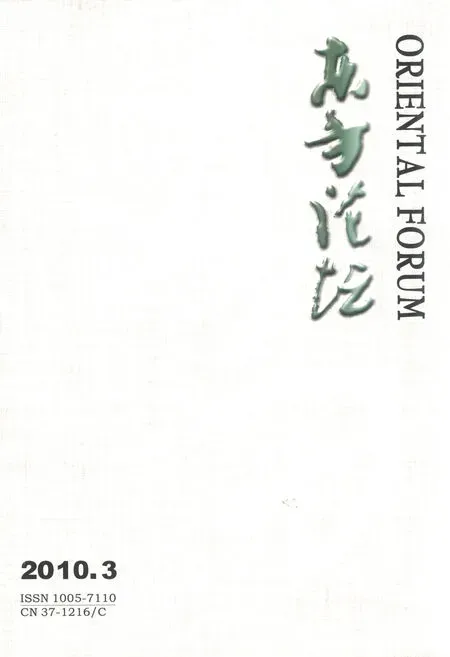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单 纯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70)
论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单 纯
(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70)
宗教与哲学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两种普遍表现形式。宗教的本质在于表达人类对于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其方式多见于情感性的执著;哲学的本质在于表达人类对于世界的本原、思维的性质以及生活价值的探索,其方式多见于理性的反思。宗教信仰与哲学反思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导致它们精神生活的客体表现出真实和虚幻的特征,但是它们在追求人生意义的答案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方法论上也相互影响。从中西方宗教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来看,哲学的思辨理性在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促使宗教传统中人格神的意义向非人格神的人文主义观念转化,为世界多元性文明形态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奠定了客观的思想基础。
终极关怀;反思;天人合一;人文价值
一、宗教与哲学之异同
宗教通常被理解为“人与神的联结”,神后来被解释为“人格神”、“非人格神的灵性存在”或“终极实在”,而“联结”历史上曾被解释为“信仰”,现在也可以理解为“体验”,甚至一定程度上的“理性论证”,如神正论者所做的那样。但是在现代神学的层面,为适应各种经验科学和理性思维所取得的最新成就,传统宗教中的核心概念“神”不再被信仰成为“绝对外在的超越性”(或“绝对他在性”:the absolute otherness),①如几个基本的“omni-”,这是来自拉丁文的一个前缀,意为“完全”,所表达的上帝特性有:omnipresence:无所不在;omniscience:无所不知;omnipotence: 无所不能;omnibenevolence:无所不善;后来有哲学家说上帝的这些“无限性质”都是缘于人的情感方面的“无限感知力”omnipercipience (罗德里克•费斯)。而是人主体性情感的最高表达,即蒂利希所定义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的表述”(the expression of the ultimate concern)。所谓“无限性”或“终极性”都是人类思维所赋予其对象的一种极限性的“形容特性”(attributes),反映了人类思维的理性逻辑和情感色彩。因此,在对于宗教的核心概念,无论从思维或情感的表述方面看,都与哲学的思维方法论和目的论相关联。这就涉及到了哲学的问题。哲学在西方语境里是被当作“宇宙论或世界观”、“知识论或方法论”及“目的论或人生观”这“三论”的综合,中国人也喜欢将此“三论”概括为“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学问”,因为将“世界观”与“人生观”表达成一种关联性的“学问”,知识论自然也就包含在里面了。当然,用中国文化的传统术语讲“哲学”就是“寻根问底”和“安身立命”的合一。由于西方哲学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知识论转向”(epistemological turn),哲学自然又被极为概括地总结为“对一切存在的反思”,这自然就包括对宗教的反思。这又从哲学方面涉及到了宗教的问题。因此,无论是讨论宗教或哲学,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宗教与哲学的关系问题。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讲:一是总括地讲它们之间的异同;一是具体地讲它们在各种文化传统中的具体演变情况。
先讲宗教与哲学之异。这种相异的一个最基本方面是其信仰或思考的对象的性质:宗教信仰的对象其性质多有信仰者所想象的成分或特质,甚至多半是幻象或扭曲的想象所致,其中满足了信仰者的主体情感需要,如“义神”或“爱神”所具有的各种超越物理性质的“神迹”和表达伦理信息的“牺牲精神”。宗教所反映的世界基本上是经验世界,只不过其在描述经验世界时加进了许多缺乏或扭曲经验世界真实性的成份,这即是宗教现象中常见到的“颠倒了的世界观”或“幻象的反映”,即将经验世界中的存在者幻想化或神圣化后再用以解释经验世界。这个反映的对象正与科学所反映的对象相等,但科学是真实地反映或实证经验世界中的存在物,所以,宗教与科学在这方面的冲突要大于宗教与哲学之间的冲突。而哲学所反映的世界或其思维的客体是一种逻辑上的宇宙观,即经验世界加可能性世界,是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至大无外”的存在者,是一种建构在思辨理性之上的逻辑本体,西哲亚里士多德名之以“反思的思想”,中国哲人则名之以“道”。作为一种思辨客体,与宗教的信仰客体一样,它同样也不同于“科学”的对象—作为实验对象的存在者。“为道日损”和“为学日益”是中国人对哲学与科学之间在对象方面所做的区别,同样也是哲学与宗教在对象上的区别。由于哲学的对象是逻辑的观念,而不是经验的事实,所以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冲突远不像宗教与科学那样明显,甚至也可以说根本没有冲突。中国儒家的经典《中庸》里有句话很好地解释了哲学与科学并行不悖的观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里的“大”是作为哲学对象的逻辑宇宙,即“要多大有多大”,“万物”是科学的对象,“道”是哲学的对象,其不同的表现形式是“小德川流”和“大德敦化”,“德”是通假字“得”,表达“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所谓“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管子•心术上》)因此在“道”的统领下,表现在万物中的“德”和“大德”之“道”就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相比之下,在西哲柏拉图的思想里,宇宙万物的存在被分成“理世界”(world of ideas)和“经验世界”(world of facts)两个不同的部分,前者完美,后者拙劣,同样亚里士多德也将科学与哲学分成“形而下学”(physics)和“形而上学”(metaphysics)之间的关系,它们也有逻辑上的前后、高低之分。之后西方基督教的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就延续了希腊哲人的这种二分理论,形象讲就是“灵肉二分”,把“神灵”凌驾于“肉身”之上,自然也就把宗教凌驾于科学和哲学之上了。但实际上,哲学的宇宙观是一种超验的抽象概念,它并不直接否定宗教或科学的实在概念的价值,而是从一个永恒的方向引导和激发宗教观念的演变和科学思想的创新。中国传统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应该说很早就避免了类似的冲突或悖论,使中国思想史上没有出现激烈的宗教神学与科学或哲学之间的尖锐对立和冲突。这是宗教与哲学是否能够区别自己不同对象的一个重要方面。哲学这种与宗教和科学对象上的相异性可以在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中找到许多有趣的例证。当然,对于西方宗教核心的上帝概念的解释——如“造物主”(creator)和“立法者”(law-giver),我们在西方思想发展的历史中也可以发现其所受到的哲学的逻辑观念的影响,如从“物理性质的牺牲”演变为“精神性质的祈祷”,从“先知的启示”变成“因信称义”,从“原罪的洗礼”变为“基督式的自我救赎”等等。
宗教与哲学另外一个相异性表现在其不同的方法论上。我们通常说“宗教在于信,哲学在于思”就是针对二者知识论或方法论的特性和意义方面说的。哲学注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思辨;而宗教强调建立在体验或幻想上的信仰,即哲学重“思辨”,宗教重“信仰”。这种方法论的差异也见于神学家们对宗教的独特认识:即以信仰为主,以思辨为辅,其“‘以信仰为理解的基础’(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的精神,从亚力山大的克来蒙(Clement of Alexandria)提出,经过奥古斯丁(Augustine)阐释而延续下来成为基督教知识分子的一种主要传统,其意为:基督教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往往是他们所信仰的东西,其特点是将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引入基督教的信仰传统。到19世纪新加尔文运动兴起之后,其基本精神已定型:即基督教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以信仰主义的立场来探究知识问题,而不是离开信仰主义的神学传统,即神性的简单性原则或信仰主义的原则来思考一切学术、政治和社会问题。”[1](P122-123)但是,即便有哲学的理性因素,就方法论的意义讲,以信仰为理解的基础,则理解只能限于已经被信仰的客体,那当然就是加深对上帝的理解,其结果可能沦入“迷信”,即“信仰太甚必然窒息理解的主体性”。这是宗教信徒的精神生活中常见的危险。与之相比,哲学则是以“理解为本,以信仰为末”,是先理解了再信仰,其本质是强调人的理性主体意义,其结果可能完全排斥宗教式的信仰,即“理解太甚必然排斥信仰”。因此,从方法论讲,哲学与宗教正好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相异性,甚至是排斥性。这是西方文明中宗教与哲学关系所固有的特征,即权威教父哲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所谓的“雅典相异于耶路撒冷一如柏拉图的学院相异于保罗的教堂”。但是,在中华文明体系里,宗教与哲学在方法论上并不是特别地相异,“天人合一”能够将“寻根问底”与“安身立命”综合成一个相融的命题,这与西方宗教“神人相分”和哲学“理世界与物世界相分”的特点确实不同。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在他的思想里,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前提就是理性,是独立自主的思想,不过中国人认为理解源于“心”,所谓“心之官则思”,“心思”和“立命”即能将理解与信仰合成一个命题。西方人的哲学理性和宗教信仰在方法论上的区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完全可以是相容的命题,所以不少西方学者以及追随他们的某些中国学者也都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儒释道三家既可以视为宗教亦可以视为哲学,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它们既非宗教亦非哲学。前者是看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后者只看它们的相异之处。
二、“2H”与“天人合一”
如果说整个西方文明的传统是一个“2H”统一的传统,即“Hebrew religion”(希伯来人的宗教)和“Hellenistic philosophy”(希腊化时期的哲学),那么,它们的宇宙论都被基督教综合成了一种设计论或机械论的宇宙观。《圣经》开篇就讲上帝“无中生有”地制造宇宙万物,一如柏拉图哲学将宇宙万物解释成绝对理念的“拙劣仿制品”(poor copies)和普罗提洛新柏拉图主义中的“多”对于“一”的绝对依赖性,这样,以上帝或者逻各斯所代表的“宇宙单元”或如莱布尼兹的“前定和谐”,就成了宇宙观的核心和人生观的价值追求,表达了哲学家所理解的生命的全部含义。照罗素的说法,“中世纪神学原是希腊才智的衍生物。《旧约》中的神是一位权能神,《新约》里的神也是个慈悲神;但是自亚里士多德,下至加尔文,神学家的神却是有理智力量的神。”[2](P111-112)即偏于政治的“义神”、偏于伦理的“爱神”和偏于哲学的“理神”。可见,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对于“神”的理解表达的正是“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统一”,自然也表达出“2H”的统一。依我看来,从统一的立场讲,犹太教时期的神可以称为“义神”(以“上帝的选民”和“应许之地”所表达的哥们义气的那种神,不够真正宗教求善的涵义,所以斯宾诺莎称其为“神学政治论”—这个新的哲学解释给他自己惹来了杀生之祸),柏拉图思想中的神就是“理念神”(the holy idea reflected universally in all poor copies,宇宙万物皆神圣理念之拙劣衍生品),基督教的神是“爱神”(universal love:博爱成为三种民众的必然选择和精神追求:那些不为罗马市民法—基督教形成之后才产生了万民法—保护的千百倍于罗马市民的帝国臣民,那些成千上万的处于犹太教之外的“非上帝的选民”,那些属于“一多关系”中的绝大多数在柏拉图的宇宙论中以铜和铁做成的农民和艺人),经院哲学的“理性论证之神”,斯宾诺莎的“宇宙万物自然之神”,康德的“道德自由之神”以及佛洛伊德的“人类心理之神”,这些多元性质的“神”代表了多元和历史发展的宇宙观,同时也反映出相应的人生观,即生命哲学。如果这个观察可以成立,则我们可以概括出神的三个基本特点就足以将“宇宙观与人生观统一”的哲学的奥义揭示出来。这三个特点分别是“造物的上帝”(creator)、“制定规律的上帝”(law-giver)和“救赎人类命运的上帝”(savior)。这三个特点在“二希”传统中可以解释哲学与宗教在思想上的相互补充关系,同时也很可以与中国哲学的特点相互借鉴和发明。中国学者传统上都喜欢以司马迁的人生哲学为自己学术使命的参照系,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报任安书》)如果按照范文澜先生的说法,中国文化的传统是一种“史官文化”,即“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则其哲学即为“春秋大义”,这是中国人生理想成为“义人”的标准,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上》)作为中国“义人”或人生哲学典范的“圣人”的标准和前提都是宇宙论的—天,但它却是与人生哲学和谐交融的,所以用不着特别地标志其为“绝对他在”或“超越性的理念”,中国人的宇宙论化生出万物完全是出于善意和生命情感,不是靠神迹和客观规律。所以它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统一就被顺理成章地解释成为“天人合一”,人的生命的终极意义就自然地包含在宇宙论里,是“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周敦颐《通书•志学》)。
但是,我们从柏拉图的“理世界”或基督教的“creator”、“law-giver”和“savior”里面很难找到类似中国天人和谐那种类型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统一性。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代表人的主体性的生命哲学往往要经过革命性的反叛才能被揭示出来,如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和克尔恺郭尔的“存在主义”,它们必须要将传统世界观中“绝对他在性”的神圣权威解构之后,才能确立人的主体性生命意义。由于西方传统的宇宙论的超越性、客体性和绝对他在性,生命的主体性意义总是被抑制或蔑视的,这就使得强调主体性的思想特别受到推崇,如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康德的“自由意志”以及克尔恺郭尔的“真理就是人的主体性”(truth is subjectivity),不过,可悲的是,像克氏这样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存在主义大师仍然不敢说这是自己的独立见解,而是将它追溯到拿生命去唤醒人们主体自觉的苏格拉底:“对于克尔凯郭尔而言,‘外在地在那儿’的只是‘一个客观的不确定性。’无论他对柏拉图的批评是什么,他的确从苏格拉底对无知的断言中找到了这种真理概念的一个好例子。因此,他说:‘因而苏格拉底的无知正是这一原则的表达,即永恒真理是与存在着的个体相关的,而苏格拉底始终以他个人经验的全部热情持有这一信念。’”①Socrates to Sartre:A History of Philosophy, Samuel Enoch Stumpf, printed by McGraw-Hill, Inc.1993, P.486.在西方这种机械论和设计论的宇宙观下面,宗教徒的生命意义是信仰上帝,爱上帝,最终等待上帝的救赎,而哲学家的意义则是认识上帝所制定的规律,按照认识到的客观规律而理性与自由的生活。这两者形式上确实有些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都在“神人对立”或“客主对立”关系中来确立主体的人的有限意义。这一特点,即便我们拿“近代哲学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philosophy)笛卡尔的箴言“我思,故我在”来分析也是这样。从表面上看,“我思”是在确立主体的人的独立思想地位,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在拿“思考客观真理”与“感官经验的客观真理”作比较,以见理性的思想比感性的直觉更容易获得客观真理,而我的思想的对象本身仍然是一个以外在的上帝为代表的绝对客观真理:“我们理解为至上完满的、我们不能领会其中有任何包含着什么缺点或对完满性有限制的东西的那种实体就叫做上帝(Dieu)”,[3](P162)因此“在上帝的观念里,不仅包含着可能的存在性,而且还包含着绝对必然的存在性。因为,仅仅从这一点,他们绝对用不着推理就可以认识到上帝存在。”[3](P164)既然上帝已经作为一个无限完满的客观真理而存在,“我思”的结果无论如何是不能超越它的,充其量只能无限地接近它,因为它是“我思”的最高标准和思考者的最终人生目标。正因为如此,西方人所能给予笛卡尔的最高赞誉也只是说他是一个“二元论”者,上帝的那一元是绝对不能动摇的,而笛卡尔这一元只是史无前例地肯定了“我思”的主体性地位,但其存在仍然以不削弱上帝作为绝对真理和思考的终极的标准那一元为前提。
三、宗教与哲学的人文价值
无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如何相异,宗教与哲学都有人生论的共同议题。大体上说,宗教方面所体现的人生论的议题是“天国”的外在救赎,即上帝的末日审判;而哲学的人生论的议题则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充分实现,即人的全面自由。这类议题正好反映出了宗教与哲学各具特色的人文价值。
大体上讲,哲学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一切存在物的发展、演变,这是由它的“反思的思想”所具有的无限灵活性所决定的;而宗教也似乎是从一个“永恒”的角度看待“一切存在物”的演变,但它所谓的“永恒”和“一切存在物”都是在对经验世界中的存在物作幻想的类比而形成的,如以“天国”折射“人世”,以“永生”折射“长寿”,以“地狱”折射“苦难”等。而在哲学的最高概念中只有超验的“理念”、“物自体”或“绝对精神”等。但是,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领域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宗教与哲学相同的一面,即两者都十分关注诸如生与死的意义、善与恶、美与丑、秩序与自由等。对于这些共同的方面,尽管哲学对它们的解释有思与信的差别,但它们对人类所提供的“安身立命”的功用却是相同的。
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大学讲《中国哲学简史》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哲学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历来可以与宗教在其他文化中的地位相比。”[4](P1)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他又给哲学下定义说:“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4](P4)“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现在引用它,只是要标明,中国哲学传统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4](P8)他在这里是参照西方思想所做的解释,西方的宗教本来的功能是“为道”的,即所谓“哲学(科学)求真,宗教求善,艺术求美”中给宗教所确定的功能,现代美元上的标记“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就是将宗教信仰视为其社会生活的价值基础:“关于美国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美国人自己的概念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他们和许多非基督徒都认为,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犹太-基督教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①《交流》,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编译2000年第1期第29页。仅从宗教的伦理功能来看,它应该与日益的、积极知识的科学传统不相干,而是与日损的、提高精神境界的哲学相互关联。可是,在西方的中世纪,宗教则没有恪守好自己的职责,经常犯规,侵袭哲学和科学的领地,甚至凌驾于它们之上,将科学和哲学视为自己的“婢女”和“仆人”。启蒙运动之后,这种“思想犯规”的情况已经得到很大纠正,当时激发西方人纠正宗教思想“犯规”的重要启示就是来自于中国的思想传统,即天和人不是主人和奴仆,绝对他在和受造存在,神圣客体与世俗主体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是合一的相容关系。这一点给了西方的启蒙运动新的“人本主义”启发:中国人的心可以是知识的本体,也可以是信仰的本体,理性与情感,理解与信仰可以由人的心得到统一;中国儒家所提倡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和“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思想给了西方近代哲人深刻的启示,使他们从“道成肉身”和“因信称义”的宗教观念中转化出新的人文信息,这些信息很多都被运于解释主体性的自我救赎和世俗性的天赋人权。
因此,根据中西思想的同异比较,我们大体上还是可以说:宗教与哲学的异同关系可以总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它们涉及的领域有“大小”之别;一是它们进入自己领域的思想方法有“思”与“信”之异。宗教的领域一般不超出人类的经验世界,而哲学的领域往往在经验世界之外还有可能性世界,在经验世界之内,古今中外一切的宗教现象也是哲学思考的领域之一部分,而哲学的可能性世界则不在宗教建立信仰的领域里。在思想方法上,宗教要求其信徒对最高的神圣存在者,无论是人格性的上帝还是绝对灵性存在,都呈献不假思索的虔诚。而哲学对宗教所谓最高存在者一定要诉诸理性之思考:最高存在的证据何在?如何证明此证据的可信性?最高存在的本质定义与经验事实有无逻辑矛盾,如神之全善与人世之恶当作何解释?这些出自思想的问题都是哲学反思的对象,哲学家们视其为生活的乐趣。这是它们从宇宙观与知识论的关联中所转化出来的人生价值观或人文价值取向。
在东方的文化传统中,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其特点是两者之间的若即若离,界限模糊。
我们知道,作为印度婆罗门教最早的经典之一的《奥义书》(Upanishads)既可以看成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教义基础也可以看成是它们在哲学方面的基础。它是印度最古老的《吠陀》(Veda,形成于公元前2000-1000年之间)经典的最后一部分,其中所宣传的“梵我同一”和“轮回解脱”等概念是具有宗教意味的,而其对于物质存在的原素论的解释和对社会伦理的乐生论的解释,又是具有哲学方面的人文主义意蕴的。因此,《奥义书》既是古印度的宗教经典又是其哲学经典。特别是在公元前后,在《奥义书》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印度教正统的哲学流派“吠檀多派”(Vedanta)。
佛教的传统也可以分成哲学和宗教两个相互交融的层面:作为宗教的佛教和作为哲学的佛学。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乔答摩(Siddhartha Gautama)或称释迦牟尼(Sakyamuni)本人展现出来的乃是其哲学思想,倒是后人把他的思想和探索人生意义的行为改造成了宗教中的教义和奇迹故事。此后,作为宗教传统的佛教在南亚、东南亚、中国西藏、中国内陆、朝鲜、日本等地得到传播,其特点是强调修炼、戒律、出家及庙堂等形式,也是其宗教传统中人文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作为哲学传统的佛学也在印度、中国、日本等地得到传播并在历史上形成了大乘佛学(Mahayana),龙树(Nagarjuna)创立的中观派(Madhyamika),在中国、日本和美国西海岸的禅宗等,这些新宗派在创新方法论的同时也揭示出了独特的人生论的意义。
中国儒家的传统也是这样。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本来也是继承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其中包括宗教中的神话传说、巫术思想等而形成的。在孔子的思想里,既有属于他自己创新的、具有哲学意味的仁义道德思想,也有古老的文化传统中沿袭下来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天命鬼神思想。在这个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体系里,《中庸》中的天赋人性论、孟子的“养气”、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宋明理学家致良知的修养功夫②研究中国宗教思想的学者认为,宋明儒家在修炼方式上具有浓烈的宗教色彩。所谓“理学家的修养工夫,无论主诚主敬主静主寡欲主返观内心主致良知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等等,莫不含有宗教上祈祷面目。因此,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宗教思想的表现。”见王治心:《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康有为的“孔教”运动、钱穆用火珠林法卜“国运”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敬天祭祖”的传统,都是在表达儒家思想在宗教层面的人文含义了,所谓“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当然,儒家传统也有明显的哲学层面的意蕴,如孔子强调人世伦理的“仁”、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朱熹以“理气”关系解释事物的存在、冯友兰以“理、气、大全、道体”建构“新理学”的思想等。这些都与西方传统的哲学具有相同的理性思辨旨趣。不同的是,儒家的传统强调“天人合一”,总是将这个传统的宗教性和哲学性意蕴融合在一起,没有造成明显的互相冲突和紧张关系,而是在哲学的思辨理性中贯彻了人生论的意义。我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中国哲学具有西方宗教所强调的“终极关怀”或中国语境下的“安身立命”的功能。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以“人生境界论”为其主要特征,就是中国哲学传统在当代转化的一个显例。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更强调宗教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与冲突;宗教的启示性不断受到哲学的思辨性挑战,在思想方法上来自希腊哲学的思辨特征主导着整个宗教神学思想的发展方向。其结果是导致宗教的“外在启示性”向“内在体验性”转化,这种转化不仅表现为宗教自身的演变,也反映出了其中不断被强化的人文价值取向,所谓“道德宗教”,“人道宗教”,“解放神学”和“上帝之死派”等等,都可以视为人文价值观对传统宗教救赎论的深刻影响力。
我们知道,西方宗教传统从其源头开始,就突出信仰的启示特色,以与哲学从其源头开始的思辨特色相区别。在形成于公元前7-6世纪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圣书《阿维斯塔》(Avesta)、犹太教(Judaism)的律法书《托拉》(Torah)、基督教(Christianity)的“上帝之道”(Word of God)以及伊斯兰教(Islam)的《古兰经》(Qur’an)中,充满大量神的启示的信息。可以说,在西方宗教的古典时期,其主要思想特色是启示性的。但到了中世纪以后,希腊哲学的思辨性特色开始影响这一宗教传统,基督教神学的思想中心转向了思辨方面,其人文主义特色在希腊哲学的刺激之下逐渐显露出来,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形成高潮。
虽然基督教在最初的时期仍带有希伯来(the Hebrew)人的宗教在启示方面留给它的影响,但很快就转向了希腊哲学的理性思辨传统。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在奥古斯丁时代形成一个高潮,而其特点是柏拉图式的思辨性。到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全盛时期,基督教神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则转向亚里士多德并以其思辨方法建构自己的神学体系。自近代以降,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D.E. Schleiermacher)和基督教加尔文派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又明显表现出康德(Immanuel Kant)哲学思想对他们的影响。接下来却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神学家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过程哲学对过程神学运动的影响。从基督教的发展方向看,哲学的思辨性在对宗教信仰的“理解”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结果是培育出了宗教自身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蒂利希才可能在当代的思想环境下给宗教下一个具有人文主义价值取向的宗教定义—“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的表述”。
在伊斯兰教的发展方面,自穆罕默德之后有两个趋向:一是受柏拉图影响的苏非派(Sufis);一是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伊本•路西德派(ibn Rushd)。然而,这两派都是深受古典希腊哲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其中的人文价值取向经过拜占庭帝国崩溃后传播到西欧社会,对那里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西方的宗教特别是其神学思想传统一直在接受哲学方面的思辨性影响,但其哲学传统却很少受到宗教启示性特征的影响。中世纪神学在哲学思辨性传统的影响下居于西方思想传统的主流地位,以致于哲学本身淡出思想领域,成了神学的婢女。可是,自从笛卡尔(RenéDescartes)建立近代哲学以来,哲学则完全又恢复了古希腊哲学的思想活力并脱离了宗教神学的束缚,更加迅猛地发展出枝繁叶茂的诸多新流派。特别是经过康德和黑格尔(G.W.F. Hegel)的洗礼,20世纪的哲学开始全面清算宗教神学在西方传统中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形成于对希腊哲学传统的曲解和篡改。在这期间,诞生了排斥宗教传统的、无神论的逻辑实证主义和否定上帝绝对存在的以人为核心的存在主义,最精彩的是萨特(Jean-Paul Sartre)对上帝的宣判:“我给大家讲一个天大的笑话:上帝根本不存在!”[5](P141)存在主义发展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哲学对神学的否定传统,萨特则在承认人的存在高于一切、提倡人的独立意识和与生俱来的绝对自由的前提下,把宗教传统中那个外在而超越的上帝完全否定了。自那以后,在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中,根本的问题不是哲学在面临新问题时回到宗教思想中去寻求答案,而是宗教若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系其信众对神或终极实在的信仰,不得不借鉴哲学的方法并协调自己与哲学在发展方向上的关系。也就是说,西方文化传统在启蒙运动之后所呈现的宗教发展趋势是哲学化的、人道化的。总体上讲,人文主义最终形成了近代西方宗教和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主流性议题。
[1] 单纯.当代西方宗教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M].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 (法)笛长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5] 萨特.魔鬼与慈善的上帝(英文版)[M].纽约:兰登出版公司,1960.
责任编辑:郭泮溪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SHAN Chun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70, China)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are two universal expressions of human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progress. Religion in its essence is to express the pursuit of the ultimate meaning of human life while philosophy in its essence i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s origin, the nature of thinking and the value of life. The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in seeking answers to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so they influence each other in terms of methodologies. As far as the ess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religions are concerned, the speculative reason of philosophy holds a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ultimate care; reflection;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humanistic value
B91
A
1005-7110(2010)03-0001-06
2010-05-10
单纯(1956-),男,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