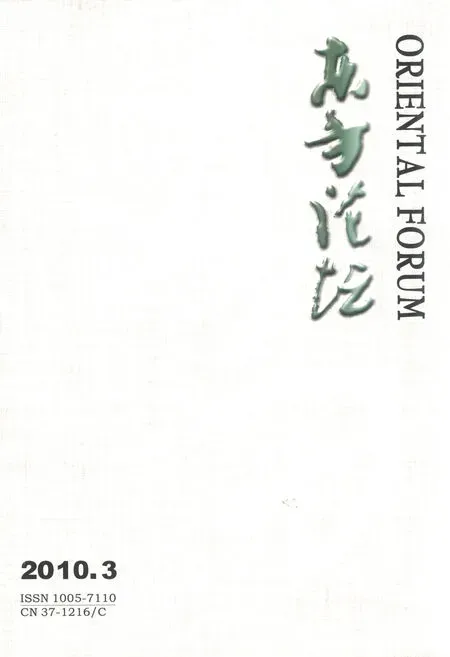新生代作家的影视生存与文化立场
周根红
(南京体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
新生代作家的影视生存与文化立场
周根红
(南京体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4)
1990年代以来与市场化浪潮同步成长的新生代作家表现出对城市生活想象性的写实,使得他们的写作与影视有了某种一致性,进而成为影视改编的一种基础性资源。与此同时,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影视浪潮之中,参与影视编剧,使他们的作家身份带有明显的影视特征。在这种强烈的影视文化和商业意志的渗透下,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出现想象贫乏的状态,自我重复现象比较严重,作品的原创性逐渐减弱。
新生代作家;影视文化;商业渗透
1990年代,文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一批具有实力和锋芒的青年作家日益活跃,最后成为一种具有代际色彩的作家群体,批评家将他们称之为“新生代作家”。新生代作家登场的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变革和大众传媒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推动力,商业话语成为影响1990年代各种文学艺术形态的主导性力量,它逐渐颠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因此,1990年代成为一个中心价值观和主流文化趋于消解式微的时代。与之前的先锋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几乎与市场化浪潮同步成长,他们已经充分地适应甚至主动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发展洪流,商业化写作成为新生代作家最为重要的创作特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总体上指向了物欲和性,“表现现实时采取便捷、近距离的审美视角,在贴近生活的体验中,消解生活和艺术本身的双重诗性特征,实现对生活欲望化、平面化、世俗化的存在性表达。并且,他们在写作中竭力张扬自身对世界本能的、质感的生命冲动,外化为纯粹的现实世界图景,从而形成其小说文本的自足性个人性话语,以致构成对权利性主流话语的一种强力冲击。”[1](P91)为寻求自身写作的合法性,新生代作家甚至以“断裂”的姿态告别传统,然而,在商业的包围和影视等大众传媒的聚拢下转而形成了更为强烈的商业意志。新生代作家以一种彻底和决绝的姿态进入影视制作环节,成为影视的二传手,逐渐被影视的商业化潮流所瓦解,模糊了文学的精英与通俗的边界,日益染上了文化工业的品性,他们自身也完成了一个作家向影视人的转型,进而远离了文学创作的初衷。虽然新生代作家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他们在创作风格和题材上都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90年代文化和其他文化(包括80年代文化)的杂糅,显示了文化间对文学这一大众媒介的争夺。”[2](P247)
城市化想象
1990年代是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一个以商业化和大众传媒为主导的多元话语模式开始形成,大众文化以一种突飞猛涨的姿态进入我们的消费空间。“一方面执政集团通过机制修复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强化,加固了政治的一体化体系;另一方面已经形成惯性运作的经济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又使得市场经济逻辑渗透和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层面。”[3]因此,在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社会日益现代化甚至出现所谓的“后现代化”的生活场景,“进城”与城市化等成为1990年代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现象。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市民阶层甚至乡野村民,城市∕城市生活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文化资源和特有的文化张力,影响着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文化艺术形态,文学和影视艺术也在这一时期将目标转向了城市生活。
1990年代,以张艺谋和陈凯歌为代表的一批导演,先后执导了《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黄土地》、《边走边唱》、《五魁》(黄建新导演)、《二嫫》(周晓文导演)等电影,展现了中国乡村的生活和民俗,形成了1990年代新民俗电影的浪潮。这些新民俗电影的出现,“为中国的影视导演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有效手段。”[4](P22)这一类乡土化电影的出现,可以说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城市与乡村所形成的空隙所造成的,他们试图缝合城市和乡村、本土与国际等关系的裂缝,于是在这两者之间徘徊,而又无法彻底指向某一方。然而,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城市化的发展,我国影视的创作方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都市现代化为背景的生活表现日益增大比重。“由于现代生活方式迅速成为我们时代的生活主体,人们被现代思潮所感染,瞬息万变的信息、蜂拥而至的各种物质诱惑、纷繁复杂的思想情感和快捷多变的节奏,使现代人处于张望、惶恐、焦虑不安的心态中,老迈缓慢的传统生活情趣、与世无争的闭锁田园乡村生活所带来的情感需求被甩到时潮之后,都市影片应运而生。”[5](P298-299)风行一时的由王朔小说改编的《轮回》、《顽主》为先导,其后的《站直啰,别趴下》、《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没事偷着乐》等电影,以及生活情节片《渴望》、农村少女闯都市的《姊妹行》、中国人在外国的《北京人在纽约》、反映社会改革生活的《编辑部的故事》、反映都市男女情感的《过把瘾》等都市生活题材成为1990年代影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的叙事资源,这些影视表现了现代人在身处嘈杂而混乱的现代生活漩涡中的种种情感困惑、心灵挣扎,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影视对日常生活的消费和对城市资源的借用。
当现代城市生活成为影视对当代人精神内核进行深刻挖掘的重要“场域”时,新生代作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入城市生活的书写、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叙事,表现出漂浮的成长经历。面对日益城市化的进程所表现出的迷茫和慌乱时,“新生代作家以动荡不居的城市生活作为主题,以第一人称的独白口吻表现主人公的‘漂泊’状态。”[6](P202)毕飞宇的创作转向就较好地说明了这一时期新生代作家的主题书写策略。“(1994年之前,笔者注)我是一个比较看重历史语义、过于着重小说修辞学的这样一个作家。……(1994年之后,笔者注)我把触角伸向了当代生活。”[7](P121)这之后,毕飞宇转向了城市写作,如《飞翔像自由落体》、《家里乱了》等,展示着城市的一种宁静、凄凉、感伤的和绝望的情绪。张旻的《伤感而又狂欢的日子》、《远方的客人》、《两个汽枪手》则与以往的《情幻》、《审查》的不确定性有了很大的变化,小说的现实感进一步增强了,但也缺乏了深度而过于平面化。邱华栋的《城市战车》、《哭泣游戏》、《都市新人类》等,以繁密的都市景观和应接不暇的信息书写了城市的诱惑。此外,丁天的《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何顿的《我们像葵花》等也专注于城市成长小说的写作。新生代作家对城市生活和社会底层的琐屑叙事,无一不表现出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特征。
当“城市生活”成为1990年代以来影视和文学共同的主题时,影视和文学便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新生代作家的一些小说陆续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对城市生活想象性的写实,使得他们的写作与影视有了某种一致性,即影视所需要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城市空间的想象和新型文化的体认,新生代“写本能、写欲望、写生存的浅层次状态”的写作正好顺应了这一文化潮流。新生代作家中接触影视较早的应该是毕飞宇和述平。1995年,毕飞宇的长篇小说《上海往事》就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1997年,述平的《晚报新闻》被张艺谋改编为电影《有话好好说》,这是张艺谋第一次真正涉足城市题材电影。《上海往事》、《晚报新闻》让一些导演和作家逐渐认识到新生代作家的影视潜能,可以说,1990年代成为新生代作家和导演相互磨合和认识的时期。正是在这种影视和文学的文化合流背景下,张旻甚至还主动写了电影剧本《向红》,“《向红》一开始是为电影写的故事,后来没有搞成电影,就当小说发表了。”[7](P165)新世纪以后,一批新生代作家的小说被大量地改编成影视作品。2000年,根据毕飞宇的小说《青衣》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长期“霸占”荧屏,许多人认识毕飞宇就是从这部电视剧开始的。随后,著名导演杨亚洲和演员宋佳相中了毕飞宇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2004年,著名导演叶大鹰则拍摄了根据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改编的同名电影,但是后来没有发行。在文坛引起很大轰动的中篇小说《玉米》同时受到数位影视界重量级人士的青睐,说毕飞宇与影视特别有缘似乎并不过分。目前东西的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应该算是最多的。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在获得鲁迅文学奖后,被改编为《天上的恋人》,由著名演员刘烨、董洁、陶虹主演,该片在2003年第十五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作为唯一一般入围的华语影片,被定位电影节的首映片。而真正使东西在影视圈站稳脚跟扬名的,大约要算长篇小说《耳光响亮》改编为二十集电视剧《响亮》和电影《姐姐词典》。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的是根据东西短篇小说《我们的父亲》改编的二十集同名电视剧。除此之外,东西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还有:中篇小说《美丽金边的衣裳》改编的电视剧《放爱一条生路》、《没有语言的生活》改编的二十集同名电视剧以及《猜到尽头》改编的电影《猜猜猜》。一时间,东西的小说成为影视改编的富矿。邱华栋更是以一个城市文学家的姿态书写着城市的奢华和悲凉。2000年邱华栋的长篇小说《正午的供词》被广东巨星公司老板邓建国买下其电影拍摄权后,由于作品将导演和演员的都市艳事作为主要内容,被认为影射张艺谋和巩俐而一推再推。2001年再次被北京金英马公司买下其电视剧改编权,邱华栋亲自担任26集同名电视剧的编剧。触电较晚的何顿也在作品中展现出城市生活的想象甚至是浪漫,改编自同名小说的《我们像葵花》中一群文革中成长起来的文化人、小商人以及个体经济阶层,他们自以为“我们像葵花”,怀抱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浪漫与梦幻,但在汹涌而来的商品大潮冲击之下,他们的人格和命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为了生存,为了发财,为了女人,他们不惜铤而走险,坑蒙拐骗,走私贩假,背信弃义,打架杀人……此外,由陈染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与往事干杯》(夏刚,1995年),1995年被选为国际妇女大会参展电影。2007年鬼子的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也进入了改编环节,这部小说不仅是鬼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从事创作以来惟一的一部写爱情的小说。[8]
“随着90年代初知识分子‘精英集团’的瓦解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曾经弥漫在80年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逐渐发生改变,围绕着共名而尖锐对立的两极意识形态也随之逐渐淡化;随着大众文化市场的形成,传统文学的审美趣味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群众性多层次的审美趣味分化了原先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各自所提倡的单一的艺术标准。”[9](P192)新生代作家的创作正是以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想象取代群体的意识形态和集体文化观念的狂热,进行着一种私语化、个人化的创作。他们在“个人化写作”的名义下,展示着城市生活、青春成长的经验和想象,这些无疑成为影视改编的一种基础性资源。新生代作家与1990年代中后期的影视一起形成了商业意识勃兴后的大众文化浪潮,进而颠覆和消解着文学经典和精英文化。
身份的重塑
新生代作家是在1990年代的市场化浪潮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与这之前的作家所不同的是,新生代作家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体制外生存和自由写作的意识,这种体制外的写作,一方面使得新生代作家急于逃离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转而面向社会生活∕城市生活的琐屑叙事;另一方面,他们又被迫或自觉地以一种自由职业∕商业意志的身份进行写作,他们的职业和文学创作没有太大的关联,他们不是专业作家,他们既选择了文学创作,但又时刻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意志的控制而使写作成为一种谋生的工具。毕竟,“90年代的作家不能自恃清高埋头写作,他必须时时抬起眼来,因为他们已被置身市场。市场经济铁面无情,它使一部分作家紧张也让一部分作家放松,或起始紧张继而放松,使读者快乐是适应市场的一条便捷通道。”[10](P11)因此,新生代作家比其他作家更懂得经济利益在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为了“适应市场的一条便捷通道”,在这种经济大潮中寻找自己的出路,新生代作家主动步入文学的商业化窠臼,与1990年代颇具影响的影视媒体一起,成为制造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
虽然1980年代崛起的大多数先锋作家面对影视并不拒绝,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仍然将影视和文学截然分开,仍然对文学充满眷恋和激情,即使那些与影视结缘较深的作家北村、潘军等人,仍然坚持文学的独特性。而大多数新生代作家则全身心投入到影视浪潮之中,参与影视编剧,并逐渐脱离了文学创作的本真道路,甚至许多新生代作家彻底放弃了写作,而成为一个职业的编剧,即便仍然坚持“编剧和创作两不误”的作家也大多只是面向影视的商业化写作,比较典型的是李冯、东西、鬼子、王彪、述平等,他们中的有些人在编剧这一行当中已经成为知名的成功人士。述平在继《晚报新闻》改编为《有话好好说》之后,参与了编剧《赵先生》(吕乐,1998年)、《鬼子来了》(姜文,1999年)、《太阳照常升起》(姜文,2007年)以及中国首部现实魔幻题材电影《走着瞧》(李大为,2008年);王彪参与了改编自军旅作家吴强的经典名著《红日》(苏舟,2008年)的编剧工作和2009年国庆献礼电视剧《东方红》(苏舟,2009年) ;丁天则编剧了《铁血青春》(刘江,2003年)和《陈赓大将》(叶大鹰,2006年);张旻曾参与编剧池莉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水与火的缠绵》(李自人,2006年);东西直接参与了自己小说的影视改编过程,在其中担任编剧,同时还参与了其他影视改编活动,如铁凝的《永远有多远》(陈伟明,2001年)。遗憾的是,他们在影视编剧过程中并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也没有借助影视成名。朱文更是走得比其他新生代作家更远,在编剧了影视作品《巫山云雨》、《回家过年》、《海南,海南》之后,直接当起了导演,执导了《海鲜》、《云的南方》等作品。但是,朱文至今仍与早期第六代导演一样,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体制外的生存,尚未完成自身的商业化、主流化转型,限制了其发展的生存空间。参与影视编剧最为成功的当属李冯、东西和鬼子,他们成为新生代作家群体中少数借助影视而声名俱隆的作家,也是少数实现了从作家向编剧的完美转型。李冯相继编剧了《英雄》、《十面埋伏》后,成为张艺谋的御用编剧,也成为当前影视领域的金牌编剧。随后他还编剧了《霍元甲》、《疯狂白领》等影视剧。2008年由深圳市凤凰星传媒有限公司、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山东广电总台联合打造的106集动画片《孔子》的编剧就有李冯和叶兆言、张炜等,计划于2009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60周年时在央视首映。鬼子曾经为张艺谋担任电影《幸福时光》的编剧,2001年,陈凯歌想改编鬼子作品《上午打瞌睡的小女孩》时,鬼子亲自参与到编剧中去,为陈凯歌写出了剧本初稿,但因为题材较为敏感而被搁置。据说这个剧本之所以被陈凯歌搁置,“一是因为题材敏感,二是因为他在处理故事和人物上还没有找到一个满意的表现方式。”[11]2006年鬼子再次触电,为成龙的《宝贝计划》编剧。东西则主动参与了每一部自己小说改编的影视。可以看出,在面对影视的冲击时,新生代作家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文化姿态,正如新生代作家东西对那些不愿触电、而把精力放在写小说的作家所说:“我觉得,我们的作家不要过分自恋,对影视剧也不要一棍子打死。你看很多欧洲电影,会认为电影比原著差?小说不一定比电影更高雅。让读书的人读书,让看电影的人去看电影吧。”[12]无论新生代作家介入影视后的生存空间如何变幻,新生代作家通过对影视的深度介入,很自然地就融入到影视大潮中,完成了从一个“作家”身份向一个“编剧”身份的转变。
新生代作家对影视的深度介入,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影视所带来的名利双收的巨大回报。正如毕飞宇在面对影视改编时所说的,“就我来讲因为影视剧使我的读者群扩大了,一些本来不看我作品的人看了影视剧后又回过头看我的作品,使我的作品扩大了影响。不能说光要求作家用自己的作品为其他艺术种类提供了帮助,而不允许作家占到一点便宜,我认为这就是作家占到的一点便宜而已。如果有人找到我想把我的作品改编成好的影视剧,又有公道的价钱和我喜欢的导演,我不会拒绝。”[13]其实,1990年代以来,大多数新生代作家的生活状态并不理想,甚至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丁天没有读完高中就退学了,然后在南京一所英语专科学校上学,上了一年就去华艺出版社工作了,1994年辞职。[14](P291)韩东靠《他们》中的一个朋友的帮助生活,写作的稿费很难生活,特别是出书较少,稿费低。此外,朱文也一样,最困难的是吴晨骏。[14](P49-50)虽然韩东提及他和朱文、吴晨骏的状态时说:“我们辞职,我们养活自己,然后我们拒绝写那种副刊文章,拒绝写畅销书,拒绝很多东西。”[14](P48)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宣言,实际上,韩东也曾在各种报刊如《新周刊》(广州,2001年)、《现代快报》(南京,2007年)等开设有一些七零八碎的随笔专栏,这些稿费成为他生活的主要来源。可以说,在与影视接触(小说被改编或参与编剧)之前,新生代作家的生活状态总体上来说并不理想,尤其是那些辞职后的新生代作家。另一方面,新生代作家基本上都生活在城市,他们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与现代物质文化和城市文化有着不解之缘,也使得他们成为现代城市的亲和者和批判者,他们也不能不对城市的物欲表现出影响,就像邱华栋所说:“我只管做好编剧,挣点‘小钱’买辆车开。电影电视请谁拍都行,拍得如何与我无关。”[15]由于1990年代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状态,各领风骚的1990年代,他们必须立足于1990年代的文化资本中表现出一种更加明确更加现实的写作路径。在这一现实路径的寻找过程中,新生代作家作为1990年代文化的直接参与者,在早期表现出一种“断裂”的姿态——与1980年代文化表示断裂,与1990年代文化一起作为自身发展的文化起点。“断裂”者们是“新生代”中的代表和极端,其实,整个“新生代”作家的心态与“断裂”者只是程度上的区分而无实质上的差别,他们在写作中普遍表现的迷茫和空洞,以及他们整体的言语大于行动的创作表现,都显示了他们反叛的表层化和形式化。他们的反叛姿态,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个姿态而已,没有取得真正的实质性成果,也难以形成对时代文化的真正反叛。[2](P25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当新生代作家急功近利地介入影视或进行商业化写作时,1998年新生代作家的“断裂”事件,不过是一场故作姿态的闹剧,最终他们还是回到了1990年代以来的商业文化逻辑,投身影视文化所构建起的话语系统,完成了商业社会的身份重塑。
匮乏的写作
1990年代以来,强烈的影视文化和商业意志的渗透,对作家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一种改写和潜在的影响。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出现想象贫乏的状态,自我重复现象比较严重,同一故事、细节、场景、元素和叙事方式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作品的原创性逐渐减弱。邱华栋的《把我捆住》、《偷口红的人》、《红木偶快餐店》和《蝇眼•遗忘者》对打胎细节的描写;《闯入者》和《夜晚的诺言》对摸得大奖的奇遇的玩味;《眼睛的盛宴》和《公关人》对假面舞会的渲染大同小异;《城市战车》中朱温和《蝇眼》中的袁劲松相同的性病方式。张旻在《枪》、《叛徒》、《永远的怀念》和《两个汽枪手》中对“枪”和“弹弓”的反复渲染;小说《回身遥望》不断引入散文《永远的女孩》的故事,可以说《永远的女孩》是小说《回身遥望》的故事生长点。何顿的作品在人物关系、故事情节、叙述语调和结构关系上都同出一源,《自我无我》中的李茁、《无所谓》中的李建国、《不谈艺术》中的肖正和《生活无罪》中的湘潭人都是怀才不遇的落魄者;《告别自己》中的雷铁、《喜马拉雅山》中的“我”、《生活无罪》中的“我”和一系列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辞去中学教职后转入商海的突围者,《我不想事》中的袖子、《弟弟你好》中的丹丹和《生活无罪》中的狗子在暴死前都散发出“神秘的臭味”。丁天的《流》以《饲养在城市的我们》中的一个人物刘军为主角,细节与情节的重复无可避免。①新生代作家小说中自我重复现象比较普遍,对此学者黄发有曾详细地做过论述,本部分论述也参考了其部分资料,在此不再赘言,详见黄发有:《媒体制造》,第280—28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林白的小说很多是将几个短篇组成中篇,几个中篇组成长篇,里面的细节和故事重复较多,如其自传体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和《瓶中之水》、《青苔或火车的叙事》、《守望空心的岁月》等小说里的不少细节都出现重复甚至雷同。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作家总体上过于关注身体欲望和金钱物欲,使得他们的叙事主题千篇一律,没有任何突破。刁斗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和《延续》、张旻的《情幻》、林白的《致命的飞翔》、海男的《我们的情人们》、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韩东的《障碍》、朱文的《我爱美元》、《五毛钱的旅程》等,大量对性细节、性体验的描写前后重复,话语模式和叙事方式大同小异。与此同时,新生代作家的叙事彻底投放在商业语境内,表现出强烈的实利主义原则。无论是何顿的《我们像葵花》、《生活无罪》,还是邱华栋的《城市战车》等,其叙事的中心无非都是“世界上钱字最大,钱可以买人格买自尊买卑贱买笑脸,还可以杀人。”(《生活无罪》,曲刚语)邱华栋本人也承认:“我本人也想拥有这些东西,当然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就不好说了。”[16](P44)朱文小说引发的“《我爱美元》事件”无疑是新生代作家与传统观念之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价值冲突。新生代作家这种迎合商业的写作姿态,对现实物欲的沉迷与认同,已经脱离了一个作家应该追求的审美理想,最终损害的必将是文学的原创风格和艺术品味。
另一方面,新生代作家的小说表现出强烈的影视痕迹。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就借用了一些影视剧的创作方法,比如观察和描写的视觉角度,场景的描写和人物的对话。与东西过去的小说相比,《后悔录》结构更为简洁紧凑,描写的角度和手法更丰富,人物的对话也更准确。小说的结构犹如一部影视剧的叙事方式,小说开始是一个男人的自述,叙述的对象是“你”,似乎是以读者为倾诉对象。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又察觉到他的倾诉对象是一个女性。但直到小说的结尾,读者才会发现:这原来是一个性无能的老处男面对一个色情服务的“小姐”的自述。《后悔录》通过这种叙事结构,一层层抽丝剥茧式的叙述逐渐揭开倾听者的面纱。这种独特的小说美学有似影视作品的表现手法:先将镜头近焦锁定讲述者,再随着讲述过程逐渐将镜头拉远,最后展现全部背景。东西自己也承认,“写了几年剧本,我再写长篇小说《后悔录》,有读者说这个小说比我过去的小说好读,这和我写剧本有关系。因为,我懂得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17]林白也是一个深受电影影响的作家,她曾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当文学编辑,可以说是一个与电影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她的小说《子弹穿过苹果》和《致命的飞翔》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受到电影影响的作品。《子弹穿过苹果》的构思与希区柯克的《蝴蝶梦》有着非常相似之处:绝对的主人公在小说和电影中都没有出现;小说中七叶和朱凉的关系与电影中女管家和女主人的那种主仆、情人、追随者的关系极其相似;小说的悬念氛围和电影的悬念氛围也颇为雷同。《蝴蝶梦》这部电影在林白的多部小说里提到,也是林白最为喜欢的黑白电影之一,因此,这部电影对林白小说的潜在影响自然不足为怪。而《致命的飞翔》这一意象则来源于希区柯克的电影《鸟》。同时,林白小说的结构也深受电影的影响。她的小说结构打破了小说的线性叙事,呈现出交叉、平行和并置的叙事结构,如《同心爱者不分手》中的月白色绸衣女人和男教师以及“我”和嘟噜这两条平行线索、《致命的飞翔》里的北诺和秃头男人以及李莴和登陆的平行结构。除此之外,林白的小说中还运用了大量特写、主观镜头等电影语言的表现方法。林白的一部虚构性自传也打上了电影的烙印,《玻璃虫:我的电影生涯——一部虚构的回忆》。可以说,电影对林白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被电影彻底浸泡过,我无法摆脱这一点,我眼前总要出现银幕,正如我笔下总要出现女人,我永远只写进入我视野里的东西。”[18](P91)
由于商业因素的影响和生存的需要,新生代作家对影视表现出急切的认同,影视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相当一部分新生代作家的主要职业,许多新生代作家甚至放弃或半放弃了文学创作。影视培养了作家的市场意识,作家在影视的潮流中摸爬滚打,也渐渐熟悉了影视的生产工序,新生代作家随着不断滋长的市场意识而走向身份的消解。以朱文和李冯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彻底转向了影视行业。李冯在担任张艺谋的影片编剧之后,成为身价百倍的“金牌编剧”,然后彻底告别了文学创作。朱文转行导演,执导了多部影片,并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东西、鬼子、何顿则热衷于影视编剧,虽然还继续小说的创作,但小说创作上鲜有建树。这些新生代作家实际上已经从作家转向了影视。当然,在经历影视之后,有些新生代作家表示不再涉足影视编剧这一行当,要将精力放在小说创作上,但是当他们再次回归文学时,却很少能见到他们的作品有什么进步。当自己声望俱隆时,邱华栋成为涉足影视之后退而守之的作家,“他不否认自己曾为了个人的经济利益写过一些剧本,而有些剧本是媚俗的。但是现在,他坚决不会去写了,他信奉文字本身的魅力,尽量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不媚俗,不出卖文字。”[19]鬼子也在小说《一根水做的绳子》卖出电影改编权后表示,虽然影视公司希望他来当编剧,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想再做影视了。“因为我前些年在影视圈里面晃荡了一些时间,我觉得这耗费了我大量的时间。我现在从这部小说开始,将回归到写小说中去。”[8]但是,虽然他们再次转向文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创作出相对优秀的作品。只有那些仍然坚持文学道路,较少参与到影视的新生代作家还仍然创作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如毕飞宇和李洱等。毕飞宇自觉地与影视保持着一段距离,即便自己的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也不介入编剧过程,而主要进行小说创作。李洱虽然也有一些作品被被改编为影视,如《石榴树上结樱桃》(陈力,2008),但是他对影视还是保持警惕,“我的小说现在也被改编成电影。改完以后我不看。制片人让我看,我也不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人物关系变了?你尽管变。让我署名,我说我不署名。如果放弃署名权给更多的钱,那我选择要更多钱。”正是这种创作心态,近年来,毕飞宇的《平原》、《推拿》和李洱的《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等作品广受好评。然而,这样的新生代作家已经越来越少了,许多新生代作家仍将小说作为影视的一个过渡阶段。这种状态和理念所创作出的小说自然丧失了文学的基本品质,正如作家李洱说,“小说中不能被影像化的部分,就是小说性最强的部分。如果一部小说很容易改编成影视剧,它的小说性就值得怀疑,即使不能因此说这是部烂小说,起码它不算是好小说。”[20]
结语
学者黄发有在考察1990年代以来影视与文学创作主体的分层现象时发现,第六代导演与新生代作家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精神纽带,第六代导演的生存方式、审美观念与新生代作家殊途同归,“影视主体与文学主体的呼应共同地印证着当下中国的文化逻辑。但是,这种过度膨胀的代群化特征抑制了创作个体的文化独创,同时也使影视与文学的交流缺少互补的良性循环,精神基调的过分一致使影视与文学难以相互激发,也使文化格局显得相对单调而不够丰富。”[21](P203)当一些新生代作家纷纷逃离文学,加入了影视编剧行列或商业化浪潮的时候,新生代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游离状态。一方面,1990年代以来的影视文化和商业逻辑潜在地影响到了新生代作家的创作行为,使得他们的创作脱离了文学本身;另一方面,在这一文化氛围中,许多新生代作家在影视、商业和文学之间不断徘徊,表现出身份的漂泊不定。正是这种双重的游离状态,我们发现,在今天我们再次回望“新生代作家”这一群体时,除1990年代新生代作家初登文坛时创作了一些优秀作品以外,1990年代后期和新世纪以来,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1] 张学昕.诗性的消解和精神的遁逸——九十年代年轻作家小说创作的精神走向[A].唯美的叙述[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2] 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 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历史见证——论90年代中国影视文化[J].天津社会科学,1998,(1).
[4] 尹鸿.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5] 周星.中国电影艺术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黄发有.媒体制造[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7] 张钧.小说家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8] 莫俊.鬼子新作即将改编成影视剧《一根水做的绳子》:生命永远为了爱[N].南宁日报,2007-09-13.
[9] 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N].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0] 张岩泉.社会转型与文学媚俗[J].中国文学研究,1997,(2).
[11] 石宇.爱上“瞌睡女孩”暂不“梦游桃源” 陈凯歌找新震撼[N].每日新报,2002-04-01.
[12] 曹雪萍.著名作家东西:我就喜欢新奇的野路子[J].新京报,2005-10-14.
[13] 肖煜.毕飞宇:小说改编成影视剧很正常[N].燕赵都市报,2005-12-02.
[14] 张钧.小说家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5] 陈蕙茹.邱华栋:邓建国再不拍《正午的供词》就收回版权[M].成都日报,2001-09-17.
[16] 洪治纲.无边的迁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
[17] 东西.小说与影视的跳接[N].文学报,2008-12-11.
[18] 林白.子弹穿过苹果[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9] 赵慧.邱华栋:不断超越自我[N].新疆经济日报,2008-09-11.
[20] 周代红.价值彷徨时代的文学坚守[N].大连日报,2004-11-30.
[21] 黄发有.媒体制造[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Survival through Film & TV and the Cultural Posi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Writers
ZHOU Gen-hong
(Nanjing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jing 210014, China)
Since the 1990s, the new generation writers who grow with a wave of marketization begin to write realistically about urban life, which makes novels and films conform to each other to some degree, which becomes the basic resourc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he wav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involve themselves in the writing of film and TV play scenarios. Because of the strong penetration of film and TV culture and the commercial will, those new generation writers lack imagination and suffer from serious self-duplication.
new generation writers; film and TV culture; penetration of commercial will
I207
A
1005-7110-(2010)03-0064-07
2009-12-07
周根红(1981-),男,安徽安庆人,南京体育学院新闻学专业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学与传媒、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