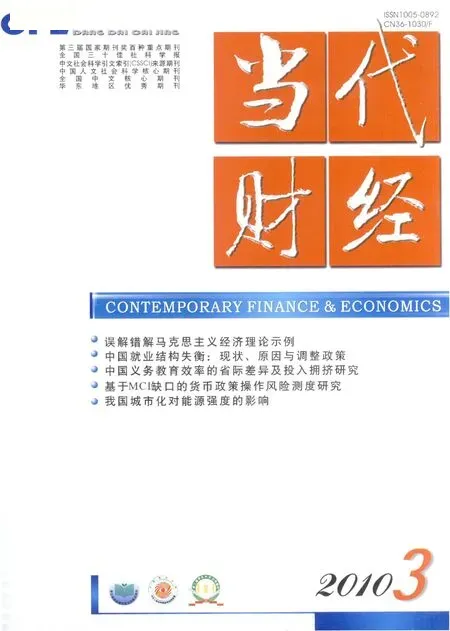误解错解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示例——谈读书要力求“甚解”、求真解
卫兴华,马东生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古人有“读书不求甚解”之说,为今人所不取。郭沫若批评有些人“不读书好求甚解”,也颇言之中的。今人读书,既要勤读书、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又要读书力求“甚解”、贵在真解。至于不读书好求甚解者,夸夸其谈、言不及义、误人害己,亦不可取。读书,并不只限于增加知识、提高文化素质和理论水平,还要运用获得的知识和理论,进行交流、发表议论、关注现实、把握国情、提供见解、解决问题。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读社会科学著作,尤其是读马、恩、列、毛、邓等的著作,要力求“甚解”、真解,领会其要义,把握其精髓,才能正确运用于实践,把握方向,做好工作。
今人读马克思主义(包括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与古代文人读经史子集不同。他们读经籍可以不直接与经济社会实践相联系。“诗无达诂”,一首古诗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与释义,一篇古文可以有解读深浅的差异。因此,“不求甚解”也无关大局,不会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盛衰。晋人陶潜《五柳先生传》中讲“好读书不求甚解”,其本意并非主张不认真读书,浅尝辄止。其本意是指领会其要旨即可,不必在字句上去深究,带有洒脱不羁之意。然而,今人读书,特别是读有关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以及改革与发展等方面的经典著作,就不能持“读书不求甚解”的学习态度。因为这类著作是用以指导实践的。若不理解和把握其本意、真义,发生误解、错解,就会给实际工作带来损害。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但在理论认识上误解、错解的东西并不少,兹从经济学的角度试举几例。
一、关于“过渡时期”问题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时限是什么?有个曾起过重大社会影响的解读,是把过渡时期定断为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时期。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说成是过渡时期,背离了原意。需要说明:马克思在这里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成熟程度不同的阶段,即“第一阶段”(或称低级阶段)与“高级阶段”。其“第一阶段”就是我们所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其高级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共产主义社会。从理论逻辑上来解读,所谓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应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不应是把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也作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此讲得很清楚。他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又说:“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1]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列宁又讲: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2]显然,所谓“过渡时期”,就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主席1953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过渡的时限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于1958年1月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也明确讲的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他又讲将来还有一个“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3]毛泽东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结束语”时,在批注中讲: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必然性,指出这个时期是用革命手段把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历史时代”。显然,将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依然解读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的历史时期。但是,在毛泽东读教科书的谈话中,又指出了对过渡时期存在不同理解的问题。他说:“过渡时期包括一些什么阶段,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也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另一种说法是,过渡时期只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究竟怎样说法才对,要好好研究”。这里没有否定第一种说法,就为在后来一个时期内将“过渡时期”错解和宣传为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理论”埋下了伏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左”的一套盛行的一个时期内,在我国的理论宣传中,硬说马克思和列宁认为过渡时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历史时期,把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为“过渡时期”,再把列宁所讲的过渡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空前尖锐的话加之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以此为搞阶级斗争为纲提供理论依据,提出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矛盾和斗争,从而忽视或模糊了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目的,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损害。
二、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经济是否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近些年来,有的学者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并分别从恩格斯和邓小平的论著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其实,这完全是出自他们对原著本意的误解和错解。他们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批评过冒牌社会主义,把一切国营企业看作是社会主义。又说邓小平讲过,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是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非公有制经济符合这三个标准,所以说统统姓“社”,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的学者还说,国有经济是“国家社会主义”,来源于希特勒,希特勒搞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又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人民社会主义”,有的称“民间社会主义”。主张否定前者而发展后者。这样理解和宣传,完全与马克思主义论著的原意相悖。先看看恩格斯的原话是怎么讲的:“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无条件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皇家海外贸易公司、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显然,恩格斯是否定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化即某些国营企业看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是为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的利益服务的,也是为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服务的。且看恩格斯紧接着的说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关系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4]国有化的性质同国家政权的性质相联系。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器下的国有化,是资本主义国有化,其国营经济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下的国有化,则是社会主义国有化,其国营或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理论观点在马列主义经典论著中有明确说明。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无产阶级将把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指出:“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5]所谓“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就是指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在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的论著中和我国宪法及许多中央文献中对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都有明确的肯定。单从我国宪法来看,它明确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又讲“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由此可见,离开马列主义著作和毛泽东、邓小平、中央文献以及我国宪法中的正面的明确说明,而刻意从对恩格斯的上述一段话的误解和错解中,得出我国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论断,是一种轻率的非科学的读书和治学态度。
三、邓小平提出的三条“是否有利于”是判断什么的标准?
对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南巡谈话中提出的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同样存在误解和错解。将它理解和宣传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离开了原意。邓小平的原话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段话中,因为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的论述在文法上是紧接着“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提出的,就容易误解为这是讲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有人还误解为邓小平在这里主张不要再问姓“资”姓“社”。其实,邓小平这里是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主张不要老用边界不清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干扰改革开放。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过去把发展商品经济看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连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发家致富等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个体经济更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用这种是非不清的姓“资”姓“社”观去判断和评价改革开放的是非得失,只能会阻碍改革开放迈步前进,导致“迈不开步子,不敢闯,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且,即使真正是姓“资”的东西如引进外资,只要符合三条“有利于”的标准,就可以大胆引进,可以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在战略上依然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请注意:邓小平讲的三条“有利于”的标准是社会主义的标准,无论讲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还是讲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前面都加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性范畴,并不是从改革的方向与道路上主张不问姓“社”姓“资”,像有些人误解的那样。
如果将邓小平所讲的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误解和错解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会带来偏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后果。
第一,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因为后者比前者更符合三条“有利于”的标准。难道能由此认为,传统计划经济姓“资”、市场经济姓“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有经济计划,但不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因而不存在计划经济姓“资”的问题。过去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始终实行市场经济,邓小平讲“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难道现在要反过来把市场经济断定为姓“社”,变成了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
第二,我国在改革中调整所有制结构,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所有制结构符合三条“有利于”标准,但不能由此认为,公有制和私有制统统姓“社”。有的学者正是由于把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错解为姓“社”姓“资”的标准,便断言我国目前与公有制共同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姓“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然而,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这是邓小平明确讲过的。私营经济,是以私有制和资本与雇佣劳动相结合为基础的经济。有的雇佣几百几千甚至上万的工人,其社会经济性质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它们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与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所不同。但其社会经济性质是一样的。不能因作用不同而改变其性质。在邓小平、江泽民的讲话和中央有关文件中,都曾讲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或讲“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就表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存在于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它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经济性质,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在“左”的年代,将个体经济看作资本主义予以消灭。改革以来,又有人说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在理论上都不能成立。社会主义可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但应弄清社会主义经济和非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自己,但不能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有人说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实际上是指“资”为“社”,重“资”轻“社”,扬“私”抑“公”,为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如果将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解读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就会由此得出结论:凡姓“资”的东西都不符合三条标准,那就不应引进外资和发展私营经济了。实际上,将三条标准正确解读为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就可以用以判明,包括私营经济、外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的非公有制经济,都符合三条“有利于”标准,因而可以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会不断改革与创新,不断完善与发展。不适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某些原有关系和体制需要除旧布新。总不能说,原有经济关系和体制适合生产力发展时,它就姓“社”,需要改革变新时,它又姓“资”。其实,新旧体制都是社会主义体制的更替与发展。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条标准,究竟是判断什么的标准,中央文件已再三做了明确的、正确的解答。不应离开这种正解的解答,硬去宣称是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
有必要说明:1992年3月9日至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报道中,曾提出:“判断姓‘社’姓‘资’,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6]显然,中央很快认识到问题所在和应有的准确解读,并在此后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中改变了提法。在同年同月的20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是这样讲的:“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进一步将三条标准解读为“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说明: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就是说,在开拓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的“一切”方面,都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判断标准。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所谓“一切”,包括经济社会建设与改革开放及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央一再正确说明邓小平提出的三条标准是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如果再坚持和宣传是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就不是科学的治学态度了。
最后讲一下:“不读书好求甚解”,与“读书不求甚解”、真解一样,都会错解原著的真谛。比如,前些年在深化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中,有的学者著书立说,有的在大报发表文章,宣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体力劳动价值论,是简单劳动价值论。这种论断是应当破除的附加于马克思的不实之词和错误观点。《资本论》中明确讲过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因而它创造的价值大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是一切政治经济学教材中都讲得很清楚的初级知识。马克思还在有关著作中强调指出,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在社会化的生产劳动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离开来,不同劳动者的劳动“同生产对象之间直接存在的关系,自然是各种各样的……工程师又有另一种关系,他主要只是从事脑力劳动”。[7]又指出,在分工协作的总体劳动中,“有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师等,有的人当监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之下”。[8]马克思还肯定资本家的管理劳动具有二重性,其中一重性质是为了剥削剩余价值而进行监督管理;另一重是任何社会化的共同劳动需要管理,就像乐队需要指挥一样。资本家在第二重意义上的管理劳动或称监督劳动,马克思肯定它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由此可见,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无论是一般工人的劳动,还是经理的管理劳动,还是工程师、工艺师的科技劳动,马克思都视其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注 释:
[1]列 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6、199-200.
[2]列 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4.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1-35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28-62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0.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7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