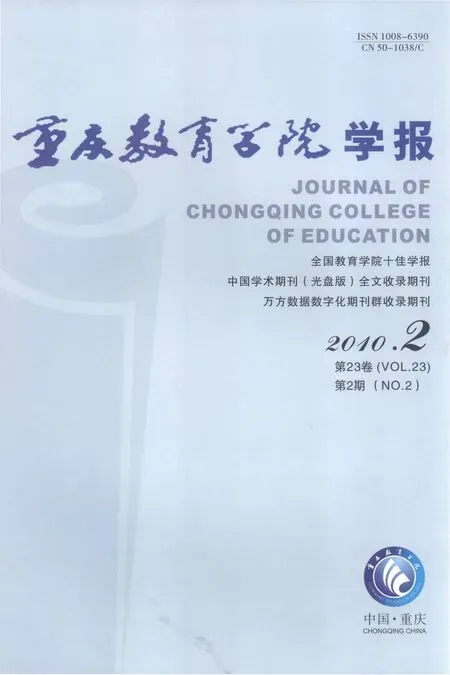论质的方法在我国比较教育微观研究中的应用
王红丽
(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重庆北碚400715)
比较教育研究对一个或多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背景因素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多元观察和多角度审视,具有多重面相性。这种研究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如描述研究法﹑历史研究法﹑统计分析法﹑因素分析法﹑阶段分析法﹑问题分析法﹑假设验证法﹑教育洞察法等。可见比较法不是比较教育研究唯一的方法,也远远不能满足比较教育研究的需要,必须从其他学科借用研究方法。质的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我国比较教育中的运用还比较少,很有必要加以介绍和探讨。
一﹑质的研究方法的特征及其运用
(一)质的研究方法的基本特点
质的研究方法根据我国学者陈向明的定义:“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景下采用多种资料搜集方式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质的研究强调在自然情景下,即要求研究者对自己的前倾性个人观点进行客观的审视,同时承认研究者主体认识的理解和认可。质的研究建立在对研究对象长期深入的观察和体验之上。与其他的研究方法相比,质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平民性”。[2]主要对社会微观层次的现象和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注重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和理解沟通,多以个案为主。通过对社会现象及其背景进行整体性的理解和解释,并发掘事物的深层次的原因,归纳概括而形成理论。[3]
(二)质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比较教育的发展历史中,在古希腊时代,就有不少旅行家和商人将自己在异域的见闻等记录下来介绍到国内,其中也包括国外的教育信息。这种非正式﹑不成熟的教育考察活动或许可以算是质的方法最早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运用。自从比较教育学建立以来,历代比较教育的研究中无论什么研究方法都一致强调提供全面的﹑真实的具有原始色彩的教育情境和资料。资料和文献的丰富性﹑真实性对于比较教育的研究至关重要。因此在比较教育的方法论演进中,从未忽视过对真实性、客观性和睿智性的诉求。埃德蒙·金就特别强调深入到背景中去,并且坚持忠实于这个背景,这意味着要有真实的知识,忠于本国人所理解的制度,并对他们所看到的问题产生移情作用。[4]加拿大的比较教育学者梅斯曼1982年在《比较教育评论》上发表了《论人类学的方法在比较教育中的运用》一文。她最早提倡在比较教育研究中采用民族志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众多的比较教育学者的采用质的方法进行研究。卡洛伊﹑阿普尔﹑阿尔特巴赫﹑凯利等比较教育学家在个案研究、传记学方法和田野考察等领域都做出了一定的探索。[5]
二﹑微观层面的比较教育现实之需
(一)后现代理论的冲击
后现代主义正式出现于西方的文化领域是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前期,流行于70-80年代,后现代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去中心,反基础,主张多元方法论的思想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原有范式提出了挑战。以往的比较教育研究多是以民族国家的教育系统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后现代的代表人物利奥塔主张用小叙事代替大叙事,用无说渺小的差异代替所谓伟大的体系。[6]布罗德富特(Broadfoot)指出,比较教育中量的研究方法向质的研究方法的转向,折射的是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哲学转向。这种民族国家本位,教育借鉴本性,奠基于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崇尚实证研究的比较教育。[7]兴盛于20世纪下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给质的研究带来的一个重要的影响是重视文化多元。同时也对比较教育方法和理论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
(二)我国的现实需要
钟启泉教授在《比较教育学:传统﹑挑战和新范式》这本书的序言中说:“国人的研究喜欢大题小做,过于宏观和笼统,因此对实践很少具有指导意义。”8]对于小问题学者们都不屑一顾,比较教育应该从小做起,从问题做起。教育研究不是静态的﹑理论的,它是在实践的﹑动态的过程中发生,脱离了实践取向的研究有违教育的初衷。早在1990年全国比较教育年会的致辞中,顾明远教授就指出,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严重脱离中国教育实际,由于长期缺乏对本国教育实践的关怀,停留在翻译和介绍层面的比较教育,使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大多停留在半空中。直到今天,比较教育研究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再者,由于我国以前从国外大量移植和借鉴教育经验,并没能很好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使理论本土化,出现了水土不服和南橘北枳的现象,以至教育教学过程中仍然出现很多问题。因此,比较教育学者和研究人员需要在深刻了解我国教育问题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的教育提出解决问题的良方,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外国教育的介绍和借鉴之中。
(三)比较教育研究新的发展取向
2001年7 月在韩国举办了第11届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新挑战和新范式:迈向21世纪的教育”。马克·贝磊主编的《比较教育学:传统﹑挑战和新范式》收集了这次大会提交的部分论文。这些论文大多以问题入手,进行了新的研究方法的探索。马克·贝磊和大和洋子提交的《微观的比较教育:从方法论的视角看待香港国际学校》采用了国内研究的国际比较这样一种交叉的比较研究方法。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教育研究选题的转向:宏观到微观,中心到边缘,总体到差异。[9]当代比较教育研究正发生着如下变化:实质性问题与更为多样的﹑多层次分析单元的研究潜力正在得到重视和研究。已经可以进行全球﹑国家间﹑更微观层面的质性研究的比较。从中心国走向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从国家宏观的教育现象研究到关注学校教学效果和教学方法的研究,注重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比较教育的教育关系建构活动必须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各个层面展开,不独在民族国家间进行。[10]但是现在国别研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很少有人明确考虑过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11]克罗斯勒曾指出,在比较教育领域,“我们可以从分析单元的变换中学到很多东西。”[12]微观层面研究的兴起正对我们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宏观的比较教育研究提出挑战。然而直至今日,这种国内比较所具有的潜在洞察力还未被我国充分意识和利用。
三﹑质的研究方法在微观层次比较教育中的应用
(一)对研究目的的反思和批判
质的研究是一种研究的方法,同时也是批判与反思的过程。受到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冲击,质的研究强调研究者的自我反省意识,研究人员对自己的行为有很强的责任感和道德意识。以前的比较教育的研究只是一贯的介绍和借鉴的做法,那种不顾本国实际情况推行发达国家教育经验和模式的做法,曾经对我国的教育产生过很不利的影响。以单纯的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来衡量教育的教育发展观使我们的教育走向了歧路,这其中比较教育学者们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
康德尔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任务不包括判断一种教育是否比其他的更好。比较教育是什么?我们进行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何在?是借鉴与输出?还是不同教育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人是否在研究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思考?这对于我们从事比较教育的人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研究目的的混淆不清对于我们的研究也就无价值可言。研究者应该就自己的整个研究过程进行反思,包括研究目的﹑如何收集资料﹑如何进行资料的分析等等。应用质的研究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之中,不再把“科学”、“实用”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它只是在微观层面对个别教育现象进行细致的、动态的描述和分析,整体地理解在不同文化和民族背景下的教育体制和过程,并以其为参照对本土的教育实践进行深入的反思。
梅斯曼、劳伦斯·斯腾豪斯和理查德·海曼为代表的比较教育学者提倡人类学研究方法。他们认为比较教育应该更多地以描述社会和教育现象为主,更多关注学校里的“日常生活”(day-to-day life),较少地进行科学预测。朱旭东认为比较教育这个学术领域,既没有去有意识地利用自己所研究的成果或创造的话语去解释当下的教育问题,也没有为其他的学科提供可供消费的学术观点,放弃以自己的话语去解释教育的权利。[13]以往的比较教育的借鉴和输出模式使比较教育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生产出了大量的外国教育的资料信息知识,然而对本国教育实践和问题没有给与很好的指导。因此,我们的研究者应该对我们的研究目的进行反思和批判。
(二)对本国比较教育理论的构建
教育是承载一个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基础,有学者指出:今天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文化是引起冲突的最主要根源。比较教育正是通过这些跨文化的教育考察和对话,来为本民族国家的教育发展提供进行变革与创新的启迪。[14]在我们进行对国外教育的考察和借鉴时,也应该注重对本国教育理论的建设。质的研究在于了解事物的动态发展过程,理论的形成是自下而上形成的。
比较教育研究者们的任务应该将比较教育的研究意向由单一地介绍其他民族教育转向为对本民族教育的发掘和传播,将焦点更多地聚集在对本民族教育的特色性展示方面。这样比较教育的双向性功能才能得到体现,而且这种趋势也日益成为一种主流。我们的民族教育应该主动融入全球教育化进程之中,研究者肩负起本民族教育在国际教育交流的重任,多在国外教育期刊和学术会议上发表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文章,促进不同文化﹑不同教育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促进双向的互动交流。
王长纯教授曾说过,我们应该在了解本国现状的基础上,有批判地吸收并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的形成,这就是“和”,而不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制造一个美国教育或德国教育,不是“同”。[15]认识不同文化的差异,认识文化的独立性;给予不同民族文化以尊重,中国比较教育研究者要理解“不同”,创造“不同”,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研究者要关注实践,与实践者对话,推动实践的发展。[16]比较教育传统的借鉴模式使研究者们通常把研究对象锁定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上,而缺乏将本民族教育特色展现在全球教育交流舞台上的努力;研究者们不自觉的这种潜在价值体系的影响有走向本民族教育自我异化的趋势;原方法论视角上的局限性使我们的比较教育陷入了求同的研究趋向,而对存异的关注不够,对建设我们自己的比较教育理论体系重视不够。
(三)研究者个人身份的定位
质的研究承认对研究者本人的倾见,并加以认可和利用。金认为,研究者的主观性是进行比较研究的主要理由或中心旨趣,“观察者”是通过他的主观性及过去生活经验来选择观察的对象及理解所观察的一切的。[17]埃普斯坦也曾指出,比较教育是不可能脱离各种意识形态特别是研究者个人所持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教育的研究应该体现比较教育学者的自身价值,体现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而不是身处研究之外的局外人。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是不可能客观的而具有主观性,理解不仅是主观的,它本身还受制于“前理解”。比较教育的研究对象是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学校社区中的教育,是一种人性化的活动,而大多比较教育研究者放弃以自己的话语去解释和分析教育问题,对研究似乎要做到客观公正和价值无涉,但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是无法做到完全客观的,在进行研究之前研究者的背景﹑价值观﹑知识体系都会影响研究结果。
如果比较教育只停留在教育事实的陈述阶段,就无法凸显研究的成果和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同时也无法很好的发挥研究者的作用。造成比较教育身份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比较教育学者对自身主体角色特别是创造者角色意识的严重忽视,对人性和人文性等非理性因素的有意回避。[18]薛理银的博士论文中指出:在以往的比较教育研究中,人们关心的是比较教育的方法和客体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目的,而较少论及主体和媒介,对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探讨也较少。[19]因此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应该确立研究者的地位,理解关注不同研究者所从事的教育研究活动。研究者们通过阐明自己的观点,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多角度的审视,这种丰富的理论构建活动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建设比较教育。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缺乏多样性视角的方法同一问题,会带来认识上的局限,使比较教育学科陷入僵化而失去活力。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自然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局限性,没有一种方法是尽善尽美的,都有其局限性。方法并无好坏之分,重要的不是用好的方法而是对方法的合适的使用。需要我们批判地认识和运用方法,认识到它的界限和范围,相信在比较教育以后的研究中还有更多的方法被使用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研究中,使我们对比较教育的研究更深入,更有创新,使比较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
[1][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2.9.
[3]嘎日达.论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两种取向和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2004,(1).
[4]埃德蒙·金著,王承绪等译.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之比较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49.
[5]陈时见,徐辉.比较教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15.
[6]徐辉.现代西方教育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53.
[7][10][18][19]李现平.比较教育身份危机之研究[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83,88,57,50.
[8][11][12]马克·贝磊主编,彭正梅等译.比较教育学:传统﹑挑战和新范式[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8.54.
[9]崔随庆,张长江.比较教育身份危机之病理、表征及其消解[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5):20.
[13]朱旭东.民族-国家和比较教育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1999,(2):3.
[14]项贤明.比较教育的文化逻辑[M].比较教育研究,2001,(23).
[15][16]王长纯.和而不同:全球化条件下中国比较教育发展的方向(论纲)[J].比较教育研究,2002,(S1).18.
[17]王承绪.比较教育学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87.
[20]李现平.比较教育学与教育学[J].比较教育研究,2001(9):16.
[21]刘彦尊.人种志方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外国教育研究,2006,(9).
[22]周成海.论质的研究方法在我国比较教育中的应用[J].外国教育研究,2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