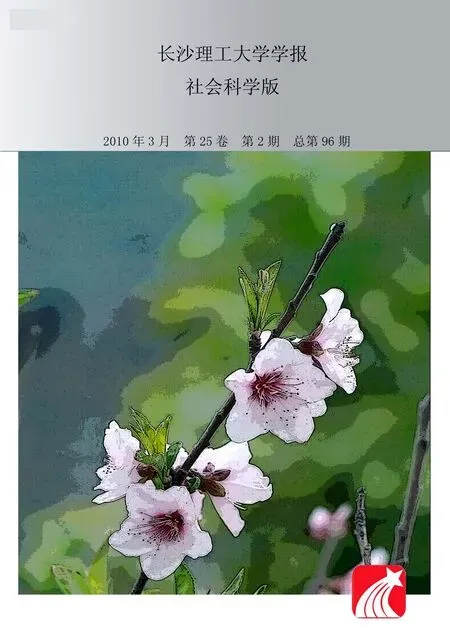从认知角度看词汇衔接的翻译
周雪婷,穆玉苹,潘卫民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一、引言
著名语言学家Guy Cook曾提出,语篇分析就是研究和解释语篇连贯性[1](P25)。对于逐渐以语篇为分析单位的翻译研究来说,对连贯性的分析和重构非常重要。衔接是连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被某些语言学派视作构建连贯大厦的基础[2](P94)。以往学者多从衔接角度来分析语篇连贯以及用于翻译中的连贯重构,并已经取得了有效成果。但不可否认,衔接还仅仅停留在语篇的表层,仅用于分析现象,而未把握本质。语篇的连贯性还必须从认知角度才能作出较为合理的解释,因为语篇连贯不是仅靠衔接手段和语篇结构取得的,而主要是靠心智上的连贯性取得的[3](P357)。
唯物主义辩证法提出,认识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将现象和本质相结合才能由外而内地全面认识事物。本文认为,对连贯的把握可以以衔接这一表象为探寻的出发点,以认知思维为探寻途径,来探索出语篇中衔接达成连贯的认知本质。在翻译中,也应根据“现象-本质-现象”的辩证认识论,首先识别出原文的衔接手段,再用认知思维把握到连贯的本质,最后重新以译文的衔接表现法将本质重构出来。
二、ICM理论与词汇衔接
上述理论就是要求将衔接手段置于认知世界中接受剖析和重构。“认知世界”是指人们在体验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形成的各种知识,内化储存于人们的心智之中,分为ICM和背景知识。所谓ICM(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即理想化认知模型),就是特定的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作出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理解,是建立在许多CM(即认知模型)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形结构[4](P68)。ICM相对于背景知识而言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和典型性,它是一个社团中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规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语篇读者,在理解语篇时,需要根据语篇表层信息,运用ICM和背景知识进行“搭桥”操作,通过表层的衔接建立深层语义的联系,从而把握语篇的连贯性,理解整个语篇。作为语篇构建者,在构建语篇时,需要遵循一定的ICM,按照其规律来组织信息,构建出符合ICM规律的衔接,从而就使构建的语篇具有了连贯性和可接受性。
关于衔接,这个被Halliday等功能语言学家视为连贯要素的语言组织方式,从认知角度看,仅仅属于语言表层现象。的确,语篇缺少衔接不一定不连贯,充满衔接的语篇也不一定就连贯。但是这个表层现象可以被用作把握本质的现象出发点。一般认为,衔接是语篇的有形网络,体现于语篇的表层结构上。Halliday和 Hasan从表观层面上首次将衔接分为了五个类型:指称、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衔接[5](P6),前四类并称为语法衔接,而词汇衔接则是通过选择与上文有某种关系的词汇项而实现的,分为“重复衔接”、“泛指词衔接”、“相似性衔接”、“可分类性衔接”和“搭配衔接”[6](P114)。Halliday和Hasan统计过,词汇衔接与其他四类衔接相比,出现频率更高,在语篇流畅建构中起主导作用,占48%。而词汇衔接又是最具直观性的、最便于把握的衔接现象,且其以意义为中心的理念与ICM理论是相一致的。所以本文尝试以词汇衔接为例,将认知语言学中的ICM理论用于语际翻译中对词汇衔接的分析和重构,以证明语篇连贯的把握和语际重构应透过表观语言现象,把握内在认知本质。
三、用ICM理论进行词汇衔接的分析和翻译
传统语言学将词汇视为音义结合的语言符号,认为意义包含在语言符号中,语言符号预定着语义,受其影响;传统翻译理论把词汇层面的翻译视为一个语码转换的过程,词汇层面的翻译也就是一个语言符号的转换问题。而按照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词不是简单的音义任意结合的语言符号,而是具有认知和心理基础的[7](P46)。传统翻译理论将词的翻译视为一个语码转换的过程,从形式上看虽无不妥,但是由于这一观点完全建立在对语言形式的现象理解基础上,因而忽视了语言意义的认知本质,而译者的任务就是努力使原词语所体现的认知模型在译文中得以移植,也就是说,在翻译中,对词汇的处理应遵循译文所在认知世界的认知规律,应该首先分析词语构成语篇的认知本质,然后在翻译中再以译文的认知规律为基础,再现此认知本质。
在认知语言学中,对认知规律的把握往往以ICM理论最为有效,ICM理论本身就是关于人的认知加工规律的理论。另外,ICM具有关联性,一方面指各个CM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另一方面也指一个CM中各成分也是相互关联的,不相关联的成分就不会被置于同一个ICM之中[3](P366)。词汇衔接实质上是统一ICM中各个CM或CM各成分的关联衔接,衔接词汇在读者心智中所激活的各个CM之间相互关联,使读者可以建立起语义联系,从而实现了语篇的连贯性和可接受性。所以在翻译中,不应仅停留在词汇衔接的形式表象。译文的词汇与原文的词汇所激活的CM不尽相同,机械的复制原文的词汇衔接形式往往并不能达到语篇的连贯,在翻译实践中应该从词汇衔接所激发的CM关联本质着手,再现CM关联性,唯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准确地再现语篇的连贯。借鉴李延林[8](P5)的分类方法,根据原文词汇衔接手段在译文中的复现与否,可以把词汇衔接的翻译手段分为四种:复现原文词汇衔接、重写原文词汇衔接、增加词汇衔接和省略原文词汇衔接。
(一)复现原文词汇衔接
此类方法在翻译中是最易操作的,即把原文中的衔接词汇对应翻译为译文词语后,同样在译文语篇内保持词汇衔接手段。人类认知思维的共性和不同语言的相通性使这种方式具备可能性。不过,此种翻译方式要求原文衔接词语与译文衔接词语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意义,从ICM理论来讲,一般要求译文词语所激发的ICM与原文相同或相似。
1) A little fat man of Bombay
Was smoking one very hot day,
But a bird called a snipe
Flew away with his pipe,
Which vexed the fat man of Bomday.
译文:孟买有个胖老头,
大热天里把烟抽;
一只鹬鸟飞过头,
抢走他的大烟斗,
惹得老头把气怄。
这是一首孟买的儿歌,展现的是一幅充满童趣的场景。在读到第二句时,读者很自然地通过“smoke”激活一幅胖老头抽烟的ICM,而因为此抽烟者的身份(A little fat man)和抽烟背景(one very hot day,带有滑稽色彩),读者所激活的“抽烟ICM”中“烟具CM”应该是或接近于pipe。从而“smoke”和“pipe”构成搭配型词汇衔接,一个是“抽的动作”,一个是“动作的对象”,在译文中可以予以保留,被翻译成了“把烟抽”和“大烟斗”,也是一个为动作CM,一个为动作对象CM,同属于一个“抽烟ICM”中。这种的处理方式保留了原文的意蕴,也是符合译文读者思维连贯性的。
(二)重写原文词汇衔接
不同语言间各种差异的存在,如语言规约、文化背景、思想观念等,使得在很多情况下不同语言读者头脑中已有的认知世界有所不同,对ICM理解的把握也会产生差异[9](P23),因而原文词汇衔接方式往往不能直接复现。我国著名翻译家傅雷提出:“翻译的人应当把原文彻底弄明白了,完全消化了之后,再重新写出来。”这里,对词汇衔接“完全弄明白”,就需要深入到其心理和认知底线,从人所激发ICM去按规律把握起其连贯本质,正确把握具有一词多义特点的词汇在原文中所欲传达的CM[10](P109),然后再重新在译文中以另一种衔接方式构建可搭起思维连接的CM关联性。
2)Although schoolmistress’ letters are to be trusted no more or less than churchyard epitaphs; yet, as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a person departs his life, who is really deserving of all the praises that stone-cutter carves over his bones; who is a good Christan, a good parent, child, wife or husband; who acturally does leave a disonsolate family to mourn his loss.
译文:一般说来,校长的信和墓志铭一样靠不住,不过偶然也有几个死人当得起石匠刻在他们朽骨上的好话,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女,尽职的丈夫,贤良的妻子,他们家里的人也真的是哀思绵绵地追悼他们。
这是杨必先生在译作《名利场》中广为人称道的一段译文。译文斜体部分采用了“good”作重复型词汇衔接,其连贯本质是“good”这个无标记词语使读者激发出了两个相同的ICM,即“为世人所普遍认可的、称赞的一种性质”。然而在译文中,若同样翻译为“好教徒、好父亲、好儿女、好丈夫、好妻子”,不仅语言会很苍白,而且由于译文读者缺乏原文的宗教、家庭观念等背景知识,便无法确定出原文“好”的内涵,即不能充分、正确地激活“好”的不同CM,这样导致认知加工所需的努力过大,句间语义联系就过远,其连贯性也就降低。而杨必的翻译则照顾到了这一点,将“好”这个ICM所含的CM对应性地显化了出来,因为“虔诚”、“慈爱”、“孝顺”等CM都属于读者心智中关于“好”的ICM,从而建立起了语义连接和语篇连贯。
(三)增加词汇衔接
如果译文中的语言符号所激发的CM之间联系太远,往往需要增加衔接方式。另外,汉语是讲究意合的语言,所以更多地是通过CM之间的“搭桥”连接而实现的语篇连贯。而英语注重形合,还必须在语言形式上达到连贯,即必须通过语言符号来“引导”CM的激活和衔接。
3)这些书,都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来到我家的……最初,囊中羞涩,也曾交臂相失。中间也曾一掷白金,稍有豪气。
译文:During the first few years, as I was financially embarrassed, sometimes I had to turn from the books that I would have liked to give every thing in exchange for.However, there were occasions on which I threw my money on books with quite a sense of lavish generosity.
此篇为刘士聪先生翻译的孙犁《书籍》中的一段话。原文读者能够从“书CM”和“购书钱CM”间的联系,借助背景知识进行搭桥操作,建立起语句之间的语义联系,从而理解了本段的意思。但在译文中还需要满足英语形合的语法特征,而代词是英语中起衔接作用的重要词汇。所以译文中多处添加了“I”做ICM的参与者,用词汇重复衔接的手段使语篇各个CM均以“I”的中心,从而使语篇在符合语法的基础上达到了连贯。
(四)省略原文词汇衔接
当然,词汇衔接的增加也是以认知心理为基础的,是以迎合人的认知思维为目的的。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进行适当的复现、重写、增译之外,有时还可根据ICM的需要进行必要的省略,使译文简介晓畅,文约而意丰,但前提是不破坏CM间的连接。
4)打起黄鹂儿,莫叫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译文:Drive orioles off the tree,
For their songs awake me,
From dreaming of my dear,
Far off on the frontier.
这首唐朝金昌绪的《春怨》描述了女主人公因思念远在战场的丈夫而迁怒于黄鹂儿的场景。诗歌第二句句尾的“啼”字与第三句句首的“啼”字构成了明显的词汇衔接。而第二句的“啼”属于“主人公制止黄鹂啼叫”这一CM中的成分,第三句的“啼”属于“主人公因黄鹂啼叫而梦醒”这一CM中的成分。两个成分的重叠使得两句建立起了语义关联。在翻译中,因为语言规约性往往难以再现原文的词汇衔接方式。许渊冲先生把握了“啼”的衔接实质,在译文中省略了原文的词汇衔接方式,而将两个CM的重叠成分融为了一个“song”,以这种方式很自然地将两个CM融入到一个ICM之中去。这样的处理方式把握了原文的CM关联本质,并使语言简练、自然。
四、结束语
认知语言学关于词的认知和心理基础的论证确定了词语翻译研究的认知取向。虽然从表现形式上我们依然可以把词汇层面的翻译视为一个语码转换问题,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语码这一表层现象分析出语码转换的本质,具体来说就是从认知层面上来探讨词语的翻译问题。ICM理论从认知角度为我们从认知本质上把握语篇的连贯提供了利器,且该理论已广泛应用于语篇解读中的连贯问题,而理解和重构在认知角度上是相通的,所以ICM理论同样可应用于翻译中的连贯问题,本文仅从ICM的模型完形特征进行了分析,另外还可将其建构原则(如转喻、隐喻、意向图式和命题原则)应用到对词汇衔接的本质挖掘和语际翻译中,从而为语篇翻译的认知研究开拓一条更宽阔、更深入的道路。辩证的认识论能使翻译研究更具科学性和准确性[11](P90-92),词汇衔接表象与认知理论本质的创新性合作,必然可开创翻译的辩证认识与研究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Cook, Guy..Discourse and Literatur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Halliday, M.A.K.& Hason, R.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M].Geelong Vic.: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85.
[3]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4]Lakoff, G.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5]Halliday, M.A.K.& Hason, R.Cohesion in English[M].London: Longman, 1976.
[6]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7]肖坤学.试论词汇层面翻译的认知取向[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1).
[8]李延林, 刘连芳.科技应用语篇中的词汇衔接与翻译策略新探[J].中国科技翻译, 2008, (2).
[9]陈建生, 姚尧.理想化任职模型与诗歌语篇连贯[J].外国语文, 2009 (1): 23-27.
[10]潘卫民, 毛荣贵.汉英词汇转义与翻译审美价值[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2006, (3).
[11]肖志红.辩证法关照下的翻译标准[J].外国语文, 2009(2): 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