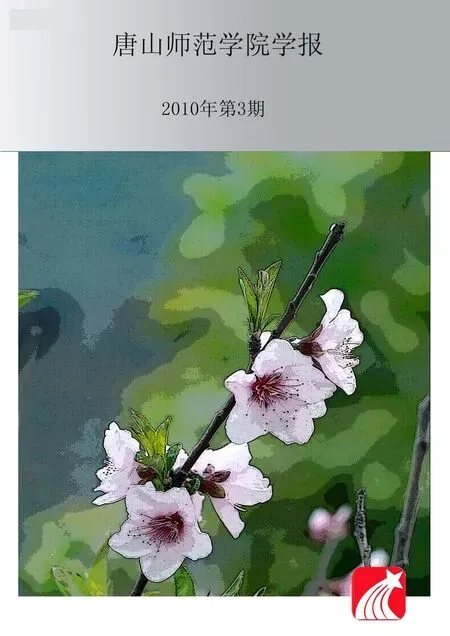超性别意识写作的现实可能性
吴 春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1450)
女性写作之所以区别于男性写作,是由于它是一种具有性别意识即具有女性性别意识的写作,也就是强调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应该铭记自己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女性身份。长期以来,我们的女性写作基本上是进行着缺少性别意识的“中性化”和“无性化”的“花木兰”式写作。从杨沫的《青春之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草明的《乘风破浪》,一直到新时期初期谌容的《光明与黑暗》,都是这样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单一到多元的社会文化转型语境为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一个多元发展的机遇,特别是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的推动下,女性作家在写作中出现了性别意识的大面积的苏醒,许多女作家的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而备受关注。“性别意识”既指女性意识,也指男性意识,但通常说的“性别意识”主要是指女性意识。女作家的“性别意识”浮出地表不久,“超性别意识”的创作理念被提出,学界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一、何谓“超性别意识”
1994年,女作家陈染发表了《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一文,文中提出了“超性别意识”的观点。其归纳起来应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爱情,所谓“我的想法是:真正的爱超于性别之上”,“异性爱霸权地位终将崩溃,从废墟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这里讲的实际上是一种同性爱或同性恋,是为她的作品写的“姐妹情谊”所作的一个注脚。第二层是指“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融洽地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情感和思想传达得炉火纯青地完整”。这里指的是把两性融合起来的一种写作姿态。第三层是“一个具有伟大人格力量的人,往往首先是脱离了性别来看待他人的本质”。这里指的是要以超性别意识来看待人,欣赏人。从陈染的以上表述可以看出,“超性别意识”是要超越单一的性别视角来观察世界、看待生活[1]。
严格来说,“超性别意识”的观点并非陈染独创和首发,其他女作家和女评论家也曾在不同角度上表达过类似观点。如铁凝在谈到自己的女性题材长篇小说《玫瑰门》时说:“我本人在面对女性题材时,一直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我渴望获得一种双向视角或者叫做‘第三性’视角,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我更准确地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当你落笔女性,只有跳出性别赋予的天然的自赏心态,女性的本相和光彩才会更加可靠。”[2]评论家王绯在谈到女性文学批评的时候提出了“两种眼光(女性的眼光和中性的眼光)”。而若追溯得更远些,我们会发现早在1987年我国出现的较早的女性文学研究著作《女性主义文学》中,著者孙绍先在考察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历程,指出女性主义文学的困惑并预测女性主义文学的走向时指出:“女性既不应该继续做父系文化的附庸,也不可能推翻父系文化重建母系文化。出路只有一条:建立‘双性文化’。”[3]1995刘慧英出版的《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中也提出:“我反对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我也不赞成男女两性长期处于分庭抗礼的状态之中,我比较赞赏西方某些女权主义者提出的建立和发展‘双性文化特征’的设想,它是拯救和完善人类文化的一条比较切实可行的道路。”[4]“双性文化”和“超性别意识”用词不同,但二者传达的思想大体是一致的。它是“性别意识的一种升华,是性别意识与人的意识的一种融合”[5]。
二、“超性别意识”提出的背景
“超性别意识”的提出是我国女性文学发展过程的必然。首先,中国的女性文学创作一直是在一条布满荆刺的坎坷道路上艰难跋涉,是在一种困境中发展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是活跃、蓬勃的,很多人也在赞扬肯定女性文学,但是女性文学也一直处于一种被质疑和批评的境地。从张洁的《方舟》、《祖母绿》,张辛欣的《我在那儿错过你》,铁凝的《玫瑰门》,到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没有一部作品不是在文坛上引起争议的。张洁和张辛欣的作品被看作是典型的“仇男文学”,陈染、林白虽然被一些女性评论家(如戴锦华、徐坤)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但不乏批评的声音。
某种程度上来说,女作家们提出“超性别意识”可以视为突围困境的一种努力,是她们将自己的写作置于更广大的文化场景之上,以女性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立场和观照方式,面对现代人的存在境遇而传达出“禁中守望者”的另一种话语,是让女性言说从自我封闭走向艺术开放与文化开放可能性的可贵探索[6,p24-29]。
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超性别意识”的提出,也是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的一种贯有的创作心态在20世纪90年代延续的具体表现形式,这种创作心态是女作家不甘于只作为女性作家。从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变化,可以看出她的创作历程是从女性意识的显现宣泄走向女性意识的消失隐匿。张抗抗、张洁、王安忆都明确表示过不是也不愿被人视为女性主义者。虽然到了陈染这里,她已不讳言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了:“我想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我的立场、我的出发点,我对男性的看法,肯定都是女性的,这本身就构成了女性主义的东西。”但陈染还有另外一个观点:“人类是什么呢?不就是由个人组成的吗?‘我’就是人类之一。”她认为“个人化”写作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能够有所呼应的‘个人’其实就体现了一种共同性。”[7]女性体验的“个人化”写作是全人类的,全人类的自然就是超越性别的。从这一角度看,“超性别意识”是女作家们显示自己视野开阔、境界高远的一种自我表白。
“超性别意识”也是对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移植和借鉴。西方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就女权运动而言,它的纲领是男女平等,但发展过程中一度为男女二元的对抗,出现了一些“反家庭者”、“逃离母职者”和“女同性恋者”等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这使女权运动走入了歧途。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一代女权主义者则不再强调男女的二元对立,而旨意消除两性间的冲突、对立,主张超越性别本质论,走向双性和谐。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西方文化理论不断涌入,逐渐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参照。
就文学创作而言,我国将西方要花一百多年走过的文学历程在新时期以来的一二十年中演练了一遍;文学理论、批评上也如此,在20世纪西方文论的各种派别中,从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到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等都被“拿来”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也在“拿来”之列,而“超性别意识”也就包含其中。
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超性别意识”的提出也反应了当代批评家和一些女作家对女性性别意识的误解。在批评界存在的误解主要表现在,把女性意识简单等同于独特的女性经验,特别是身体经验和性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一些批评家认为关注社会问题的女性写作就成为了超越女性意识狭隘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一些女作家对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意识不分明。在描写女性生活时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只是停留于对女性的困境的呈现,而不能有力地挖掘种种冲突的焦点所在[8]。
三、超越性别意识写作的可能性分析
“超性别意识”的提出,引起了女性文学关于性别意识与超性别意识的一番激烈讨论。1995年,南京大学教授丁帆发表了《“女权主义”的悲哀——与陈染商榷“超性别意识”》一文,回应1994年陈染《超越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文章主要针对陈染提出的“我的想法是:真正的爱超于性别之上”,“异性爱霸权地位终将崩溃,从废墟上将升起超性别意识”的说法“可谓女权主义歧路的悲哀。她不去首先推翻一男性视阙为霸权地位的现行世界的不平等,而企图在同性之中群迷柏拉图式的自以为是最人道最人性的精神之恋。其悲哀之处则是在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副唐吉柯德与风车作战的视觉图画。”“真正的爱超于性别之上”的理论完成似乎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并提出“在这一个具有浓郁封建色彩的男性权力国度里,不去要求男性应有的权力,而去奢谈生命”超性别意识“的情爱,无疑是起着一种助纣为虐的作用,同样也是破坏了女权主义运动自身的发展而误入歧途。”[9]
在1996年召开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超性别意识”的观点也得到了理论批评界的响应和首肯。刘思谦在会议论文《女性文学的价值目标》中就明确指出:“女性文学……虽然以性别命名,其内涵与生命的活力是超越性别的,其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盛英在会上发言中谈到女性文学的发展方向时,也认为应该是男女互补互动,男性女性双向共建。
1997年5月,降红燕在《文艺争鸣》第五期发表了《关于“超性别意识”的思考》一文,对“超性别意识”的概念及相关问题作了梳理和探讨。文章对“超性别意识”的实现作出了理性分析:“从终极关怀的意义上说,‘超性别意识’是女性文学(应该不限于女性文学而是整个文学)的发展方向。……但是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并不是推翻男权统治,把男性赶下宝座,自己再戴上王冠,把‘男尊女卑’改为‘女尊男卑’。女性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要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双性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性文化”是应该提倡的,‘超性别意识’也是应该具有的。但是还应该看到,在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下,‘超性别意识’的提出可以理解,然而不宜把它作为女性文学的创作信条,评论界若拿‘超性别意识’来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尺,还会在某种程度上压抑女性文学创作,甚至成为横亘在我国女性文学本已艰难的路途中的一个
障碍。”[6,p24-29]
的确,从总体环境上来看,中国目前的写作环境并不能给“超性别意识”写作提供一个可能实现的环境。在“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很高,但女性意识很低”的现状下,在许多人还搞不清楚何谓女性意识,许多人的女性意识还未被唤醒时就谈超越女性意识,则显得操之过急。就现实状况来看,“女性意识在目前不是溢满得应该超越了,而是张扬得远远不够”[6,p24-29]。
另一方面,就创作而言,作为创作主体的女性,她们也无法做到完全抽离出她们作为一个女性的现实存在。正如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所说:“想象力逃脱不了性别特征的潜意识结构和束缚,……不能把想象力同置身于社会、性别和历史的自我割裂开来。”[10]这是写作主体也无从感知而随天然的性别差异自然产生的。作家如何希冀超越性别,都无法完全做到完全的超越。而对女性作家而言,她们往往也总是通过恋爱、婚姻、家庭这些女性所熟悉的内在生活场景去透视外面的世界。女作家胡辛明确宣称,她就是为女人写作的;王晓玉谈到她在创作时很少有“我是女作家”的框子指导着创作,但上帝既把你造成女人,你就必然在写作时投射进女性意识。
因此,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超性别意识”都处于纯理论层面,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操作性还待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