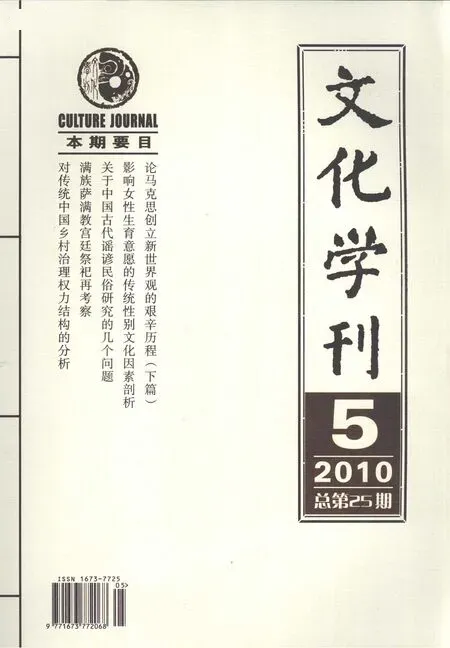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分析框架和进路选择
李丽丹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困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5年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之后,在各级政府部门广泛动员、全面主导之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保护工作已在各地陆续开展起来。截至目前,已有民间文学、传统技艺、传统音乐、民俗等十大类117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或扩展名录,更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了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已初步建立。[1]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自开展以来,一直都在希望与困难中前行。综观这些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实践,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各地政府部门往往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成可供开发利用的“遗产”资源和品牌,更多地关注其对推进当地旅游经济和树立文化形象的价值,对促进和实现其传承与延续这一保护的根本目的反而少有关注甚至完全撇开不顾。随之而来的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便是“政府拼命干,俗民一边看”,政府部门在保护工作中出头露面甚至越俎代庖(以至于保护性破坏时有发生,本文暂且不议),而作为创造和传承文化遗产的主体——俗民却基本上处于被动参与甚至缺位的状态。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并将继续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陷入无法可持续、健康、科学发展的困境,因为从长远来看,单靠政府部门“一厢情愿”地热闹推动,缺少俗民的自主、自愿、有效的参与,保护是无法向纵深推进的,更无法达至“使我国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扬”的目标。①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设定的目标任务。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实践也告诉我们,俗民的自主参与才是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主体保障,相反,如果一个民俗事象失去了俗民的自主参与,就一定会走向枯萎,甚至灭亡。[2]此外,就我国浩如烟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而言,能够进入各级政府保护视野的只能是极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然要依靠其创造和传承的主体——普通俗民自主进行保护。因此,尽快解决俗民自主、有效参与保护程度过低问题,真正形成俗民自我创造、传承、保护和发展的局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出困境,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本文尝试引入自组织理论,通过对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良性运行个案的分析,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组织机制,同时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合理、可行的分析框架。
二、自组织理论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自然科学前沿兴起了复杂科学研究,研究对象主要为复杂性和非线性复杂系统,并出现了“协同学”、“耗散结构论”、“混沌理论”等一批新自然科学理论群,这一理论群被统称为“自组织理论”。自组织理论产生后,很快被广泛移植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并成为炙手可热的前沿研究领域。上世纪末,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和应用自组织理论及其方法论,并取得重要进展,如吴彤将其应用于哲学研究,沈华嵩将其应用于经济学研究、孙志海将其应用于社会发展研究等。
自组织理论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或从低层次有序升级为高层次有序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自组织,就是“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自主实现有序化;另一种方式是被组织(或他组织),就是“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存在外界的特定干预,其结构或功能是外界加给系统的,而外界也以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系统”,系统依靠外界指令被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3]自组织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长期演化,不断试错而选择的进化方式。作为一种复杂系统形成和演化的方式,自组织要比被组织更为优化,更具活力,更符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脉络和趋势。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总体优于计划经济,自由恋爱总体优于包办婚姻,前者是“自组织”的,后者是“被组织”的。同时,该理论还指出,就人类社会进化而言,很多时候自组织机制和被组织机制是并存的,各有其适用的时空范围,相互组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系统,推动社会进步,不能无视具体的社会发展过程和历史条件,简单断言哪一种组织机制更好、更有效。此外,被组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自组织事物的,而只有实现了这种转化该事物才能更好地“维护下去、运行下去”。
自组织理论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将它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实践,无疑能够给我们提供新视角、新启发、新思路。依据自组织理论及其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可以分为两种机制:俗民自组织保护和外部力量被组织保护。如果俗民能够自主、自发、完整、原汁原味且因时、因地制宜地传承好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保护就是自组织保护;反之,如果俗民通过自身力量无法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由政府等外部力量通过行政动员等手段“替代”俗民进行保护,这种保护就是被组织保护。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看,自组织保护显然优于被组织保护,因为自组织保护成本更低而收益却更高。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被组织保护一时很有成效,最终也需要转化为自组织保护,否则,这种保护很可能只是一种保存,无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好地传承、发展下去,是不可持续的。下面,笔者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相声的自组织发展为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选择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以天津相声为例谈自组织传承与发展
(一)天津相声传承与发展概述
“天津相声”于2007年6月入选天津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2008年6月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年天津市共有4项“非遗”入选国家名录)。从光绪初年北京艺人玉二福来津长期演出到今日“天津相声”成为天津地方文化的一个代表,近百年的天津相声大致经过了“传入——繁荣——稳定——沉寂——复兴”这几个时期。
清末民初北京相声名角“八德”①“八德”指裕德龙、马德禄、李德锡、焦德海、刘德志、张德泉、周德山、李德祥8人。频繁地往来于京津之间,天津相声逐渐兴盛起来。直到上世纪2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前,天津相声才进入繁荣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一大批著名相声演员的涌现,如李德锡、张寿臣、马三立、侯宝林、常宝堃、郭荣起等,他们生于天津或长于津门,都在这一时期穿行于京津两地表演。
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60年代初,相声平稳发展。一方面是新的传承人加入,如苏文茂、高英培、李伯祥、魏文亮、马志明等。这一时期,不少传承人被纳入政府组建的文艺团体,如马三立进入天津市曲艺团,郭荣起加入天津广播曲艺团,后又转入天津市曲艺团。另一方面是相声创作的稳定发展。以侯宝林、马三立先生为代表的相声艺人为适应新时期新文化的需要,对相声进行改革,一方面整理和改编传统相声,从表演形式和思想倾向上对相声进行改革,去除相声早期因“撂地摊”而带的各种粗口,如侯宝林对《改行》、《关公战秦琼》等传统相声的改编。[4]另一方面又以时事入相声,以增强相声的时代性。
自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天津相声渐趋沉寂,不少艺人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或者下放农村,或者进工厂,如1971年马三立和马志明被送到了农村,高英培被送入工厂锻炼。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天津相声才开始进入复苏时期。相声艺人逐渐恢复演员身份重新投入到艺术表演,如马三立、马志明、李伯祥、高英培等相继回到文工团,但演出活动仍是以文工团的剧场演出为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天津相声逐渐复兴,主要以相声艺术专业团队的形成和固定的茶馆相声表演为标志。1987年,群众性文艺团体哈哈笑艺术团成立;1998年,中断已久的相声大会在相声艺人的策划下开始逐渐恢复;1999年,相声艺人们才开始有意识地组建相声团队,如哈哈笑相声队、众友相声队;2004年,哈哈笑艺术团又成立了哈哈笑群星相声队;2005年,九河相声团成立等。这些相声团队近百名相声演员穿梭于各个茶馆之间,为热爱天津相声的人们感受原汁原味的茶馆相声而奔走。
(二)天津相声之自组织实践
天津相声兴起、繁荣、稳定发展、归入沉寂的这段旅程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同命运,其缓慢复兴则是在多种力量博弈后产生的结果。天津相声在峰回路转后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保护名录、一段历史,而是天津人休闲生活中的文化选择:时尚的青年和铁杆相声迷们一周两三次去茶馆听相声,影视迷收看天津电视台的“鱼龙百戏”专栏,网民点击天津相声网,出租车司机长期锁定“FM92.1”天津相声频道,甚至坐公交车时也能听到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熟练地唱太平歌词,打听一下原来是想进戏曲学校学相声……以相声作品为基础的衍生产品也不断产生,如相声剧、相声的动漫配图等。天津相声在沉寂后能够得到有效的传承、保护与发展,大致有以下几种路径:
第一,相声艺人自发组织相声团队,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完成市场化生存的回归
自上世纪90年代哈哈笑相声队、众友相声队、九河相声团成立以来,津门较为成熟的相声演员基本荟萃于此,2009年还新增了女子相声队、群芳社等。据调查,这些只是目前在天津市能够产生较大影响的民间相声团体,其他还有各区文化宫的相声团体。
艺人自发组成的团队对相声从沉寂走向复兴至少发挥了以下作用:一是适应茶馆表演的需求,为相声成功回归市场赢得机会。相声平稳发展时期依附于综合性晚会而只能在剧场表演,而团队则可完成一场两至三个小时的专场表演,符合茶馆表演的时间与内容需求。团队的成立增加了演员的演出机会,自然有利其生存。名流茶馆、中华曲苑、谦祥益啜茗阁茶园、燕乐茶社、中国大戏院小剧场、乐海茶社等是以上相声团队固定的演出场所。茶馆根据座次、时间和相声艺人的知名度来定票价,一般每场从10元至60元不等,茶馆一场可以容纳80至200人左右,每天一至两场不定。再加之电台、电视台、节庆演出等,为相声艺人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其二有利于相声的传承。相声团队成立之初带有艺人自娱和相互交流的性质,如哈哈笑相声艺术团,但后来无论是专业团队还是业余表演团,都有几名自己团队的“攒底演员”,①相声表演讲究“攒底”,在一段相声结尾最强烈的“包袱”,把整段相声推向高潮,而技艺达到一定高度的好演员常被作为一场相声表演的“攒底演员”来压轴,许多相声迷常常也是冲这些演员而跟踪场次。如众友相声队的尹笑声、黄铁良、佟手本等,哈哈笑相声艺术队的佟有为、马树春、刘文步等。“攒底演员”对于相声队演出的声誉、团队内新进人员的表演技艺的提高等都有重要的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是传承人的保护和文化空间的存在,传承人的良性传承应该是一种自愿传承,且是符合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传承,而文化空间更应如此,现在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虽被列入名录,却无法改变逐渐消亡的命运,就在于传承的消亡和文化空间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消失,尽管政府出人、出力、出钱,给传承人一定的经济补助,建立民俗博物馆等,甚至组织一些节庆活动为文化展演提供变异的空间,但被组织起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不能恢复元气,甚至日渐消亡。天津相声较早地自发组织成团队,并较适时地抓住茶馆表演的机会,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完成了市场化生存的回归,为传承赢得了时间和机会。
第二,天津相声传承既保留传统,又兼具创新,传承方式趋向多样化
历史上的相声传承有着严格的师徒体系和门第规矩,②相声艺人在过去只有举行拜祖师爷、拜师父的仪式,立字据,鞠躬叩头,“摆知”吃酒,要“三年零一节”方能出师,且拜师必须要有引师、保师和代师,在卖艺的过程中也必须遵守各种规矩,如不能抢同行的饭碗,不能说唱同行的经典段子等。并常伴随着家庭传承。如相声名家的马氏与常氏,都是父子、兄弟,甚至祖孙三代为相声艺人,如马德禄、马三立、马志明。施爱东在对郭德纲的相声进行研究时,曾列出了七代“相声界族谱”,[5]有些相声迷在网络上对相声传人的代际则已推至九代。以近十年的拜师情况来看,这种传承依旧兴盛,如2000年,台湾相声艺人朱德刚拜天津著名相声艺术家魏文亮为师;2006年,于琪、吕小品、李苏、王悦、李庆丰五人拜李伯祥为师;2007年4月,刘春慧拜张文霞为师;2007年6月,于磊拜宫兰欣为师;2007年8月,于浩成为相声名家刘聘臣的弟子;2008年4月,王闰、李业胜、郭全伟、吴钢、曲玉亮拜杜国芝为师等。但拜师的内涵和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学艺,更多的是一种身份的认定和提高知名度的方式。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相声出现一种“复合”传承的趋势,即家庭影响、拜师学艺与专业学校学习集相声艺人于一身。如马志明先生既受家庭氛围的影响,又曾于1957年进入天津戏校学习,又于1962年加入到天津曲艺团,20世纪80年代由侯宝林先生代收师弟,拜已故相声前辈朱阔泉先生为师。而青年相声艺人杨化然则可视为“80后”新一代相声艺术传承人的代表,他出生于相声世家,其祖父杨少华、其父杨威和叔叔杨议均为相声演员,曾就读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大专部,在学校教育中自然能师从多人,且获得了正式的曲艺学校的“文凭”,又于2008年拜第七代相声艺人佟守本为师。“复合”式传承中,师承的讲究不再是学艺和卖艺的必经手段,而成了提高技艺和增加知名度的方式。
传承方式多样化主要是源于相声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和政府积极参与和支持相声曲艺的传承。电视、电台、录音、录像等增加了相声爱好者的自学渠道,大学校园相声协会成员和许多业余相声演员多是通过这些方式开始学习相声,大大扩充了相声传承的队伍,为专业相声艺人储备了力量。如南开大学国乐相声社团的裘英俊,由爱好相声,到拜师姜宝林先生,最后在择业上成为相声主持并穿行于各个茶馆间说相声。另有2009年成立的“女子相声团”,五位女传承人都是从业余起步,并拜师魏文亮先生。
第三,天津市民自主、自愿参与相声的传播、传承与保护
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难常常被描述为传承人的困境,刘锡诚先生指出:“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同,在长期的发展嬗变过程中,大都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差异的,即使同源的项目,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也会发生异变。……大都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发轫期无一例外地都是为谋生的手段”。[6]作为大都市的文化事象,受众的参与程度直接关系到相声传承人的生存。正如相声艺人常宝华所认为的,听众(观众)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有活力的文化事象应是传承人与受众间的有效互动,只有双方受益的传承才能持续有效地生存下去。天津市民多样化地参与到相声的传承与保护中,主要表现除了前文提到的诸多方式外,还有市民从幼儿、青年至老者对相声传承与保护的广泛参与,这种参与正是市民自组织传承的选择。
自组织传承也有被组织的参与,就学校教育而言,天津市民从幼儿园至大学,都不缺乏接触相声的机会。一方面是政府通过开办学校、成立曲艺团等方式支持相声传承,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列入相声曲艺,如南开艺术小学、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天津艺术职业学院都有相声的教学;另一方面,孩子们也可以自由选择拜师学艺、参加各种曲艺竞赛。相声的普及和教育对相声的普遍接触最直接的一个成果反映在天津高校的社团中。大部分高校以及中高职专都有自己的相声社团,如南开大学国乐相声队、天津大学北洋相声队、天津财经大学博乐相声社、天津工业大学同乐相声社团、天津师范大学相声协会、北方曲校的春林社等。这些社团由学生自发组织,学习和表演相声,部分成员因为杰出的才艺而参与到能获取报酬的茶馆相声表演,甚至有的还拜师学艺并在毕业后以其为职业。其他中小学也有相声团体,它们是近年来天津相声艺术普及与复兴的明证,也是来天津相声在年轻市民中受喜爱和支持的表现。
父母积极支持小孩学习相声表演,大学生积极参与相声创作和表演并乐此不疲,这是天津相声能够在相声艺术发展不利的形势下逆势繁盛的思想基础,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称的“文化自觉”。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普遍困境就是缺乏年轻一代的参与,而天津市民自主、自愿参与相声的传播、传承与保护,为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也为其发展准备了后备力量。
(三)个案简评
纵观天津相声的发展之路,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参与程度和天津相声的发展直接相关,政府不管不问与过度参与都对其发展不利。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吸纳相声艺人进入文工团等政府组织的团体,从保证艺人生活与表演场地、建曲校帮助艺术传承等方面为相声传承提供支持,鼓励和要求相声的创作和革新等,因此相声能得到平稳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干预太多,艺人四散,相声的发展不仅停滞,而且是断层,传承静止。一旦政府不再过度干预,回归到自身应处的位置,积极参与,有力支持,相声就能够顺应自身发展的脉络健康发展。
近二十年来,政府等外部力量的参与包括从学校教育的发展上支持相声艺术的传承以及从宣传的角度与市场运行上支持各种赛事以扩大相声的影响等。相声是天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第一批项目,而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也是地方政府支持的结果。除此之外,在天津市政建设的整体规划上,把相声视为可开发利用的资源嵌入整个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战略中,也是作为外部力量与相声内部自身发展相结合的重要渠道,如2009年天津市推出的“津味相声风景线”中的谦益详茶社与已有近十年历史的名流茶馆等都与天津市的旅游项目结合在一起,为天津相声争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尽管目前天津相声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新相声段子的创作不尽如人意,茶馆相声容量有限等,但各方力量的汇集为相声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文化空间,而不是被动地成为历史,被存入博物馆。
四、余论
总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静态保护,即博物馆式保护,也就是对一些不符合现代生活需要、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式搜集、整理,保存在博物馆或“集成志书”;另一种是动态保护,即活态保护,也就是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存在的“生态场”,使其保持生命力,活在民间,传承下去。[7]以自组织理论观之,静态保护应以政府力量为主导和主体,而动态保护应以俗民为主体,以俗民自组织为基础。但是,由于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加速,俗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审美观已经或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传承、保护和发展的意识日渐式微,甚至消亡,因此,要想真正达至俗民自组织保护状态,需要一个较长的引导、培育过程。通过对天津相声传承与发展的自组织实践的探讨和分析,笔者认为,要想尽快建立以俗民自我保护为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组织保护机制,目前至少需要解决以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要唤醒俗民的自组织保护意识。当下,要通过加强教育引导、加强对传承人保护等措施,唤醒俗民特别是杰出传承人的自主、自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让其认识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关乎其个人,更是关乎我们的精神家园和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其次,要培育和发展俗民自组织保护的民间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在现代社会,民间组织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市场在保护的某些方面“失灵”的不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和中坚力量。因此,大力培育和发展俗民自组织保护的民间组织,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再次,要正确处理俗民自组织保护和政府被组织保护的关系。自组织的形成虽是自创生的过程,但仍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不可能是“无米之炊”。外部环境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等要素的输入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是要正确处理俗民自组织保护和政府被组织保护的关系问题。由于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仍处于初期阶段,俗民自组织保护意识不强,自组织保护能力和经验缺乏,因此依然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积极有力的支持。需要强调的是,政府支持的方式不是具体的包办替代,而是从宏观层面做好引导、指导、服务等工作,促进俗民自组织保护机制的形成。
[1]刘守华.“非遗”保护热潮中的困惑与思考[J].文化学刊,2009,(2):4-7.
[2]贺学君.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以江陵端午祭为例[J].民间文化论坛,2006,(1):67-75.
[3][德]H.哈肯.协同学[M].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29.
[4]田莉,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其文化史意义[J].中国文化研究,2003,春之卷:168-173.
[5]施爱东.郭德纲及其传统相声的“真”与“善”[J].清华大学学报,2007,(2):49.
[6]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6,(5):24-36.
[7]段宝林.保存与保护——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误区[J].上海工艺美术,2006,(4):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