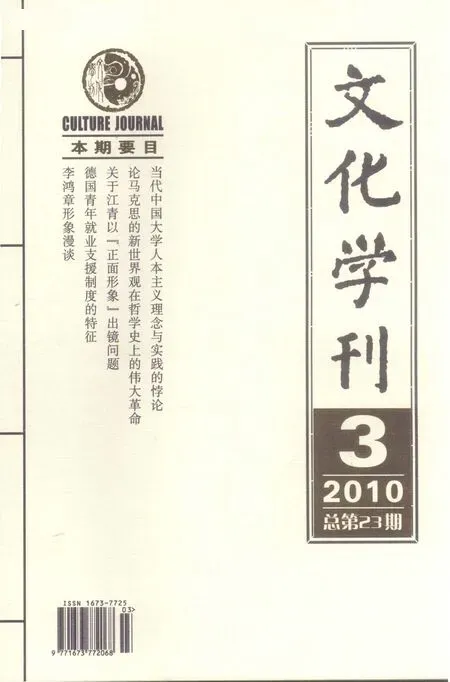东南士子与清代天津科举的昌盛
张 森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天津是元、明以来运河北端的新兴城市,文化、教育事业起步较晚,但进入清代以后,天津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迅速发展,逐渐兴盛起来。由《畿辅通志·选举表》统计可知,整个明代天津府只有进士83名,天津县进士10名,天津府举人322名,天津县25名;而到了清代其进士达到295名,其中天津县123名,天津府的举人数为1400多名,其中天津县为730多名。虽说苏州、杭州、福州等城市,文化底蕴深厚,在科甲及第的总体人数上要比天津多得多,但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天津科举及第数量增加之多、增幅之大也是这些文化古城望尘莫及的,在全国各个地区的科举发展史上也是罕有匹敌的。
天津科举的迅速增加不仅得益于经济、教育的飞速发展,而且也得益于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他们对进一步繁荣天津经济作出了贡献,同时在这些大量的外来人口中,有着高文化层次的也不占少数,这些文化水平高的士子为天津的科举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天津的这些外来人口,总体上讲,来自南方文化教育发达地区的人数较多。我们知道,宋元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已经移至南方,明清时期,虽然通过南北分卷和直省配额等项制度对南方进行限制,但东南士子在科场中依然独领风骚,在全国所占比重极大。例如,科举中的殿试考试,清代114名状元中东南三省(江苏、浙江、安徽)共有状元78名,为全国的68.4%,如果再加上福建和广东两省,几乎占据3/4强。不仅如此,东南地区还是许多文化的发源地,如乾嘉考据学派、清代小说等,都与这一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南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底蕴,由此可见一斑。
一、天津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是吸引东南士子流向此地的主要原因
天津距北京东南约120公里,是南北往来的必经之地,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其本身的移民文化更是吸引外地人来天津的重要原因。天津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城市,明初三卫的官籍名册显示,调守天津的官、军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来自南方省区的人口占官籍人口的绝大多数。309名军官的原籍分布在15个省份,其中原籍安徽省和江苏省的最多,占45%;其次是山东省和河北省,占30%。清代这一移民趋势发展更是迅猛,“津邑居民,自顺治以来,由各省迁来者,约十之八九”。康熙时,天津“军民商贾虽云杂沓,屈指版图,土著仅什之二犹歉”,移民竟占了当时天津城市居民的八成多。有学者统计了《天津县志》、《续天津县志》和《天津县新志》中记载的66名清初迁徙来天津者的原籍,发现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等南方地区的人超过一半,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明初移民以来自南方者居多的传统。[1]这样,伴随着南方及各地移民的迁入,南方以及各地的文化便开始传入天津。处于文化多元环境中,士子在此驻留并没有客居他乡之感。
再者,文化发达地区的士子,由于整体水平都较高,尤其每省乡试竞争异常激烈,较其他地区获取功名更为艰难,于是一些士子为减少阻力,不得不迁徙到其他较容易考中的地区。直隶省处于天子脚下,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和心理感受,非偏远地区可比,并且名额较多,竞争相对不太激烈。所以一些江南才华之士,纷纷迁居河北直隶。直隶京城是权贵之地,对于没有政治背景的士子无疑不是理想的居住之地,而作为畿辅喉襟之地的津门,因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风景比较秀丽,十里鱼盐酷似烟月扬州,创作的氛围比较宽松等原因,使得各省宦商晋京者、四方人士来游者接踵而至,进而带动了天津文化教育的繁荣与昌盛。
二、东南士子来天津后在文化教育领域中的表现
(一)东南士子及其后裔在天津的兴学助教活动
无论是科场的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经历了残酷的科场竞争,其思想意识中不免有对文化学习的紧迫感。客观来讲,越是文化发达地区的人们,文化意识和紧迫感越是强烈,对教育也就越是重视。这些人,不管因生计原因落户天津,还是因游玩滞留天津,他们大都不忘捐资兴学,执鞭任教,为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贡献。比如嘉庆戊午举京兆,壬戌成进士的陆樟,浙江山阴人,族祖某家于津,延课家塾,遂占籍饮泮食饩,从游甚盛。[2]再者康熙五十九年乡试,雍正元年成进士的王又朴,号介山,江南仪征人,6岁随父北迁,又朴入籍,补卫学生。出沈近思之门,朝考选庶吉士。[3]他倡建了天津的第一所书院——三取书院。而天津最大、最著名的问津书院,是由原籍浙江海城人——盐商查为义于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捐出废宅基地一块、用银2400余两建成的。
这些有着东南先进文化基因的人才,不仅积极创办义学和书院,而且还积极开展教学活动。叶绍本,浙江人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道光初年任长芦盐运使。他重文爱士,尤其擅长古文,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在书院讲授经古课,与阮元在南方倡建的学海堂相媲美。[4]再者,在问津书院北海堂任主讲的还有著名的学问家李慈铭,浙江绍兴人,曾经主讲过浙江蕺江书院,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举人,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得赐进士出身。光绪十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邀请其来天津主讲问津书院北海堂,还同时主讲三取书院。两年后,李慈铭回到北京,仍在北京寓所为问津及三取两书院出课题,然后评改两书院诸生卷,偶尔也为来北京的生徒评改试艺。天津著名诗人梅成栋,为江苏著名诗人朱岷的外孙,也算是半个南方人,嘉庆五年举于乡,晚岁家居创辅仁书院,招收学生80名入学,亲自执教十余年,从游者室至不能容,培养出了不少人材。由于这些主讲人大部分都是科名的获得者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从而使得天津教学的水平迅速提升到了全国最高水平。
(二)东南士子在天津的文化活动对天津文风潜移默化的影响
清代东南文人、士子聚集天津,他们由于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迎合了盐商附庸风雅的需要,受到一定的尊重,成为盐商私家园林的座上客。如康熙年间,全国著名的学士姜宸英(浙江慈溪人)、梅文鼎(安徽宣城人)、赵执信(山东淄博人)、朱彝尊(浙江嘉兴人)、方苞(安徽桐城人)等都曾到过张霖创办的著名文化园林——遂闲堂。他们在这里不但创作了大量的诗词,还与天津的文化人频繁接触,使天津文化颇极一时之盛,为天津的社会生活增加了新的内容。
到乾隆时朝,朝廷又开博学鸿词科,大江南北饱学才高之士乘舟赴京城者络绎不绝。天津正处于南北要冲,当时驰誉全国的一流文人学者杭世骏(浙江钱塘人)、汪沆(浙江钱塘人)、厉鹗(浙江钱塘人)、朱岷(江苏武进人)接踵而至,与久居天津的诗人、画家、书法家、鉴赏家胡捷(浙江绍兴人)、元弘(浙江绍兴人)等,都聚集查氏水西庄,一起吟诗作画,研讨学术。将南方的文化艺术带到天津,通过水西庄这个文化学术交流中心摄入吸收,把清代天津的文化发展推向高峰。
在此文风的影响下,天津本地人士与南北各地人士也成立了各种文化团体。仅以诗社为例:康熙年间,黄谦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草堂社,以诗饮誉津门的张霖、龙震等人都到大悲院聚会畅咏。同时,张霖还与刘文彬等人创立了近古社,以饱满的热情进行诗文创作,将唱和之作汇集为《近古社集》。查昌业与客津诗人王秋寻、陆慎斋在天津结成诗文社。乾嘉时期梅成栋在天津查氏水西庄故址创办了梅花诗社,招集诗界名流互相交流。同时,梅氏还与高继衍、崔旭等人创办“研庐诗社”,为天津诗坛的繁盛作出了贡献。[5]
不仅如此,天津还有许多眼界开阔、学识渊博的寄籍之人。他们或潜心修学,或游历四方。如程 ,浙江山阴人,16岁来天津,遂寓焉。……事母以孝著,不嗜荣利,有勉之就试者援笔立就,辞采甚伟,……不试而出,性倜傥,游历南北,好施济,不胜枚举。撰有《斑管录》70余种,《豹隐斋》诗文集若干卷,生平好施济,遇匮乏者,虽旅邸倾囊赠之。徐兰,绍兴人,以诗名吴越间,中年走长安王公贵人争延致之,间游天津,遂占籍焉,后卒于天津。刘文煊,浙江山阴人,乾隆丙辰举鸿博,性峭峻,交游皆名士,屡中副榜,年80余,卒于津。“康乾盛世”时代,天津经济欣欣向荣,吸引了许多“善词赋、好讲学”的流寓人才的迁入,这无疑对当地的文风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带动作用。“国朝由卫升州升府,邑属赤望沐浴圣化,涵濡最深,比年以来,户诗书而人礼让,隐然邹鲁之风”。[6]
(三)天津科举功名中具有东南籍血统的后裔士子
在天津众多的举人、进士中,不难发现很多祖先是东南籍人士。这些生活在文儒之乡的东南文士,由于直省配额制度和竞争的激烈,其优势表现并不突出,可是一旦他们迁居北方后,其后裔由于遗传的关系,在北方顺天乡试中往往出类拔萃,容易脱颖而出,折桂蟾宫。如李云楣,字采仙,道光五年举人,国子监算学助教。其祖李承鸿,原籍浙江山阴人,业盐来津,遂家焉,工诗好客,筑寓游园,城东有半舫轩、德月楼、枣香屋诸胜馆。吴景周,嘉庆由浙江钱塘迁天津,中嘉庆癸酉副榜,……子起元惠元振元皆由科甲出仕,遂引疾归,著有《强识择言》。这种带有南方人血统的天津士子很多,不仅一代科举得中,而且福泽绵长,门中下几代也竞出功名。杨光仪,其先世籍浙江义乌,后迁静海,自曾祖杨世安始迁天津,业盐致富,祖父为廪贡生,官主事,父亲为庠生,家中落,课读自给,光仪幼从父受书,……举咸丰二年乡试,选补东光县教谕,主讲辅仁书院。……子葆元,廪贡生,候选训导,葆中国子监生,孙鸿系受优贡生,农工商部主事。
南方人不仅把对科名的热爱之情传到北方,而且儒商的结合思想更进一步在北方得到发扬。例如天津的查氏,原籍浙江海城,是从第七十三世开始北迁的,到第七十八世查日乾时移居天津,经营盐业发了家。其子查为仁,才藻横飞,于康熙五十年举乡试第一。其孙善长,乾隆十八年举人,联捷进士。另一孙善和,善居积,重振家业,学问博雅,著有《东轩诗草集》。善和子诚,乾隆四十二年举人,官员外郎,积书满架、无不批览,然不事生产,家又中落,著有《天游阁诗稿》。查氏子孙有5人中举人,3人得进士,有十几人在朝廷为官,故各种官衔的服饰便成为水西庄服装的一道风景线。
天津最有名气的应该是津门的姚姓,原籍浙江余姚,乾隆年间为了躲避文字狱,先是来到河北省沧州,不久又迁居天津。姚家成为天津地方上的名门,始于始迁天津的姚逢年(公元1745年—1813年),《续天津县志》上说他:“幼具夙惠,四岁读《孝经》及《滕王阁序》诸古文,背诵如流。”曾于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乡试中举,两年后(公元1781年)又考中进士,外放河南、福建任知县。其子姚承恩(公元1796年—1851年),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乡试中举,道光十三年中进士。父子同为进士,所以在姚家大门洞悬挂有“世进士第”的横匾。其弟姚承丰,于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中恩科举人。姚学源(公元1843年—1915年),系姚承丰次子,为秀才。姚学源的长子姚彤章(公元1874年—1942年),为监生出身,曾在山东一带游宦。[7]其实,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中举士子大部分只是限定在迁居者的五代之内,如果寻根溯源,那么可以断定,出自南方拥有南方优越文化基因的天津中举士子还应该更多。如1882年通过顺天乡试,第二年得中进士并选入翰林院庶吉士的著名近代教育家严修,其远祖就是浙江慈溪人。
清代天津的文化教育与科举,由于东南士子的加入及南方发达地区文化思想的影响,获得了极大发展。如梅成栋在《文昌宫重修碑记》中写道:“每春秋两闱计偕赴都乡试多至数百人,会试不下数十人。”[8]这是天津科举事业昌盛的最好写照。
三、东南士子与冒籍问题
事实上,东南士子移居天津,有的进而参加顺天乡试,在推动天津科举兴盛的同时,必然会挤占天津本地人和先来天津定居者的科考名额。可以说,这种带有冒籍性质的现象,是当地人不愿见到的。按理推断,本地人和外来者必然会因为科名分配而发生激烈冲突,但事实并非如此。
虽然天津本地人的科举利益会受到江南等外地人的冲击,但由于天津本身的商业经济繁荣,人们谋生手段多元化,随之价值也多元化,并不把科举登进作为唯一出路,所以在天津科举繁荣的同时,本地人与外地人在科举方面的利益因此并没有发生激烈冲突,“天津皆用盐,盐为业,居则连甲第,出则联车骑,列鼎选妓,相竞为豪,故家子往往弃所业,为之握筹自效,冀获重利。诸生老于黉序者,求为之指书奔走,恐不得路也”。[9]天津科举在蓬勃发展时,也是天津经济快速繁荣时期,对科考功名的追求与经济利益的向往,各有自己的领域和信服人群,而且在商人向士子转化的同时,大量的士子也在向商人转化,这样,科举和经商在天津这块独特而宽松的土地和氛围中取得并行不悖、双向共赢的局面。可以说,这也是天津吸引外地人入住的魅力之一。
除了遍布城区的塾馆、义学、社学等正统儒学教育外,天津也出现了一些“屯学”、“运学”的行业学校,这是行业办学的发端,亦可谓中国最早的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教育事业。其书院教育,也增加了许多实用知识的学习,如为旅津子弟创办的集贤书院,于制艺、试帖外,还学习天文、算学、时务等科目。这种带有职业性质的教育淡化了人们非走科举之路的期望,起到分流缓解矛盾的作用。因此,天津的外籍人虽多,但并没有产生“攻冒籍”事件。由此可见,由于商业城市的特殊性,掩盖并消除了东南士子涌入天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突显了其对天津文化教育发展积极方面的影响。
四、天津科举昌盛的启示
(一)东南士子从元代开始,有一种向北流动的趋势,即文化发达地区向文化落后地区流动的趋势
东南士子经过南宋时期的培养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当时南宋的进士就有一种去贵州、广西等偏僻之地做官讲学的趋势。当元朝统一后,发源于南方的理学开始北传。明代迁都北京后,为学术思想和人才流动北迁提供了政治上的吸引力,大量的东南士子因为科举考试和从政的需要来到北方,从而使得这种趋势更加显著。而有着发达商业经济和优越地理环境的天津,成了这一趋势的浓缩点和显示器。在这片土地上,东南士子演绎着独特而又辉煌的文化再生产工作,为发展、繁荣相对落后地区的文化和平衡南北地区的文化差距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对文化教育有着无比的重视与热爱,是提高本地的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记述清代天津的史书中,经常可以发现,那些文化发达地区的东南移民通常文化水平较高,文化意识也较强,一旦他们落户天津,或者积极读书应试,或者是捐资兴学,为发展地区文化作出了许多贡献。比如:“郦世澍浙江会稽人,侨居天津,食贫励学,屡试不售,临终嘱子延本,以范文正义田事,妻陈氏备历艰辛,延本成立克乘父志,教授省衣节食,置本邑后补屯田民地二顷零五十八亩五分,遵遗命输义学为诸生膏火资,有司详请旌之。”宋朝贤相的兴学义举在浙江会稽人郦世澍这里得到传承,其临终嘱子捐田输资的慷慨悲歌也必将感动所有诸生、地方官员及民众,这种楷模式的善举,在推动本地文化教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三)要坚持文化的开放心态和多元发展观,吸引先进地区的人才
天津作为一个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的移民城市,在社会中最明显的反映是巨大的人口异质性,因此,必然产生各种异质文化的混杂与碰撞。在这个环境中,这些文化的混杂和碰撞,使得天津居民的开放意识、文化的多元化和生活的多样化得到充分体现。天津人眼界开阔,豁达大度,对外地人从不分此境彼界,不论来得早晚,也不论在天津居住时间长短,只要此时此刻共同生活在天津,就认作同一个群体,没有歧视,没有欺生,有的只是互相帮助和共同开发建设这块沃土。再者,天津为四达之地,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旅客,长期以来在天津川流不息,这使天津人更减少了对外地人的陌生感,并有较多发现其各自优点和长处的机会,从而容易与之相互交往,并产生与之相互交流的强烈欲望,而一旦尝到接纳外地人、包容外地人的益处,便越发重视对包容精神的奉行。正是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精神,使得移民一批批地相继迁入,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人才。
(四)需要注意的是,在引进人才时不忘培养本地区的文化名人,这是保持本地区文化教育发达之路
天津后来的科举兴盛不仅取决于东南人良好的遗传因素,还有天津优良的教育水平,这些优良的教育环境,使得东南士子后裔和久居天津的士人获得了极大发展。如前文提到的主讲辅仁书院的杨光仪先生,因他捐款补给膏火,维持书院正常教学,诸生莫不感泣,学习加倍努力。每年春秋两试,多中高第。如胡浚、陈石麟、王守恂、华瑞东、徐沅青、严范孙、高凌雯等天津大儒,都受业于他的门下。这些本地人的学术成就,无疑为天津日后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奠定了基础。
最后一点就是不要忽视本地的经济发展。经济的飞速发展会为教育、科举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同时,教育、科举出现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经济而得到缓解,这一点已在天津科举事业发展中得到明证。
[1] 陈卫民·天津的人口变迁[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95.
[2] 沈家本.光绪天津府志·卷四十三·人物[M] .天津:天津学生书局,1985年版.
[3] 新凌雯.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一·人物[M] .民国20年(1931年)刻本.
[4] (清)吴惠元.同治·续天津县志·卷十三·人物[M] .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刻本.
[5] 范丽珠.清代天津文化刍议[J] .天津社会科学,1988,(1).
[6] (清)吴廷华.天津县志·卷十八·人物志·流寓[M] .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刻本.
[7] 罗澎伟.天津的名门世家[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63—71.
[8] 天津文钞·文钞5[M] .
[9] (清)吴惠元.同治·续天津县志·卷十七·艺文二[M]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