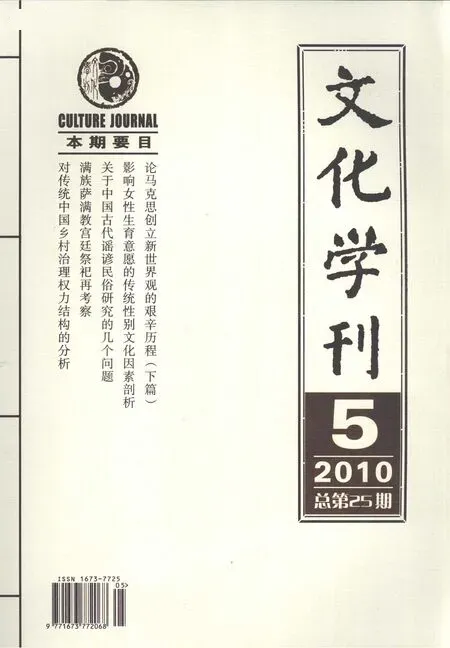略说辽宁文化的特点
张永芳
(宁波大红鹰学院,浙江 宁波 315175)
辽宁文化的本质是地域文化。所谓地域文化,是指发生在一定地域内的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关的特色文化。从这个意义讲,辽宁文化是中华整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了解辽宁文化,不仅对认识地域文化来说有重要意义,对于认识和评价中华整体文化也有重要意义。
辽宁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必然有自身的特点。当然,这些特点必然带有国家主体文化发展的共性,不一定是自身独有的特征,但其表现程度与表现方式必然有自身的特征。要真正认识某一地域文化,必须了解这些特点及其具体表现。
近年许多学者对辽宁文化的特点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它相对中华整体文化来说是一种亚文化,而历史性、民族性是其基本特征。这种说法当然正确,但比较笼统,应当作更细致、更具体的理解。归纳起来,辽宁文化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边缘性
边缘性指的是辽宁地域文化与中原地区所代表的中华主体文化既相对独立又密切相连的特殊关系,与辽宁的独特地理位置直接相关。
辽宁位于祖国东北,但又与中原地区紧紧毗邻,陆地同河北省和内蒙古接壤,隔海同山东省相望,自古以来驿路交通和水上交通都极为便利,与我国传统的文化中心并无阻隔。正因如此,辽宁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对于离中原地区稍远的吉林、黑龙江来说,要有利一些,在多数时期发展也稍快一些。其文化构成,也更加容易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较早开化。如清代的学府与文人团体,都是辽宁设立在前,吉林、黑龙江尾随其后。东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也大多在辽宁,如辽阳、朝阳(上京、黄龙府)和沈阳(奉天、盛京),都曾是管理东北全境的军政重镇,只有渤海国、满洲国的首都设在吉林省境内。也正因如此,把握辽宁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理清边地与内地的领属体制,是理解辽宁文化演进的主线。概括地说,辽宁的政权建制由方国到郡县 (州县、府县),由“依俗而治”的多头体制到行省府县的单一建制,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而与中原政权由从属到对峙,及至攻灭、取代,由偏安一隅的少数民族政权到成为统一天下的多民族政权,更反映出社会变动的严酷事实,毋庸置疑地说明中华民族大家庭历来是多民族的共同体,说明中华古国历来是内地与边地的统一体。辽宁虽属边地,却与内地密不可分;北方少数民族虽然曾与中原汉族争斗、对峙甚至征伐杀戮,却是血肉相连的同胞亲人。这种文化血脉上的关联性,是认识辽宁文化特质时首先应注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辽宁文化始终只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绝不能离开其文化母体。
文化是由人来创造的,所以人是文化承载的主体。地域文化的边缘性,与相邻地区的人口流动密切相关。没有人口的流动,就不会有不同地域文化的冲突与互补,也就不会有主体文化与边地文化的区别。辽宁地区在历史上有多次人口大迁移,如商周交替之际、秦汉交替之际、汉末大动乱时期、唐末五代时期等等,都发生过人口的大批流动。主要是更北方的少数民族南迁,关内的汉族北迁,也有当地人口被大批驱赶入关,如曹魏时期司马懿就曾强令30余万辽东人众迁入中原,再如三燕时期大批辽东人、渤海人被迁往辽西和幽州,这必然会引起不同地域文化的冲撞与交融,对中原内地文化与辽宁边地文化都有深刻影响。在人口流动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三类人,一是被迫迁移的职务人口,如边境的戍卒和修筑边防工程的劳工,内地最早进入辽宁的人口,正是这类人员及其家属;再如清代被征调入关的旗丁及其家眷,即满族、达斡尔、锡伯等少数民族的职务移民,对中原地区乃至南部边疆、西部边疆都有不可忽视的文化影响;二是被谪贬流放的囚犯及其家属,即所谓的流人,主要是从中心文化区流放到当时比较蛮荒的边缘地区。他们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产生了所谓流人文化现象,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第三类人是真正的外来人口,即外来政权和外国人士,如古代高句丽就多次占领过辽宁的土地,近现代时期的俄罗斯人与日本人,更使辽宁深受侵略之害,但作为历史后果之一,其在文化方面的影响也不容置疑。辽宁之所以有今天的面貌,辽宁文化之所以有如今的样态,与以上三类人口的流动密不可分。
边缘性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不同质文化的紧密接触与互补、交融。因地理毗邻,不同质文化相互碰撞时,总是最先体现在边缘地区;而因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必然会有所不同,两相接触,自然会形成互补或交融的趋势。但是,无论多么频繁的接触,也无法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完全一致,总还会有相对的差别,这也正是地域文化的特性之一。
二、差异性
差异性指某一地域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或其他地域文化的不同。就地域来说,本身的文化基础是在本地形成的,即具有原生性;就国家或其他地域来说,某一特定的地域文化既与自身并存,又可丰富自身,即具有互补性。正因各地域文化丰富多彩,国家的总体文化才缤纷绚烂。
辽宁这块土地,几十万年前就有原始居民,其创造的红山文化甚至远比中原地区先行,被称作中华文明的灿烂曙光。甚至有学者断言:“它标志着中华文明正在这里发生。”[1]因而,“牛河梁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和它的‘母体’辽河流域,就是东北地区文化的源头,同时又是东北地区华夏——汉文化的发源地”。[2]因而辽宁文化的原生性,不只与地域文化有关,也与中华整体文化有关。
当然,因为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辽宁文化在发展层次上往往落后于中原地区,这就形成了文化“落差”,这正是辽宁地域文化差异性属性的核心。这种落差,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生产方式的差别。中原地区很早就进入农耕文化、工商文化为主的社会形态,辽宁则始终是渔猎生产、游牧生产与农耕生产、工商生产并存的状态。直至近现代,辽宁的交通、工商才居于全国前列;二是政治体制的差别。中原地区很早就进入大一统的王朝,辽宁则直至清代末期才废弛双轨制,即以部族制(八旗制)治理少数民族、州县制治理汉族的体制,进入行省(府县)制的单一体制;三是文化教育上。无论在普及程度与受教水平上,辽宁在很长时间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故内地流人对辽宁地方文化发展的贡献十分重要,直至近现代辽宁的教育水平才迅速得到提高,以至能同内地抗衡。其他如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民风民俗、生活习惯等等的差异,更是十分明显,以至有“关东三大怪”(糊窗纸朝外、大姑娘叼着大烟袋、生下孩子吊起来)等民谣,反映内地民众对辽宁(关外、东北)地方风物的诧异、陌生之感。但也正是这些明显的差异,保留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如找人参、伐林木的生产仪礼,玩嘎拉哈(羊拐)、荡秋千等民俗游戏,都穿过历史的迷雾,传承到今天。所以,不能因有一定的文化落差而轻视地域文化的独特性。
可以说,任何一种独特的文化,都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这种与中心文化、主体文化的差异性,恰恰是地域文化、边缘文化的特殊价值。换言之,差别性体现了我国文化的丰富性,各地的特色文化大大补充了、丰富了中原地区的主体文化。
三、多样性
多样性主要不是强调地域文化与主体文化的差异,而是强调它自身的丰富性,即不论从纵向来看还是从横向对比来看,辽宁这地方从来没有一种文化定于一尊,而是多种文化类型并存,以其丰富多姿展示于世间。
文化的多样性,可从多角度观察。如从生产方式的演进看,渔猎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曾经长期并存,即在辽宁这片土地上,辽东平原主要是农耕区,辽西草原主要是游牧区,而在山区和水边(辽河、大凌河、鸭绿江三大水系及沿海)主要是渔猎区,多种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社会结构长期并立共存,造成多种文化类型并立,形成多种特色鲜明的生产生活技能和习惯。晒盐业、采参业、马具产业等特色经济的传承,也与之有关。从民族看,众多北方少数民族不仅先后兴起,而且长期共存,在每一个历史时期辽宁都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区域,这自然使辽宁的地域文化保存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分。可以说,从古至今,辽宁始终不是单一民族的统治地区,也从未曾有单一民族的文化一统独尊。即使单从汉族文化来看,因为居民成分的复杂,其文化类型也并不单纯,主要有山东代表的齐鲁文化、河北代表的燕赵文化以及山西代表的晋文化几大部分。近现代则因海运发展使福建移民大大增加,八闽文化也随之引入辽宁,因汉族的乡土观念较重,使各地的文化特征在辽宁得以长期并存,各地方的会馆、同乡会是维系这些在辽宁扎根的非原生的地域文化的重要方式。从历史进程来看,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直至现代工商业,新的文化类型层出不穷,旧的文化类型却不会完全消失,往往既累积叠压,又历时共存。如玉器的制作,自古以来一直是辽宁的特色产业,玉文化的传承历久弥新。有关研究者早已指出,“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历来为人们所喜爱。中国玉文化历史极为悠久。早在数万年以前,生活在辽东半岛的先人,就已使用玉料制作工具,并在新石器时代形成以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和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北南两大玉器原生地,而辽西红山文化的时代早于良渚文化,是史前的玉文化的中心之一”。[3]尔后各个朝代的玉器制作,都传承着远古文化,又有新的时代特征。这种不断的变化也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是使国家整体文化形态保持鲜活的根本动因,显示出人类文化的无限丰富性。而且越是特色鲜明的文化类型,越有普遍的价值,对于主体文化甚至人类文化才能有更大的互补意义。
四、趋同性
广义的文化趋同性,是指人类文化的总体的发展方向大致相同,如由农牧生活向城市生活过渡,由石器时代向金属时代过渡等等,即“一种文化变化的过程。指不相邻地区诸文化的不同文化特征未经实际接触而在一段时间内逐渐向相同方向发展直至变为相同或几乎相同的无中介共向变化现象”。[4]这里所说的趋同性,是指地域文化向主体文化的靠拢与归顺,即越来越受主体文化的影响,与主体文化渐趋一致。
严格说来,主体文化固然接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地域文化必然更受到主体文化的影响。相对说来,主体文化之所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其代表的生产力更加发达,生活方式更加精致,思想内涵更加丰富,精神世界更加完美,受众也数量更多。既有发展层次上的优势,更有人口数量上的优势,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文化“落差”,这种落差,造成强势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使得弱势文化逐渐向其靠近,以至不同的文化特质逐渐趋于统一。从历史发展看,辽宁文化在远古曾经领先于中原文化,如红山文化曾处于领跑地位,殷商时期便开始并存和归属中心文化了。尔后中国多数时间是大一统的汉族王朝,但在很长时期内,辽宁的少数民族十分强悍,往往建立自身的民族政权,不仅能同中原地区的汉族中央政权相抗衡,甚至能攻灭之、取代之,如三燕、大辽、金、清等朝代。元代蒙古族虽非从辽宁起兵,也是先占据辽宁后攻灭中原政权的。但是,在文化上,中原地区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文化趋同的步伐始终未曾停滞。即使在攻灭中原汉族政权的时期,如金代、元代、清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却日益汉化,推行的主要是汉文化,甚至连官方语言文字也是汉语汉字,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逐渐被冷落和废弃,本民族的制度、礼仪甚至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也趋于汉化,乃至失去本民族特征,融入汉族大家庭。
中原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一,大一统的文化观念上,即从古便认为天下是一家。中国居天下的中央,中原内地则是国家的中心地区,只有建立多民族的大一统帝国,才符合正统,这是维系民族团结和中央政府权威的强大力量;其二,以儒家学说为主的正统思想,其影响不仅限于中原内地和辽宁等地域,早已达于中国全境乃至亚洲多国;其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其四,较为先进的农业和建筑业、手工业等生产技艺;其五,佛教。另外,因使用人口众多,汉语汉字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各种少数的语言文字。这些中原地区的文化优势,至今仍是中华文化强大凝聚力的由来,是各地区域文化具有很强一致性的原因。辽宁地方文化正是深受中原主体文化的影响,才具有了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才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有研究者断言:“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类似于辽宁地域文化这样的各边缘地区的子文化对于中原华夏母体文化始终保持着稳定而强烈的向心力和趋附性。华夏母体文化的巨大的核心凝聚力量,使它成为各地域文化的共同的精神轴心。”[5]
不过,趋同性与多样性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文化属性,两者不可偏废。有关学者早有共识:“总之,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是:一方面,文化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另一方面,文化的分化愈来愈复杂多样;一方面,文化联系的规模、程度和深度愈来愈扩展,另一方面文化的分化也愈来愈精细、复杂、多样化……正是从文化发展的多元相对化、多样化、复杂化的总趋势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人类文化的丰富、兴旺和无限活力。”[6]
五、交融性
交融性也叫开放性或兼容性,也就是一种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包容程度。中华文化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虽有乡土性,其居民很重视自己生活的地域和传统文化,更有开放和兼容的气度。“中华文化能够兼收并蓄,这不但指诸子百家在争鸣中能够取长补短、相互融会,也指汉民族文化能够长期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更指对外来文化也能敞开它博大的胸怀,有扬有弃地吸收、整合……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7]这里要强调的是,趋同性偏重的是区域文化向中心文化的靠拢,交融性偏重的是区域文化的内部整合以及对外部文化的吸收。
交融性首先是内部多种文化类型的整合,如不同生产方式的并存,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等等。辽宁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民族均以自身的特色文化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许多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如辽代、元代、清代,均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其文化传承自有汉族所没有的成分;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也极大地丰富了东北地区的生态文化,如睡暖炕、食火锅、玩羊拐、荡秋千、挂摇篮、跳大神等,都是汉族本来没有的习俗,尔后才逐渐成为辽宁地方的特色民俗,为各个民族所共有。移民文化对辽宁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是这种内部整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有学者指出:“这种移民现象对于辽宁地区历史文化的沉淀影响,至今仍潜移默化地表现在辽宁地域文化的表象特征中。辽宁是中国的一个移民比例很高的省份。今天的辽宁地域文化并不是孤立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带有周边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某些特征,是一种后起的,混合型的文化形态。”[8]
交融性的另一方面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汇。在古代来说,主要是对高句丽文化的接受,近现代主要是受俄罗斯、日本等外来侵略的影响。辽宁在近现代时期不仅同全国一样,门户被迫开放,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更直接成为外来侵略者相互搏杀的战场,成为日本铁蹄蹂躏的殖民地。可以说:“辽宁人民在这段历史上所受到的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之深,时间之长,精神上心灵上所遭受的摧残之惨痛,都是国内其他地区的人所不曾有过的,这些无疑都深刻地影响着辽宁地域文化的发展轨迹。”[9]这一方面激起辽宁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反抗斗志,更加自觉地珍爱和传承自身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接受了现代的思想观念、现代的生产方式与文化教育,在社会现代化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东北(包括辽宁)之所以能在解放战争中成为主战场,成为大后方,成为全国最早解放的地区,成为支援全国解放的重要基地,与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前列地位直接相关。而这,又与其较多较早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
交融性的又一重要方面,是历史的传承性,即历史上曾经有过各种文化的迭兴与积淀。也就是说,辽宁文化不仅是横向的空间的交融产物,也是纵向的历时性的文化积淀。“辽宁地域始终延续的主体精神,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继承性。这种文化的继承性要远大于它的独创性,这是认识辽宁地域文化的一个历史基点。”[10]如辽宁现在是中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而行省制的由来,则经过数千年的变迁,是一个长期的渐变过程。再如省内有数个自治县,即新宾满族自治县、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等,又何尝不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依俗而治”,给少数民族一定自治权的“双轨”制治理模式的延续呢?区域文化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改变,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消失,它的发展只能是连续的渐变过程,是长期的积累过程。
六、曲折性
曲折性是指文化发展的非直线性,即文化的发展不是简单、顺利、平稳的过程,而是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复杂的、坎坷的、有盛有衰的曲折过程。恩格斯指出:“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11]
曲折性首先表现在辽宁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中地位的变化,即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较,发展程度是领先还是落后,对整体文化的影响力是较强还是较弱。众所周知,辽宁文化不只有原发性,而且有早发性,一度领先于中原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地之一。再如青铜器的铸造,辽宁地区约略与中原同时起步,但又有与中原青铜器不同的风格,“青铜种类之多,造型之丰富,用途之广,比之中原地区,毫不逊色,堪称是华夏青铜器制造中心之一”。[12]这以后,其文明的进程始终与中原地区密切相关,但大体说来稍稍滞后,如铁器的使用与冶炼、火药兵器的使用与制造等等,都滞后于中原地区。但也有时因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如辽金时期,比中原地区更为繁华,虽然在社会形态上未必居前。近现代则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其资源、交通、工商、文教等方面的优势,又重新走在全国文明进程的前列。由此可见,辽宁文化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却从未停滞不前,是不断进步的文化,是富有活力的文化。
曲折性更表现在多种文化的历时性积累与共时性并存上,即任何一种文化形态本质上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也不会简单地在现实中消逝。如古代的玉器可能没有后世的玉器精美,但那种朴拙样式和特殊的象征意义却是不可复现的,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传世价值。再如不同的民族服饰,很难说谁美谁不美,自有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和实用价值。再如“依俗而治”的多头管理体制似乎比较落后,不如单一制的政治体制进步,但大辽的南北官制度、部族制,金代的猛安、谋客制,与清代的八旗制、盟旗制,都曾与六部制和州县制并立过,与当今的“区域自治”制也不能说毫无关联。历史为什么会反复重复,这其中难道没有一点可以追寻的借鉴吗?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但不是凭空改变,而有着很强的受制性,即人类的活动有积累性和延续性,人们创造文化成果,却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成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得它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3]这就是说,文化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如何变化却并不完全受人类控制,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反复性。
以上各点就是辽宁文化的主要特征。其形成主要有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民族成分、移民状况、政治体制、文化累积等要素,是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
[1][2][12]李治亭.东北通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30.33.39.
[3]张锡林.辽宁历史文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21.
[4]冯天瑜.中华文化辞典[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5.
[5][8][9][10]白长青.论辽宁地域的多元结构[A].白长青,等.辽宁地域文化发展战略研究[C].沈阳:辽宁社会科学院,2002.22.
[6]李德顺.“文化趋同”的神话与现实[A].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价值与文化[C].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91.
[7]辜堪生.中国传统文化概论[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205.
[11]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C].507.
[13]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