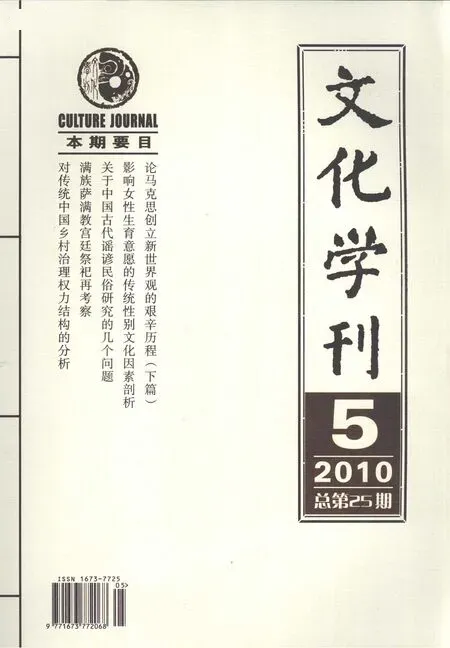学术文摘
“非遗”保护:应避免认识的片面性
安葵在《文化遗产》2010年第1期撰文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复杂工程,既具有学术意义,又与社会生活有密切联系;包含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因此要避免认识的片面性,不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狭隘化,不要把民间文化与文人文化对立起来,不要把保护传统文化与文化创新、社会生活现代化对立起来,不要把保护与利用对立起来。
被遗忘的辫发史:华夏先民也曾有一段辫发史
朱笛在《东南文化》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通过如上论述可以肯定,尽管辫发被长期视为夷狄发式,但华夏先民也曾有一段辫发史,当时的辫发与宋元以后的辫发有本质的不同,不带任何征服和强迫的性质。当礼制成熟后,束发加冠逐渐取代了辫发,故史料中少有关于华夏先民辫发史的记载,所幸在人们的生活中仍遗留辫发的痕迹,帮助后人追溯。不过,华夏先民也曾有辫发这一事实,也许会让后来在为捍卫头发而在“留发不留头”剃发令下舍生取义的悲壮之士始料未及。
发展伦理的使命是解决人的生存的问题
马宁、黄瑞雄在《江汉论坛》2010年第3期撰文指出:发展伦理的出场在于人们期望用伦理或道德的力量破解发展困境和发展危机的难题。“伦理道德的根基在于它首先是人的现实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实践方式之一,而不是仅仅是生于观念中的东西;因为它必然与人的生存发展实践相联系,并由人的生存发展实践强有力地创生出来。”作为对现代化发展进行反思的必然产物,发展伦理解答发展中的三大基本道德问题:一是“人类在有限而脆弱的地球应当如何生活”的问题,亦即“能够做”与“应当做”的关系问题;二是“我们应当如何共同生活”的问题,亦即发展中的公平公正问题;三是“人们应当如何幸福生活”的问题,亦即发展中生活美好与物品丰裕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及解决,为人类活动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引领。
复制:创新的起点
潘智彪、李丹媛在《学术界》2010年第3期撰文指出:复制事实上是一个动态的创造过程,它寓“变”于“不变”之中,是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对原作所进行的一次深入、全面的挖掘和再现。对于戏剧、舞蹈等艺术,他们的复制事实上也是一次表演;对于文学作品、绘画作品等,他们的复制是增加一次被阅读的机会,是提供给欣赏者一次接近原作的机会;对于雕刻、陶瓷作品,他们的复制是某种程度上的重新创作……换句话说,不同的复制品包含了原作不同的感性要素,它正是通过对感性显现加以选择和发挥,使原作的意义得以不断深化的一个升华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复制正是创新的起点,在复制的宏观不变的整体呈现之中,实际上经由复制者主体的情感渗透和主观选择,已蕴涵着深刻的创新的因子。
正视一个模糊身份的真实存在
何希凡在《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撰文指出,作为一种以文学的名义凸现于世纪之交的青春文化现象,“80后”在人们的众说纷纭中已历时十年左右。但时至今日,不论是文学界还是学术界,不论是肯定“80后”还是否定“80后”的人们,乃至被人为圈定在“80后”命名中的青年写手们自己,都强烈地感到这个命名的笼统性、模糊性甚至是粗暴性。质疑、指责、调侃、反拨这个模糊命名的声音可谓此起彼伏,但又始终未能诞生一个无懈可击的科学命名。因此,就正名意义而言,“80后”的身份至今仍是模糊不清的。正名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化,并形成足以涵盖其本质特征的概念命名过程,但社会文化急剧转型后的中国文学容不得我们等到正名的问题彻底解决之后,才去关注和阐释那些逼到我们眼前而不可小觑的文学现象。我们的正名工作理应在正视和探讨这些鲜活存在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完成,不能因为某些文学现象和写作群体身份的模糊而无视它的真实存在。
很多研究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影响“80后”写作及其“崛起”的几个重要的现实性因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激发、市场经济的推动、适应广大学生的需要。在这几个现实性因素中,人们又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市场的推动和商业效应。这样的定位无疑是切中要害的,很多研究者的具体分析也是至为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然而,这些不乏学理性的定位却引起了“80后”写手们的一再反弹,甚至导致了纯粹意气层面上的人身攻击。这种反弹无疑蕴含着有些曾被市场和传媒炒得太热的青年写手们心理上的浮躁和人生阅历上的稚嫩,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正常的文学对话的不屑,对曾经承载着人们过多憧憬和崇仰的文坛的鄙薄,但我认为也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我们的评论和研究与他们的真实存在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错位。
中国国民文化特性的分析模式
秦德君在《学术界》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对于中国国民品性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分析,辜鸿铭注重从中国人的精神特质与中国文明价值的结合点上以及中西文化之间的对应、相鉴中展开,这使他的分析具有突出的特点。辜鸿铭指出:要估价一个文明,不在于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壮丽的建筑和宽广平坦的马路;也不在于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出漂亮舒适的家具、精致实用的工具、器具和仪器,甚至不在于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而在于必须问,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这才是“文明的灵魂”。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核心价值的对接思路
辛秋水在《学术界》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温情脉脉”的文化,具有“阴柔性”,以“仁”“义”“礼”为交际原则,讲究人情,注重面子,是一种道德本位的德行文化。儒家思想统治着中国的古代社会,它排斥法治,主张德治,再加上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一直奉行的是人治原则,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法治缺位,不过这并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思想就没有参考价值,因为:①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早就存在“法治”观念,战国时期韩非子的思想也一直蕴藏在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中。以“法”“术””势”为手段的法制观也被统治者采纳过,虽然由于集权统治淹没了法治,但是传统文化中的法典法仪也可以为现代文明提供借鉴。②法治本身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社会的复杂性让我们看到法治的不足之处,如果需要构建一个真正的文明社会,中国传统社会道德价值观就是参考范例。
集体主义公正性原则的落实与维护:道德赏罚
马永庆、肖霞在《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2期撰文指出:集体主义公正性的落实,还需要建立健全道德赏罚机制。道德赏罚是增强集体主义外在道德动力的一剂良药,是有效地解决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的重要手段。马克思认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道德赏罚正是基于人之趋利避害的本性,以利益为杠杆,通过对道德的行为予以奖赏,对不道德的行为予以惩罚,使人们在一定道德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道德心理、道德情感,最终实现对人们行为的调节。其实质是在不公正的利益分配面前,恢复利益分配应有的公正。当今社会,人们在价值观的确立上面临着诸多困惑,道德赏罚正是帮助人们明辨是非、区分善恶的有力武器,有利于对维护和破坏集体利益的行为作出明确的奖惩,以一种实实在在的方式来树立集体主义的权威,加重人们践行集体主义的砝码。
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的“本土”建构
张其学、姜海龙在《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撰文指出:身份主体是文化殖民化与非殖民化争夺的主要领域。如今,身份已日益意识形态化了,以意识形态化的身份认同观看文化身份,就不可避免地把文化人种化,认为一个种族一种文化,种族决定文化,人种间的差别决定精神、能力和习俗等的差别,并把这一差别绝对化,对混血现象加以排斥,反对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混合,表现出对玷污的焦虑,害怕失去血统的纯洁性,从而强调身份的纯粹性和同质性。这正是文化殖民在身份主体上的逻辑。实际上,身份不是静态的,而是构成性和流动性的。针对西方对东方民族文化的“妖魔化”,我们认为重建东方民族的文化身份是文化非殖民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但这种重建并不是“本土主义”的重建,不是基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之上的重建。这些所谓的重建仍然是二元对立、本质主义身份认同观的体现,我们要强调的是东方民族文化身份的“本土”建构。
建构自觉信念体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网络文化
杨立英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3期撰文指出:在网络文化的多样性价值环境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实现对复杂多样的社会思潮与价值观的有效引领,除了确立广大网络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性认知与认同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确立起其信念体系,即要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向网络受众自觉的价值信念体系转化。在网络文化多样性价值并存的环境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发挥对其他价值观的统摄力与整合力,塑造广大网络受众的价值信念体系。为此,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性,能够超越体系外知识与价值系统的逻辑障碍,具有整合体系外优秀理论知识的强大逻辑力量,从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微传播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
何国平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10年第4期撰文指出:以美国的Twitter和中国的饭否、新浪微博、腾讯滔滔为代表的开放式社交服务平台所汇聚的微博体现微传播个性的首要特点即“微”。微构成微传播的核心特征即发布者去中心化和内容碎片化。“微”是微传播的核心特征,即传播的内容是“微内容”:一句话、一张图片等;传播体验是“微动作”:简单的鼠标点击就能完成选择、评价、投票等功能;传播渠道是“微介质”:手机等;传播对象是“微受众”:网络社群。基于技术创新而又暗合时代需求的微传播,从交往方式到行为习惯、从社会民生到公共管理,具体而微地改变现实世界的信息呈现与使用者的思维。此处将这种改变分为机遇和挑战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