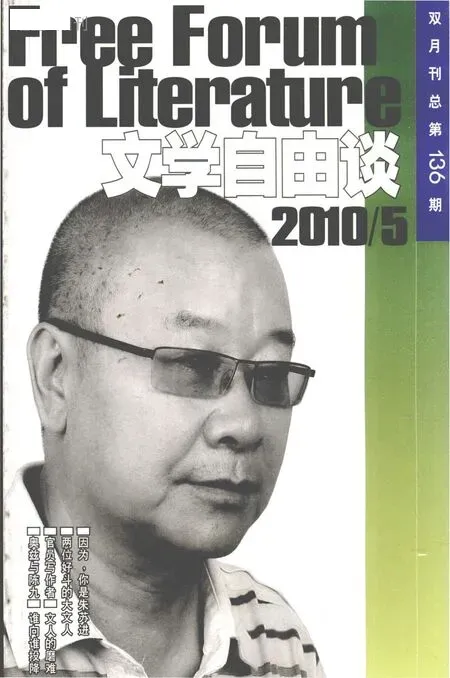因为,你是朱苏进
●文 李美皆
“只要精彩,你骂我爹都行。”从手机报上看到这句话,我还以为是冯小刚说的。再看下面内容:新《三国》开播后,编剧朱苏进发现自己被网友封为“中国编剧界的凤姐”。现在,寻找“骂得精彩”的帖子,是朱苏进一大乐趣。
是“乐趣”还是刺激?外人没法说,但见朱苏进变得如此慷慨,如此大方,如此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简直是“不过了”!
没几天,又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关于《三国》的报道,包括朱苏进自己的讲话,全是正面的了。是不是借助《南方周末》这样的精英媒体来树立《三国》及朱苏进的正面形象,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看出,朱苏进还是要“过”的。
嗣后从网上知道,手机报上的内容来自《中国周刊》记者的采访。这是一个很有水平的采访,记者功课做得很足,从各个向度含蓄巧妙地推出了一个潇洒又尴尬的复杂矛盾的朱苏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朱苏进在尚属主流的军旅文坛已是一位“知名”作家,有着自己的风格和精气神。他的《射天狼》至今在书店里卖得“还行”,由《三国》电视剧“改编”的同名小说倒是卖得“一般”。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朱苏进成了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的编剧。他说:“我那时候瞧不起影视,但我非常敬仰谢晋。”他想浅尝辄止,结果却整个被吸进去了。他的创作走向从此就拐了,再没回到小说上来。因为他发现,一部电影得到的钱,比他所有小说的稿费要高得多。九十年代曾经有过一阵文坛下海潮,下海的契机和方式各有不同,据说,有位作家因为一次桑拿就改变了人生观,当场决定下海。编剧,是朱苏进的下海契机和方式。“我觉得这个影视剧毫无价值。但这个价格,是我以前做的很多自认为很有价值的事情所得不到的。这个咋办呢?兄弟。”在“价格”面前,朱苏进很无奈。
2001年,朱苏进改编了二月河的《康熙王朝》,这是他的电视剧处女作。朱苏进是一个骄傲的作家,对于二月河的原著,他的反应是,“还以为是盗版”,言下之意当然是不屑。《康熙王朝》的走红使朱苏进成为“金牌编剧”,又在电视剧领域一发不可收。据传,电视剧投资人像狗仔队一样追逐着朱苏进,为了得到他的剧本,绞尽脑汁,出尽奇招:比如,把他安排到东北深山老林的别墅里;比如,从讨他女儿的欢心入手。据传,朱苏进写剧本时桌子上垒着墙砖似的人民币,没动力了就抬头看一眼,或抬手摸一把。据传,朱苏进已经成立了工作室,拥有一个写作班子,同时也为找不到满意的写手而苦恼,每每还要自己动手,对写手的“货”进行再加工。
作为军旅作家的朱苏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英雄主义者,骨子里有着军人的基因,他说:“我就是个男军人和女军人生出来的杂种。”——朱苏进的语言从来都像子弹一样狠而且准,对自己也不例外。“他赞美强者的竞争,他崇尚阳刚之气,歌颂胆略和勇敢,对于非战争年代军人的尴尬感同身受。他的故事里没有温良恭俭让,场景常常是斗兽场般的死寂而暗藏杀机。那些有着超人智慧的主角们在山穷水尽的绝境中斗智斗勇,又在绝顶的孤独中一路沉沦。朱苏进说,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精神自传。”这是记者报道中的一段文字,对于作为军旅作家的朱苏进是一个很好的概括。
可是,为什么不再写小说而写起剧本呢?朱苏进避开锋芒,答曰:“是两种不同的情怀。”“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写小说是一对一。读者永远只有一个,一个人写给另外一个人看。……影视是一个群体做给另外一个群体看,本质上造成了欣赏素质的平均化。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寻找的是知音,不是读者。而电视剧寻找的是观众。”既然是两种不同的情怀,小说的情怀是英雄主义,是“绝顶的孤独”,那么,电视剧的情怀是什么呢?从朱苏进的比方来看,应该就是“绝顶的不孤独”,就是“与民同乐”,就是泯然众人矣。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已经强调了大半个世纪,作家们的努力却仍不理想,还是朱苏进有水平,用小说和剧本分头完成了提高和普及,加起来不就是既普及又提高吗?一谈到电视剧,朱苏进就含蓄起来,只说“电视剧寻找的是观众”,不说观众意味着什么,还要让别人替他说:观众意味着收视率,收视率意味着钱。那么,说到底,电视剧寻找的就是钱。小说寻找知音,满足的是精神欲求;电视剧寻找观众,满足的是物质欲求。加起来,也算两手都抓两手都硬了。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省略:朱苏进的电视剧还有没有英雄主义情怀?当然是有的,否则它便不是“朱苏进制造”了,朱苏进在电视剧领域胜出的关键就在于英雄主义。如果说写小说的朱苏进是一个怀抱英雄主义的失落者,就像一个学会屠龙术却找不到龙来屠的悲士,写电视剧的朱苏进则是一个终于成功地把英雄主义兜售出去的巨贾。比如在《三国》中,他说:“这才叫军人。无数的理由会说服你执行命令活下去,但拒绝来自于你天性中的固执。”他把“伟大的拒绝”的基因放入《三国》,便是陈宫拒绝曹操的释放,那是《三国》里的一个催泪弹。朱苏进的英雄主义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使用价值,那就是做催泪弹。虽然英雄主义的卖家成功地找到了等待煽情的买家,但此种英雄主义却总让人感觉不那么地道,说“疑似英雄主义”也许更恰当。“疑似英雄主义”是为电视剧量身定做的,产品优势就在于做催泪弹正好。其“疑似”首先就在于,连朱苏进本人都做不到所谓“伟大的拒绝”,面对电视剧的“价格”,他是何等的无奈,何等的软弱无力!不要说面对生死存亡的更大的考验!朱苏进不过是在贩卖悲壮,不过是在“曲线救国”:以英雄主义为桥,抵达拜金主义。当然,这是一条比较高雅的捷径。即便俗,也不是一般的俗法,也要俗得雅一点。——因为,他是朱苏进。光凭这一点,朱苏进也值得降半旗致敬了。应该承认,有点英雄主义的精神底子还是占优势,不管怎么个意思,“前英雄主义者”表达起来总比别人悲壮。
朱苏进“电视剧版的英雄主义”不令我崇拜的另一原因在于,他喜欢把英雄主义的宝押在帝王身上,他的帝王戏在反复说明一点:英雄出在帝王家。他几乎自创了一个封建世袭帝制可以造就英雄王者的历史规律,那么,对比之下,大相径庭的现代民主岂不就显得多余和可疑?还有,朱苏进的帝王简直都是劳模,朱苏进的帝王戏就是在表彰顶级劳模,那么,劳动人民上哪去诉说苦难和委屈呢?
朱苏进自己认为,《三国》里有军人的基因。其中主公与谋臣的关系被他重新诠释,充满军中独有的微妙和玄机。他欣赏下级对上级的那种感情:我服从于你,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你。他把诸葛亮对刘备也划入这种关系。“诸葛亮有句台词:与其寻找主公,不如为自己创造一个主公。我把自己交给你了。这两个人是相互创造出来的。”多么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多年的军旅生活史上,朱苏进听过、见过创造“主公”的英雄吗?朱苏进自己首先就做不到,谈到由小说写作转入剧本写作的原因时,他坦白,“写小说也碰到了一些窘境。自己的一些作品,让自己尊敬的首长们忧心忡忡”。服从就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服从的“天职”之下,有什么“创造”性可言?服从就是服从,军队只能如此,对“服从”进行如此生机勃勃的“建构”,实乃不符合精神逻辑。
朱苏进也有写电视剧太累的感慨,他说,“做电视剧也并不总是让人愉快”。我的一个在电视剧上小试牛刀便迅速回归的作家朋友则说:“做电视剧总是不让人愉快。那是一个对于写作的蹂躏过程,本身你在写的时候已经考虑到观众了,但制片方还嫌不够,不管识字不识字的,都可以提出来要你修改,谁都可以强奸、轮奸你的写作。这种写作对你本人没有提升,不像小说写作,是一个充实的精神劳动过程,有一种痛并快乐着的幸福。”一写剧本就特别烦躁易怒的情形,我还听几个作家说过。
朱苏进承认,“为了收视率,需要做出牺牲和妥协——把你真正感动的东西和那些庸俗拌在一块,包成个饺子”。收视率,这是目前朱苏进最关注的,他对记者说,每天,索福瑞34个城市《三国》的收视统计数据都会发到他的手机上。收视率是朱苏进的上帝、灵魂,收视率是理解朱苏进的核心词、关键词。《三国》之“雷人”使网上板砖之凶猛远远超过朱苏进预期,以至于家人对此都“偶有伤感”,但朱苏进却哈哈一笑,表示根本不在乎,因为:收视率不赖。不过,应该提醒的是,凤姐的“收视率”也不赖。
卖得好,才会被骂也快乐,才会连自己家人搭上都在所不惜。如果朱苏进不是装潇洒,如果朱苏进还有些许真潇洒,那都是因为:有金钱挺着。这是朱苏进所有实力的终端。
朱苏进为写剧本做了一个形象的辩解:“一棵树的老根在那里是不动的,只是花粉到处飘飞。飘到纸上那是小说,飘到电视机上是电视剧……好的东西是相通的,何况挣钱多。”影视没价值有价格,小说有价值没价格,还有“包饺子”论,朱苏进自己已经把小说与影视的区别说得够清楚的了,这里却又磨平了。很显然,这是狡辩。花丛中飞的是蝴蝶和蜜蜂,粪堆里爬出来的是“圣甲虫”,怎么能说一只昆虫从花丛中飞出来就是蝴蝶和蜜蜂,从粪堆里爬出来就是“圣甲虫”呢?有这样的昆虫吗?变色龙都没这本事。不在于“真正的感动”,不在于“老根”如何,也不在于“好的东西”是不是相通,关键就是挣钱多。假如挣不到那么多钱,电视剧做得再满意他都不会如此自诩的。
朱苏进说:“挣钱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要被一种低级的因素制约,那是很烦人的。”“生活需要钱,但钱的欲求很快就容易得到满足。我现在挣的钱就够我用的。”“够用”只是朱苏进的自谦,“金牌编剧”挣的钱岂止是够用!据悉,今年5月,朱苏进已经荣升为“文职少将”(技术三级),体制内的待遇绝对不低,绝对不至于为“低级的因素”制约了。窃以为,朱苏进现在即便不靠编剧,光靠体制内的待遇,也能生活得相当不错了,万万不会到“逼良为娼”的程度。也许,我是个太容易满足的人,无法理解朱苏进的消费诉求,如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也许,从前偏低的军人待遇给朱苏进留下的物质创伤太深,一时难以恢复。现在的朱苏进,“低级”的“烦人”是没有了,但新的、高级一点的“烦人”,是不是又有了呢?
朱苏进已经盆满钵满,完全不必恋栈了,那么,支撑他走下去的是什么呢?据说,朱苏进如此阐释他做电视剧的动力:“想想看,每天晚上,全国有几亿人在看你的东西,那是多大的满足,多大的成就感!”这话曾经让我深以为是,直到凤姐出道后,我才明白,不全是那么回事,凤姐何尝不是万众瞩目呢?而朱苏进目前也被封为“凤姐”了。以娱乐大众为己任的人,也难免被大众所娱乐,我们这个时代最不缺乏的就是娱乐精神。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绝对不能只看受众数量多寡,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情形是常有的。就当世来看,钱钟书所有学术著作的读者可能都不如一本《围城》多,《围城》小说的读者可能又不如《围城》电视剧的观众多。但衡量其价值,却未必是一个不如一个。对于一部作品受众多寡的判断,也不能看一时一世,就后世积累的受众总量而言,《围城》小说肯定多于电视剧。文艺作品有畅销的,也有常销的,再好的电视剧也是一时的,而好的小说却是长久的。王朔曾说,我当年的电视剧还有谁看?可我的小说还有人在看。
惯性、惰性、麻醉或欲罢不能,都不能成为真正的支撑,所以,支撑朱苏进在电视剧领域走下去的,也许恰恰就是无支撑。朱苏进之所以为写剧本狡辩,就是因为内心的虚弱和不自信。今日的朱苏进俨然已由愤青变成了嬉皮,但他的毫不吝惜的自嘲,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上的退守和自我保护!如果不认为有什么可“嘲”的,还何必自嘲?朱苏进的名气和财气足以使他在某些方面很潇洒很有底气。但是,在另外的方面,朱苏进明白自己的虚处和软肋,那是理想主义折翼后的颓败。他并不能说服自己,并不能真正从电视剧中获得自己认可的成就感。在一部小说的前言里,他曾这样感慨:当年我把小说写完后经常丢了自己,找不着回到生活的路。后来写剧本了,逐渐有些像怨妇。离了龙门,浓妆淡抹地过来,低眉垂眼中动无数心眼,内里还想招人注目。“内里还想招人注目”,说白了,就是希望得到一点真正来自灵魂来自精神世界的肯定。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还有比文学更好的精神回馈吗?所以他说,“我不写小说只是暂时的,从事影视剧编剧对我来说绝对只是个客串”。这个话是2009年说的,当记者问他现在是不是还这样想的时候,他回答:“是这样。起码在自己欺骗自己这个角度,是这样的。”这是多么沮丧的坚守!文学的牌坊,只做了渺远的精神自慰。
我从不认为作家应该清贫。财主问阿凡提,你要真理还是黄金?阿凡提答:黄金。原来阿凡提也像自己一样贪财,财主终于找到了嗤笑阿凡提的理由。可是,阿凡提说,因为我缺的不是真理,而是黄金。朱苏进现在也跟财主一样,缺的不是“黄金”,而是“真理”。所以,田园将芜,胡不归?
行内人士说,写电视剧的回报太大了,人被诱惑着,牵扯着,身不由己,下不了船了。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很难回来,心态、思维、语言和写作方式,都回不来了。写电视剧就是整合、借势、取巧、拼装,就是把文学、历史等领域的很多树上的桃子摘来,安到自己的桃树上,集大成也。写电视剧就要迎合大众欣赏口味和思维走势,不能有过多自己的思想。所有畅销的东西几乎都是这样的生产模式,包括书。剧作者就是勾勒草图,点染填色由他人来完成。写小说必须解决的许多基本问题,都可以交给导演、服装和道具去做。写电视剧还可以流水线生产,可以逐级发给承包商去做,或者自己拉个粗糙的东西出来,由别人分头去“补锅”。所以,一个较公认的说法是:尽快毁灭一个作家的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去写剧本。
只有业已收手的作家,才肯承认写影视剧会写坏了手,继续在那个行当里发财的作家,当然是硬撑着不肯承认的,哪能塌自己的台!靠电视剧发达到一定的份儿上,对文学自然已经没有公开的敬意了,但文学作为一种“影响的焦虑”,却顽固地蛰伏于内心,于是,只好夸大金钱带来的快感和满足感,来抵消面对文学的自卑,以及缓解来自文学的压迫。一些改行写剧本的“前作家”坐到一起相互比的是:一集多少啊?是不是进入十万元俱乐部(一集十万)了?别墅多大啊?如果在座的还有“现作家”,就看他们的得意吧,总有人有意无意地,试图以自己的金钱把旧同行的尊严压扁。这些高兴地放弃了文学理想、愉快地挣钱去了的“前作家”会这样回头鄙薄旧同行:谁还写小说啊?!好像写小说是一件十分滑稽十分蹩脚十分恐怖十分无地自容十分令人惊诧的事情。理想肯定是个折磨人的东西,人一没理想就快乐,就有钱,就轻舞飞扬,何乐不为?
但理想又是个很顽固的东西,尤其文学的理想,很难彻底消泯。那些“十万元俱乐部”的会员们转头到了文学的现场,又会变得特别自卫:怎么了?好像我们被打入另册了!没人说他什么,他就自觉地敏感起来了。他们与作家打交道时特别敏感。如果真那么肯定自己,又何来这份敏感呢?又何来这种虚火上升的症候呢?
为得不到文学方面的承认而叫屈和愤愤的剧作者大有人在,可是,让这些人自己说:有谁在制造剧本时首先考虑的是文学价值而不是商业价值呢?如果这个人连文学价值都不懂,那就更不用废话了。金牌编剧朱苏进都以亲身体会说明了写电视剧是个什么活儿,有些人却偏偏要为自己竖座文学牌坊。朱苏进高出一筹的是,他不竖牌坊,不叫屈,他承认“无价值”。这叫聪明。即便“堕落”,也“堕落”得坦然,至少说明判断力没问题,至少没有侮辱自己的智商。既要不管不顾地为赚钱而写剧本,又急赤白脸地要求竖一文学牌坊,真是有点捞过界了,难不成好事都成你家的了?这样的人多为由作家改行者,那些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写剧本的人,心里是不会不平的。
这样的人,可能是有一种蝙蝠心态:在鸟类面前,他以兽类来自居并自卫;在兽类面前,他以鸟类来自居并自卫。这样的人,原本很容易找到自己存在的支点:因为有钱,他可以傲视许多作家同行;因为有才,他又可以傲视许多编剧同行。或者,在物质面前,以精神自慰;在精神面前,以物质自慰。可是,在才气面前比才气,在精神面前比精神,他们就捉襟见肘了。这样的人,可能还是愿意被归入作家行列的,可能还是不愿意将电视剧行当里的人引为同道的。鲁迅的《二丑艺术》写戏班里的一个角色,叫“二花脸”,具有两面性,即便“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作家改行写剧本可以是件好事,老舍由小说而剧作就很成功,可是,有几个人敢说“我的改行跟老舍一样纯粹”呢?
朱苏进是典型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一面为写剧本辩解,另一方面又否认影视剧有价值,这岂不又背叛和蔑视了“平均化”的观众?这种矛盾抵牾,两面均不能自圆其说,正是朱苏进真实的内心状态。历史的朱苏进、“现行”的朱苏进,本质的朱苏进、具象的朱苏进,在这里相互打架。
曾经在一次会上,我终于见到了久仰的朱苏进。我很注意地观察着他,发现那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充分后现代的朱苏进,一个狡黠如“老滑头”的朱苏进。总觉得哪里不对劲,或许他不该那么爱笑,而且又笑得那么“闷坏”,那么让人不放心?钱钟书和杨绛资助了许多贫寒学子,并捐立现已达800多万的奖学金,自己却一生俭朴,钱钟书故而自嘲:“我生来就是寒士骨相。”邻居说杨绛犯傻,有钱不拿去买别墅,杨绛说:“人的追求境界和想法,有没有‘形而上’,总是不一样的。”也许我对于朱苏进的想象,就是那种肃穆的“寒士骨相”和矜尊的“形而上”?那次是一个文学的会,朱苏进建议四人或六人一组讨论,引来哄笑,我暗暗地不明就里,旁边有人指点:打牌。大概越是在文学的会上,朱苏进越不会谈文学,不管是不屑,是“不肖”者的自卑,还是近乡情怯,反正,他绝不会谈文学。他的态度似乎在表明:文学是你们的事。这种明智的回避,当然出于免受刺激的自我保护的需要。当下,不谈文学是文人之间交往的一种时尚,越高级的文人聚会越不谈文学,谈文学的人是不入流的。会上发了两套献礼书,转头我就在电梯里发现了其中一套,显然是故意的遗失。莫名其妙地,我第一个就怀疑到了朱苏进。也许是我小人之心,但完全出自本能。但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他干的。
当下,“剧作是不是文学”正在被热议。窃以为,这个问题简直如“骡子是不是马”一样匪夷所思。不能说骡子跟马毫无关系,但骡子就是骡子,马就是马,这难道还有什么可争议的吗?首先,谁能说清楚,现在的“剧作”是指什么?剧本,电视剧,还是根据电视剧“改编”的小说?传统地看,剧作当然应该是指剧本。可是,现在的电视剧作者提供给大家的,几乎都是由剧本或电视剧改编的小说,那么,你让大家讨论什么?对着小说讨论剧作,这不是荒谬吗?如果剧作者对自己的剧本真那么自信,就应该直接出版剧本,看自己的剧本能不能跟同名电视剧一样成为“名作”和“巨作”,而不要“改编”成小说。剧作者渴望得到肯定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你连让人“肯定什么”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这肯定如何进行呢?下一个问题是:肯定谁?现在的“剧作”,如果是由剧本改编的,往往就是集体制造一人署名而已,里面含有多少署名者自己的东西?如果是由电视剧改编的,那就加进了更多人员更多环节的再创造,那么,即便要加以肯定,你去肯定谁?
所谓“剧作”,根本不能一概而论,契诃夫、奥尼尔、曹禺的剧作叫剧作,集体制造又进行了许多商业加工的剧作也叫剧作,能相提并论吗?何况,根本就没看到剧作。要是有剧作摆在这里,就算比不上,至少可以成比,但根本不是一个同类项,怎么比呢?中国现在写剧本的数不胜数,但是,有几个是契诃夫、奥尼尔、曹禺那样的剧作家呢?——不论水平,论水平那是挤兑人家,单就创作心态而言。
由剧本改编的小说,这是中国的新生事物。就拿朱苏进来说,一面《三国》小说在卖,一面他自己坦白尚未回到小说上来,那么,卖的是什么?这种疑似剧作的小说如何认识和如何界定,是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理论显然是滞后了。所以,与其探讨剧作是不是文学,不如探讨一下这一新生事物的性质类别内涵外延,也算找到了一个所谓的“理论生长点”。
朱苏进是个有性格的人,他的“转场”很大气,一旦转行做编剧,就绝对不再写小说了,不像有的人那么不彻底,既做编剧,或干些别的,又担心在小说领域被遗忘,抽空还要跑回来应付一下,然后争名分。
《三国》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文本,每个时代都可以改编,但朱苏进只有一个。如果朱苏进是一个彻底丧失原创力的作家,他去编电视剧是不会令人遗憾的。但我相信他不是。有朱苏进这样的编剧是观众的幸运,因为毕竟朱苏进的档次在这里。但是,对于朱苏进本人,却未必是一件幸事。他应该拥有更大的可能性,实现更大的价值而不是价格,使自己的存在指向深远。电视剧是一定会有人去写的,但像朱苏进这样的小说作家去写却是可惜的。
有人说,荣誉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已远离江湖,江湖却还有你的传说。我就是那个犹记小说家朱苏进的江湖传说的人。我仍然迂腐地假道学地期待着:小说家归来。因为,你是朱苏进。
不过,我又想起沈从文《边城》的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