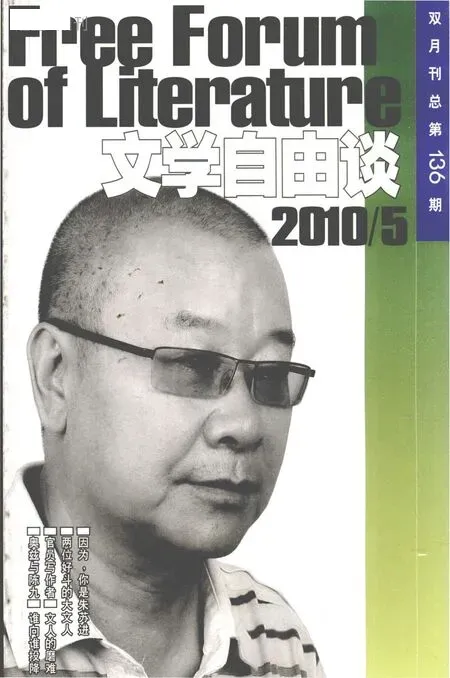谁向谁投降
●文 陈 冲
如果让我选择2009—2010年文学界的三大事件,其中之一,我会选择“投降事件”,即《人民文学》和《收获》相继发表了郭敬明的两部长篇小说。
这是一个“投降事件”。有人说,这是“文学向市场化、庸俗化妥协”,我认为“妥协”一语用词不妥。“妥协”含有折中之义,且其结果应是妥协双方均从中获益。这件事却没有这种性质和结果。郭敬明的小说刊登在《人民文学》和《收获》上,完全没有形成任何“折中”的形态,只能说是一不留神长出一个怪胎,类似于喇叭花上长出一根紫色的狗尾巴草。从这个怪胎身上,充其量也就是某家刊物、某个人得点小名小利,“文学”、“市场”、“庸俗”这三家,都占不到任何便宜。但是,任何事情的发生,总有它发生的原因。喇叭花上长出狗尾巴草,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人民文学》、《收获》刊登郭敬明的小说,是因为某种投降——没错,不是妥协,是投降。
但是,这并不是文学向市场化、庸俗化投降。两本刊物代表不了文学。
甚至也不是两本刊物向别的什么什么投降。两本刊物并没有从此变成专发、甚至也没有变成常发此类作品的刊物。说白了,不过是偶尔为之,近似于“玩票”。这类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别,只要不是故意去混淆,原是很容易分开的。比如,两本刊物用来刊登郭敬明小说的,都不是正刊,而是“专号”。虽然这两家杂志社都没有调查、没有公布相关的数据,但我可以有把握地推测,热心购买那两本专号的,仍然是郭的“粉丝”,其中不会有太多正刊的热心读者。反过来也一样,热心购买专号的读者,也不会有多少人从此便热心购买这两刊的正刊,事实上也没听说那两本刊物从此销量大增。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件事都属于个别性事件,不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正如虽然长出了一根狗尾巴草,喇叭花还是喇叭花。《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说,“一个郭敬明不会使殿堂倒塌”,是有道理的。当然,如果要进一步较较真,他后面那句“要是那么脆弱就成草棚子了”,或多或少有点问题。《人民文学》在60年里发表一个郭敬明的小说,发了也就发了,就像李所说,是在“九十九次靠谱”之后,“试着不靠谱(了)一下”。这与“殿堂”的性质有关,但与它是否坚固无关。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而是此后每年都刊登“一个郭敬明”,那么这“一个郭敬明”虽然不一定会使殿堂倒塌,但一定会使殿堂变成草棚子——即使这个草棚子像殿堂一样坚固,它仍然是个草棚子。
那么,究竟是谁向谁投降呢?
要弄清这个,先要明白这个事件的内容——是哪些“事儿”构成了这一“事件”。如上所述,两家刊物前后各发表了“一个郭敬明”的小说,不构成一个“事件”,甚至构不成一个“事儿”。任何一个刊物,偶尔刊登了一个不该刊登、不够资格、不够水准刊登的稿件,原是很正常的事,甚至可以说是正常现象,若是说得再极端一点,简直就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尤其是晚近以来,几乎每一期都有这种现象。登了也就登了,然后就过去了。即使有人提出一些批评指责,编者也不难回答:好稿子太少呀!所以,在我看来,构成这一“事件”的“事儿”,不仅仅是刊登了郭敬明小说本身,甚至不包括这本身,而是刊登之后所引起的“热议”或“争议”。我把这两个“议”都加了引号,是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并没有多少“热”,也没有多少“争”,只是确实有“议”。而从另一面说,热不热或争不争都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那个“议”。媒体喜欢把事情往大里说,喜欢用那个“热”字,我一般不上这个当,尤其是涉及到网络的时候。大家都清楚,1000次点击,或1000条评论,绝不代表那背后是1000个对此事真有了解的人,甚至也不代表是1000个人。所以,从“铺天盖地”,到“网站瘫痪”,我都不相信它一定是真正的“热”。至于“争”,我更想不出足以让我相信的理由。我压根儿就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值得“争”的。不就是喇叭花上长出了一根狗尾巴草吗?有什么好争的?难道你真以为狗尾巴草普遍都能长在喇叭花上,或喇叭花普遍都能长出狗尾巴草?
真正有意义的是“议”,是《南方周末》提供的对两位当事人——《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和《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的采访。这两位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所发的“议”,为我们解开“谁向谁投降”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首先,这与对郭敬明小说的评价无关。郭的小说,我一个字都没有读过。而且我承认,这个不读,存在着主观故意。其一,我接触过对郭敬明小说热捧的介绍,从而知道了我不该浪费时间去读它们,更别说花钱去买了。其二,我知道郭敬明被判抄袭且不道歉的前科,读他的书对我的眼睛是一种道德的亵渎,买他的书等于买赃物。这是我的看法;别人有权不这样看,正如我有权这样看。
但是对郭敬明的小说很容易定性:它与文学无关。我在一篇旧文中曾提出过一个标准:文学影响人的心灵,娱乐影响人的心情。以这个标准衡量,郭的小说显然无涉人的心灵。郜元宝点评郭敬明的《爵迹》,点出郭在不长的一段文字里,即存在着大量的语法错误和文理不通之处,点得都很对,却有迹近迂腐之嫌,类似于责备狗尾巴草没有开喇叭花。《爵迹》不管存在多少语法错误和文理不通,都不影响许多人津津有味地读它,说明在它那个阅读语境里,根本就不讲究这个。
李敬泽、程永新都是目前一流的编辑家,前者还是一位颇有功底的评论家。正因为这个,李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所发的“议”,也更有理论色彩和理论意义。我还想特别指出,李先生对以什么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有很深刻的理解。举例来说,他在2010年6月2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题为《当下中国文学缺乏力量》的文章中认为:“文学作品好坏与否,标准其实很简单,就是恩格斯谈到马克思时所指出的达到对活的历史现象的本质的有力的理解。”这个标准,可能也有人不同意,反正我是深为赞同的。
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郭敬明的小说,能得出什么结论是确定无疑、不必废话的。它们完全没有文学价值。当然,若要全面、公允,也可以换个说法——它们的价值不在文学方面。值得称道的是,李先生在评价郭敬明的小说时,并没有使用双重标准,所以在接受采访时,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喜欢它。”当然,他也很清楚此说直接带来的下一个问题是什么,所以紧接着就说:“但我不认为一本刊物或一份报纸是只发主编喜欢的东西或信息的地方。”
可不可以把这个话,理解为文学刊物,至少是“这一个”文学刊物对编辑方针做出的重大改变呢?
我这里所说的“编辑方针”,是一种“潜方针”。潜方针也是方针,而且更有效。表面上,没有任何文字规定,涉及“喜欢”或不喜欢可以或不可以成为编辑们取舍稿件的依据,但实际上,所有的投稿者都明白,如果编辑不喜欢你的稿子,它是根本不会被刊登出来的。正是《人民文学》,据说当年就发生过一桩公案(我特别标明“据说”,是因为事情确实是听来的,但消息来源则是该刊的一位资深编辑,因而应该是可靠的):在新评出的某一年全国短篇小说奖20篇获奖作品中,就有5篇曾被《人民文学》退稿,有的还是在一审就被退稿的。新上任的主编提出“这是个问题”,但仍有一些编辑认为“这很正常”,别人喜欢别人可以发,多数评委喜欢可以获奖,但是我不喜欢,我怎么填稿笺建议发表呢?对这样两种不同的意见,作家们也有所议论,我理解的多数看法是:主编的意见是对的,编辑的意见也有道理——对于文学作品,编辑的取舍很难完全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所以,不要说主编不喜欢,就是责编不喜欢,你的稿子也会被退回。我自己的经历同样证实了这个现实。在原来那几位编辑“主政”时,我的投稿没有被退回过,有的还发了头条,得了刊物的年度奖;等到编辑部新老更迭,当我知道我的稿子已不被新人们“喜欢”,我就不再向这个刊物投稿了,两年后即被取消了刊物的赠阅。我对此毫无怨言,因为我的的确确认为“这很正常”。
现在,这个刊物的现任主编公开宣布,主编不喜欢的作品也可以在刊物上发表了!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如果说这也是事实,那也是只适用于郭敬明的事实,不然你就投个他们肯定不喜欢的稿子试试看。至于为什么独独是郭才能享受到这个特别待遇,连韩寒都不行,倒很可能是问题的核心或根本,但不在本文题旨之内。
《收获》的执行主编程永新显然也不喜欢郭敬明的小说,不过他没有这样直接表述,而是说“我觉得他这种写作,作为一种文本的存在,没有什么太大害处”。都是搞文字的,这个话的意思不难理解:“这种写作”是有害处的,而且害处还可能比较大,只是不“太大”。他也没有像李先生那样宣布本刊可以发表主编认为有害处的作品,倒是说了一个更正面、更具理论色彩的理由:“《收获》这些年的变化试图在调整文学跟时代的关系,跟当下生活的对接。”看来,在理论上程先生不如李先生严谨。如果要把郭的写作逻辑地“代入”这个命题,立刻就会遇到不“同一”的障碍。郭的写作很“时尚”,但与“时代”风牛马不相及;郭的作品很畅销是当下的一种生活现象,但他的文本与文学意义上的“生活”根本不搭界。这应该是文学概论中的常识。
郭有一个致命的死穴:那桩被判抄袭仍死不道歉的前科。任何职业都有特定的职业道德,其中又有一些是职业道德的底线,郭触犯的就是文学创作的道德底线。当他的活动仅限于娱乐范畴,他的文本仅仅作为一种娱乐消费品出售时,这个事还可以有点含糊。应该说这仍然只是一种“特别国情”。在任何一个具有规范的娱乐市场规则的国家,这种事仍然为职业道德所不容,只不过在缺这少那的中国,抄袭、剽窃才会成为这个行业的普遍现象,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然而,阿弥陀佛,即便在中国,截至2008年为止,文学界幸而还没有糟糕到这种程度,这条职业道德的底线还没有被弃守的先例。所以,当郭的小说出现在《人民文学》、《收获》上之后,自然而然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一片反对、谴责之声。的确,这是针对郭的“人品”而进行的谴责,说得再直白些,这是对人不对文。即便真是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在作者就已被法院终审判定“抄袭事实成立”的行为正式道歉之前,其任何文字都不配出现在负责任的文学刊物上。
但是这样的事还是发生了。对于发生了这种不该发生的事,两家刊物的主编显然有责任做出某种说明或解释,而在接受采访时,二位选择了为自己辩护。当然,他们都意识到这是一个困难的选择,所以也都很自然地努力先把自己“择”出来。用李先生的话说,就是“我反对不诚信,反对抄袭,也反对不道歉”。但是,反对归反对,却只能白说说,不能动真的,否则就是“一棍子打死”(程先生语),就是“不给吃饭”(李先生语)。这就又回到一个逻辑问题:一个抄袭者在承认错误(道歉即是一种向受害人认错的表示)之前,暂停他在正式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资格,跟“打死”、“不给吃饭”是一回事吗?许多行业对于严重违背职业道德的行为,都有类似的惩戒措施,例如竞技体育方面有“禁赛”直至“终身禁赛”,机动车驾驶员有“吊销驾照”直至“终身禁驾”。这些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绝不罕见的事例,二位主编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任何一个行业要维护其职业道德的底线,从而保证行业的基本秩序,是不能只讲“恕道”,不讲约束的。明白归明白,因为要为自己的刊物没有守住职业道德底线的做法辩护,就只好假装不明白了。比如,李先生就有一问“:我要是有个孩子,我是不会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还要逼着认错道歉,不道歉就不给吃饭,你会吗?”如此设问,真的有点过分了。打了、骂了还“逼着认错道歉”,李先生所指的那个“你”会不会咱不知道,但我知道,而且我相信李先生也知道,法·院·正·是·这·样·判·的·。尤其过分的是,李先生还正面提出了一种普适性的道德原则,即“但是我从不认为别人的错误给了我某种道德优势”。这算什么逻辑?第一个层面,它直接推导出的结论是:凡是谴责郭敬明的人,就是自认为拥有“道德优势”;第二个层面,再普泛一点,那结论就是:人人都有错,所以谁都别说谁。
这是不是太近似于想一巴掌就把天下所有人的嘴都捂住?
那么,李先生(还有程先生)是糊涂人吗?不是。文坛所有对这二位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他们决不是糊涂人。正相反,二位都是极聪明的人,最低限度也是明白人。
得。现在我要给出“谁向谁投降”的答案了。在避开那些刺激人的、“宏大叙事”所惯用的词语之后,我从最生活化、最日常化的词语中选出了两个,叫做:
明白向糊涂投降。
至于明白为什么要向、为什么会向糊涂投降,超出本文的题旨了,您自个儿琢磨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