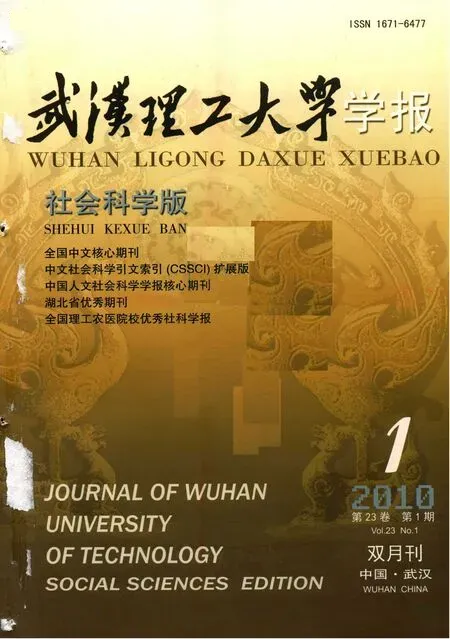政党依法执政之价值分析
胡晓玲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3)
政党依法执政之价值分析
胡晓玲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3)
依法执政成为法治社会所普遍采用的执政方式,缘由在于其自身的魅力价值:体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增强了党执政的人民代表性;拓展了执政资源,夯实了党执政的正当性;塑造了党权威的形象,有利于执政公信力的发挥;契合了制度经济学,降低了执政的成本。
依法执政;正当性;权威;交易成本
执政是人类社会产生国家,有了政权以后的一种普遍政治现象,即当政者掌握国家政权命脉,并在国家生活中贯彻自己政治主张的现象。在传统社会里,执政多是掌权者切身躬行的事业,在社会发展进入到近代以来,基于社会生活的纷繁复杂和社会分工的更加细致,作为权力主体的人民没有更多的精力切身从事日益变动的政治事业,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种新兴的政治力量——政党[1]470相继登上各国的政治舞台,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此时的国家实行起了以政党制度为国家权力配置基础以及运作体制基础的政治运作模式,故而又称为“政党国家”。这种机制下,政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学者所说,在现代国家的政治过程中,政党是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主体[2],它一端连结着国家政权,另一端连结着市民社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纽带,是社会能量转换的中介[3]。
为什么要选择此党而非彼党,是源于人民的选择,而如何得到人民的拥护进而掌握国家政权,必然和其执政的方式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一个政党对执政方式的选择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政治背景的产物。在整个社会进入到宪政与行政法治时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无论是依靠传统、神权、暴力还是依靠个人魅力的执政方式都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了,毋庸质疑,执政党必须采用新的执政方式才能满足变动后社会对执政合法性的要求,执政合法性的诉求必然要求执政方式的创新。人类绵延多年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法治”是一种比“人治”更为有效和合理的治国模式[4],因为依法可以“防止反复无常和怪诞的政治行为”[5],在整个世界进入民主政治的时代里,法治成为了世界的普遍潮流,政党作为一个对国家政治生活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政治主体,其依法执政更是历史发展和时代选择之必然。
一、依法执政体现了执政为民,增强了党执政的人民代表性
人民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问题,历来为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所关注,并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学说。
西方最著称者为古典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统治者必须统一按照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公正地进行统治。臣民们则必须保证服从统治者公正地统治。只要任何一方违反契约,另一方就不受契约的约束,有权采取行动加以纠正”[6]。其倡导者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认为国家权力即公权,是由社会中各个人为解决自然状态下的困难与不便,舍弃其自然权利的一部分或全部,以社会契约的形式让渡出来,凝聚成人民权力,并派生出国家权力,使之能以其获得的权力,反过来保障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古典自然法学派揭示了社会契约论中的民主内涵,杰斐逊则继承和发展了人民主权思想,提出了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如果政府滥用了这种权力,人民有权收回,他认为,“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整个国家中的一切权力的源泉。他们可以自由地通过他们认为是适当的代表处理他们所共同关心的事情,他们可以随时撤换这些代表,或者正式改变代表的组成。我不知道除了人民本身之外,还有什么储藏社会的根本权力的宝库”[7]84,为了实现人民主权,杰斐逊主张将立法权的根基归于全体人民,他说:“宪法是由人民的智慧制定的,并且是以人民的意志为基础的,人民的意志是任何政府惟一合法的基础。”[7]129他认为,在宪法化契约关系中,人民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
中国古代,贤人智士对人民和国家治理的关系有深刻认识。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8]管子说:“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民归之。”[9]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10]这些话都涉及到如何取信于民以使拥有的权力具有合法性。唐代政治思想家提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等论断,也是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经验性总结。我国现行宪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它用根本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民是权力的主人。十五大报告也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这都向世人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人民是依法治国的唯一主体,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政党包括执政党,都不能成为人民之上的治理国家的主体。现代社会庞杂事务的存在,使得人民不可能事事躬行,各国普遍采用了代议制民主的方式,代议制民主在承认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前提下,通过确立一种合理的程序与机制推选出人民代表,人民代表通过一定的组织和形式来行使权力。在社会发展到政党政治的时代里,政党成为代议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从本原意义上说,政党是人民基于结社权这一基本人权而组成的政治性团体,政党取得执政权乃是基于人民的同意和授权,民众的支持是一切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政党要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得反映人民的利益,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人民意志是一种政治术语,它在提出宏观政治策略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上,就可能会显得不易操作。我们必须寻找一种具体的载体将其落实,在法治时代中这种具体的载体就是法律,法律将人民的利益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我们只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保证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实现,那么也就是同时维护或实现了人民的利益,这样一种转化让抽象的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变得直观且容易操作。只要我们保证实践运行中的法律是真正反映人民意志的法律,那么运行它就是在实现人民的意志,这样依法办事的政治体制事实上就是在维护人民的利益,而这也使得政治体制因为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政治体制而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其合法性在客观上得以实现。
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提出了执政为民的口号。执政为民也就是说,执政党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执掌者”,要做到“权为民所用”,绝不能把公共权力当作一己谋私利的工具,更不能把自己视为公共权力或公共权力的一部分。政党执政为民还要擅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协调好执政过程中的各种利害与冲突,“有许多人有一种不智的意见,就是人君治国,要人治事,其政策之大要,在乎照顾各党各派利益与愿望;然而道理与此相反,最要的大智乃在如何擅为规划有关大众的,使人们虽有党派之别而不能不一致赞同的事务,否则就同如何与私人个别地用适当的手腕进行交涉”[11]181。政党要执政为民就绝不能将本阶级或本阶层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只有“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的拥护。
在宪政与行政法治的时代里,要做到为民执政就必须要依照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执政,党要严格按照宪法与法律,在宪政体制内运作,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办事,因为只有依靠法律才会反映人民的意志,才是执政为民。否则,执政党会丧失掉作为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存在价值,而最终失去自己的执政地位。江泽民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然垮台。”[12]只有做到始终执政为民,才能始终获得人民的选择与认同,从而保障党的执政资格。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政党只有做到依法执政才能始终如一地代表人民利益。无疑,依法执政增强了党执政的人民代表性功能。
二、依法执政拓展了执政资源,夯实了党执政的正当性
合法性是政治权力“正当”、“合法”运转所必需的资源和支持,它一方面表明政治权力具有使人们认为其统治是“正当”、“合法”的特性;另一方面表明人民在没有强制力迫使其服从的情况下对执政者的自愿服从、支持乃至忠诚。一旦执政者具有这样的合法性,其所制定、倡导和实施的措施,就能获得人民的普遍信仰和尊崇。所以,合法性不仅使执政者具有了“正当”、“合法”的地位,而且能使执政成本较低且执政保持相对的持久稳定。也就是说,对任何政治体系来说,合法性都是影响和控制社会最为有效,最节约成本的政治资源。回顾近代中国历史,诸多政党林立且良莠不齐,军阀割据混战,各种势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导演了一幕幕血淋淋的“城头变换大王旗”的闹剧。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是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对内反对剥削压迫,对外抗日反帝,自强不息,用革命实现了孙中山先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遗志,并在人民支持和拥护的基础上缔造了新中国。可以说,从国共合作到国共分离,从积极抗日到推翻国民党独裁统治,从反帝反封建到建立爱国统一战线,从打破一个旧世界到建立一个新世界,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生活和建设美好家园的追求和努力。中国共产党坚持为劳苦大众谋福利求发展不是停留于表面的宣扬,而是用事实证明给国人的:在暴力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人用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情怀,播撒着一个政治团体为民谋福利而身先士卒,乃至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它深深打动着那个时代大多数国人,让他们为中华民族出了共产党而感到振奋,感到民族有了希望,让他们觉得这个政党值得支持、拥护和信赖,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的救星。
正因为这些,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开始形成,其执政的合法性也得以确立。这种合法性源于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支持、拥护和信赖,其实质是源于对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广泛认可。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追求幸福和安康过程中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使得人民拥护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种通过历史演进历程来论证政党执政合法性路径的方式,从某种角度看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这种思考可以证明过去,但却未必能说服未来,因为“凡物都是在不停的变化之中,永不停歇,这是的的确确的”[11]200,“政治制度是会坠落的”,一时的现状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并不会影响或阻碍历史发展的进程,而现状也必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的变化而出现很多变化。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的选择不是永恒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的发展是呈螺旋式上升的,社会的进步在一时一地难免起伏不定,“如果没有某种认同的基础,任何政权都无法持久”[13],我们必需寻找新的合理有力的依据,以适应变化后的社会背景对执政合法性理论的要求,而且“只有根据新出现的社会条件带给我们的问题,重铸社会理论的概念工具和方法论工具,我们才能走出这种困境”[14]。
一个政党只有时刻关注自己的执政资源才会做到长治久安,静止的执政观,不根据变化后的执政环境调整自己的执政手段,最终只会走向灭亡。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整合党的执政资源。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这一脉相承的理论,与时俱进地深化了共产党执政的理论资源;新时期提出的依法执政口号又契合了世界政党执政方式演进的必然趋势,反映了宪政与行政法治时代行政活动要科学运行的客观要求,体现出法治社会大背景对诸多政治主体行为的必然要求。依法执政,即执政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现实政治法律框架,从根本上有利于整个社会人权的保障,可以说,这不仅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而且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即对于公共利益和社会进步具有正当性,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
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根基。党提出要依法执政,反映出其防范执政风险的政治意识,并不断探索执政危机的新出路,顺应了新时期对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需求。可以说依法执政拓展了党执政的合法性、正当性资源,夯实了执政的法理基础。
三、依法执政塑造了党的权威形象,有利于执政公信力的发挥
“权威”是由“权”和“威”组合而成,权威即“权力与威势”[15]。权力反映了一种支配与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广泛存在于任何在一定时空中具有规则化形式的社会体系中,一个能够合法地获取权力的个人或集团就可称为该领域的权威。可以说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衍生物,是合法化了的权力[1]498。政治权力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政治权威即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16]。美国学者约翰逊说,权威是“一个人在相信他或她施加影响的权利的合法性基础上要求别人服从的可能性”[17],权威的特点在于它的合法性,而权威的合法性“归根到底是个信念问题,这种信念关系到权威在其中得以运用的制度体系的正义性,关系到运用者在这个制度体系中充任权威角色的正义性,关系到命令本身或命令的颁布方式的正义性”[18],由于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因而,权威总是表现为一种“使人信从的力量和威望”[19]。可见,权威是人类特殊社会关系的反映。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权威反映了一定社会秩序的内在需求。秩序是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进程运行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20]。秩序是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良好的秩序是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基本前提,无序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一定的秩序需要有共同的权威来维持。权威是社会秩序维系的有机环节和必要机制,凡是有秩序的地方总能发现维持秩序的某种权威形式。酋长、族长、君主、皇帝、国王、政府、议会等等,在历史的时空中,都充当过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权威。恩格斯深刻考察了权威的历史演进过程,认为权威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特征要素,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他指出:“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21]可见,权威是植根于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普遍现象,是社会秩序维系的有机环节和必要机制。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都是希望有所寄托和依靠的,这可能源自内心安全感的需要,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被“管教”传统的大国,儒教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统治者种种愚民伎俩的使用,在客观上给我们留下了种种仰视权威,依靠权威的心理。固然从根本上而言,尤其在民主、自由、平等成为世界政治发展主潮流的时代,鼓吹权威似乎与这些宣传口号相抵触并应受到批判,宣传树立权威似乎是一种背离历史发展进步潮流的。但事实上,相对于人类悠悠历史长河,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了的。在社会仍然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在人具有心理上依附和安全感需要的背景条件下,权威这种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自身利益的东西,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的稳定。现代社会中民权理论的发展使得人有着一种傲视权威的资格,因为从根本上说作为权力运用者的政府或政党只是人民行使自己权力的一种具体运作工具而已,但是在权力已经让渡以后,权力就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我们只有尊重权威,才能将权威代表的人民利益加以贯彻落实;而且鉴于人民内部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进行权力分争的可能性,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可能被异化,并背离权力创设之初的目的,固必然需要对权力运行进行监控,使得权力以一种中立的色彩在其创设初衷的轨道上运行,这样才有利于更多数人利益的贯彻落实。为此可以说权威形象的塑造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的现象,尤其在传统政治文化气氛比较浓厚的国家中,权威的存在不仅可能而且很有必要。
比较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的类型通常可以分为“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类[22]。在“早发内生”型国家中,政党是与现代化变迁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分化的结果,政党政治是随着选举制和公民权利的发展而形成的,今天的西方国家大抵如此;而在“后发外生”型国家中,政党并不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发展了的政治结构分化的结果,而是在外在影响和压力下,政治体系为了维护其生存和发展,对强大组织力的现实需要,在功能上体现的则是政治资源整合优先的状态,即政党政治是国家危机和近代政治秩序发展的共同结果。中国是一个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后发型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实现现代化的赶超性,这就要求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发挥其导向和组织功能,而且后发型国家在社会转型期存在着的大量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也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来予以协调,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否则,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的进程就会失去秩序保证,出现所谓的“现代化中断”现象[23]。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也说:“现代化是一个包含了人类思想和行为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24]32他认为:“现代化需要推动变化的权威。”[24]110我国目前正处于一个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市场化进程、法制化进程、世俗化进程与一体化进程的统一,与此相伴随的是一系列混乱和无序现象,致使社会转型过程中充满了变革与保守、分化与整合、多元与一元、无序与有序等激烈的对抗与冲突,使得社会转型呈现出了纷繁芜杂的态势[25]。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权威被分散,原有协调和控制机制被破坏,转型社会中必须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权威来对政治权起到保障与促进作用。权威的理性化,亦即实现传统的人治权威向现代法理型权威的转变,是国家政治转型的根本标志[24]92。在习俗、宗教、领袖魅力等传统合法性衰落后,这种“理性的形式原则在实践询问中取代了诸如自然或上帝一类的物质原则”[26],成为现代合法性的主要基础。
对一个政治体系来说,政治权威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社会治理不仅要靠权力,而且更多的要靠权威。执政党可以通过掌握的权力进行政治统治,但是如果权力不变成权威的话,这种统治不可能长久。因为权力只表明服从,而服从却可能是被迫的。出于被迫服从状态的人们总是会寻找机会摆脱这种状态,现行的统治也因此变得极其不稳定。权力转变成权威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权威表示自觉的服从,而自觉的服从意味着一种协调、稳定、良性互动的体系和状态[27]。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也证明,一定的政治权威是现代化启动和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环顾全球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的日本、新加坡,都经历了权威的推进[28],当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府推进式的(尽管不完全是这样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29],这有力的政府推进背后必然是依托中国共产党的,因为中国的法治道路是党领导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模式,诚如学者所言,“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决定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权威推进要靠中国共产党,这也是我国法制现代化道路的特色之一”[30]。这必然要求党要依法执政。可以说,依法执政是党在新的时期塑造权威形象的有效实现途径。
四、依法执政契合了制度经济学,降低了党执政的成本
近年来,西方兴起了一种新的学派,即新制度经济学,它是以交易成本为核心范畴来分析论证制度相关问题的经济学派[31]。该学派的兴起及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使得效益这个传统的经济学概念被导入到法学研究中,并形成了以效益为基点的新的法律分析方法。学派的鼻祖科斯对法律作经济分析后导出的结论就是:选择法律的目的就是要尽量降低交易成本,法律制度的基本取向在于效益[32]。学派的认识对于政治体制的高效运作也是适用的。高效的政治体制是能够用较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用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更大效果的体制。高效的政治体制需要政治体制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活跃起来,都发挥其功能,这首先就要求各国家机构和政治组织要有明确的职能规定和权责界限,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权责要分明,职能划分及相应的权利义务配置要科学,并用法律固定下来,这事实上就是说政党要在法律的轨道上运作,政党依法执政才降低了执政的交易成本,才符合法律对其制度化创设的原因。
党实行依法执政会节约交易费用,并契合新制度经济学中所言的成本——效益最大化,这具体可以分析如下。
首先,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一般表现为由立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的规则。规则的作用在于减少信息费用,减少不确定性[33],规则将权利义务的界限加以明确,并向社会公开,使得人们的行为有了可预测的基础,降低了守法的成本,为政治稳定提供了基础性保障。众多的规则便构成了法律,福勒曾这样表述法律的8项形式特征:一般性,公布或公开,不溯及既往,明确,不自相矛盾,不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的同一性[34]。从法律的形式特征我们可以看出,法律的稳定有利于减少个性与非理性,遵循法律有利于促进政治行为的有序化,而这无疑节约了政治交易中的成本。
其次,在传统的执政方式上,政党、国家和社会几乎是三位一体,该种体系是极不稳定的,它使党内和国家很难形成有效的制约力量,不利于发展党内民主,不利于执政党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影响党执政能力的提高。而依法执政,即依靠法律使政治权力规范化,把政治治理方式纳入到法律轨道,保证政治法治化的形成。美国著名法学家庞德说,文明意味着对自然界的控制与对社会的控制,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35]9210。法律几乎总是同秩序相联系,许多法学家都从这个角度界定法律,而制度经济学家更从这个角度把法律确定为一种能建立预期的正式制度。
再次,依法执政可以引导民意取向,规则的制定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长远化。历史上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些政策的制定,因为过分迎合民意中极易发生的短期收益最大化的不良倾向,或是受了一些不合乎实际的思想潮流的影响,最终导致了大量资源的浪费。按照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学观点,人是有理性预期的,但是理性的人拥有的只是有限的价值预见及有限的知识能力,亦即“有限的理性”,变动社会的复杂局面使其难以看到自己的影响力,这样就需要有相对稳定的规则存在,对各种社会交往建立起预期,以此规制人们的行为,人们根据这些规则明确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而形成采取怎样的行动更为合算的理性预期,这就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早期法律之所以能代替习惯和习惯法的主要原因也就在于它能够有效地节约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36]。
法治的经济效益一般是非显形的,它不像资金投入那样可以提高直观的劳动生产率,而是如同科学技术一样渗透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通过合理安排资源管理和利用的方式,明确市场主体在经济交往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使之能最大化地利用经济资源,节约交易费用,最终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37]。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治活动常常被视为一系列政治市场中的交换,其往往寻求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公共目标,将资源引向最佳用途[38]。而依法执政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无疑将有利于此,诚如庞德所说,“法律制度安排的直接目的是通过经验来发现并通过理性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各种方式,使其在最小的阻力和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35]70271。
实际上法治的效益还不仅止于此,如果引入康芒斯宽泛的“交易”概念,将政治行为也纳入到交易的范畴,那么法治还可以产生巨大的政治效益。比如季卫东曾敏锐地指出,法治可以提供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相互信赖”,所谓相互信赖就是指“即使把政权转交给反对党,也不必担心仅仅因为政治见解和政策的不同而被杀头或送进监牢,即双方都能做到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同时法治还可以提供作为民主政治组织技术的程序规则。这些程序规则是指,“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论证要件讨论和审议国家大事的机会以及可供不断利用的各种制度,它们都与法治有密切的联系,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认为没有法治就不会有安定的民主,考虑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让法治秩序的建构先行一步”[39]。
在法治背景下政党依法执政恰是一种有效的节约政治交易成本进而节约社会成本的有效制度创新模式,是宪政时代执政方式的最佳选择,这必然要求在我国实行依法执政。
五、结 语
可以说,依法执政承载着宪政、民主、法治、人权、自由等高尚价值,具有不可抗拒的独特魅力,在宪政与行政法治时代,政党依法执政是有效执政的历史必然。
[1]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2]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111.
[3] 彼得梅尔.政党体系的变化:方式与解析[M].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962107.
[4]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84.
[5] 西奥多A哥伦比斯,杰姆斯H沃尔夫.权力与正义[M].白 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98.
[6] 爱德华美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2卷[M].罗经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10.
[7] 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 杨伯俊.孟子译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1960:7.
[9] 管子全译:下[M].谢浩范,廖小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600.
[10] 韩非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644.
[11] 培根.培根论说文集[M].水天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72.
[13] 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P.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1262.
[14] 罗伯特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吴玉章,周汉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6.
[15] 辞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1411.
[16]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60.
[17] 约翰逊D P.社会学理论[M].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279.
[18] 邓肯米切尔.新社会学辞典[M].蔡振扬,谈谷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2223.
[19] 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375.
[20]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07.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3.
[22] 方 雷.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53.
[23] 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杨 豫,陈祖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3.
[24]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张岱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32.
[25] 夏立忠.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执政党权威的加强[J].红旗文稿,2003(5):11213.
[26]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90.
[27] 王长江,姜 跃.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52.
[28] 谢 晖.权威推进与权威转化[J].法学,1998(2): 427.
[29] 苏 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1.
[30] 孙天全.从现代化的反思探索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M]∥张文显.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262236.
[31]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7.
[32] 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233.
[33] 理查德A波斯纳.法理学问题[M].苏 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58.
[34] Lon L Fuller.The Mo rality of Law[M].Yale Uni2 versity Press,1969:46291.
[35] 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沈宗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6] 冯玉军.法律的交易成本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1(6):10216.
[37] 冯玉军.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0:149.
[38] 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视点:第二版[M].王 询,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5. [39] 季卫东.秩序的正统性问题——再论法治与民主的关系[J].浙江学刊,2002(5):57267.
(责任编辑 高文盛)
Abstract:Exercising state power acco rding to law has been the w idely used means in the society w ith rule of law.The reason may be exp lained as follow s:it embodies the peop le rep resentativeness having been in power for the peop le;strengthens the resourcesand testifies reasonable and legitimate ruling of the party;it also moldes the Party asan authority image,being in power has been believed more benefi2 cal of the force bringing into p lay;in addition,it agreesw ith the system economics,and the cost w ill be reduced if the Party being in pow er according to law.
Key words:exercising state pow er acco rding to law;being reasonable and legitimate;autho rity;transac2 tion cost
Analysis on the Value of Party’s Exercising State Power According to Law
HU Xiao2ling
(School of A dm inistrative L aw,N orthw 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Law,Xi’an 710063,Shanxi,China)
D911.01
A
10.3963/j.issn.167126477.2010.01.023
2009-07-19
胡晓玲(1979-),女,山西省大同市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政治学、宪法与行政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