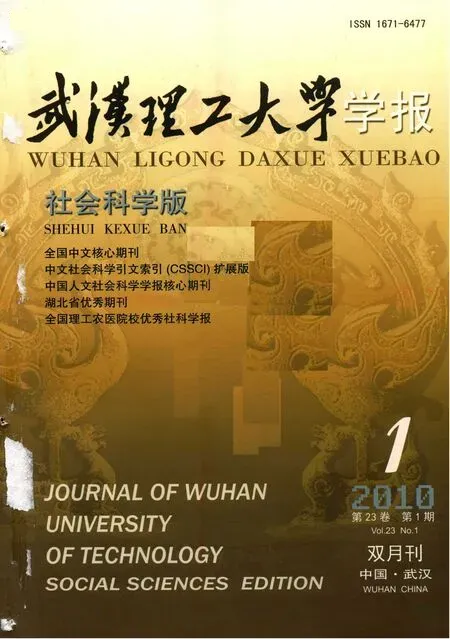图像时代中国电影文化的审美反思
宋 薇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图像时代中国电影文化的审美反思
宋 薇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作为图像时代主要代表之一的电影,因其可视的影像对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文学的倾轧和替代而引发了一场艺术的革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它以强大的生命力冲击着文学阅读的同时,电影自身的审美转向也正在悄然来临。如果说,传统电影的图像是为了叙事的需要,而现在,图像已成为电影的中心。观赏性、愉悦性的影像奇观成为电影的主要追求。但是,图像的独裁无论走多远,也不应该离开精神的家园。如何走出影像的误区和图像的霸权,给予观众深情地看的影像并引导观众深情地看,是中国电影文化寻求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
图像时代;电影;视觉文化;叙事;影像
“世界图像时代”是海德格尔在20世纪提出的一个文化现象的预见性论断,如今,视觉文化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成为活跃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审美图景。当代学者周宪在《视觉文化的转向》一书中指出:“当代文化不但体现出高度视觉化的特征,而且是一种普遍视觉化,这就意味着视觉化对非视觉化领域广泛而深层的‘殖民’。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并不是视像(或形象、图像、影像等)本身 ,而是‘世界被把握为图像’。”[1]7的确 ,在视觉文化突显的时代,文学的叙事被瓦解了,具有强烈冲击力的画面和过分渲染的色彩扮演了重要的视觉传递符号。
作为图像时代主要代表之一的电影,因其可视的影像对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文学的倾轧和替代而引发了一场艺术的革命。丹尼尔·杰·切特罗姆曾经指出:“电影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关键的文化转折。”[2]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它的羽翼逐渐丰满,并且以强大的生命力冲击着文学阅读的同时,电影自身的视觉转向也正在悄然来临。
一
从电影自身的发展轨迹看,除了视觉形象的独特性之外,它同时还兼具文学的叙事功能。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学性曾经是电影的重要特征,是电影存在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对白、画外音、剧本和情节的逐渐深入中,叙事电影曾经是电影话语模式的主导形态。
在叙事电影中,它的最大功能就是把故事讲精彩。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它主要的叙事方式是对电影情节的精心处理和安排,运用蒙太奇、画外音、长镜头等电影手法,把不同的素材和画面组合成一个完整体,通过前后关联的逻辑与因果关系,传达出特定的意义,产生出戏剧性、文学性的效果。其中,所有的画面与图像服务于故事发展的逻辑,其目的是让观众沿着它的叙事进入到故事的情境中去。正如周宪所言:“叙事电影的艺术魅力来自于画面本身的叙事逻辑所产生的认知意义上的理解或愉悦,而不是直接来自于电影画面表层的视觉效果。”[1]249总体而言,叙事逻辑主宰着电影的画面构成和视觉效果,视觉技术服务于隐含在画面背后的叙事主题。
在我国,20世纪30—40年代的许多黑白电影,其叙事主题十分突出。无论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展示的史诗情怀,《万家灯火》呈现的伦理魅力,还是《乌鸦与麻雀》体现的喜剧效果,均表现出文学叙事的审美特征。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例,影片采用章回小说的结构方式,将巨大的时空跨度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庞杂的各类事件有条不紊地组合成一幅历史的画卷。影片同时借鉴了中国传统戏曲的叙事模式,把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集中在一起,以主人公张忠良为中心,分三条线索展开叙事。电影借助深情的音乐,特写的镜头,唯美的对白,精心设计的春水、月亮等自然形象,使影片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叙事电影的经典之作,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电影的面貌。
新中国成立以后,叙事依然是电影的主旋律,由于过于强调思想文化的高度统一与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电影的叙事以简单直接的方式传达出英雄主义的颂歌和家国梦想的宏大主题。作为寓教于乐的最佳载体,电影在光影叙事中,承传着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及引导观众的历史重任。从1949年到1979年,绝大多数的电影人都汇入到战争叙事的洪流中去,形成中国电影最为宏大的战争片高峰。在崇山峻岭、林海雪原、茫茫大漠、古道小城等自然景观的衬托下,上演着一幕幕感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传奇,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叙事风格和影像记忆。
1979年开始,由于特殊的机缘,第四代导演的叙事不再局限于意识形态化的主题和崇高的理念,导演的内心体验和个人情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种相对抽象的、诗意的、诉诸人性情感的人文主题之门被徐徐推开。以《城南旧事》为例,影片虽是以精巧的艺术构思获得了国内外的各项大奖,但其真正的艺术魅力在于将“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3]这种情绪基调与时空浮现的叙事策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导演吴贻弓把这种叙事称为“叙述上的重复”[3],实际上,这是叙事策略与主体意识的一次完美结合,是以电影语言的表达方式对思想和人性的一次启蒙,在不断重复的“骊歌”声中,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城南,成为一篇温暖而又忧伤的故土,政治和社会的宏大叙事,终于被个体的情感和心灵所取代,影像呈现出浓郁的诗意和理想主义情怀。
第四代导演更多地把镜头对准了天空、大地、草原,对亲情、爱情、人伦的由衷热爱使得电影的画面和语言趋向唯美、真挚,导演的情感投入成就了电影叙事的诗意与浪漫,也成就了影像的唯美与自然。灵魂的对话、深情的凝视表现在镜头和画面的组织上,形成了中国电影难得一见的内省气质。
至此,中国电影仍然是以叙事作为中心通过光影讲述故事,无论是宏大的历史事件、政治题材还是细腻的个人情怀,电影语言是服务于叙事主题的。无论是线性蒙太奇还是平行、倒叙蒙太奇,都是依照某种故事结构和叙事原则来展开的,其目的是通过声像的配合服务于某种预设的主题。在叙事风格上,虽然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但是叙事的中心地位未曾动摇。
二
假如把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叙事电影笼统地称为电影的传统形态的话,那么以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则把传统电影的叙事中心进行了转换,这种转换不仅是电影形式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和电影形态的转换。有学者称这是从叙事电影到奇观电影的转换,是电影文化里图像战胜情节,外在感性对内心情感侵占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中可以清晰地捕捉到这种转换。
以陈凯歌为例,《黄土地》是他的导演成名作,由张艺谋担任摄影。在这部影片里,第四代导演时空复现的叙事策略和蕴含丰富的长镜头都获得了突破性的运用,但在影片结尾,并没有出现观众预期的完美结局,一个“缺席者”的形象对英雄主义和主流话语进行了颠覆和解构,对历史的反思和重构在影片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无论如何,《黄土地》依然是叙事性的,对文化的反思依然是电影的主题。正如陈凯歌自己所说:“黄河和黄土地,流淌的安详和凝滞中的躁动,人格化地凝聚成我们民族复杂的形象……我们且喜且悲,似乎亲历了时间之水的消长,民族的盛衰和散如烟云的荣辱。我们感受到有快乐和痛苦混合而成的全部诗意。出自黄土地的文化以它沉重而又轻盈的力量掀翻了思绪,搥碎了全身,我们一片灵魂化作它了。”[4]虽然,电影叙事的逻辑期待已经悄然变化,但是,《黄土地》的文化反思仍然内在地主导着电影的图像。
与陈凯歌一样,张艺谋的早期电影同样不乏历史重构与文化反思的创作动机,他把沉痛浓郁的人文精神和象征中国文化的民俗民风作为其电影叙事和影像传达的重点。以《红高粱》为例,在这部影片里,虽然有强烈的影音造型、仪式化的民俗民风,红色成为色彩的主调,造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绪感染力,但是这些图像仍旧是为叙事的主题服务的,是为了突出对生命意识的觉醒和民族性格的张扬。红色作为民族文化的密码,具有强烈的象征和意念性,图像契合沉郁浓厚的人文情怀这一叙事需要。
但是,也正是在对图像色彩的大胆运用中,图像的魅力得以被重新挖掘。当陈凯歌、张艺谋懂得以文化为旗帜来经营电影的时候,中国电影正迎来市场化的高峰。实际上,在他们的影片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呈现了由图像重构的影像奇观。像《红高粱》里的“颠轿”和“酿酒”,《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捶脚”、“点灯”等,虽然是中国文化的特定所指,他们一方面是为电影叙事主题服务的静观对象,但却又有意无意地向观众呈现出令人惊异的影像奇观。
《英雄》的出现使得影像的意义出现了大的转变,蒙太奇叙事组接的理性原则让位给视觉的快感。正如张艺谋所言,场景“独特而好看”。影片最具观赏性的影像有两处,一处是残剑与无名在水上较量,在画面处理上,水滴成了利器,琴声与雨声就是千军万马,意念促成成败。在另一场极具观赏性的对打中,飞雪与如月在黄杨林中穿梭,与其说是在对打,不如说是在翩翩起舞,伴随着轻烟般的音乐,仿佛置身于曼妙的仙境。这所有的图像设置,其用意正如动作导演程小东所言:“让大家都没有看过,也觉得很新奇,动作也很好看。”至此,以《英雄》为代表的奇观电影完全抛开了之前还深深眷恋的叙事主题和深刻意蕴,义无反顾地踏进了影像奇观带来的快乐世界中。
陈凯歌的《无极》,同样把影像的渲染营造到极致。海棠树的粉艳欲滴,鲜花草原的嫩红鲜绿,灰茫大地上血色的王城,白得耀眼的雪国故地,让人惊艳的女性形象,大将军军队的红盔甲,北公爵士兵的素衣衫……一直以来以厚重的文化味和浓郁的个人情怀而著称的陈凯歌,淡化了主题,放弃了深沉,用科技堆砌的“唯美”影像掩盖了虚无的内容,他以一部《无极》宣告了对图像时代感性愉悦的妥协和接受。
影像正以各种各样的独特姿态显示出当代电影与传统叙事电影的不同。如果说,传统电影的影像是为了叙事的需要,那么,现在,图像已经成了电影的中心,观赏性、愉悦性、影像的奇观成为电影的主要追求,也成了谋求商业利益的一种有效手段。
三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陈凯歌、张艺谋正以自己的图像方式迎接新电影时代来临的时候,一批新生代电影人在全球化的电影格局与中国电影独特体制的双重境遇里寻找着出路,这批以贾樟柯、张元为代表的新生代电影人试图冲出由“第五代”导演组成的电影围城,无论在题材选择上还是画面营构上都力求突出个性与自我。在影像表达上,远离了“第五代”的形式感、仪式感、厚重和绝对感,而以偶发性、随意性、边缘性来组织图像。于是,道具是有名但毫不出名的小城小镇,演员是名不见经传的非明星。在叙事题材上,他们不同于传统叙事电影重视历史忽视个体的模式,而力图描绘属于个体的小生活。
在新生代导演的影片中,自语式的“独白”与看似无序的“空镜头”超时空地、主观地接入到每一个表述的故事中,影像被有意安排得随意而自然。新生代影片的影像呈现出复杂的双重倾向,一方面是对20世纪30—40年代黑白叙事电影的回归,另一方面,影像的主体性已经显现,甚至默画面、白画面和对白都成为了吸引视线的主要图景。相对于人物镜头而言,写景写物的大量空镜头替代了叙事的功能,导演似乎让人在影像前迷失,又似乎让人在影像符号中找寻自我。以《小武》为例,影片中多次出现对于“墙”的空镜头,“墙”这个图像型符号的多次出现绝不仅仅在于它的物性,而是某种概念性的符号。这堵具有极强隐喻性的“墙”作为图像符号的意义表明“小武”像古墙一样,破败无力,陈旧而不合时宜,其视觉传达应和了导演的表达意图。
即使如此,新生代的导演们同样意识到市场的重要性,在保持自己叙事风格的同时,“好看”仍然是他们电影的最终选择,而到达“好看”的途径则充满了个性。新生代导演之一的张元表示:“人真是千奇百怪,而我最感兴趣的往往是比较极端的人。”[5]122张元电影的“好看”之处大多是通过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边缘人或为主流意识所排斥的异类。弑父的女儿,沉湎于愤怒的摇滚青年,游荡在公园里的同性恋者均以明显的反叛个性暗示着导演表达上的自我。另一位标榜以独立影像书写个人记忆的电影导演贾樟柯,则把电影的“好看”视线投放到普通人的生活里。他表示:“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5]368以《小武》为例,被郝公安用手铐铐在电线杆旁的小武,承受着围观者肆无忌惮的目光和充满好奇的私语,导演用了3分钟的长镜头,拷问着人们的心里期待。这些边缘人物又常常由非职业演员们进行原生态式演绎,这样一来,更是消解了镜头的经典叙事法则与潜在的表意功能,也自然解构了布满象征隐喻修辞的宏大叙事丛林。长镜头下对现实人生的还原与再现,其逼真性、当下性、现场感或在场感,其好看性并不亚于华美包装下的影像奇观。
让我们反观一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电影,可以发现在形式上完全不同但在追求上有着一致性的两幅视觉图景。如果说,以张艺谋、陈凯歌的《英雄》、《无极》为代表的影像冲击带来的是一场视觉美学的暴力,那么新生代的影像选择则是另一个极端,呈现为刻意的不刻意。一面是大量科技手段下华丽的、奇特的梦一般的视觉奇观,一面是摊在那里毫无修饰和未经雕琢的赤裸裸的现实;一面是光彩照人的明星依次粉墨登场,一面是毫无名气的普通人“不经意”间组成了镜像。这是当代电影在图像时代的两种显见模式。
四
在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在电影文化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探索性、先锋性是必然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电影人已经意识到商业社会消费文化中对电影需求的改变。一方面,他们创造出许多新的视觉形式和图像,另一方面这些影像又引导了观众的口味并造就了观众眼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眼光和图像的互动构成了图像时代的视觉文化范式。
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视觉文化主要代表的影视文化,在以它的图像霸权日益向商业化、娱乐化进军的时候,作为审美主体的观看者和倾听者也在发生着视觉审美的转向。对于审美主体来说,电影的这种难以抗拒的视觉化趋势所带来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是相当复杂的。视觉文化消解了传统影片所具有的叙事色彩和深刻意蕴,观赏者在一刹那被“震惊”的同时,“看”成为绝对的权力。没有时间留给观众凝思遐想去追求所谓的意蕴和内涵,观众似乎也没有耐心去细细品味影像背后的意蕴,面对强大的视觉冲击波,观众收获的是目不暇接的震惊和愉悦。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说:“图片能够俘虏了我们,而我们无法逃脱。”[6]他在哀叹图像的世界将禁锢哲学的思维,如今的我们恰恰在饕餮着视觉的盛宴,享受着视觉冲击的愉悦。应该说,“看”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行为,但人怎样看,如何看,显然要受其社会文化的制约,构成社会文化的图像则引导了这种对奇观的审美追求。电影的图像化正以动作奇观、身体奇观、速度奇观、场面奇观、明星奇观、乃至写实奇观,制造出无数的暴力图像、华美色像、科技幻像、明星视像和苍白影像。一盘盘图像的快餐让人目不暇接,不再是审美地看,深情地看,用心地看,而是轻快地看,娱乐地看,享受地看,乃至刺激地看。艺术中“韵味”、“意蕴”的生产和对现实的陌生感和超越性让位给平面化的快乐叙事和欲望表达,深层的文化情怀和情感的神圣性被消解和搁置,艺术成为自娱自乐的游戏与消遣的对象。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电影图像制造快乐,走向商业化、娱乐化和追求视觉震撼的同时,也给我们的审美带来了深深的困惑。来自影像的迷幻图像让我们沉溺于快乐的想象中,忘记了自己真实的情感与存在的境遇,人们在图像的狂欢中麻醉了自己,迷失了心灵,落入到图像的圈套中,而隐藏在图像背后的文化霸权和由此引发的精神危机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
如何走出影像的误区和图像的霸权,引导观众深情地看,并提供给观众深情地看的影像是电影文化寻求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有些电影人已经意识到图像的狂欢对人内心世界的掠夺和侵犯,开始反思视觉冲动所带来的文化危机。他们试图摆脱这个刻意追求人为视觉效果的符号世界,去发现和聆听精神世界真正的声音,重新捡拾被人们忘记的纯静与自然。无节制的视觉独裁无论走多远,也不应该离开思想与精神的家园。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电影的世界中,图像会找寻它的存在之家,从而使中国电影走进一个新的电影时代。
[1] 周 宪.视觉文化的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丹尼尔 杰 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曹静生,黄艾禾,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64.
[3] 吴贻弓.《城南旧事》导演总结[J].电影文化,1983(2):17-19.
[4] 陈凯歌.我怎样拍《黄土地》[M]∥电影导演的探索:第5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286.
[5] 程青松,黄 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先锋电影人档案——生于1961—1970[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
[6]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 朝,范光棣,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67.
Aesthetic Reflection on Chinese Movie Culture in Image Times
SONGWei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 aw s,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Hebei,China)
A 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image times,the movie caused a revolution in art through its visual image provoking a strife and substitution for the literature of paper-based media as the carrier.However,it is noteworthy that while it makes a strong impact on the vitality of literature,the movie’s ow n aesthetic shift is also quietly coming.If the traditional movie images are the need for narrative,and now the center of the movie.Ornamental,pleasant spectacle of images become a major pursuit of the movie.However,no matter how fa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images goes,nor should they leave the home of spirit.It is a practicable wa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vie culture to go out of image errors and image hegemony,and provide the audience with affectionate images and guide the audience affectionately to look at.
image times;movie;visual culture;narrative;image
J01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0.01.009
2009-10-25
宋 薇(1970-),女,河北省衡水市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美学研究。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