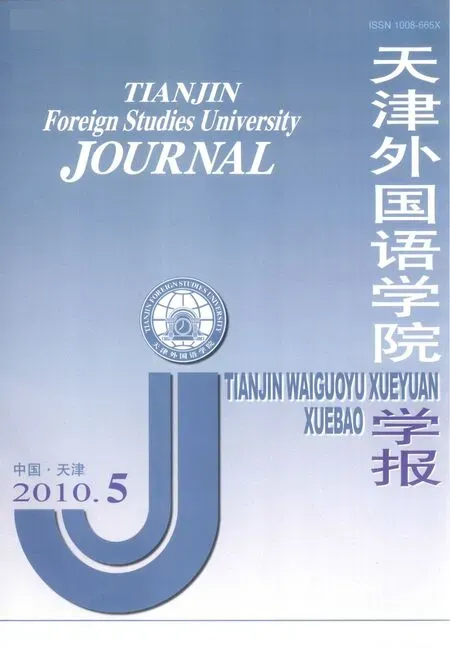托妮·莫里森的黑人男性想象
刘国枝,李 祥
(湖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 430062)
一、引言
托妮·莫里森是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迄今已发表九部小说,生动而多角度地呈现了黑人民族——尤其是黑人女性所经历的苦难及其为争取独立地位而进行的反抗。鉴于作家自身的身份及创作倾向,其作品中的黑人女性形象已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母亲群像、姐妹情谊、性别和种族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黑人种族的文化身份,成为莫里森研究中的长期热点,相比而言,其笔下的黑人男性形象则往往被边缘化或影子化。实际上,莫里森在其“富有想象力和诗意”(毛信德,2006:1)的作品中,通过对黑人男性的想象,塑造了具有不同行为和意识模式的黑人男性人物,从而以两性关系的视角,为探讨黑人女性的各种生存状态开凿出可能的生活空间。黑人男性虽然并非小说中的主角①,却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女性的生活态度和最终命运。如果说莫里森对黑人女性形象的刻画勾勒出一条明线,映照出作家对于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思考,那么,对黑人男性人物这条暗线的探查,则可以为此提供有效的参照和佐证。
本文将历时性分析莫里森作品中的黑人男性形象,考察作家对黑人男性想象的模式转变,以期遵循作家对于两性关系的思考以及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探索路径,展现其女性主义思想的变化历程。
二、黑人男性的集体逃离
在《秀拉》的序言中,莫里森(Morrison,2004:pxvi)写道:“叛逆的女性是迷人的,常常不是因为她们的行为,而是因为从历史上说,人们认为女性具有天生的破坏性,如果她们从出生开始不是在男性的支配之下,那她们就不被认为具有合法的社会地位。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女性对男性支配的摆脱给她们造成的如果不完全是灾难的话,也是悔恨和苦难。在《秀拉》这部作品中,我想探讨一下女性的这种摆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不仅是对于传统的黑人社会,也是对于女性间的友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莫里森早期创作中的一个倾向,即倾力探索女性在摆脱男性支配后的生存状态,试图通过对女性独立生活空间的营造,来揭示黑人女性的苦难与创伤,唤醒和激发黑人女性的独立主体意识。为此,在最初的两部小说《最蓝的眼睛》(1970)和《秀拉》(1973)中,莫里森塑造了模式化的逃离型黑人男性形象。这里的逃离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为文本外逃逸,是一种不在场的缺席,指作家通过情节的安排和角色的设计,造成黑人男性从故事的发展中退场,为黑人女性腾出独立的生活空间;其二为文本内逃逸,指人物对自身责任和义务的规避而形成一种在场的缺席,作家以如此情势架构出他们与黑人女性的对抗,从而凸现黑人女性在这种对抗和压迫下的生存状态。
《最蓝的眼睛》讲述了黑人小女孩佩科拉由于周围环境的冷漠和歧视,而渴望拥有白人一样的蓝眼睛的故事,“展示了由白人强势文化冲击所造成的黑人心灵文化迷失的悲剧”(王守仁、吴新云,1999:27)。佩科拉的父亲乔利以及乔利的父亲都是典型的逃离型男性。在乔利出生之前,他父亲就离家而去,当他刚刚出生四天,又被母亲所弃,所幸他被姑母发现而带回抚养。长大后,他从姑母口中得知父亲的下落,于是十四岁那年独自出门寻父,及至终于找到沉迷于赌局中的父亲,迎接他的却不是亲人重逢的喜悦,而是父亲的拒认与喝骂。心灵遭受重击的乔利不知所措,他“坐在甜蜜的阳光下,绷紧身上每一处神经和肌肉阻止眼泪流下来”(Morrison,1994:157)。从此,乔利像无根的野草四处游荡,直到遇见波琳并与她相爱结婚。接着,两人来到北方安家,并生下佩科拉和她弟弟萨米。可现实与他们的预期相去甚远,各种压力以及白人的歧视终于使乔利不堪重负,他逐渐冷落家人,终日酗酒,把内心的挫折和愤懑转换成暴力,发泄在家人身上。很显然,在乔利的成长过程中,除却外在的影响,父亲的“不在场”为他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反面榜样,及至他自己成为丈夫和父亲,他也无法履行相应的职责,反而以暴力的手段规避自己的责任,从而以“在场”的形式,效仿了父亲的缺席和逃离。乔利的逃离为他的妻子波琳营造了巨大的苦难空间,波琳“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而信仰基督的仁慈女人,担负起了一个不能依靠的男人,而这个男人是上帝让她去惩罚的”(ibid.:42)。所以乔利“堕落得越深,人变得越是狂野,越不负责任,她和她的使命就显得越崇高”(ibid.)。由此看出,作家试图在困境中赋予女性拯救和坚守的力量,来探索女性独立的潜能与可能。但是在白人文化强势的冲击下,这种力量十分单薄,最终导致波琳人格分裂。值得注意的是,每当家庭发生冲突时,两个孩子的反应也迥然相异,萨米据说“到十四岁的时候已经离家出走不下二十七次……而另一方面,佩科拉由于受年龄和性别限制,总是尝试用各种方法忍受着。尽管每次方法不一,但痛苦总是一样的深”(ibid.:43)。这不仅预示着不同性别角色的命运向下一代的传递,更在纵深的意义上通过复现男性的逃离与缺席而彰显了女性的坚韧与坚守。
在第二部作品《秀拉》中,莫里森续写了对黑人男性的逃离想象。故事主要讲述了两个黑人女孩内尔和秀拉成长中的友谊,以及她们在人生道路上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在主人公秀拉的生活中,有一群逃离型男性。秀拉的外公鲍伊鲍伊在和伊娃结婚五年后,抛妻弃子,留下伊娃独自艰难地养育三个孩子。当儿子三岁时,鲍伊鲍伊带着另一个女人回来了一趟又匆匆离开,对子女甚至没有丝毫的关注。在这里,通过鲍伊鲍伊为人父、为人夫的失职和缺位,作家旨在探讨单亲家庭中的女性能否从困境中突围,并获得独立的自主身份。诚然,伊娃肩负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但苦难并没有随鲍伊鲍伊的离去而终结,唯一的儿子虽然从战场上归来,却意志消沉,沉溺于毒品之中。为了避免儿子步父亲的后尘,伊娃将他放火烧死。通过情节上的如此安排,作家制造出家庭中男性成员的群体缺席,以最为彻底的方式为女性清理出绝对独立的空间。遗憾的是,“虽然在家庭内部可以摆脱父权制的阴影,但她们无法摆脱整个社会的父权制文化,以致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孤立无援,很容易再次受到世俗的影响”(乔雪瑛,2007:69)。因此,拥有这种独立的空间之后,我们看到的非但不是女性的自由和自主,反而是进一步的困境,其结果是伊娃的女儿汉娜烈火自焚以及她的外孙女秀拉郁郁而终。
秀拉的朋友内尔的家庭格局呈现出某种微妙的类似。内尔的母亲海林是妓女所生,这意味着海林从小无父。为了使海林免受母亲的影响,外婆独自将她抚养长大,后来海林嫁给了一位海员。在作品中,这位海员丈夫无名无姓,只是以第三人称“他(He)”和“他的(His)”被叙述者提及几次就退出文本,他的作用似乎只在于为海林提供了当母亲的机会,“他的长期不在家对海林来说是非常习惯的,尤其是他们的女儿在九年婚姻后出生了”(Morrison,2004:17)。海林是一位传统保守的女性,在家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她爱她们的家,享受着对丈夫和女儿的控制”(ibid.:18)。作家通过对海员这一特殊职业的选择,而造成作为丈夫和父亲的黑人男性角色的虚置,搭建出一个失衡的家庭,探讨身处其中的黑人女性的生存境遇。内尔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深受母亲的影响,性格温顺,举止文雅,后来成为一名传统的家庭妇女,到头来却遭遇婚姻的背叛。内尔的丈夫裘德当初之所以决定娶内尔为妻,并非出于真爱,而是因为在受到种族歧视而未能实现去镇上修公路的理想之后,“他需要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希望自己的男人身份得到认可,但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有人关心抚慰他的伤痛”(ibid.:82)。在这里,作家一方面批判了黑人男性的自大和软弱,另一方面也揭示出黑人女性的边缘地位,她们往往不被视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而被当成供男性所利用的工具。当黑人男性在外面遭受挫折和打击时,黑人女性便可以成为临时性的疗伤之药。由此建立起来的两性关系显然摇摇欲坠,难以维系。裘德的背叛和抛弃粉碎了内尔相夫教子的梦想,终于使她意识到独立自我的重要。
基于对逃离型黑人男性的多视角刻画,莫里森屡次对比了男性的软弱和女性的坚守,从中可以透视出作家初期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思想:将男性置于女性逆向的“他者”地位,表现出对黑人男性群体的失望,以此挑战男权文化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莫里森虽然利用男性的逃离所造成的缺席和对抗,为探索女性解放开拓了独立的空间,但从女性难以脱身的窘境及其在小说中的结局来看,作家显然也流露出了疑虑和困惑:通过对黑人男性的挞伐与弃绝来重建黑人女性的主体身份,或许是一条值得尝试之路,但必定也是一条艰辛之路,甚至可能是牺牲之路。
三、从逃离到反省
以上的分析表明,对黑人男性不遗余力的批判并不能为黑人女性带来幸福。从生活的浅表上看,黑人男性确实直接造成了女性的创伤和苦痛,但是,摆脱男性控制和压迫后的女性也没有实现精神上的成功突围,那么黑人女性的出路何在?不难发现,自第三部小说《所罗门之歌》(1977)起,莫里森开始重新思考男性在女性获得独立主体身份中的作用,并将两性关系置于文化和历史的维度,深层探讨黑人女性的苦难之源,试图探索出女性的出路。
《所罗门之歌》讲述了黑人男青年奶人寻求自我身份的成长过程,并遵循着这一过程展开了奶人家族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奶人出生于一个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安逸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自私、懒散、没有责任心的性格,所以在和他姑妈的孙女哈加尔恋爱一段时间后,热情减退,把她看成是“第三杯啤酒,而不是第一杯。喝第一杯时,喉咙里简直感受到一种令人落泪的感激之情。她也不是第二杯。喝第二杯时,会加强和扩展第一杯带来的愉快。她只是第三杯。你之所以要喝这第三杯,只是因为现成摆在那里,喝下去不会有什么害处,当然,不喝又有什么两样呢?”(莫里森,2005:109)最后,他终因厌倦而抛弃了她,而深爱着他的哈加尔由于无法承受这一打击而伤心致死。在这里,莫里森似乎延续了塑造逃离型黑人男性的套路,但故事情节并没有就此为止,而是继续推进,使奶人通过南方的寻找身份之旅找到了祖先的传统,成熟为一个敢于检讨和担当的人,他意识到自己对哈加尔的伤害,并愿意承载永远的愧疚。由此我们察觉到,莫里森对黑人男性想象的转变,由前期的彻底失望到这里的轻度和解。而黑人女性牺牲的代价则表明,女性对男性的过分依赖只会使女性丧失自我,甚至湮灭生命。
如果《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从历史维度对男性的反思,则《柏油娃娃》(1981)体现了作家在文化维度上的探索。后者讲述了一对黑人青年男女森和雅丹在交往过程中因各自不同的文化信仰而几经波折的故事,莫里森借此探讨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以及黑人和白人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作品中,森是黑人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偶然来到白人商人瓦莱里安在加勒比海所拥有的骑士岛,结识了黑仆夫妇蔡尔兹的侄女雅丹。由于受到瓦莱里安的资助,雅丹在欧洲接受了现代教育,深受白人文化的浸染。而森体格健壮,阳光俊朗,散发着与大自然亲近和谐的气质。随着了解的加深,雅丹对森从最初的厌恶转变为欣赏和迷恋。两人相恋后,森带着雅丹回到自己的故乡,认为那里是最自由美好的地方,而拥有白人文化价值观、习惯了现代生活方式的雅丹却无法适应原始落后的黑人社区生活,两人冲突不断。于是,森又陪着雅丹来到纽约,希望重新开辟两人的新生活,但固守黑人传统文化信仰的森又与这个大都市格格不入。他讨厌白人文化的虚伪,憎恨现代物质文明对自然的破坏,认为现代文明只是教会我们“怎样制造垃圾,怎样制造那些可以生产更多垃圾的机器”(Morrison,1983:204)。最后,两人终因坚守各自的立场而分手。
森和雅丹,一个是黑人文化的坚决守护者,另一个是黑皮肤的白人文化代言人。在这种角色布置背后,蕴藏着两层意味:第一,莫里森对黑人男性的想象部分地延续了其初期的思考定势,即黑人男性对外界事物变化的逃遁,他们不是积极地去适应,而是顽固守旧,封闭自我,不过作家又突破了之前的片面性,透过黑人男性对民族文化的坚守,而看到其中优秀的、值得守护的成分;第二,通过对黑人男性角色的指派,莫里森为黑人女性打开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空间,雅丹是这一空间的适应者、成功者,但她同时也割断了与自己民族的血脉关联,产生了身份的焦虑。因此可以看出,莫里森在继续探索黑人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之路上,表达了对像雅丹一样能够融入白人主流文化却缺乏本民族文化根基的黑人女性的担忧。不过在小说的最后,雅丹离开森后,森又踏上了找寻雅丹之路,对于这一开放性结尾,莫里森本人在接受采访时的一段话颇有意味:“森被赋予选择的自由,如果森决定加入 20世纪,他会去跟随雅丹。如果他决定不加入 20世纪,他会把自己封锁在未来之外。他完全可以彻底地与过去认同,但这是一种死亡,因为这意味着你没有未来,只有一个悬浮的地方。”(Taylor-Guthrie,1994:112)在这里,作家无疑表达了对黑人男性觉悟的期冀,以及对两性关系和谐的展望,由此似乎也为随后的创作埋下了伏笔。
总结以上两部小说中的黑人男性形象,我们不难看出,莫里森在对男性的想象中增添了反思的元素,批判中加入了理解,重新追问男性在女性获得独立主体的身份中的作用,因此,黑人男性形象不再是符号化和平面化的,而变得立体和丰满,闪烁出人性的光彩。这一模式的转变反映出作者对女性独立主体意识的思考更为深入和全面,初期的比较激进的女性主义思想也趋于温和。
四、逃离和反省后的回归
从上文提及的《柏油娃娃》的结尾以及对莫里森的访谈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的信息,在构建女性主体意识的探索之路上,莫里森开始认识到,“只有女性和男性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两性和谐、平衡发展的世界”(曹威,2009:141),因此,在寄希望于男性的反省和自觉之后,自第五部小说《娇女》(1987)开始,作家对他们发出了回归的召唤。
在《娇女》中,作家将笔端倒转,触探到不堪回首的历史深处,再现了 19世纪末黑人在奴隶制及其余波下的苦难生活和内心创痛。小说情节主要围绕曾为黑奴的女主人公赛丝为逃避奴隶主的追捕而弑女的事件展开,但黑人男性保罗·D在作品中显然颇具份量,是他陪伴着赛丝面对过去,走出阴霾。保罗·D曾经与赛丝一样,也是“甜蜜家园”的奴隶,后逃离出来,十八年后来到一百二十四号农舍与赛丝重逢。而此时的赛丝正和女儿丹芙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愿面对令人心碎的过去。随着保罗·D慢慢地融入赛丝的生活,往事也逐渐浮现,两人在交谈回忆中抚慰彼此受伤的心灵。可是当保罗·D得知赛丝的杀婴事件后,他太过震惊,无法把自己深爱的女人与一个杀死亲生女儿的母亲联系起来,于是惶然离去。保罗·D此举又一次显示出黑人男性的脆弱和逃避,不过,他的离去并不是决然的、了无牵挂的逃离,他依然深爱和惦念着赛丝,因此在痛苦迷茫中挣扎。小说临近结尾时,他终于醒悟,决定返回心爱的女人身边。他来到赛丝的病床前,对她说:“我和你,过去的往事比谁的还多。我俩也需要来一点明天的什么啦。”(莫里森,1990:350)由此可见,在这部作品中,作为黑人男性,保罗·D不再是影子或反衬,而是一个有爱、有责任、能理解、能担当的伴侣。
实际上,保罗·D的意义远远不囿于他个人的自救和对赛丝的救助。沿着《最蓝的眼睛》到《娇女》这五部作品的系列,不难发现,保罗·D虽然也有过逃离,但那不是剔除道义和情感羁绊的一去不复返的单程之旅;他虽然有过迷茫和反省,但不必以遗憾之心检讨自己的过往;他的回归是他自己的觉醒,而在作家而言,更是积聚此前的黑人男性的教训而水到渠成的结果,从而使得他的生命轨迹更为完满。这种轨迹既反照出黑人女性获得主体身份的艰难历程,也让黑人民族温馨和谐的两性关系变得可以期待,由此也传达出莫里森的女性主义思想从温和到温情的转变。
莫里森此后的作品虽然背景设置各不相同,但整体上是对其温情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多角度阐发,表明作家试图超越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或一元论,将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和身份建构问题置于两性关系之中进行探查,从而帮助黑人女性走出饱受压迫、孤苦无依的困境。
《爵士乐》(1992)的故事发生在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讲述了一对中年黑人夫妇在北方城市的情感纠葛,男主人公乔因自己 18岁的情人多卡丝移情别恋而将她杀死,乔的妻子维奥莉特带着满腔怨恨和嫉妒闯进多卡丝的葬礼,用刀去划她的脸,被人赶了出去。后来,通过与多卡丝的姑妈艾丽斯的沟通、交谈和回忆,维奥莉特逐渐理解并原谅了多卡丝,并跟丈夫重归于好。《乐园》(1998)以鲁比小镇上的黑人男性血洗修道院的事件开始,展开了黑人男性和修道院里五位女性的冲突和对抗以及小镇内部黑人男性与女性的矛盾,但在最后,小镇打破常规,为丝薇蒂女儿举行葬礼,象征了黑人民族将敞开胸怀,拥抱新的生活。发表于 2003年的《爱》被评论家视为《秀拉》和《柏油娃娃》融合后不完美的翻新(Kakutani,2003),但笔者认为,在这部作品中,莫里森对黑人女性身份建构的思考更为成熟。《爱》中黑人女性克里斯蒂、希德、梅、L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轴心是一个死去的黑人男性科西——她们分别是他的孙女、妻子、儿媳和厨师,科西以缺席的在场影响着他身后的女性。不过,与早期符号化和平面化的黑人男性形象相比,科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正如在 L的回忆中他是一个“很好的坏男人,或很坏的好男人。取决于你看重的是什么——是内容还是原因”(Morrison,2005:200)。小说中两位主要女性人物克里斯蒂和希德就是通过回忆她们与科西的往事而冰释前嫌的。莫里森最新的作品《仁慈》(AMercy,2008)将故事置于17世纪殖民初期,探讨了奴隶制下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的生存状况,以及更为深层次的人的自由问题,反映出作家更具超越性的女性主义思考。小说中出现了黑人铁匠这个身份特殊的人物,他是可以获取劳动报酬的自由人,而来自欧洲的带着劳动契约的白人却需要用一定时间的劳动换取自由。莫里森通过这一人物形象表明,“种族或肤色并不成为一个人是否受奴役的标志”(王守仁、吴新云,2009:43),从而质疑和打破了奴隶身份与黑人之间的对等关系,并且进一步探索了什么是人的真正自由的问题。当他拒绝爱慕他的黑人姑娘弗洛伦斯时,他说:“你的头脑是空的,你的身体是野性的……先拥有你自己吧。”(Morrison,2009:141)也就是说,黑人女性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
由此可见,从《娇女》开始,莫里森作品中的黑人男性显得更加复杂多样,并且客观真实,保罗·D、科西、黑人铁匠等比较正面积极、德性上有所提升的黑人男性的出现,延续和发展了作家重视男女性别关系,意在构建理解、包容与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女性主义思想,同时蕴含了作家对黑人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
五、结语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克里斯特瓦曾经将女性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的女性主义者都将男性置于女性的反向“他者”地位,不同程度地对父权制象征秩序进行颠覆和解构,而到第三阶段,女性主义者不再强调男女的对立或一元论,而是注重消弭冲突、对抗、暴力等男性统治话语,并推进爱、温情、友谊等新的文化政治话语,使世界成为具有新生意义的后现代世界(罗婷,2002:53)。本文的分析表明,莫里森在创作中,对黑人男性的想象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呈现为渐次“递增”的三个阶段,从黑人男性规避责任的逃离,到逃离后的反省,再到经历逃离和反省后的复归,其“递增”性表明后一阶段对前一阶段既有包容,更有延展,从而清晰地体现了莫里森的女性主义思想由激进至温和到最后温情的转变过程,而这种转变也大致吻合了克里斯特瓦之说。在探索两性关系以及建构女性主体意识的路径彼端,莫里森为我们提供了清楚的答案:女性的独立并非与男性的隔绝和对立,恰恰相反,只有在两性和谐的关系中,在彼此的理解、关爱和尊重中,女性才能真正找到主体身份。
注释:
① 《所罗门之歌》例外,但也有学者指出,虽然这部作品是以男性人物为小说的主人公,可是“就描写黑人女性这一方面来看,它不过是换了一个观察视角而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莫里森的所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对黑人女性身份认同的思考与再现”。参见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283.
[1]Kakutani,M.Fam ily Secrets,Feuding Women[N].The New York Times,2003-10-31.
[2]Morrison,T.AMercy[M].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2009.
[3]Morrison,T.Love[M].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2005.
[4]Morrison,T.Sula[M].New York:Vintage International,2004.
[5]Morrison,T.Tar Baby[M].London:Triad Grafton,1983.
[6]Morrison,T.The Bluest Eye[M].New York:Plume,1994.
[7]Taylor-Guthrie,D.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C].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8]曹威.给黑色的亚当命名——托妮·莫里森小说中黑人男权批判意识流变[J].外语学刊,2009,(2):138-142.
[9]罗婷.女性主义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10]毛信德.美国黑人文学的巨星——托妮·莫里森小说创作论[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11]乔雪瑛.托妮·莫里森作品中家庭演变之女性主义透视[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1):67-70.
[12]托妮·莫里森.娇女[M].王友轩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
[13]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胡允恒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2005.
[14]王守仁,吴新云.超越种族:莫里森新作《慈悲》中的“奴役”解析[J].当代外国文学,2009,(2):35-44.
[15]王守仁,吴新云.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的其它文章
- 《心灵的谎言》:男性自我身份认同的幻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