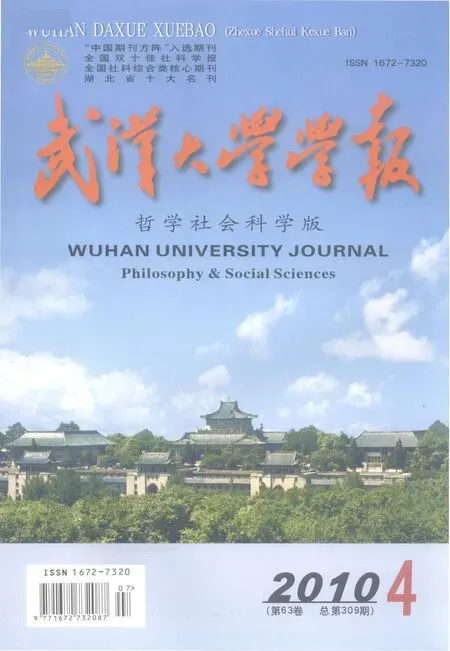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选择——基于管制暗示理论的思考
李仁真 杨 方
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选择
——基于管制暗示理论的思考
李仁真 杨 方
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经历了从一致行动条款占据主导地位再到集体行动条款成为主流的历史选择过程。集体行动条款之所以成为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现实选择,是因为其相对于一致行动条款具有制度优越性,而较之于法定方法更具现实可行性,同时也与晚近主权债务市场的结构变化及现实需要息息相关;基于管制暗示理论来分析,有关国家和国际机构向主权债务市场及其当事人发出的各种管制暗示是一个重要因素。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未来选择应该注重管制暗示的作用,公共机构可以通过管制暗示促使主权债务人和债权人进行有效选择。
主权债务重组;集体行动条款;管制暗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体系的剧烈震荡,不仅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受到严重冲击,一些主权国家也陷入了债务危机。自2008年10月冰岛因银行业崩溃而率先爆发债务危机之后,巴基斯坦、阿根廷、乌克兰等国面临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的压力也日益增大,人们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信用风险的担忧逐渐增加,主权债务危机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09年末至今,迪拜、希腊债务危机相继震惊世界。据穆迪、惠誉等评级机构的预测,西班牙、爱尔兰等欧元区国家在2010年也很可能出现债务危机。从全球范围看,各国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正在逐步增大,因此,对主权债务重组方法及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研究就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历史选择和现实选择
长期以来,围绕主权债务重组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提出了多种方法,其中备受关注的有两种:即合同方法(contractual approach)和法定方法(statutory approach)。所谓合同方法,指利用主权债务合同中的协议条款进行债务重组,主要通过修改现有主权债务合同中的条款或在新的债务合同中引入相关协议条款的方式来促进债务重组的实现。这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主权债务合同的违约救济问题主要是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债务国与债权人之间的法律问题,因此债务重组应该由债务国与债权人依照他们双方达成的协议条款来进行。实践中,合同方法又分为一致行动条款(unanimous action clause)与集体行动条款(collective action clause),前者要求主权债务合同中基本融资条件的修改必须经过全体债权人的一致同意;后者则实行主权债务重组方案只需经特定多数的债权人同意,即可以约束所有债权人。所谓法定方法,指的是以制定法的形式建立一个主权债务重组的法律体制,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或修改现有法律的方式对主权债务重组进行引导与规范。这种方法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提出的“主权债务重组机制”(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 Mechanism,以下简称“重组机制”)为代表。该机制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修订现行IMF协定或订立新的国际条约的方式建立一个独立的争端解决法庭,以促进债务重组方案的达成,对债务重组纠纷进行裁决,并保证债务重组协议的履行[1](第123页)。
考察近百年的国际实践,主权债务重组的合同方法大致经历了从一致行动条款占据主导地位再到集体行动条款成为主流的历史选择过程,而法定方法还只是IMF关于主权债务重组制度改革的一种建议方案。
(一)历史选择:一致行动条款与集体行动条款
集体行动条款的典型模式是“多数行动条款”(majority action clause),该条款允许绝对多数的债权人调整与债券发行有关的基本融资条件,包括更改清偿条款、调整利息率以及减少票面价值等。自19世纪末开始,依英国法发行的主权债券大都包含着多数行动条款,而依纽约法发行的主权债券则固守传统的一致行动条款,要求基本融资条件的修改须经全体债权人的一致行动,只要有一个债权人不同意重组方案,则其他债权人与债务国达成的重组协议就不能约束该债权人。
伦敦和纽约的发行市场在主权债券重组条款上的这种差异,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英美两国公司债券的发行。早期的英国公司债券均包含有一致行动条款。这种设计的弊端在于:其一,直接导致那些只是暂时遭遇流动性问题而实际并未濒临破产的债务人被强制清算;其二,某些债权人利用这种流动性威胁以债务人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优先清偿。为了克服这些弊端,伦敦债券市场推行革新,将多数行动条款引入公司债券的发行。多数行动条款的应用和推行,使得多数债权人就债务的延期偿还和清偿条件的变更等事项所达成的协议能够约束所有债权人,有利于提高债务重组的效率,并成为依英国法发行的公司债券和主权债券的标志性特征。
必须指出的是,多数行动条款长期未被纽约债券市场所认同或接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2](第420-422页):第一,债券发行人和投资者认为包含多数行动条款的债券很难转让,缺乏市场接受度,发行人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担心外国投资者不愿购买含有这种条款的债券;第二,随着公司并购浪潮的兴起,一些公司所发行的债券在金额、种类、抵押资产的数量上都非常庞大,加上公司结构的复杂性,多数行动条款在债务重组中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率。第三,美国《1939年信托契约法》第316(b)条明确排除在公司债券中引入多数行动条款。这无疑为依纽约法发行的主权债券提供了参照。由于当时的新兴市场大都倾向于依纽约法发行主权债券,因而直到20世纪末,一致行动条款在全球主权债务市场实际上占据着主导地位。
(二)现实选择:以集体行动条款取代一致行动条款
随着一致行动条款固有缺陷的日益显现,许多学者及业内人士开始呼吁摒弃受纽约法管辖的主权债券合同的这种传统方法,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也提出了以集体行动条款取代一致行动条款的倡议。2001年阿根廷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为促进主权债务危机的化解,IMF提出了“重组机制”的整体设计方案,希望融合所谓的合同方法和法定方法,以比较激进的方式促使债务国与债权人提高主权债务重组的效率。随后,一场围绕主权债务重组方法是应实行契约性变革还是制度性变革的争论在国际范围内展开。IMF及大多数成员国主张完全或部分接受“重组机制”方案,而美国和一些私人债权人以及部分新兴市场的债务国则主张推行集体行动条款,并认为这种方法足以解决传统的一致行动机制所带来法律问题。国际主权债务市场随即作出反应,墨西哥率先宣布将依纽约法发行引入集体行动条款的主权债券,乌拉圭、韩国、阿根廷等国也陆续在新发行的主权债券中纳入该条款。于是,集体行动条款迅速取代一致行动条款,成为全球主权债务市场在债务重组方法上的主流选择。
二、集体行动条款成为主流选择的主要原因
集体行动条款之所以成为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主流选择,主要是因为这种方法相对于一致行动条款和法定方法具有制度优势,同时也与晚近主权债务市场的结构变化及现实需要密切相关。
首先,集体行动条款取代一致行动条款,具有历史必然性。前已述及,正是为了克服一致行动条款的弊端,集体行动条款应运而生。它的功能,就在于使特定多数债权人就债务重组所达成的协议可以约束所有债权人,从而保证债务危机得以及时而有序的化解。相对于一致行动条款,集体行动条款更有利于解决主权债务重组过程中通常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与少数不合作者问题[3](第42-43页)。当主权债务危机发生时,债务国与债权人进行债务重组谈判的一大障碍是集体行动问题。尽管从整体上讲,债务重组对所有债权人都是有利的,但是对于某一债权人而言,不同意重组可能更有利于其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每个债权人都只顾自身利益而不同意重组,那么就无法达成重组协议,最终对所有债权人和债务国都是不利的。主权债务重组的另一难题是少数不合作者问题。由于主权债务融资工具和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了债权人利益的多样化,因此,即使债务国与多数债权人能够达成重组协议,少数债权人为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仍有可能拒不参加重组,而希望通过其他方式获得优先清偿,这些债权人即为主权债务重组中的少数不合作者。很明显,一致行动条款很容易被少数债权人滥用,致使主权债务重组协议的达成和执行遭遇极大困难,而集体行动条款的首要功能,就在于保证多数债权人可以对主权债务合同的融资条款等进行修改,其与债务国达成的债务重组协议可以约束所有债权人,从而推进主权债务重组迅速而有序地进行。
其次,较之于IMF“重组机制”,集体行动条款更具有现实可行性。从理论上分析,IMF倡导的法律机制比集体行动条款在适用范围、适用效力、重组目标的实现程度等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但其最大的障碍在于政治上的现实可行性。就性质而言,IMF“重组机制”旨在将主权债务国与债权人的债务重组问题纳入到国际公法体制的规范之下,这必然要涉及 IMF成员国的主权让渡,而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不同决定了这种让渡必将面临极大的困难。而且,该方案的通过必须得到3/5以上、拥有总投票权85%的成员国的支持,需要对现行IMF协定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这就意味着该方案的通过必须得到超过投票权15%的美国的明示同意。此外,IMF“重组机制”的真正实施还有赖于各成员国国内法的修订,这也降低了在短期内引入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必须承认,在 IMF“重组机制”提出之后,纽约及新兴市场的实践迅速转向,以集体行动条款作为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首要选择,也反映出主权债务市场及其当事各方的一种强烈意愿,即力图避免通过具有管制性背景的措施来解决主权债务重组问题,而是坚持以市场为基础,仍然通过主权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合同方法来实现债务重组。这无疑是出于对法定方法的警惕和不信任[4](第197页)。
其三,集体行动条款成为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现实选择,也与主权债务市场的结构变化息息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的主权融资主要来自大型跨国银行联合提供的银团贷款,这些银行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和未来的商业利益需要大大减少了少数债权人破坏集体债权人债务重组方案的动机。此后,随着墨西哥债务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爆发,跨国银行纷纷逃离新兴市场,主权债务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由银团贷款转向债券发行。主权债务的融资来源变得分散,许多中小规模的、甚至不知名的投资者都可以成为主权债务的债权人。债权人主体结构的多元化导致债权人利益的多元化[5](第64-65页),少数债券持有人恶意阻挠债务重组、债权人集体合作障碍等法律问题便陆续凸显,而相关债券的可交易性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直到此时,一致行动条款的局限性才真正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集体行动条款作为债务重组的最优选择才成为主权债务市场的现实而迫切的需要。
三、管制暗示在主权债务重组方法选择中的体现与作用
为进一步说明集体行动条款成为主权债务重组方法主流选择的原因,有必要借助管制暗示理论(regulatory cues theory)进行分析,以便深刻认识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向主权债务市场施加的影响及其法律意义。
(一)管制暗示理论的基本内涵
管制暗示理论是法律暗示理论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具体运用。所谓法律暗示理论,是美国宪法学者就法院的司法功能所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判有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并非为某种行为提供合法化依据,也不是监督政府的权力或为司法审判提供法律渊源,而是起到一种暗示功能,即法院通过审理案件向政府部门传递某些信息,并藉此就公共事务的处理促成彼此间的协调与合作。有些学者将这种理论运用到金融法的研究中,认为有关国家机关通过改变管制重点可以促使私人主体在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交流与相互协作,在此意义上,以“管制暗示”一词来指称管制与法律在金融市场变化中所起的作用[6](第44,53页)。
具体地说,法律与管制实现暗示功能的方式包括:为金融市场提供信息并为市场主体的合作提供相关环境;抑制某些消极性的后果,例如制裁某些破坏金融市场协作环境的行为;促进市场主体之间及其与监管者之间的交流,通过强化公司治理等方式促进这种交流的有效性。按照这种理论,金融法的暗示功能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它并不依赖于管制法的具体适用或者监管者约束行为的实际实施,这种暗示所起到的是一种非定向和非后果的限定法作用;第二,它实现的是法律的宣示意义,表达的是法律和监管者对相关行为的态度,也就是说,“法律的效力不仅在于它做了什么,也在于它说了什么”;第三,它并不限于监管者对市场主体的单向指导,有时也会涉及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反向作用,市场关注的重点也可能源自非政府的第三方。
(二)管制暗示在主权债务重组方法选择中的体现
在集体行动条款成为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现实选择的过程中,存在两个方面的管制暗示: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权债权国以及IMF等国际组织发出的管制暗示;另一方面是一些新兴市场主权债务国发出的管制暗示。这两方面的管制暗示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主权债务市场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对于这项选择的预期。
就第一方面来看,最重要的管制暗示应该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集体行动条款的强烈支持。例如,在2003年4月IMF会议上,美国财政部极力主张应当积极推行集体行动条款,并认为正是这种合同方法,而非统一的法律机制,才是解决有关主权债务重组问题的手段。随后不久,墨西哥宣布依纽约法发行25亿美元的债券,在相关重组方案中引入了集体行动条款,对此七国集团迅速给予了肯定,认为其作为投资性借款人为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欧盟国家在境外发行债券时也宣布将集体行动条款引入相关债券合同。上述这些,无疑都是在向国际金融市场发出强烈的信号。其次,七国集团提出的有关IMF紧急援助最小化的目标也是实现这种选择的重要暗示。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地向IMF发出建议,主张严格限制IMF章程中关于救助条款的适用。事实上,这种建议正在逐渐成为现实,例如在俄罗斯、厄瓜多尔、阿根廷等国发生债务危机时,IMF所提供的资金援助就是极为有限的。上述建议及国际金融组织对于危机发生国债务违约的政策态度,迫使债权人对有关集体行动条款适用的市场预期加以调整。再次,IMF提出“重组机制”方案,对于主权债务市场引入集体行动条款也起到了直接的管制暗示作用。借款人之所以会改变对集体行动条款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IMF“重组机制”方案生效的担忧。IMF“重组机制”方案的提出,使市场参与者感受到官方干预的真实压力,与其说被动地实施 IMF的“重组机制”方案,倒不如主动地选择集体行动条款这种市场导向型的解决方案。
就第二方面来看,在集体行动条款成为主权债务重组合同方法之首选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管制暗示。实际上,新兴市场国家早就有改革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意愿,如果不是担心资本市场的声誉风险,债务国可能会更早地引入集体行动条款。比如,厄瓜多尔就曾于2000年提出了以期限更长、利率更低的新债券交换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并为降低重组成本而创造性地使用了所谓“退出同意”(exit consents),这种正式协议允许多数债权人改变债券的非融资性条款,从而使债券的实际价值对于少数不合作者而言大为降低。由于原有债券的流动性和整体价值的急剧减少,少数债权人已经没有动力去拒绝这项新债务交换的方式。此后,面临类似问题的俄罗斯、乌克兰、乌拉圭等国也纷纷效仿,实现了主权债务重组。可以说,新兴市场国家的这种做法为原有市场预期的改变也提供了重要的暗示,它们在IMF没有提供多少支持的情况下实现主权债务重组的能力表明,“债券持有人豁免债务重组的时代已经结束了”[7](第44页)。
(三)管制暗示在主权债务重组方法选择中的作用
分析起来,不同层面的管制暗示所具有的性质与作用并不完全相同。主权债权国和国际组织对于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干预,有的纯粹是暗示,有的也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而债务国的做法则更多的是在对金融体系中的其它合作伙伴释放信息。来自不同方面的暗示以各自的方式对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选择施加着影响。
其一,管制暗示区别于法律管制的重要特征,在于其有效性并不依赖公共机构的强制力。但是,这并不等于管制暗示中不存在某种程度的强制性因素。例如,美国对墨西哥在新债券合同中引入集体行动条款所给予的压力就具有某种程度的强制性,这种压力可以看作是一种暗示作用,但的确对当事方行为的调整起到了一定的强制。又如,IMF坚持尚不具现实可能性的“重组机制”以及美国后来对该方案的态度变化,也是有一定强制性的。与之相比,源自债务国的暗示大都不具有强制性,如墨西哥及一些国家在国际债券发行中适用集体行动条款,起到的是纯粹的暗示作用。当然,带有某种强制性的管制暗示也并没有对上述国际合作起到支配作用,其更多的是通过影响当事方的预期来促进各方的有效合作。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法律和管制是通过调整当事方的动机来实现有效合作,而管制暗示指向的则是当事方的预期。过于草率地引入相关国际法规则而改变当事方的行为动机,无疑会使管制的成本大大增加。由此可见,要实现金融关系的有效调整,管制的强制力并不总是必需,监管机构可以尝试在某些领域通过法律的暗示功能来实现政策目标。
其二,管制暗示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向其它当事方释放信息,通过提高各方可获信息的质量和共识程度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信息可以促进当事方围绕特定问题的协作更为集中,从而有助于相关各方的妥协。管制暗示的信息功能在主权债务重组方法选择中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墨西哥率先在主权债券发行中引入了集体行动条款,尽管可能会对吸引投资者造成负面作用,但墨西哥并未采取折扣式的发行策略,这对于其它潜在的债券发行国而言就释放了相关的信息。又如,IMF在一些债务国发生债务危机时并未介入,而是默许这些国家违约并进行相关债务重组,这也对潜在的债务人和债权人表明了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对集体行动条款等新方法的态度。
四、关于主权债务重组方法未来选择的思考
以上论述表明,管制暗示理论有助于分析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推动主权债务重组方法选择中的作用和互动关系。考虑到管制暗示的重要作用,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在主权债务重组方法未来选择中可能具有的意义。
首先,管制暗示有助于推动主权债务市场就债务重组制度的完善开展进一步的国际合作。尽管集体行动条款已经在主权债券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关于这种条款的具体设计、标准化、少数债权人滥用等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这种情况下,管制暗示的作用就在于促进债权人和债务人就有关规范的确定进行主动磋商与协调,促进当事方在各种可能性和不同的规范之间做出有效选择。随着多种方法和建议的出现,管制暗示可以鼓励特定标准,为各种选择方案提供充分的信息,从而促进有利于主权债务危机化解的有效机制的形成,并尽可能避免一些不成熟的方案成为主流。
其次,管制暗示所具有的灵活性特征为主权债务重组的当事方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有助于提高主权债务重组的效率。考虑到主权债券市场的发展程度、债务国和债权人的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情况,要求统一的方法或许并不合适,而过度的司法审查又会造成法律解释的不一致,反而会增加债务重组的不确定性。相对于监管机构通过法律直接干预集体行动的方式,以列举方式规定诚信义务在成本、实践难度上更为可取,这样,管制暗示所具有的灵活性就得到了凸显。从本质上说,管制暗示为主权债务人和债权人提供了选择他们所偏好的债务重组方式的自由,有助于实现主权债务重组效率的最大化。
再次,管制暗示理论对主权重组方法选择的分析表明了主权债务市场自身在制度引入方面的局限性,来自当事方的管制暗示并不能保证制度选择的最优性。目前,国际上关于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集体行动条款与IMF提出的“重组机制”之间的优劣上。尽管前者在实施成本、政治可行性等方面优于后者,但是后者在加强集体行动、重组程序的透明度与合作性、债权人利益保护等方面都远胜于前者。从理论上说,IMF的“重组机制”应该成为国际社会加强主权债务危机防范和解决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助于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由低效率的一致行动条款向集体行动条款的转变历史过程已充分说明了市场的局限性,而强制因素在管制暗示中的作用也意味着不应过度依赖主权债券市场自身衍生规范的能力,管制暗示并不能保证自发规范的最优性。如果市场自主选择不能奏效的话,那么,IMF及相关国家就有必要动用金融强制手段来促进主权债务重组方法的改革和完善,而恰当的管制暗示有助于实现相关制度的有效选择。
[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Law Committee.2004.“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Berlin Conferenc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LawReview1(1).
[2] David,Skeel.2003.“Can Majo rity Voting Provisions Do It A ll,”EmoryLawJournal52(1).
[3] 李仁真、张 虹:《论国家债务重组的新方法》,载《河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4] 张 虹:《主权债务重组法律问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刘 音、薛 林:《论IMF国家债务重组办法的改革思路》,载《学术论坛》2008年第6期。
[6] Klausner,Michael.1995.“Corporations,Corporate Law,and Networks of Contracts,”VirginiaLawReview81(3).
[7] Bratton,William,&MituGulati.2004.“Sovereign Debt Reform and the Best Interest of Creditors,”Vanderbilt LawReview57(1).
(责任编辑 车 英)
Choice of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 Approaches
Li Renzhen,Yang F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w,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There is a historical stage during choice of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 approaches,i.e.the stage from unanimous action clause to collective action clause.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why collective action clause has become the primary approach of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Compared with unanimous action clause,it ha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in solving problem 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minority holdouts.It is mo re realizable than statutory approach,while it is also concerning the actual structure and demand of sovereign debt market.By the regulatory cues theory,important function of regulatory cues should be valued for choice of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 approaches,while public authorities may propel debtors and creditors choose the efficient approaches in the future.
sovereign debt restructuring;collective action clause;regulatory cues
DF9
A
1672-7320(2010)04-0486-06
李仁真,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杨 方,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9年度重点研究项目(09AFX004)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两种路径之争:公共管理与私营管理关系研究述评
- 权利不可让与规则与环境侵权救济
- 试论夫妻家事僵局及其司法介入
- 票据无因性之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