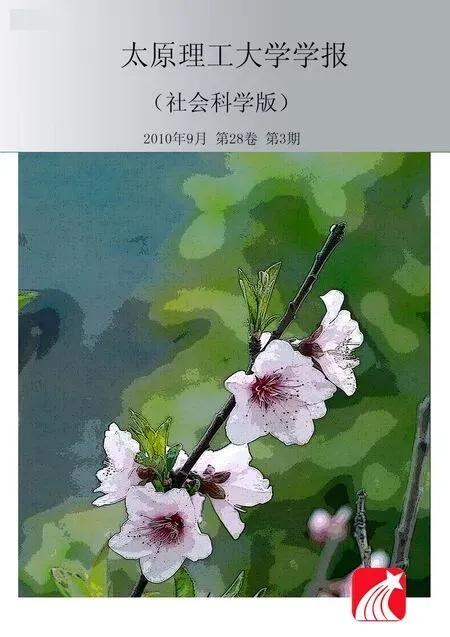心灵在神圣的远古之乡流淌*
——试论吕德安诗歌的美学意蕴
林平乔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史系,湖南 长沙 410002)
虽名列“他们”诗群,但相对于那些热衷于以“冷抒情”的方式沉浸于对鄙俗的生活细节进行罗列的第三代诗人,吕德安的诗呈现出独特的思想意蕴与美学意蕴。他的诗歌语境透明,语义单纯,重视对个人本真的生命经验的表达,在口语语态和纯净心态合一的直接呈现里,体现出个体灵魂的澄明和对温蔼优美的人性的抒写。这种对“简单”与“纯净”品格的有意识追求,可以说既是他诗歌创作的审美观照方式,也是他的表现方法。吕德安在谈到他写诗的动机时曾说:“我把写诗当做自我净化的过程,同时我不希望给读者上轭(所谓的历史感或更堂皇的形式),而是平凡和愉快。我的词汇必须是人在谈话中的词汇,它要支配着我的整个的创作情绪。我追求亲切和睦,做到不把诗当做诗写,而是当做一件事或一个事物。”[1]并承认,他的诗歌“带有一种愉快的倾向。”[2]这种“愉快的倾向” 和“自我净化过程”,集中表现在他虔诚地倾听和静默地感受外物时,对外在世界所取的静观、欣赏的审美态度,以及灵魂与外在世界的无碍沟通和对生命本体意义的会心领悟。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迎合大众化的品位与商业化的浪潮而出现的文学粗鄙化现象,曾经长期迷惑和困扰着人们的心灵。而吕德安这种对具有精神升华意义的“纯净”品格的追求则使他的诗歌创作回归到了传统美学的正途,为人性的净化指明了一种方向。这种在物欲横流和浮躁的时代汹流里的“净化”追求,可以说,既是一种“寻根”之旅,也是一种“返乡”之举。在众声喧哗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诗坛,吕德安以脱俗的气质和对“纯净”这种可贵的精神品质的心灵接近,保持了对无法舍弃的人类灵魂家园的固守,并以他的单纯、质朴、澄静、温暖显示了他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高傲。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读其诗歌的美学意蕴。
一
吕德安和张枣、柏桦等诗人一样,耽于对往昔的怀思,作品中充满着怀旧的意味。这集中地表现在对故乡马尾镇的热爱、眷念,以及在社会转型时期对丑恶的回避,对简单纯明雅致的诗意的坚守。他的许多诗歌,如《献诗》、《沃角的夜和女人》、《小小广场的情歌》、《父亲和我》、《纸蛇》、《吉他曲》、《陶弟的土地》、《另一个冬天》、《泥瓦匠印象》等,就都是对家乡怀想的产物,所以他曾自比为“蟋蟀之王”,说是“要去收回逝去的年月”(《蟋蟀之王》)。他在《天下最笨拙的诗》一文中也坦率地承认:“在我诗歌创作的某个时期,我的灵感主要来源于小时候我在那里生长的小镇,那时候,有人称我是家园诗人,歌谣诗人。”[3]可以说,家乡是他的写作起点,他的创作题材和情绪大都来源于他的家乡——福建的马尾镇。他的这些带有浓重乡土色彩的诗歌,是在他充分感受和体验了故乡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的内蕴后,在 “回忆”中呈现出的心灵化了的乡土生活经验。他试图以这种“乡土叙事”来体认世界和自我,来探究人类的生存本质和生命的本原意义,表现出对自由生命与优美自然极力讴歌的浪漫倾向。在这些诗歌中,家乡的星星、村庄、船坞、断木、向日葵、屋顶、月亮都凸现出鲜明的轮廓,留下醇厚的韵味,表现出静穆、和谐、超脱的文化氛围和纯净朴素的人生景况。而由此形塑出的马尾渔村,则表现出纯洁自然的生活之真和平和淳朴的人性之美。例如《沃角的夜和女人》表现的就是马尾镇这个独具特色的渔村小镇恬静和谐的生活和富有人情味的人生,构筑的是一个安乐、平和、温情的乡土世界。这首诗描写了“沃角”这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小渔村自然平和的“呼吸”,充满着盐味、海风和肉体气息。在这里,人和大海之间充满着亲昵的诗意,而且这种诗意是用日常经验化的意象来表达的,就更显得真实自然。“人们睡死了,孩子们不再啼哭/沃角这个小小的夜已不再啼哭/一切都在幸福中做浪沫的微笑/这是最美梦的时刻。”这种自然内容,和谐、安谧,可以说完全是一种生命情调、生命意志的“物质”表现。生活在此处的人们平和安宁、怡然自得,心灵与外物及环境和谐融洽,显现出“天人合一”的妙境。此外如他的《天鹅》也以优美隽永的笔调发掘了童年记忆中难以忘怀的永恒“美丽”:“圣诞节前的一个傍晚,小镇附近的海面,/一群天鹅游弋;他们十几只,足够可以/在一起度过冬。波光中,它们的逐渐靠近/使一座堆满废物的房子生辉。那是童年的事了。/那时大家不懂得孤独,只知一味地玩。/直到潮湿的春天,来了个流浪汉,一身雪,/要求住下来,又好像要将自己在屋子里埋葬,/而等他终于睡着,大家才感到了某种释放”。 这种回忆虽潜藏着不易觉察的忧郁,却以一种少有的透彻和练达,不动声色地超越了生活本身,抵达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精神向度,沉静地表达了对乡土的眷念与感恩。
可以说,多数时候,吕德安是以温情的眼光眺望乡村,以内在的生命感知接近着乡村,乡村生活已经楔入了他的灵魂,并深深地影响着他诗歌的精神向度。和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乡土作家不同,吕德安笔下的乡土不承载过多的政治反思和文化批判,他总是以感恩的心和宗教般的虔诚对待“乡土”,因而他笔下的乡土形象总是多情、唯美、纯净、感人。他以略带伤感的笔调叙写着记忆中的多情乡土,安静地描绘生动鲜活的乡村图景,在淡定的叙述中,贫穷和苦难都被他悄然消解,只有朴拙纯净的人性与大自然自在地融为一体。因而,这些诗歌带给人的感觉就总是和谐而纯美。在他的《小小广场的情歌》、《纸蛇》、《吉他曲》等诗作中,他都着意地描绘了马尾镇那种宁静古朴的自然环境,写出了这一方土地上乡民特有的禀赋与气质。
和小镇的纯朴风貌、乡民的淳朴人性和他自然的本真情怀相匹配的是,他的诗歌既没有技术上的故弄玄虚,也没有修辞的诡异手段,而是显现出单纯而自然的乡村谣曲气息。正是民谣自由奔放的本色旋律使他感到温暖和自在。他自己曾这样承认:“我觉得我与海子的共通之处就在于:我们彼此都有点乡土味,在诗歌写作中都较大程度上受了民谣的影响。”[4]例如他早期的《芦苇小曲》就用了反复、淳朴的吟唱,有浓浓的民谣风:“飘飘芦苇花/青青芦苇草/抽着假麦穗/泛起层层的浪/用水灌饱她的心/抽着假麦穗/用太阳使她低头/只当作一次收获/用雨水使她哭/还要送到风里去/芦苇花/假的爱情/芦苇花/骗人的爱情”。 语言轻灵飘逸洁净,有着清透而丰厚的情感蕴藉。此外,《小小广场的情歌》、《吉他曲》也集中体现了这种谣曲特点,音调唯美柔和,风格清新脱俗,内容返璞归真,准确而生动地反映了故乡马尾镇的风俗民情、山水特色。这些具有乡村谣曲印记的诗歌,意象洁净质朴,意境恬美安谧,思想如净水般透明,情感如春光般温暖,洋溢着热爱生活、拥抱自然的纯真情怀。
为了忠实于这种乡村谣曲的单纯朴素,在内容的表达上,他的诗作表现出了对沉重的思想内容的自觉“抵制”和对自然景物、日常事物的“竭力求近”,以一种淡定的心态接近事物,聆听“天籁”,描写对象。他自己就曾这样说过:“我倾向于诗歌作品首先是事物而不是思想的再现。所谓的思想只是诗外的功夫,当你面临某种主题时,思想已在其中,表现了对某种价值的关注,但是一件成功的作品是对它的成功转化,使它在诗歌文字里形象化地获得澄清。在我身上,将思想消解为对事物的一种深层的态度和趣味,或者说某种意向,不可言说,却时刻渗透在字里行间,正是我在写作中所致力达到的。”[5]事实上,他的许多诗歌也只是客观地呈现“事物”,而“思想”或“情感”则隐藏在所描写和叙述的自然景色和“日常生活”里。例如:“半明半暗的山谷/月亮高挂,星星低垂,/一条溪水旁边,/悠悠几户人家。……远处/山峦上盘绕的货车扫来/车灯,照亮了半截房子/都朝圣似的向城里爬去”(《 群山之中》),“他们全是本地人/是泥瓦匠中的那种泥瓦匠/同样的动作,同样的谨慎/当他们踩过屋顶,瓦片/发出了同样的碎裂声/再小心也会让人听见/等翻开瓦顶,下面的尘埃就升起来/像复活的虫。”(《泥瓦匠印象》)所以,有评论者认为,他的诗往往 “因质朴而简单,因简单而重获力量”。他自己也在他的《除草 ——悼念父亲 》一诗中表达了这样的写作追求:“让我们回到 /简单又简单的 /事物中”。吕德安曾将自己这种“质朴而简单”的诗称之为“天下最笨拙的诗”。而诗评家陈仲义则大加称赏,认为“笨拙,是诚实中的地道本色,是天真的原始伙伴,好比国画大写意中,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迟疑,寥寥几笔,能除祛铅华繁褥,显出‘稚拙’的意味和‘澄清’的景象”。[6]确实,吕德安的诗歌讲究删繁就简,注重对题材的提纯和净化,他善于把生活中的意象用潜藏的感情细丝进行精心的编织,而看似普通的意象就在不动声色中表达着他的思想内蕴和安宁沉潜的心境。例如《两个农民》就是这样的一首诗歌:“两个农民把篱墙外的/那片山坡上刮干净,/要不是我喊到此为止,/他们准会干到那阴森的/林子那边,不知不觉。/‘啊不!’我让他们回头/用剩下的时间清理溪水,/再将那片篱笆逐个地修长。//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我心想,过不久这里还会/长满荒草,山上的石头/还会滚入溪里,东倒西歪。/这么大的地方我可管不好,/多年来邻舍间的一块荒地,/如今让我叫人梳理出来,/才放下一片片可爱的树篱,/占为己有了,才意识到/当初谁也不愿先动它,仿佛是/大家喜欢守着它的荒芜/和那原始的静默一片。//现在可好,一整天心绪不宁,/没准邻舍还有一片怨言:/我占有了我们之间这片荒地,/就把他推向更远的荒芜”。 他以一种平和的眼光看待他生活着的那一片土地上的人与物,并力图以一种淡定的姿态发现和表现生活中的本真之美。在对外在的客观世界提纯的同时,他也简洁而隽永地表达了“自我”内在精神世界的澄明。
可以看出,在吕德安的这些乡土诗歌中,始终存在着一种躲避喧嚣、异化、龌龊的现实的乌托邦理想。在他的笔下,故乡马尾不再是纯然的乡土,而是精神的寄寓所和灵魂的栖息地,寄寓着他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审美情趣和人生理想,体现的是他诗意的乡村愿景和理想的人生形式。在马尾这个自足而封闭的浪漫化的乡土世界里,隐藏着他对古典浪漫生态的惋惜和追慕,以及对外在的病态世俗的对抗和叛逆。在对乡土人生、世俗人生的审美性书写中,他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美丽而温暖的“精神世界”。海德格尔曾说过:“故乡是灵魂的本源和本根。”[7]吕德安塑造的这个具有启示性的“精神世界”,就正体现出了意味深长的“还乡”意味。可以说,他的乡土诗歌通过对马尾风物人情的描写,对宁静和谐生活的言说,对本然纯真天性的眷恋,表达了他对生命本原意义的追诘,对和谐家园的渴望,展示出他创作思想和审美意识中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
二
另一方面,吕德安的“怀旧”又表现为在社会转型时期,对即将逝去的纯明诗意和善良人性的固守。在他的诗歌里,很难窥视到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物欲横流、实利媚俗、金钱至上的浮华场景和精神萎靡、道德沦丧、灵魂下滑的现实境遇。他就像一个隐逸诗人,专心致志地守护着他心中洁净的精神家园。他既不像“非非”诗人、“莽汉”诗人那样“冷静”、“诙谐”,也不像标举“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一样,以居高临下的圣者眼光和知识精英的悲悯情怀远距离地审视俗众和生活,而是将自己“渗入其中”,体现出与民融合、同等同乐的平和心态与俗世情怀。多数时候,他的灵魂是真诚、朴实、喜悦、圆融的。陈仲义曾这样评价吕德安:“在第三代喧嚣的诗人群中,他属于少数不紧不慢,不慑不火、悠悠恬淡的那类人。”[6]确实,吕德安的诗歌回避了沉重的话题和丑恶的事物,他总是以他的善良与宽容来化解、冲淡现实中的丑陋,力求让人们看到生活中的亲切、真诚的微笑,可以说,他是生活的化妆师、美容师,他把他的真诚、善良、澄净化作光明恬美的色彩涂抹在卑污丑陋的生活上了。譬如他的《门》就是这样的一首诗。诗中的“他”就像一个心平气和、面带微笑的绅士,在和知心朋友作着倾心交谈,他不愤怒、不气恼,永远保持着那种处变不惊、气定神闲的姿态,他叙说的虽然是一个不文明、少教养的主题,可他却以不经意的从容淡定的语气叙说着,丝毫没有把他的愤怒、不满加进去,或者说,他已经超脱了使气动怒,他就那么轻松愉快地给你讲述着。“隔壁那扇艰涩暗然的门重重关上/它砰的一声却把我的门给震开/因为在家时我的门总是虚掩着/所以隔壁的门只要关上一次/总会通过我们之间那堵薄似月亮的墙/一下子震开我的门。记得头一次/我当真吓住了,还多次本能地张望/后来到底还是习惯了/也不去抱怨这倒霉的时光/说真的,自从觉得这不是敌意的侵扰/我就一直克制住自己被动的情绪/任凭它优美而驯服地靠向一步”。以一种宽容体谅的心来对待生活中的“不和谐”。他的写作虽立足于日常经验,却又能够以一颗恬淡宽容的心超越日常与庸常。此外像他的《献诗》也有意消除了劳动中的辛苦、艰难、无奈等异化因素,散发出一种诗意化的生命情调,反映的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审美理想和情趣。“装草的人似乎很懂得/享受这一大片青草/他把草堆得很高/远看就像房子一样”,这里的中心就是“享受”。他既立足于现实,真实地反映劳动生活;又超越现实,以怡然自得、平和悠缓的笔调,抒写着劳动者的快乐。在这里,劳动是自觉自愿的、具有审美性的一种活动,不带强迫无奈,不具有“心为形役”、“人为物役”的异化特征。清香的土地,青嫩的牧草,愉悦的劳动者,透出一种纯真而浪漫的情怀。“草场上有人在装草/小小的马车闪耀金光/四周空空荡荡/唯有他在漫游歌唱……眼前还有更大块的青草/等候他下次再来/等候他记得下次再来/置身在这绿色的怀抱”。对这种悠然的农耕文明的反顾与诗意描写,应该说,包含的是他对当下的“异化”劳动的一种反驳与抵制,体现的是他对这个世界的亲切友好。即使在对“死亡”这样沉重、恐怖的主题的表达上,他的心态也是轻松的,平和的,表现出一种惊人的豁达与达观。例如他的《死亡组诗》中的死亡幻象就唯美而温馨,亡者的灵魂仿如光洁的瓷在青淡的天宇下从容地悠游,轻松而自由,闲适而美好。“由于时间,我将比自己走得更远/像泥土的瓷,光洁犹如紫晶的肉体/而灵感的手指尽头是月亮/带着十一月的寂静和温和/我看见我的庄稼一望无际,至少/我还可以暂时住下不离开/看着夜,这个即将收割的庄稼/看着它那边的黎明千万只耳朵聚集成教堂”。“多么奇险的黑暗呵,每一次经过死亡/都会抖动缀满星辰的羽毛/好像正处在难言的满足状态/借助回忆消化眼前的欢迎”。语言是那么的轻盈亲切,仿佛不是在描写死亡,而是在畅谈美妙的理想。
在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上,吕德安也表现出与许多具有先锋、激进特征的第三代诗人不同的品质。他的叙述语调始终是冷静感性甚至超脱的,他更像一个“中世纪”的隐逸诗人,静静地、远距离地打量着身外的世界,那种直接面对日常生活而生成的情感仿佛纯真无瑕、浑然天成。例如他的《父亲和我》就是如此。诗中虽然充满着对父亲的感恩,但却如静水流深般无言,情感与思想只在语流中悄然潜行。“父亲和我/我们并肩走着/秋雨稍歇/和前一阵雨/像隔了多年时光/我们走在雨和雨的间歇里/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我们刚从屋子里出来/所以没有一句要说的话/这是长久生活在一起/造成的/滴水的声音像折下一条细枝条/像过冬的梅花/父亲的头发已经全白/但这近似于一种灵魂/会使人肃然起敬/依然是熟悉的街道/熟悉的人要举手致意/父亲和我都怀着难言的恩情/安详地走着”。诗中体现的是沉默的感恩和单纯的抒情。在对父亲的欣赏和尊敬的背后,映现的是“我”和“父亲”心有灵犀的沟通。写得那么柔软入心,富有温情,充满隽永的魅力。此外,他的《夜晚的叉道上》也体现出直指灵魂本质的倾向:“不管怎样/我们都来尽情地欣赏它们/低下脖子,非常优美地/享受一天最后的青草。”他就这样以一颗“欣赏的心”和“安详的心”,袒露着不涉功利的透明洁净、冰清玉洁的自我灵魂。
确实,吕德安的诗歌是感性、透明而“浅表”的,它不深沉、不冷峻、不让人觉得压抑。但他并不排斥对题材作深层开拓,也并不“拒绝隐喻”,他的诗中流溢出的思想就像山岚、雾霭,始终漂浮在意象的上层,澹泊亲切自然得令人喜悦沉思。他似乎总是以一种轻松的语调、温柔的絮语和你谈着心。他的诗句很容易飘进人的灵魂,让人的灵魂驯服柔软,这是他诗歌的魅力。他即使表达深刻的哲理,也总是使用这种舒缓平和的超脱语气,平实的语言里蕴含着让人掩卷沉思的深意。他的语言多半是一种直觉的呈现,但又散发着洪钟般辽远的意义。譬如他的《启示》就是如此。“我们的时辰就像身边坠落的叶片/稍不在意就堆积满地/这些叶片摆脱了树枝/就来纠缠我们的脚步/如果这只是一种幻觉,而我们/又万事像风一样顺利/我们对此就会毫不犹豫地/欢笑地走向目的地/可往往因为烦躁或困惑/和树一样停立酗酒/无休止地重复单调的语言/时间就给你一身落叶的感觉/也许还会有空隙,让鸟儿啁啾/从暗里飞出,让鸟儿筑巢/也许还会有爱情,但时辰一到/这一切终将把你窒息”。平淡的语言与朴素的哲理相融相洽,轻浅的语言“表情”里映现出的是睿智而透明的“心灵”。他以冷静、平和的语言揭示着生命的本质:生命的过程就是消殒的过程,人生的忧虑和苦难与人生的年龄、深度成正比,死亡是生命无可逃避的最终走向,坦然面对死亡,尽量使生命的过程如花朵般绽放饱满的纯粹的璀璨,这就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此外像他的《沉默》也是如此:“基于我对时光的认识/我深信黑暗只是一片喧哗/找不到嘴唇的语言/像爱,像雪——/ 沉默是否就是这样一种黑暗/在他的阴影下,我尝试着说话”。在这里,陈述与评价混杂于一体,简短的说明和精当的评论让情感与思想闪烁于简明的语境中。应该要指出的是,他的“浅表”和直觉与海子不同。海子的“浅表”下潜隐着富金般的文化沉积,惹得人如掘矿般深究。或者说,吕德安表述的哲理多半是平面的“弥漫”,而海子表述的哲理则多半是立体的“深藏”,思想的触须悠长隐蔽,让读者难以企及,难以产生共鸣,这样他很容易就成了仙界诗人,而吕德安不是,他任何时候都像一个温蔼的人间诗人。他惯于从生活现象入手来抵达存在的本真,注重对日常生活与纯美情感的沉静而直接的发现与书写,在对生活的原初形态作直观呈现的同时,凸显平和温蔼优美的人性。例如他的《独生子》就着意发掘了隐藏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的纯美人性,体现出“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旨趣:“花巷幼儿园门前/父母们都来接各自的孩子/都很有耐心/手里牵着自行车/有的还干脆到附近兜个圈/再回来。都在看表/但并不焦急,因为 /时间明摆着还早/都像在等着一个天堂/把孩子开放,排队出来/当然有时是一窝蜂地/不过别急,每人都有一个/都有机会推孩子一把/去跟就近的孩子说声再见/然后大人们也可以顺便/彼此笑一笑”。又如他的《漫游者》以一种轻柔自然的语气,赞颂了一个普通人的几近透明的善良品性:“他常常让出房间 /为朋友和他们的/情人们幽会—— /就一个晚上或两个晚上/他理解这种事/过去他也有过/这样的请求——/就一个晚上或两个晚上/白天和黑夜/他家里都铺着床单/没有人会对此感到厌倦——/就一个晚上或两个晚上/听见熟悉的敲门声/他又准备好去漫游 /谁知道他会去哪里——/就一个晚上或两个晚上”。 这种善良是那样的自然本真,丝毫看不到矫情,完全是真诚地发自内心,不知不觉中就能引导人们进入了一种心地澄明、若有所思的超脱境界。
总之,吕德安描写的内容虽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独具匠心;语言看似不经雕琢,仔细品味却巧夺天工。在他的诗中,很难找到奇特的意象、瑰丽的夸张、华丽的辞藻,但平淡自然中却独有韵味。应该说,这样本色、自然、单纯、沉静的诗风是由吕德安崇尚自然纯真的人生态度所决定的,而由此映现的则是他灵魂的纯净。
三
吕德安的诗歌以热爱自然与生活的情感暖意让人看到了人性的本真透明与生活的美好轻松。人们也很容易从他的诗中读到生命从沉重走向轻逸的意味。正如他在《蟋蟀之王》中所表达的:“经过深沉的思虑,如今/天上的群星为我释放光芒/剔透净亮永无止境/就像只有心灵所能接触的河流/在神圣的远古之乡流淌”。虽同属于第三代诗人,但吕德安的诗歌与坚持“零度写作”的“冷色”诗人的诗歌却构成了生活的双面镜,共同反映了转型期人性异化、人情冷漠与人性古朴、人情本真的两面。吕德安歌吟的是立足于传统文化的人性人情,而“冷色”诗人描写的是走出传统文化、立足现代文明的荒原心态,这种情形,极似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与“海派”。虽置身1980年代中后期这个喧嚣浮艳的当代社会,但吕德安的心灵却似乎总是保持着古朴的清澈和悠缓的节奏,即使有触及到社会的不和谐或生活的卑污,他那种内在的本真朴素也会将他的灵魂引领到简单纯净的世界,这使他拥有着一份以怅然若失的、不易察觉的忧伤为生命底色的纯粹和与丑恶隔开的孤独。而正是这种来自生命最深处的忧伤和孤独,使他的心灵很容易进入到一个恬然自适的寂静之境。因为浸淫于这种理想的具有古典氛围的寂静之境,所以他始终能悠然地用近乎民谣的本真诗歌来呈现他的家乡风貌、世俗生活以及恬淡心灵,并对他所描写的对象和赞美的生活“保持一种沉静的谦恭”。[8]可以说,吕德安不是那类承担历史的诗人,也不单是为自己的心情而写作的诗人,而是以对世界的善良与诗意的感觉方式,超越着庸俗与病态,并在古朴的乡土和本真的世俗中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的诗人。从根本上说,他是一个渴望借助诗歌的翅膀实现飞离现实之丑的诗人。他就像“隐藏在寂静的花朵后面”(《狐狸中的狐狸》)的倾听者,聆听着来自大地与心灵中的纯净与澄明,并以之为人性之“根”,以之为“还乡”之本,引领人们归依朴实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 万 夏,潇 潇.后朦胧诗全集(上卷)[Z].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252.
[2] 徐敬亚,孟 浪,曹长青,等.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Z].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118.
[3] 陈 超.打开诗的漂流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306.
[4] 曾念长.吕德安:我用诗歌说话[N].厦门日报,2003-03-10(4).
[5] 吕德安.回答曾宏的十个提问[J].诗生活,2003,(1):32.
[6] 陈仲义.装草的诗歌,搬动石头的诗歌——吕德安论[J].诗歌月刊,2004,(6):9-10.
[7]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9.
[8]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