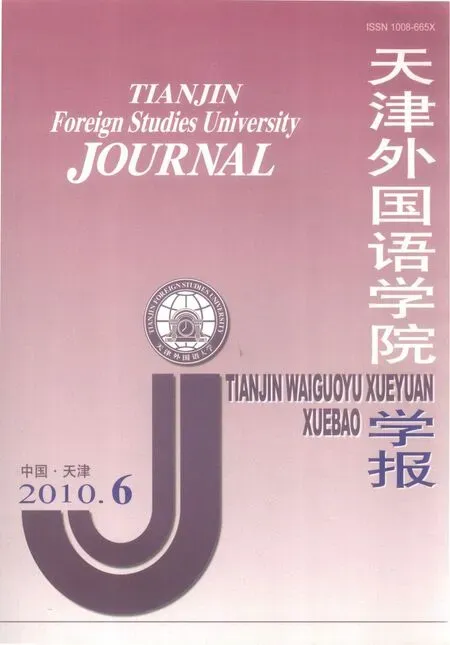论《日用家当》对日常生活的批判
李荣庆
(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临海 317000)
论《日用家当》对日常生活的批判
李荣庆
(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临海 317000)
母女关系是美国黑人妇女作家艾丽丝·沃克《日用家当》描写的主要内容,作品的主题是对母亲实用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它的发表带动了 20世纪末女性关系写作的热潮。母亲的日常生活状态决定其思维中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特征。女儿迪伊则生活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政治风暴中心,其思维更为日常生活以外的政治斗争、种族反抗、平等权利以及美学等内容所占据。因而,小说中母女关系的疏远应该从日常生活的二元对立的视角来解释。
母女关系;日常生活;民权运动;妇女作家
一、引言
《日用家当》是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于 197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小说出版后被收入美国和中国的教科书中,引起持久而广泛的评论。很多人认为,这个故事的主题写的是黑人被子文化遗产的问题 (Farrell,1998;W hitsitt,2000;Cowart,1996)。的确,在这个故事中作者对黑人被子有非常精致的描写,而且母亲、大女儿迪伊(Dee)和小女儿麦姬 (M agie)正是通过被子遗产将故事推向高潮。1982年,沃克因小说《紫色》获普利策文学奖,这一荣誉也使《日用家当》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黑人被子遗产成了家喻户晓的故事,黑人被子的遗产地位在现实中也逐渐得到确立,成为黑人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于是,当人们再次阅读《日用家当》时,小说的真正主题遂为被子遗产的光芒遮掩。笔者认为,《日用家当》主要是一篇讨论母女关系的作品,它的深层主题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本文将对《日用家当》在美国 20世纪末母女关系小说的复兴的整体经验中的意义展开探讨,并从日常生活的二元对立的角度分析作品中产生母女关系疏远的原因,从而对小说中日常生活的批判主题进行确认。
二、引领母女关系题材的复兴
对《日用家当》中母女关系的探讨应该从 20世纪末美国小说中母女关系题材的整体经验来把握。20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美国文艺界经历了女性作家母女关系题材小说的复兴。1976年,美国诗人兼文艺批评家艾德里安娜·里奇(Ad rienne R ich)在其经典著作《妇女所生》中将刚出现的少数女性关系作品称为等待界定和分析的“没有写出的伟大故事”(R ich,1976:225)。此时,这些少数的女性关系作品中就包括爱丽丝·沃克的《日用家当》。在以后的短短 20年间,美国各族裔女性作家提供了数以百计的母女关系题材的文学作品。1993年,在其专著《美国短篇小说中的母女关系》中,苏珊妮·卡特 (Susanne Carter)对美国 20世纪末 249种 193位作家的母女关系题材小说进行了界定和分析,把文学想象中的母女关系归纳为六种理论模式。这些模式对理解《日用家当》在母女关系作品中的定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1)在苏珊妮的分类中虐待和忽略(abuse and neglect)是母女关系题材中反复出现的模式。母女之间的天然联结并不总是产生亲情。一些女性初为人母时并没有作好承担母亲责任的准备。她们之所以成为母亲是由于早恋、强奸、乱伦等偶然事件。她们不愿意接受母亲这样一个事实,从心理上更排斥女儿,经常造成对女儿身心的虐待和忽略。(2)衰老(aging)和养老责任也是母女关系作品的常见主题。母亲对女儿的权力是天赋的。随着母亲的衰老和女儿的成年,母女的权力关系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化,母亲和成年女儿之间的冲突随之而来。此外,这个主题中还包括对衰老母亲照顾的责任问题。在此,母女关系的亲疏充满着变数,反映着人性的善恶和世态之炎凉。(3)很多作品的主题表现的是母女关系的疏远或异化(alienation)。母女关系经常被难以解决的矛盾所困扰。在不少情况下,母女相处一室,却终日无一句话可说。母女对待婚礼程序、民权运动、物质享受、家庭价值、同性恋等事物的不同认识和态度,均可能产生母女异化。(4)母亲的死亡(death)是母女关系中的重要时刻。母亲临终前或女儿丧母后,母女关系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5)左右母女关系的主题还有期望(expectation)和养育(nurturing)。母女之间是否能够达到相互的期望和如何对待母亲的养育之恩是一个传统主题。这个主题继续在一些作品中得到突出的反映。(6)苏珊妮把一些难以归类的若干描写母女关系的小说划入肖像(portrait)类。苏珊妮在对母女关系小说进行梳理并试图理论化的过程中,明确地把《日用家当》归类为母女关系作品,并把它定位为疏远或异化模式(Carter,1993:3-109)。
较早对黑人母女关系作品作专门研究的有格洛丽亚·约瑟夫 (Gloria Joseph)。1986年她在《黑人女性主义和白人女性主义视角的冲突》中主张理解黑人母女关系不能避开种族问题,也不能完全沿用白人母女关系的模式,更不能忽略黑人妇女自有的历史文化经验。她特别主张研究黑人母亲和女儿时要注重家庭结构等其他问题。格洛丽亚在讨论中特意把沃克列为母女关系作家(Joseph,1986:75-81)。1991年帕崔夏·贝尔斯哥特(Patricia Bell-Scott)汇集 47位黑人妇女作家探讨母女关系的各类作品为一编。这本题名为《双线缝纫:黑人妇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和女儿》的作品集虽然重点放在母女关系上,但是对姊妹、朋友、同事和情人关系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表现出黑人批评界对黑人母女关系特点的理解(Bell-Scott,1991:1-10)。《双线缝纫》收录了《日用家当》这篇小说,再次确定沃克的这篇小说是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2001年卡罗林那·罗蒂(Caroline Rody)出版评论集《女儿的回归:黑人和加勒比妇女的历史小说》。这是对 20世纪末黑人母女关系文艺作品的总括之作。其中若干议论虽非完全针对《日用家当》而发,但用以注释《日用家当》在这一时期女性关系作品中的地位却是非常合适的。第一,20世纪 70年代末开始,黑人女儿以一系列不同的角色出现在众多现代黑人妇女作家的书写之中。这个女儿不是美国黑人文化中传统的人物。她是一个求新的形象,是一个严肃、专注而强大的黑人姑娘。这样一个女儿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她现在用追求自己的复兴来补救过去的缺席。这个年轻的黑人女性形象的回归成为美国黑人妇女“复兴”的精神化身。第二,这个美国黑人妇女复兴出现在 20世纪 70年代,但却与黑人妇女 60年代的觉醒相互联系。它是民权运动、黑人权力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中的“革命中之革命”。这个复兴渗入到文学领域,并在美国文化和公共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第三,这些女儿出入于历史题材小说中。黑人妇女作家已经明白,以前历史小说总是在给定的大写历史当中进行书写,而现在作为文化权力的群体,她们产生了用文学重塑历史的欲望。由于她们的写作,历史将不再是独家历史。按照托尼·莫里森的话来说,“历史会比将来变得更加不确切”。第四,1970年以前,除了格温多林·布鲁克斯 (Gwendolyn B rooks)、玛格丽特·沃克 (M argaretW alker)和洛琳·汉司白瑞 (Lorraine Hansberry)之外,美国知名黑人女性作家不多。但是,这一年托尼·莫里森的《最蓝色的眼睛》、艾丽丝·沃克的《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和玛娅·安吉鲁(M aya Angelou)的《我知道为什么笼中的鸟儿会歌唱》同时出版,开启黑人妇女的写作热潮。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黑人妇女作家母女关系作品源源不断地出现,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成了一种出版现象。它一直延续到托尼·莫里森的《宠儿》(1987)、泰瑞·马克米兰 (TerryM acm illan)的《妈妈》(1987)、格洛丽亚·内勒的《母亲节》、夏洛特·沃特森·舍曼(CharlotteW atson Sherm an)的《黑色身体》(1993)及以母女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另外十几种作品的出版 (Rody,2001:1-50)。要言之,美国的文学从来没有像 20世纪末的母女关系作品那样解构和重塑美国的文学和历史。而正是《日用家当》等先驱作品的发表才促使了女性写作话语的形成。在以往的文学和历史的叙事中女性只是作为丈夫的妻子、儿子的母亲、父亲的女儿、男人的情人出现在男权话语的作品中。女性因男性的“他者”而有意义。而在《日用家当》中我们看不到兄弟和父亲的踪影,迪伊的男朋友也仅仅是一种打诨的衬托。自此以后,在纷至沓来的女性关系作品中,男性的缺失逐渐成为时尚。作为母女关系作品《日用家当》在这个复兴运动中占据着开创者和领跑者的历史地位。
三、母女之间的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
苏珊妮把《日用家当》中的母女关系归入疏远和异化模式。本文对此提出异议。因为用这种模式对小说中错综复杂的冲突进行单一的因果关系分析显得十分乏力。细读《日用家当》,我们发现,母亲和女儿迪伊之间的冲突并非为被子遗产所引发的,她们之间的冲突是多方面的。在笔者看来,《日用家当》中母女间的冲突应该从美国 20世纪中期现代性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二元对立的角度进行审视。唯其如此,小说中的冲突才能够得到更好的说明。日常生活理论原本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体再生产理论的余脉。法国思想家昂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1901-1991)潜心研究凡 30年,先后出版三卷《日常生活批判》,被公认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近年来西方学界对日常生活的讨论活跃,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定义及内容纷争很大。在对《日用家当》的讨论中,本文把母女生活的家庭和学校分割为日常生活空间和非日常生活空间。按照列斐伏尔的体系,这样做也许并不十分妥帖,因为在列斐伏尔那里日常生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它无处不在。以此推之,即便女儿迪伊是生活在民权运动中充满意识形态纷争的学校里,日常生活也伴随着她。不过本文倾向于采纳阿格妮丝·赫勒 (Agnes Heller)在《日常生活》和本·海默尔 (Ben H ighmore)在《日常生活和文化理论》中表述的关于日常生活空间的概念。在赫勒和海默尔看来,家庭无疑是日常生活发生的重要场所,而政治、科学、艺术和哲学活动都发生在远离日常生活的领域。
在《日用家当》的故事里母亲和小女儿麦姬过着悠闲而传统的日常生活。从小说《日用家当》(Everyday Use)这个题目和它的内容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沃克的创作本意是在书写一种与“妇女传统家庭相联系的私人”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H ighmore,2002:12)。从《日用家当》的背景中我们可以确定如下一些日常生活特征:第一,它是现代生活中单调和重复的日常生活。在小说中,母亲的日常生活就是看电视、使用手工和缝纫机进行缝纫。星期天则到教堂里参加活动。这种日常生活状况具有与现代性共生的“单调和无聊”(ibid.:6)。第二,它是现代社会中的传统日常生活。母亲用扫帚打扫庭院。家里饮食还带有种植园时代的痕迹:猪大肠、羽衣甘蓝、玉米面包和红薯。母亲食用自家奶牛生产的乳制品。虽然母亲已经知道现代汽车等交通工具的便利,但是她从未出过远门。母亲最远的出行是步行一英里半到附近的农场目睹黑人农民端枪戒备白人的情景。母亲从电视片中知道有个外部世界,不过村庄以外的世界对她来说大都只能是“想象的社区”。这种情况很符合日常生活的边界定义:对于一个终生从未离开过村庄的村民而言,村庄就是日常生活的边界 (阿格尼丝,1990:256)。第三,它是一个女性的日常生活空间。它的主角是母亲和两个女儿。故事中的主要情节围绕着母系传统展开。迪伊的名字和故事的主要道具拼花被子以及它的缝纫技巧都是从女性祖先中传递下来的。第四,这种日常生活的思维具有经济性和实用性。母亲的一切活动都与实用和家庭经济相关。她有粗壮的手,可以干男人的力气活。她肥胖的身体可以抵御冬天的寒冷。她自己屠宰生猪,并且可以把冒着热气的猪肝在火上烧烤着吃。她缝制拼花被子不是为了美,而是从节省的角度对旧衣物进行再利用。她已经有了缝纫机,但是她还是教会了麦姬怎样手工缝制被子。因为在她的思维中,手工缝纫是妇女应该掌握的必要生活技能。母亲日常生活的目的就是获得足够的食品和衣物使生活延续下去。她心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小女儿的出嫁作准备。此外,她的生活和思维中缺乏新意,缺少审美和浪漫情趣。这一切都使母亲的生活符合“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的日常生活定义 (同上:4)。
《日用家当》中的大女儿迪伊是以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身份出现的。从家庭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属于“男权社会公共空间”的非日常生活范围 (H ighmore,2002:12)。对迪伊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的高校和社会上的活动,作者沃克没有给予具体描写。但是我们从作者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品里却可以看到迪伊在学校的身影。在沃克笔下高校里的黑人女孩正在狂热地卷入波澜壮阔的民权运动和“革命中之革命”的妇女运动。在萨克逊(Saxon)大学为了反抗学校当局把她们培养成真正的淑女,黑人女学生整夜地进行示威游行,组织向政府请愿的和平进军,高唱“我们一定胜利”的歌曲,并在街头与警察对峙。(W alker,1976:38)。1967年,哈罗得 ·克鲁斯 (Harold Cruse)在《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中告诫黑人“没有一个黑人文化制度的发展,黑人运动不可能取得进步”(Craig,2002:16),从而推进了汹涌澎湃的黑人文化制度的重建运动。从《日用家当》的情节中我们知道,迪伊对黑人文化制度的重建特别关注。她亲身探索着从服装、发式、语言、名字、宗教到饮食和艺术等各个方面对文化身份的追求。在服装和发式上,黑人曾经受过种植园主严格的控制。在废奴之后的 200多年里,黑人曾努力追求和发展着自己的服装和发式风格。现在民权运动又激起新的服装和发式变换的潮流。非洲长袍成了黑人女性民权运动活跃分子将自己与白人区别开来的象征。在现实中作者艾丽丝·沃克本人曾积极参与民权运动,而且为拥有肯尼亚长袍和乌干达长袍而自豪。在作者和小说人物关系上,不少研究者指出《日用家当》中的迪伊正是作者的自我写照(W hitsitt,2000)。美国黑人的发式变换体现了黑人运动价值取向的变化。在 20世纪 20和 30年代,黑人妇女倾向于将自然曲卷的头发拉直 (conk)。她们认为,这样做不仅美观,也能表现出民族的骄傲。而在民权运动期间,拉直的头发开始遭到部分黑人的强烈反对。美国极左穆斯林黑人组织“伊斯兰国家组织”便始终拒绝直发,认为它代表白人的审美标准,主张黑人蓄天然曲发。于是直发还是曲发成了争论的焦点。1962年到 1968年之间,非洲爆炸发式 (The A fro)出现在女性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当中,成为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另一种民族自豪感的象征和时兴的发式选择 (Craig,2002:153)。在民权运动中,黑人语言民族主义激情也在挑战着英语语言的唯一性。阿拉伯语、斯瓦西里语、乌干达语和其他一些非洲语言中的简单问候语在黑人社区流行并成为时尚。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热衷于举办非洲语言学习班。将非洲语言列入社区学校语言课程成为争取平等权利的重要内容 (Farber,1994:125)。在民权运动中黑人的名字也成为改革对象,因为黑人的名字在历史上经受了太多的屈辱。先是,黑人的集体名字经历了黑鬼、黑人、有色人种、非裔美国人等一系列的变化。黑人个体名字的改变也经历了向白人求同到追求独立文化身份的变迁。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 X、拳王阿里、著名诗人勒鲁伊·琼斯都为去掉奴隶制的痕迹而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更名的风气遍及南北黑人社区。基督教曾经是美国黑人几乎唯一的信仰归宿。从“伊斯兰国家组织”30年代出现起,黑人穆斯林化就在美国蔓延开来。而在马尔科姆 X加入“伊斯兰国家组织”并以杰出的口才向黑人传播其政治理念以来,大量的黑人皈依了伊斯兰教(Perry,1991:122)。在饮食上,过去南方的奴隶主把不愿意吃的猪下水扔给黑人,逐渐形成黑人饮食中对猪内脏的偏好。现在民权运动激发了黑人对自己传统食品的热情。他们倡导这种食品,称其为“心灵食品”,为黑人文化张目。但是,反对的声音表示所谓“心灵食品”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它让人们联想起奴隶制的耻辱,而且所谓的心灵食品含有太多的动物脂肪,对健康不利,理应放弃。“伊斯兰国家组织”领袖伊利亚·穆罕莫德多次发表讲话,号召黑人放弃“心灵食品”。尽管这种被称为“心灵食品”的饮食形式颇受争议,争取平等权利的黑人大学生们仍然要求学校当局把“心灵食品”列入食谱之中 (W itt,1999:82)。而马丁·路德·金等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们则经常积聚在亚特兰大的“心灵食品”饭店里筹划示威游行活动。在艺术领域,最新的趋势则是人们忽然把艺术的目光投向了黑人被子。作为艺术收藏品,以往只有白人的被子在美国各地博物馆里占据一席之地。而现在从耶鲁大学到纽约工匠博物馆,黑人日常的被子到处被当作艺术品进行着专场展出。黑人被子背后隐藏的悲壮的传奇故事到处被人谈论。那些从南方乡下收集来的色彩反差极强、针脚极粗、用各种旧布料杂乱拼凑起来的黑人手工缝制的被子一下子成了真正震撼人心的艺术品。
与母亲所处的宁静而单调的日常生活环境相比,迪伊在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中经历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在这里,迪伊的生活不再局限于实用的和经济的诉求。即便她的活动与吃饭穿衣、头发式样相联系,但这些已经超越了果腹御寒和日常理容的意义。在迪伊的思维里这一切已经和政治、民族以及审美意念联系在一起了。
四、日常生活和外部世界的冲突
迪伊作为女儿从多变的,非日常生活的外部世界回到了家,她与母亲的冲突接踵而来。我们不能否认母亲和女儿的性格因素曾影响着这对母女之间的正常关系。迪伊秉性倔犟,蔑视一切权威。她可以一连好几分钟不眨眼地死瞪着你。向母亲索取东西时不达目的不罢休。母亲年轻时也曾经是意志坚强的女性。母亲在迪伊离开家之前就显现出与她疏远。比如,迪伊少年初恋,母亲并没有给予应有的指导。迪伊和麦姬都为母亲阅读过书,但母亲对姐妹俩阅读的评价截然不同。但是就《日用家当》中母女关系冲突的主要情节而论,疏远是源自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而性格因素或拼花被子造成的冲突则占据次要地位。
《日用家当》是以母亲叙事的形式来书写母女关系的。读者在分析其中母女关系的冲突时要超越母亲赋予文本的日常生活的思维导向。迪伊回家后由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间的冲突引起的母女关系疏远可以从六个方面认定。第一,母亲不习惯迪伊的衣着和发式。在母亲眼里,迪伊为追求独立的种族文化身份而穿的非洲长袍虽然好看,但特别刺眼。母亲不理解在大热天里,女儿为什么穿着一件拖地长裙。而且裙子的颜色也花哨得耀眼。母亲感到“整个脸颊都被它射出的热浪烫的热烘烘的”。母亲看到迪伊的“头发像羊毛一样挺得直直的”。她不懂迪伊的发式正是那种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发明的非洲爆炸式。母亲更不懂迪伊男朋友“像一只卷毛的骡子尾巴”的发式(dead lock粘结式)与爆炸式 (The A fro)一样都是利用身体表示反抗的政治表述。母亲利用妹妹麦姬发出的“呃”声表示自己的不习惯 (张鑫友,2000:56-65)。第二,母亲对女儿使用具有语言民族主义象征意义的乌干达问候语感到茫然。迪伊使用乌干达问候语“瓦 -苏 -左 -提 -诺 (早上好)”和她男友使用阿拉伯问候语“阿萨拉马拉吉姆(宁静与你同在)”与母亲沟通是徒劳的。在母亲的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存在这样反抗英语和追求独立语言身份的词句。第三,母亲对迪伊更改名字感到不满。迪伊告诉母亲,因为“无法忍受那些压迫我的人给取的名字”已经改名为“万杰罗·李万里卡·克曼乔”了 (同上)。母亲对这种改变表面接受,可是当她对迪伊失去忍耐后,脱口称迪伊为“万杰罗小姐”时,母亲的不满还是在名字上表现了出来。第四,母亲对女儿穆斯林化的倾向不置可否。迪伊带着穆斯林男朋友回家是作者艾丽丝·沃克精心安排的情节,意在表明在宗教取向上,迪伊已经背离了母亲的宗教信仰。母亲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己与教堂的密切关系。她曾经从教堂为迪伊筹集学费。并且,教堂是母亲在麦姬出嫁之后唯一的精神寄托。迪伊对基督教的背叛不能不引起母亲的愤懑。第五,迪伊对“心灵食品”的热衷出乎母亲的意料。迪伊的男朋友拒绝了母亲精心准备的“心灵食品”,这足以引起母亲的不快。而迪伊对“心灵食品”表现出格外的热情,也足以使母亲感到意外。母亲想象不到,当迪伊谈笑风生地吃着猪大肠、玉米、羽衣甘蓝和红薯时,她是陶醉在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感当中了。第六,母女之间在拼花被子上的歧见突出代表着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别。在母亲看来,被子是使用物件,其功能就是取暖。母亲用她的日常思维方式不会想到它的美学价值,更不会考虑到遗产的问题。而在迪伊看来,黑人的被子是一种遗产。它应该作为艺术品挂起来欣赏。它的内在美学价值只有在非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领域才能显现出来。
从以上六个情节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日用家当》中母女关系的不睦主要是日常生活
对非日常生活缺乏兼容性的结果。此外,一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在日常生活二元对立的视角中也显现出特殊含义。比如,作者曾在小说结尾处安排了一个母亲和小女儿使用含烟(checkerberry snuff鹿蹄草牌含烟)的情节。这个情节曾被有的教学参考书误译成母亲和小女儿在享用草莓汁(同上)。这种误译很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在美国,含烟是一种烟草使用的方式。使用时将一撮烟草放入舌下、腮间或唇齿间,靠口腔肌肉吸收烟草中尼古丁达到使用的目的。20世纪早期含烟多在美国乡村地区流行。它常引起口腔疾病,后逐渐为纸烟所取代。含烟这个情节寓意很明确,它表示母亲的日常生活还具有相当的落后性。母亲在给妹妹麦姬留下被子遗产的同时,也留下了含烟这种不健康的遗产。其实,迪伊对于她和母亲之间矛盾的性质有比较清醒的看法。她告诫妹妹麦姬:我们已经是处在一个新时代了,不能再过“你和妈妈现在仍然过着的那种生活”了(同上)。迪伊指的那种生活就是带有惰性的日常生活。
五、结语
小说《日用家当》以母女关系为线索开启了20世纪末的女性关系写作热潮。由于母亲长期处于日常生活状况,她的思维带有明显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特点。而女儿迪伊身处 20世纪 60年代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政治风暴中心,她的思维经常超越日常生活,而徜徉在政治,艺术甚至哲学范围之中。母亲的日常生活由于迪伊的到来而发生波动,又由于迪伊的离开而恢复了宁静。在《日用家当》(Everyday Use)创作之际,everyday life,everyday cu lture,everyday know ledge,和everyday thought等词汇在学术界非常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昂利·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影响很大。知名学者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 an)、费尔南·布劳岱尔 (Fernand B raudel)、艾尔弗雷德·舒茨(A lfred Schutz)、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介入“日常生活”的讨论。因而,笔者认为,此时艾丽丝·沃克写作Everyday Use,是以文学形式对当时学界“日常生活”研究的参与。作者在字面上写的是母女关系,在字里行间却是抒发着对母亲惰性的实用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
[1]Bell-Scott,P.Double Stitch:B lackW om enW rite Abou tM others and Daugh ters[M].Boston:Beacon Press,1991.
[2]Carter,S.M others and Daugh ters in Am erican Short Fiction[M].W 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3.
[3]Cow art,D.Heritage and Deracination inW alker’sEveryday U se[J].Stud ies in Short Fiction,1986,(33):171-184.
[4]Craig,M.L.A in’t Ia Beau ty Quee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5]Farber,D.The Sixties:From M em ory to H istory[M].ChapelH ill:University ofNorth Caro lina Press,1994.
[6]Farrell,S.Fightvs.Flight:A Re-evaluation ofDee in A liceW alker’sEveryday U se[J].Stud ies in Short Fiction,1998,35(2):179-186.
[7]H ighmore,B.Everyday L ife and Cu ltura l Theory:An In troduction[M].London:Routledge,2002.
[8]Joseph,G.I.&J.Lew is.Comm on D ifferences:Conflicts in B lack andW h ite Fem inist Perspectives[M].Boston:South End Press,1986.
[9]Perry,B.M alcolm:The L ife of theM anW ho Changed B lack Am erica[M].New York:Station H ill Press,1991.
[10]Rich,A.O fW om an Born:M 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 tion[M].New York:W.W.Norton and Company,1976.
[11]Rody,C.TheDaugh ter’sReturn:African-Am erican and CaribbeanW om en’s Fictions ofH isto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2]W alker,A.M erid ian[M].New York:Harcourt,1976.
[13]W hitsitt,S.In Sp ite of ItA ll:A Reading of A liceW alker’sEveryday U se[J].African Am erican Review,2000,34(3):443-459.
[14]W itt,D.B lack Hunger:Food and the Politics ofU.S.Iden tit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5]阿格尼丝·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6]张鑫友.高级英语学习指南 (第一册)[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M 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s them ain content in A liceW alker’s short storyEveryday Useand its them e is the criticism ofmother’severyday life.It isow ing to the pub lishing of suchw riting that there later burgeoned a renaissance on female relationsbywom enw riters in the late 20 th century.Themother’sway of thinking is characterized by p ragm atism andmaterialism generated from everyday life.W hereas the daughter lives in the centerof the po litical and racial struggles of the Civil R ightsM ovement,her thought is not concerned with everyday life.The alienation of daughter from mother in the story is best criticized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everyday lif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everyday life;the Civil RightsMovement;woman w riter
H106.4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8-665x(2010)06-0044-06
2010-06-02
李荣庆 (1955-),男,讲师,研究方向:中西文化、美国文学、商务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