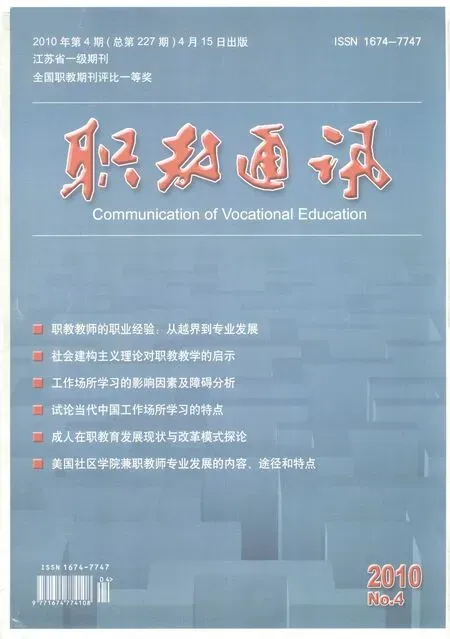作为隐喻的立交桥
臧否
作为隐喻的立交桥
臧否
如果评选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最糟糕的发明,我一定会把高速公路排在前几位。除了“快”感,高速公路更让人感到压迫:路边的护栏硬生生地把人和周边的自然割裂开来,还严格限制了人前进的方向,更为糟糕的是,路被故意弄得弯弯曲曲,让人看不到尽头,不知自己身处何方。在这样的路上,坐在高速移动的铁皮盒子里的人注定是渺小与无助的。在这幅压抑的景观中,唯一能让人产生些许欣慰的设施是立交桥,它总是以超然的高度向人提供有限的选择,让人暂时忘却自己已变成路和汽车的附属物。
正由于在道路系统里的特殊地位,立交桥成为文学、影视作品非常喜欢的一个元素,甚至作为一个隐喻进入了学术研究体系。南非、澳大利亚等多民族国家都有学者用立交桥来形容不同文化社区间的沟通,因为“立交桥可以越过横亘在不同区域间的鸿沟,使两个区域相联”。但这个隐喻显然没有得到西方世界的广泛认同,那里的人们更喜欢用“桥”这个形象来比喻两个区域间的沟通(与中文不同的是,在西方语言中,立交桥并不被认为是桥,因为桥下一般都有水),而立交桥尽管有一部分高于地面,但它所联通的两个区域大多数情况下都在同一平面。因此,就沟通一义而言,桥与立交桥基本一样。
相比西方学者的谨慎,国内职教界对“立交桥”的使用则要大胆得多,就像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所说的那样,“有了一个词,我们就像松了一口气,本能地觉得一个概念现在归我们使用了”。
有论者这样描述职教“立交桥”:通过设置不同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实现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教育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互相沟通与衔接。那么,理想的“沟通与衔接”是一个在垂直与水平方向同时展开的多元结构,既包括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提升,也包括同一层级内不同类型间的跨跃。立交桥可以帮助水平方向的跨跃,但一般不会实现垂直方向的提升,所以用立交桥这种交通设施来比喻研究者所说的“沟通与衔接”是不恰当的。
但职教界如此喜欢这个词,一定有他们的道理。立交桥的快速与畅通应该得益于两个因素:对既有行车规则的尊重与最大可能地避免使不同方向的行车轨迹相交,可以说,立交桥最本质的特性不在于沟通,而在于规避冲突。这一点倒与现行的职教“立交桥”有几分相似:现行的职教“立交桥”尽量不打破已有的招生、培养体制,所以对职教学生进入高一级学校设置了种种门槛,而对于已经走上“立交桥”的职教学生则要求他们与普通教育的方向保持一致。也许正是潜意识里对于这一现象的认知,才使人们广泛认同了这个隐喻。
当然,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样:国人在使用“立交桥”这个概念时并未想到立交桥的形象,而仅仅使用了其中的“立交”二字,并将之解释为“立体、交叉”(这里的交叉已不是如立交桥般的投影相交,而是物理相交),也就是说,这个词的蕴涵已经发生了转移,此立交已非彼立交了。
尽管不喜欢“立交桥”这个隐喻,但我相信时间是最好的筛子,有力量的总会被留下,没有生命力的总会被筛掉,所以我更关心的是职业教育能否实现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的沟通与衔接。
对沟通与衔接机制所设的诸多障碍表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希望进入这个机制的职教学生不会冲击现有的普通教育的体制;同时,有人在颇具影响力的报纸上撰文指出:建设“立交桥”的过程中“谨防出现‘两张皮’,忘了职教的办学宗旨,升学的不钻技能,钻技能的不升学”。教育界以外的人士肯定又要嘲笑这些书生了:桥还没建起来,建桥的人已经各怀心腹事了。可以想见,这桥的命运会是很曲折的。
2004年,迈克·托姆林逊爵士受英国教育部委托完成了一份报告,声称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证书框架”覆盖所有类型的学习,普通学习与职业学习被纳入一个统一的体系,从而使学生获得多元通道。可能是由于过于激进,这份建议被首相拒绝了。2008年,英国教育部决定在原有的证书体系之外引入一个包含理论学习与职业学习的新文凭,也算是对这位曾经的国家督学长的一种安慰。托姆林逊报告的遭遇告诉我们,无论在何种文化或在教育的哪一个发展阶段,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间的沟通与衔接都不容易,“立交桥”的命运肯定是曲折的。
据说,英国教育界内部——无论是普教还是职教——对托姆林逊报告都表现出了难得的一致认可(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托姆林逊的建议才会被吸纳进最新政策中)。这与我们各守疆土、各自为战的情况又大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