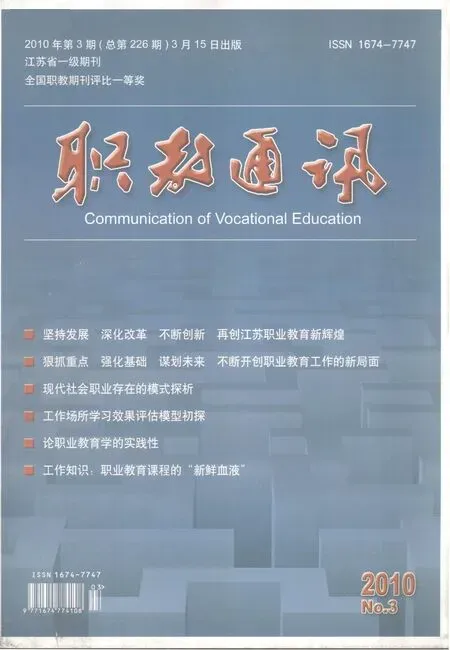大还是小?也许不仅是这个问题
臧 否
大还是小?也许不仅是这个问题
臧 否
中美两国的教育千差万别,但有时也会不约而同,比如对于关闭学校的热情。自2002年以来,纽约市关闭了91所中小学;同样的时间段里,江苏省关闭了262所中等职业学校。与通常的情况一样,同样的行为在两国总是有不同的目的、方法和结果。美国对于学校的所谓关闭其实是拆分,把大型学校拆成两到三个小学校;中国则是合并,把若干个学校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学校——在最近的建设县级职教中心的热潮中,许多县市把管辖范围内所有职业学校都合并到了大型的职教中心里。纽约最新关闭的一所“规模太大”的中学有在校生1 400人,将被拆成三所学校;而江苏省中职学校的平均在校生数从2002年的985人上升到了2009年的2 709人。
通过如此简单的对比当然不能说中国人又一次把错了世界教育发展的脉。事实上,即使美国能够代表世界教育的发展,学校的小型化也不一定是必然。自从十九世纪以来,美国的学校规模一直在扩大,只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才有了比较多的反思的声音和反向的实践。
从我国的实际来看,职业学校规模的增长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职业学校不同于普通教育学校,只有达到相当的规模才有可能向学生提供足够的课程。所以,学校规模的变化倒不必引起过多的担心,真正使人担心的是几乎没有人有足够资格反对正在进行的学校大型化,同样,也几乎没有人有足够资格支持这种大型化。美国人对学校规模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学校大小对学生的学业、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据说,梅耶就曾说过,一所学校最合适的规模为300个学生,最有利于学生的成长。但在中国,这方面的讨论几乎是个空白,很难看到一个出于教育专业判断的、令人信服的、可行的结论。如果您有兴趣,可以检索一下国内有关学校规模的研究论文与政策宣示,很容易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文字围绕以下两个关键词展开:规模经济和资源整合。学生呢?教师呢?原来,在关于学校规模的讨论中,人是最不重要的,唯一能引起我们兴趣的只是经济。可从本质上来讲,教育是一项关于人的事业,而不是经济的。
不由想起美国教育史上一桩公案:1819年,达特茅斯学院不同意新罕布什尔州政府把它扩为大学的决定,最终诉至美国最高法院,还请了它的一个毕业生做辩护律师。这位律师陈述了五个小时,据说感动得主审法官流下泪来,他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我承认,我们学院很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爱她!”是啊,在一次次的合并或拆分学校的过程中,有多少爱着或恨着学校的人。只不过他们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决策者与决策的参与者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小小的决策会对他们的感情、学业以及未来的成长产生什么影响?
能不能把学生成长当作首要问题来考虑不仅体现出教育者的师德水平,更是判断教育职业专业性的一个标志。传统上,专业人员的一个特征是专业自治,也就是在专业内拥有不受管辖而独立作出判断的权利,比如医生完全可以不管他的院长或其他什么领导的态度而独立地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病人作出诊断,否则,这个医生就会被认为缺乏足够的专业素养。同样,如果一个教师总是把领导意志或个人利益放在学生的利益之前加以考虑,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放弃了一个专业人员应有的立场,他已经从一个专业人员蜕变为普通人。
在西方,决策者经常被丑化成那些把硬币放在大拇指上,准备掷出之后就去冒险的家伙。我们当然不愿意强加这种非理性的形象于决策者,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决策者的理性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方面,而不是教育方面,毕竟政府需要保证效率,他们必然希望通过合并学校,整合资源,最终达到规模经济。于是,那些有资格参与决策、具有足够专业素养的教育工作者就成了保障学生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他们也放弃了自己的专业立场,而一味迎合,则学生的成长将有可能被放置在不太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只可惜,在目前,教育逻辑向行政逻辑的屈从已经是一种常态,最近的大学校长反对高校去行政化就是一个例证。就这样,在许多有关教育的决策中,那些最应得到重视的人——学生——消失了,副产品——经济效益(或个别集团的利益)——却成了主角。
写了这么多,其实有点求全责备了,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教师都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最为亲近的专业人员,让他们与政治或行政绝缘,或向政治发起挑战,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想做一个善意的提醒:尽管职业教育直接面向就业,与经济部门关系密切,但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仍然是它的天职,决策者、决策的参与者以及所有的职教工作者都不应把学生的成长当作最重要的事情中最不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