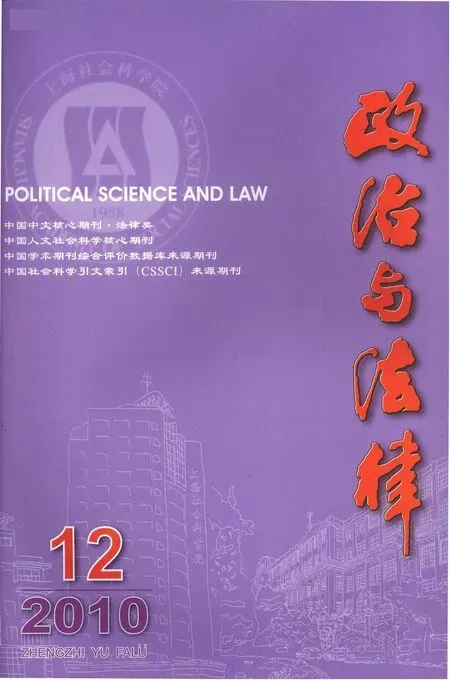刑法分则条文罪状的理解与相应法定刑配置关系研究
严明华 张少林 赵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上海200051)
刑法分则条文罪状的理解与相应法定刑配置关系研究
严明华 张少林 赵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上海200051)
刑法分则条文罪状规定的具体犯罪与相应法定刑之间存在以社会危害性为基础的相互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从法定刑的质和量两个方面,对如何理解具体罪状产生提示和限制作用。具体而言,在法定刑质的方面,法定刑对应罪状所描述的行为,务必要达到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且法定刑的刑种和严厉程度是依照一定标准而与具体犯罪的罪状内容相对应。在法定刑量的方面,对某一具体犯罪而言,同一档次法定刑所对应罪状描述的不同种类行为社会危害性应基本相同;对于不同犯罪而言,可通过对相关具体犯罪法定刑的比较,运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来确定该具体犯罪罪状的特定内容。
罪状解释;法定刑配置;相互关系
对于具体犯罪与其法定刑的对应关系,我国也有学者进行过论述,如认为“影响法定刑刑度高低的因素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即各种犯罪可能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程度。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质和量的主观与客观的综合指标,而社会危害性是由刑法规定诸要素决定的,这些要素也决定了法定刑刑度的大小。而这些要素包括犯罪行为侵犯的对象、犯罪手段、结果、主观方面、数额、行为人的身份、犯罪情节、犯罪目的”。5而这些要素基本上属于具体犯罪罪状的内容。还有学者从罪与刑立法规定模式角度对罪刑关系进行了阐述,认为法定刑的设定根据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但是该概念只是一个最高的抽象,最概括的确定,至于具体的危害性与各种刑罚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当然的事情,它仍然需要选择。而这至少有两个必须研究的问题:一是刑种与危害性的对应关系;二是各种具体犯罪类型危害性的确定与比较。对于前者,刑种与犯罪性质曾经有过形态对应的关系,但现代社会中,刑罚主要归结为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四个种类,罪与刑在形态上就不能再相对应,于是就有了各自的抽象形式:罪的危害程度与刑的严厉程度相对应。而具体犯罪危害性的确定一是价值观念问题,二是技术问题。要达到罪刑相当的立法要求,不但要在实质上注意社会危害性程度与刑罚之间关系的对应,作为立法技术,在客体设定、犯罪形态设定上,也应将其思想贯彻下去。6
笔者认为,不论是主张“以罪定刑”7还是主张“以刑制罪”,8均体现了具体犯罪与其法定刑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以该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基础,因实践中具体犯罪社会危害性的确定一般包括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裁量,所以具有不确定性,罪状与宣告刑的对应关系也难以稳定和明确。但对于罪状和法定刑而言,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具体犯罪的罪状与其法定刑的对应关系相对稳定,法定刑的比较也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不同具体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对相应罪状的解释具有提示和限制作用。对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法定刑的制约性,即:“法定刑本身属性决定了刑事立法应该接受其内在精神的制约,做到同害同罚,异害异罚,不同犯罪法定刑应该达到平衡,法定刑的设置应该为司法适度解释提供保障,不能超越法定刑本身作出司法解释……对于法律条文的理解也必须接受法定刑的制约。”9总之,具体犯罪罪状与其法定刑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从法定刑的质和量两个方面,对罪状解释产生提示和限制作用。
总之,法定刑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和其他刑事法律对各种具体犯罪所规定刑罚的刑种和刑度(刑罚的幅度)的总称。“法定刑是刑法分则条文对类型化、模式化的法定罪种所规定的刑罚规格和标准,反映犯罪与刑罚之间质的因果性联系和量的对应性关系。”10因此,法定刑从其质和量两个方面对罪状的理解起着提示和限制作用。
二、法定刑的质对理解罪状的提示和限制作用
我国刑法总则规定了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主刑,以及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驱逐出境四种附加刑。从一般意义上说,对法定刑的质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把握:一是法定刑首先反映出国家对犯罪行为的否定评价和对犯罪人的谴责态度,同时也考虑了预防犯罪特别是一般预防的需要。从这个角度分析,与法定刑相对应的罪状所描述的行为,务必要达到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这实质上是要求以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标准,对罪状所描述的行为进行实质解释。这一点与罪状解释的基本立场是相一致的,故不再赘述。二是认为法定刑的刑种和严厉程度是依照一定的标准而与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主要是具体犯罪的罪状内容)相对应。法定刑的配置并不是立法者任意行为的结果,它是深思熟虑的一种理性行为,是基于报应兼顾功利,根据犯罪的性质进行配置的。因而对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必须从法定刑的性质,以及与此相关的而为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来把握。11
如刑法第263条抢劫罪和第274条敲诈勒索罪均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性犯罪,其二者法定刑的刑种均以有期徒刑为主体,但抢劫罪的法定刑还大量配置了无期徒刑、死刑,并均要求并处罚金,或者在加重犯中还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而敲诈勒索罪在有期徒刑之外配置的主刑种是拘役、管制,且并不要求有罚金刑。立法对这两种犯罪的法定刑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区别性规定,首先,是因为抢劫罪侵害的法益不仅是财产权利,而且还指向人身权利,敲诈勒索罪的法益则虽然包括财产和人身权利,但并不当场直接指向人身权利,因而抢劫罪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抢劫罪的手段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抢劫公私财物,因而具有现实的危险性,且行为的后果往往也更为严重。而敲诈勒索罪的胁迫行为则不具有现实危险性,其获得财物也是基于被害人的瑕疵意思行为,而不像抢劫罪中被害人是在不敢、不能、不知反抗的情况下被劫取财物的,且敲诈勒索罪的危害后果与抢劫罪相比往往也轻得多。从这两点出发,刑法对抢劫罪的法定刑配置了更为严厉的刑种和刑度,这样才能体现具体犯罪与法定刑之间质上的对应关系。
又如在《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之前,刑法第239条第一款对绑架罪的规定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可见,绑架罪是一种在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同时被刑法规定了极其严厉法定刑的犯罪,其法定刑有两个特点:一是法定刑起点高,且非常严厉,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为起刑点,包括了无期徒刑和死刑,同时并处罚金和没收财产;二是该款后半段还以死刑的绝对确定法定刑模式出现。12刑法对绑架罪法定刑的特殊配置必然影响到对其罪状的解释,对其有学者曾尝试以该法定刑为依据,对绑架罪罪状的内容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解释,认为“应当立足于现有的立法模式解释绑架罪的构成要件。立法对绑架罪规定了极为严厉的法定刑尤其是法定最低刑。受其制约,对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应当尽量作限制性的解释,使绑架罪的认定与严厉的法定刑相称。绑架罪主观上应当是以勒索巨额赎金或者其他重大不法要求为目的;客观上限于使用暴力方法扣押人质,利用第三人对人质安危的担忧进行勒索;侵犯的客体不仅包括人质的人身权利而且包括第三人的自决权;绑架他人之后,尚未开始勒索之前,应当有成立犯罪中止的余地”。13而最高人民法院则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债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也排除在绑架罪之外,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同样体现了绑架罪法定刑对其罪状内容解释的限制。为解决刑法对绑架罪法定刑的规定过于严厉,而量刑情节过于简单,造成司法实践认定的困惑和分歧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进行了修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述问题,其修改后的规定为:“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犯前款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三、法定刑的量对理解罪状的提示和限制作用
法定刑对罪状解释的提示和限制功能主要体现在法定刑量的配置方面,即法定刑的幅度,“法定刑罚幅度的设置,在纵向层面上应能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之法定化、明确化要求,而具有合理的宽窄跨度,在横向层面(即罪与罪之间的刑罚幅度)上应能符合衡平和协调的原则,而具有等差性和可成比例性”。14故在分析法定刑的量对罪状解释影响时,也可从法定刑幅度的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进行,但在实践中更多情况下是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的。
(一)法定刑纵向层面的配置对罪状解释的提示和限制
我国有学者将刑法分则法定刑按其最高刑分为9格:死刑、无期徒刑、15年有期徒刑、10年有期徒刑、7年有期徒刑、5年有期徒刑、3年有期徒刑、2年有期徒刑、1年有期徒刑。15刑法分则中法定刑的配置,就是根据各个具体犯罪的不同情况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以上述刑格为标准线,规定了几个轻重有别而又合理衔接或者交叉的法定刑档次,并使不同档次的法定刑对应着不同的犯罪形式和犯罪情节。因此,可以认为对某一具体犯罪而言,不同档次法定刑的罪状所描述行为的表现形式和社会危害性应该是不相同的,而同一档次法定刑罪状的社会危害性则应基本相同。
如刑法第263条以列举方式具体规定了抢劫罪的八种加重处罚情节,其中能够直接体现对抢劫罪双重客体造成严重侵害的情节实际上只有两个,即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和抢劫数额巨大。实践中对这两种加重处罚情节一般没有争议,但不难理解的是,倘若一个抢劫行为不具有该两个情节,亦即其对抢劫罪的双重客体均没造成实际的严重侵害,这就意味着该种抢劫行为在本质上就属于情节并非十分严重、抑或相对较轻的抢劫罪,将其纳入抢劫罪的基本犯而非加重犯,在3年到10年有期徒刑这一相对较宽的法定刑幅度内裁判刑罚,应当讲通常能够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相反,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实际危害程度一般的抢劫罪发生在“户”内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上等原因,就一律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实践中的大量实例已经证明,该种裁判经常显现刑罚畸重,违背罪刑相当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为了使罪刑相当原则在实际个案中全面得到贯彻、实现,运用限制或者缩小解释方法,适当紧缩“入户抢劫”等其余六种加重犯的认定范围就显得十分必要。其基本思路就是通过设定一些附加条件,使得原本相对较轻的抢劫行为在整体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上适度增加,尽量达到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和抢劫数额巨大两种行为大体相当的水平,从而找到判处同等严厉程度之刑罚的正当理由,实现刑罚的正当性。而对于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抢劫行为,当然也就被排除在情节加重犯的范围之外,作抢劫罪的基本犯处理。16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年《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多次抢劫”、“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范围的界定上就体现了上述精神。此外,对一些罪状中诸如“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和“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内容的确定,也同样要体现与相应法定刑的对应关系。
(二)法定刑横向层面的配置对罪状解释的提示和限制
“所谓横向比较就是探究相关犯罪在同一刑罚或幅度的情况下,立法对拟认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会有什么特别要求。”17因此,法定刑横向层面的配置对罪状解释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相关具体犯罪法定刑的比较,运用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来确定该具体犯罪罪状的特定内容。如刑法第333条第一款前半部分规定了非法组织卖血罪:“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第二款规定:“有前款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如果仅仅从该条款出发认为凡是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并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而不论该伤害是轻伤还是重伤,均按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则明显存在罪刑不均衡的情况。因为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只能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而非法组织卖血罪的法定刑则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对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并对他人造成轻伤的,如也按照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则明显存在罪刑不均衡的情形。对此,有学者提出,该拟制条款中的“伤害”应仅限于重伤,而不包括轻伤,18从罪刑均衡的角度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又如,刑法第293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指在公共场所无事生非、肆意挑衅、起哄捣乱,进行破坏骚乱,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本条虽没有规定寻衅滋事,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32条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但通过对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法定刑和寻衅滋事罪法定刑的比较,寻衅滋事罪的行为内容不应包括致人重伤、死亡的内容。对此,有学者提出,只有在寻衅滋事,将他人打成轻伤的情况下,才不另定罪,直接以寻衅滋事罪论处。19
此外,对于法定刑的横向比较在某些情况下还对罪数的处理具有限定作用,如想象竞合犯定罪处罚的原则一般为“从一重处断”,即按其行为同时触犯的数罪名中法定刑最重的罪名定罪。牵连犯的定罪处罚原则一般为“从一重罪从重处罚”,即按照数罪中最重的一个罪定罪,并在该罪的法定刑内从重处罚,而不认定为数罪。如刑法第399条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第4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有前两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20,就属此例。
注:
1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9页。
2、3[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68页。
4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
5、15陈兴良主编:《刑法各论的一般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203页。
6参见李洁:《罪与刑立法规定模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159页。
7参见甘雨沛、何鹏:《外国刑法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68页。
8参见冯亚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44页。
9安文霞:《略论法定刑的制约性》,《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10、14储槐植、梁根林:《论法定刑结构的优化》,《中外法学》1999年第6期。
11、17裘霞等:《论以刑制罪及其司法运用》,载游伟主编:《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12在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下,一般认为刑法法定刑的配置模式有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模式,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指刑法分则条文对某犯罪行为仅规定单一的刑种和固定的刑罚幅度。参见韩忠谟:《刑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周光权:《法定刑配置模式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4期。
13阮齐林:《绑架罪的法定刑对绑架罪认定的制约》,《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6参见黄祥青:《刑法适用疑难破解》,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261页。
18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11页。
19参见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页。
20参见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第262页。
(责任编辑:石泉)
DF613
A
1005-9512(2010)12-0150-05
严明华,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少林,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研究室检察员,法学博士;赵宁,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助理,法学博士。
作者简介:庄绪龙,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刑法分则的罪状是对具体犯罪特定构成要件的描述,对其含义的理解一般根据其自身表述的内容确定即可,但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具体犯罪和其法定刑之间是存在一定对应和制约关系的。简言之,立法者将某行为犯罪化是对该行为不法的质的评价,而相应法定刑的配置,则是立法者对该行为不法的量的评价,因而,“人们一般将法定刑定义为,刑法规定的、与犯罪构成要件相对应的刑罚”。1因此,具体犯罪法定刑对该犯罪罪状的解释,必然具有一定的提示和限制作用,在理解罪状过程中,需要借助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将具体犯罪罪状的含义确定与相应法定刑合理地对应起来。
一、法定刑与具体罪状的对应关系
对于法定刑与罪状之间的对应关系,贝卡利亚曾进行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其认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民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的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犯罪了。”“人们能找到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行为。在这两极之间,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从高到低顺序排列……那么也很需要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2至于衡量犯罪的尺度,贝卡利亚认为是“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而不是犯罪时行为人所怀有的意图,或者被害人的地位,或者罪孽(宗教罪恶)的轻重程度。3对于贝卡利亚的这些刑法思想,有学者认为这体现了贝氏的刑罚与犯罪相适应的原则,具体包括刑罚相均衡和刑罚相类似两层含义,前者指轻罪轻刑、重罪重刑;后者指刑罚应尽可能同犯罪的属性相类似。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