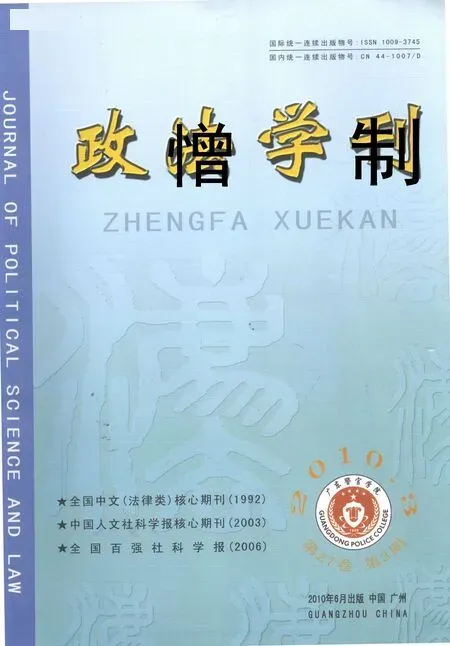美国死刑案件有罪答辩自愿性探微
郭明文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美国死刑案件有罪答辩自愿性探微
郭明文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在美国,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是保障被告人认罪自愿性的基础。在死刑案件中,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时得到了有效而合格的律师帮助、具有与其律师交流的能力、在知晓指控的性质和答辩有罪的后果是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标志,选择陪审团审判而可能被判处死刑并不是强迫被告人认罪的必然因素。
有罪答辩;自愿性;死刑案件
在美国刑事诉讼中,有罪答辩等同于被法院宣告有罪,一旦法院接受有罪答辩,就意味着被告人放弃了宪法、法律为其提供的保护。具体而言,被告人放弃了要求控方证明其有罪的权利、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与控告者对质的权利以及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①Boykin v.Alabama,395 U.S.238,242(1969).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是仅剩的司法活动了。正因为有罪答辩意味着上述宪法性权利的放弃,所以正当程序要求法庭应保证有罪答辩是自愿和明智的。②McCarthy v.United States,394 U.S.459,469(1969).
一、被告人认罪自愿性的一般性规定
在美国,犯罪嫌疑人是否选择供述、被告人是否做有罪答辩或认罪的制度性基础在于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于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被强迫成为对自己不利的证人。”根据该条修正案,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任何人”在刑事诉讼的整个阶段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在 1964年以前,第五修正案只适用于属于联邦系统,对各州并无拘束力。196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Malloy v.Hogan案的判决使美国各州也须遵守第五修正案的规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该案的判决中指出:“第五修正案关于‘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的规定属于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之列,美国联邦和州都不能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和自己做出有损自己声誉的供述,因为该权利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权利。”③Malloy v.Hogan,378U.S.1(1964).
为了保证被告人有罪答辩的自愿性,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 11条 c款规定,法庭必须告知并确定被告人理解以下事项: (1)有罪答辩针对的指控的性质、如果法律有规定法定最低刑和最高刑,包括任何具体假释或者受监督释放的期限的效果,法庭应当考虑任何适用的量刑指南但是可能根据某些情况而偏离那些量刑指南的事实,以及适用那些量刑指南时法庭可能要求被告人对被害人做出补偿的事实; (2)在刑事诉讼的每个阶段,被告人都享有由律师辩护的权利,如果被告人没有聘请律师,法庭应当为其指定一位律师;(3)无论被告人作了无罪答辩或者有罪答辩,其有权利坚持已做出的答辩,被告人还有权由陪审团进行审判,在审判中与控方证人进行对质与交叉询问,并享有不受强迫自罪的权利; (4)如果法官接受了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或者既不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那么此案件将不再进行正式审判,因此有罪答辩或者既不辩护也不承认有罪的答辩意味着被告人放弃了审判权; (5)如果法庭想要在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就已作有罪答辩的犯罪行为讯问已宣誓的被告人,被告人的回答将被用作对其提出的伪证罪指控或者证据。法官如果法庭没有提醒被告人注意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 11条规定的三个事项:不存在强迫、理解指控、知晓有罪答辩的直接后果,则会导致有罪答辩的自动撤销或撤回。此外,美国联邦和州的刑事诉讼规则都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控方向法庭出示非法获取的被告人供述。这些制度安排能够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提供充分的保障。
二、法官对认罪自愿性的审查
从表面上看,被告人是否自愿地做出有罪答辩似乎是一个仅存在于控辩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情。因为,如果被告人想做出有罪答辩而控方也不反对,那么有罪答辩就是自愿的,有罪答辩的自愿性问题似乎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把有罪答辩的自愿性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无论控辩双方达成的辩诉协议多么圆满,根据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法官仍然有义务监督、审查辩诉协商的过程和有罪答辩。法官必须确定被告人的有罪答辩的确是自愿的,也就是说,被告人在作有罪答辩时理解指控的性质和答辩的后果、放弃的辩护权,以及做出该答辩并未受到控方不当的威胁。①Janet Key,Old Countries,New Rights,80 A.B.A.J.68(May 1994).
长期以来,法官审查有罪答辩的方法是询问被告人,然后得到后者的“正确”回答,但这对于确定有罪答辩是否自愿是远远不够的。[1]569因为大多数案件接受有罪答辩的程序比较简短、马虎和不全面,然而,被告人答辩有罪的目的比较复杂,其对答辩有罪后果的是否真正了解也并非一问即可做出正确判断的问题。一项研究表明:被告人可能心烦意乱,他可能受保护其他人或隐瞒更严重行为的愿望驱使,他可能认为即使他没有罪,接受较轻的惩罚比冒险可能被宣判主要罪行有罪的风险要好;或者他可能误解他被指控罪行的要件,根据法律规定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他却认为构成犯罪或他本可以作有效的辩护而答辩有罪。美国研究家威廉.F.迈克唐纳注意到,一些法院向被告人建议他们的权利时运用的标准化形式,甚至使被告人更不能真正了解指控或答辩有罪的后果。[2]455
此外,法官在罪状认否程序 (提审程序)中对被告人的提审时间和对有罪答辩自愿性审查质量的好坏有密切的联系。威廉.F.迈克唐纳通过对 6个司法管辖区的重罪和轻罪案件的进行实证考察后发现,在提审程序持续时间的长短与法官参与提审的总体质量之间存在普遍的关系。提审平均持续时间不超过 8分钟,重罪提审持续时间在 10分钟之内。在不足 2/3的案件中法官询问被告人是否了解指控,只有半数多一点的案件,法官在记录中注明辩护律师向被告人解释了指控。不足半数的案件法官告知被告人指控的最高刑,只有 4%的案件法官告知被告人答辩有罪过程中放弃的其他权利 (笔者认为,这些权利是指除放弃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与控告者对质的权利以及反对自我归罪的权利等之外的权利。)。55%的案子法官询问被告人答辩有罪是否受到威胁、强迫或施压,法官有时小心地措词以使被告人理解检察官提供的答辩引诱不能理解为压力。[1]454-455虽然不能根据威廉.F.迈克唐纳就断定美国多数法官对被告人有罪答辩自愿性的审查都是粗糙而不负责任的,但最起码可以说明,不少法官对有罪答辩自愿性的审查是不够全面、不够仔细的,这与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 11条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认罪自愿性的司法实践
一般来说,如果有罪答辩是对被告人身体或精神强迫的结果,该答辩则不具备自愿性;然而,案件千差万别,具体的自愿性宜通过案例来予以说明。要确定有罪答辩是否自愿须综合考虑与答辩有关的整个环境。比如,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是不是对身体的真实伤害或者威胁的结果、或者是不是对被告人意志强迫的结果、陪审团审判可能被判处重刑甚至死刑是否会成为被告人选择有罪答辩的强制性因素、以及被告人为了避免死刑而答辩有罪是否丧失了自愿性等。下文将以美国联邦法院在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中的裁决为例来诠释被告人有罪答辩的自愿性。
United States v.Jackson一案是关于死刑案件被告人有罪答辩自愿性审查的重要案例。①United States v.Jackson,390 U.S.570(1970).在 Jackson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需要对以下事项作出裁决:联邦绑架法规定的犯罪指控只有经陪审团审判才可能被判处死刑,如果被告人对该犯罪做出有罪答辩,该答辩是否为自愿的有罪答辩?根据联邦法律关于绑架罪的量刑制度,被指控犯有绑架罪的被告人有三种选择: (1)对除死刑之外的其他量刑的绑架罪作有罪答辩; (2)选择无陪审团审判 (bench trial),这样其可能被判处的最高刑罚为终生监禁; (3)选择采用陪审团审判,但可能被判处死刑。这就是说,如果被告人选择无陪审团审判或者作有罪答辩,初审法官就不可能对前者判处死刑。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中应确定“宪法是否允许死刑处罚只适用于那些声称要在陪审团面前行使其权利并质疑其罪行的被告人,”即联邦法律中关于绑架罪的量刑制度是否阻碍了被告人行使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六修正案规定的两项权利:享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和关于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该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被告人应当享有由陪审团决定其罪责的权利,但是上述量刑制度给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利施加了联邦宪法所不允许的压力和负担。因为根据该量刑制度,如果被告人坚持行使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则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故此法律被裁定违宪,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也就不具有自愿性。
联邦最高法院在 Jackson案中面临着这样的情形:选择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将会得到不被判处死刑的保证,而坚持由陪审团审判并企图获得无罪判决的被告人如果被陪审团认定为有罪则肯定被判处死刑。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图亚特 (Stewart)代表法院发表了精彩的判决意见,对 Jackson的有罪答辩是否自愿作了深刻的剖析,内容大致如下:即使联邦法律关于绑架罪的量刑制度原意并非强迫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和放弃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但该量刑制度的确刺激和鼓励被告人做出此类答辩。选择陪审团审判可能意味着面临死刑处罚“不必要地抑制了”被告人行使某些宪法性权利。正是此量刑制度不必要地刺激了被告人Jackson放弃了享有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以及做出有罪答辩,这也正是本法院裁定联邦法律关于绑架罪的量刑制度违宪的原因。很明显,死刑处罚的规定促进了辩诉交易,也因此对死刑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产生了负面影响。[3]
大法官斯图亚特在 Jackson案的关注焦点是联邦法律关于绑架罪的量刑制度的要点。如果对此量刑制度采取宽容的态度可能会导致其他刑事法律的效仿,许多法律也因此会刺激被告人放弃宪法性权利。即使死刑处罚的确影响了有罪答辩的自愿性,但联邦最高法院似乎更加关注绑架罪量刑制度的架构,以及此架构对被告人行使某些宪法性权利可能产生的障碍与负面影响,而不是死刑处罚本身对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所具有的强制作用。联邦最高法院在 1968年的 Pope v.United States一案中的裁决中引用了相同的理由,在该案中,联邦反抢劫银行法中的量刑制度同样给被告人行使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施加了不应有的负担,因此,该量刑制度被裁定违宪,被告人的有罪答辩也因此而丧失了自愿性。②
在两年后的 Brady v.United States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人 Brady的有罪答辩是自愿的,而 Brady答辩有罪的犯罪与 Jackson是一样的,也就是对根据联邦绑架法规定的绑架罪做出有罪答辩。控方对 Brady提起绑架罪指控,Brady的答辩同样会受到与在 Jackson案中一样的量刑制度的影响,而该量刑制度在 Jackson案中已被裁定违宪。被告人Brady于 1959年对联邦绑架罪做出了有罪答辩,一直到 1967年他才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对有罪答辩的自愿性提出了质疑,并请求法院适用 Jackson案的裁决意见裁定其有罪答辩缺乏自愿性。对此,联邦最高法院没有按照 Jackson案的裁决意见行事,而是认定无论 Brady答辩有罪是否为了避免在陪审团中可能判处死刑,其有罪答辩仍是自愿、有效的。联邦最高法院没有简单地拒绝适用 Jackson案的裁决意见,而是立场鲜明地否定了以下观点:为了避免根据法律被判处最重的刑罚包括死刑,被告人宁愿对一个肯定或者可能较死刑更轻的刑罚的指控答辩有罪,该答辩则因为违反了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而自动无效,即被告人答辩有罪并非自愿。多数意见代表怀特大法官承认,以量刑上的宽恕换取有罪答辩也许会大量增加无辜被告人自我归罪的可能性;怀特进一步强调 “州政府不应对被告人采用人身伤害或者威胁或者精神强制等重压的方式而迫使后者做出有罪答辩。”人身伤害为法律所不允许,联邦最高法院禁止以人身伤害获取有罪答辩。尽管死刑处罚也是一种人身伤害,但是怀特所指的人身伤害不是指由法律授权的。①Loftus E.Becker,Jr.,Plea Bargaining and the Supreme Court,21 LOY.L.A.L.REV.757,800(1988).
为了进一步讲 Brady案与 Jackson案区分开来,联邦最高法院认为,Brady答辩有罪的主要是由陪审团审判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很小,死刑处罚只是其作有罪答辩的除外原因。Brady的同案犯已在Brady作了有罪答辩并且已同意做不利于 Brady的证人。怀特大法官认为,Brady如果要证明有罪答辩不是自愿的,他应当向法官表明他是如此地恐惧死刑处罚,以至于他不敢抱有任何在量刑上被宽恕的希望,也无法在律师的帮助下对陪审团审判的优点和有罪答辩的优点进行合理的权衡。因此,死刑处罚产生的恐惧破坏了死刑被告人的理性思维是裁定有罪答辩为非自愿的必要条件。但是 Brady并没有做到这一点。然而,在 Jackson案中,斯图亚特大法官没有声明对刑事被告人宪法性权利的侵害起因于死刑处罚所带来的极度恐惧,斯图亚特只是说联邦绑架法死刑条款的罪恶 “不是死刑处罚本身对有罪答辩和放弃陪审团审判权利所具有的强制性,而是死刑处罚不必要地鼓励了被告人答辩有罪和放弃陪审团权利。”这比联邦最高法院在Brady案中施加的标准要低得多。
与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的犯罪指控所关联的量刑制度相比,怀特大法官对有罪答辩本身要关注得多,他认为,在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威胁之下从来就不可能做出自愿的有罪答辩,在这种情况下,有罪答辩不应作为被告人的选项。如果以此为标准,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将被迫选择陪审团审判。而美国法院处理刑事案件却倚重于以辩诉交易为基础的有罪答辩,因此法院一般都不做出限制此类有罪答辩的裁决。因此,尽管面临死刑处罚本身对被告人答辩有罪有一定的强制性,但只要被告人是在理解指控的性质、知晓有罪答辩的后果的基础上,并且在有效的律师帮助下做出了有罪答辩,那么此答辩应该是有效的、自愿的。
布里南大法官发表了不同意见,他强烈建议“如果被告人能够证明死刑处罚制度对其有罪答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同 Jackson案一样,”那么被告人应当有权请求法院撤销因有罪答辩而对他做出的定罪,因为这是一个非法产生的有罪答辩。此外,布里南还进一步阐释到:通过赋予其他与联邦绑架法的量刑制度相似的法律同样的效力,则意味着一方面法律在给予作有罪答辩的被告人一定的回报,在另一方面,对那些坚持行使上述宪法性权利的被告人以可能被判处死刑进行惩罚。
联邦最高法院在 1970年 North Carolina v.Alford一案中甚至接受被告人在不承认罪行的前提下做出的有罪答辩。②North Carolina v.Alford,400 U.S.25(1970).这种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也作有罪答辩的就是著名的阿尔弗德答辩。在该案中,阿尔弗德以一级谋杀指控被起诉,按照北大罗来纳法律要被判处死刑。阿尔弗德给他的辩护律师一张会支持他无罪的证人名单,然而当他的律师询问这些证人时,他们却做出证明阿尔弗德有罪的陈述。因为阿尔弗德无罪主张没有佐证,所以律师建议阿尔弗德接受检察官的答辩交易并答辩二级谋杀指控有罪,最高刑是 30年监禁。在罪状认否程序中阿尔弗德对减轻的指控答辩有罪,然而在回答法官问题时,阿尔弗德陈述他没有谋杀,但是因为面对着如果去审判会判死刑的威胁,他还是答辩有罪。法官继续询问他有关决定自愿性的问题,并得出阿尔弗德知道答辩有罪后果的结论并接受了阿尔弗德的答辩。[1]后来,被告人阿尔弗德就有罪答辩自愿性问题将此案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阿尔弗德认为有罪答辩无效,因为他是在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威胁之下做出答辩的。联邦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指出:因为州证明的答辩存在强有力的事实基础,尽管阿尔弗德声称自己无罪,但他明确表述进行答辩的愿望,所以我们认为审判法官在接受答辩过程中没有违反宪法规定的错误。该法院裁定审判法官没有违反宪法错误时采纳了 Brady案的裁决意见:Brady为了避免被判处死刑而作有罪答辩没有违反宪法第五修正案。如果被告人可以证明 “如果不是”有机会限制可能被判处的死刑就不会做出有罪答辩,那么该答辩将不会被裁定为无效。但是此时被告人还需有合格而有效的律师,律师必须已经向前者建议答辩有罪是其最佳选择。联邦最高法院在 Alford案中的态度鲜明,即使被告人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也可以对指控作有罪答辩,如果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被判处死刑,而且在作此答辩时得到了有效的律师帮助,被告人是在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之后做出该答辩的,那么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是自愿、明智的,也不违反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的不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从阿尔弗德案的判决意见来看,不管被告人提供有罪答辩是否仅仅为了避免死刑处罚,似乎只要被告人在答辩有罪时是明知和自愿的,该答辩便可视为有效。如果被告人具有与其律师进行交流的行为能力且知晓答辩有罪的后果,那么死刑处罚可能鼓励被告人做有罪答辩和放弃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就不再那么重要了。
美国有学者认为,Jackson案对死刑处罚中的量刑制度做出了裁决,该量刑制度对有罪答辩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毋庸置疑的。Brady案则似乎仅仅关注死刑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本身。自 Brady案以后,死刑处罚本身不再被认为具有强制性,它只是法官在确定死刑被告人有罪答辩自愿性时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这两个案件的裁决意见之间其实没有差别,因为无论量刑制度怎么规定,死刑被告人为了避免在陪审团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他仍有可能坚持答辩有罪。尽管如此,法院仍然更多地倾向于设计出立法者应当遵守的规则,这样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才能合宪,就像联邦最高法院在 Jackson案中的裁决意见一样。同时,法院也不太可能撤销已然做出的有罪决定,如Brady案。死刑与其他惩罚都不一样,被告人为了避免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他不会考虑控方案件的强弱,他便可能作有罪答辩。因此,所有此类答辩应当以同样的标准进行评估,即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时得到了有效而合格的律师帮助、具有与其律师交流的能力、是在知晓指控的性质和答辩有罪的后果并在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之后自愿而明智地才做出有罪答辩,对答辩所针对的量刑制度则不予考虑。[2]10对于其他非死刑被告人,其有罪答辩的自愿性也同样适用上述标准。
四、余论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的被告人认罪案件,被告人认罪是否具有充分的自愿性?在庭审中,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法庭调查之前,独任法官或合议庭都按照《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 7条第 2款和《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试行)》第 7条第 1款,讯问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核实其是否自愿认罪,并告知被告人上述条款的法律规定,即基本上都能履行讯问和告知义务,并且都没有强迫被告人承认有罪。如果按照上述规定来衡量,被告人认罪似乎具备了充分的自愿性。其实则不然,我国被告人认罪自愿性明显不足,其程序主体地位没有充分的制度保障,主要理由如下:其一,被告人没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其二,被告人的律师帮助权没有保障;其三,没有建立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后,法官对被告人认罪自愿性的审查仅依据上述规定作宣读式的询问,仅具有表面性,没有如美国法官对自愿性审查的实质性意义,对保障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的作用微乎其微。笔者以为,我国认罪案件的程序设计可以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赋予被告人享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使被告人获得充分而有效的律师帮助,彻底排除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并且要求法官对被告人认罪进行综合性审查,方能对被告人认罪自愿性提供系统性的制度保障,使其认罪具备充分的自愿性。
[1]Abraham S.Goldstein,Converging criminal justice systems:guilty pleas and the public interest[M].Southern MethodistUniversityLaw ReviewMarch-April,1996.
[2]艾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 [M].陈卫东,徐美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Christopher Solgan. life or death:The voluntariness of guilty pleas by capital defendants and the New York perspective[J].New York Law Schoo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Spring,2000:705-706.
责任编辑:韩 静
A bstract: In the United States,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 is the base for the defendant to guarantee the voluntary plea of guilt.In death penalty cases,if the defendant has the effective and suitable legal aid,have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lawyer,and understand the indic tment essence and the outcome of plea of guilt,itmeans the guilty plea is voluntary.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death penalty because of choosing jury trial is not the indispensable factor of compelling guilty plea.
Key w ords:plea of guilt;voluntary;death penalty cases
A Probe on the Voluntary Plea of Guilt in Death Penalty Cases in America
GuoM ing-w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South China Agricultural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D914
A
1009-3745(2010)03-0036-06
2010-03-25
郭明文 (1971-),江西赣州人,男,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从事刑事诉讼程序与制度、证据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