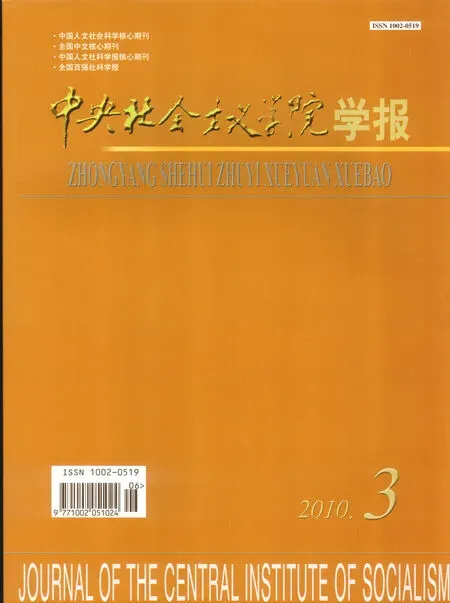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性价值——论多党合作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杨爱珍,许家鹏,张 亮
(1,2.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3.上海市新侨学院,上海 200237)
2007年发布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在论及其功能时指出: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以合作、协商代替对立、争斗,避免了政党互相倾轧所造成的政局不稳和政权频繁更迭,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内耗,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从维护政治稳定的层面上分析,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以政党合作与协商代替了政党之间的互相倾轧,其制度支撑性价值不言而喻。诚然,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但政治稳定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稳定,二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层面上分析,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扩大政治参与的渠道,其社会整合的功能尚没有很好开发。目前,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主要是靠各职能部门“发力”来实现的,很少从多党合作制度方面去寻找途径。亨廷顿在其代表作《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强调了政党制度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他认为,政党制度是形成政治参与扩大的主要制度手段,强大的政党制度具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因而有助于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因参与增长过快所引发的危机。政党政治能够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需要,在引导公民的有序参与的同时有效地抑制公民参与的热情,使公民既能感受到政治效能感,同时,其政治效能感又不会过分膨胀。认真分析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稳定中的功能,不但有助于我们突破传统的稳定观,也有助于提升对多党合作制度稳定社会功能的认识,提升对多党合作制度社会性价值的认识。
一、两种稳定观
社会稳定的内涵比较丰富,既有经济发展的因素,又有政治和社会心理的因素。社会稳定,从表象来看,通常表现为一个国家 (或地区)没有发生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政治团体和公民不会在体制外组织力量对国家政权提出挑战。从理论上分析,社会稳定是相对的概念,因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定的冲突。虽然有低度冲突,但社会还是能够规范有序地发展,因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量社会稳定的含义:一是国家政治制度及其规则能够持续发展;二是公民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认同程度比较高,愿意在体制内表达诉求;三是国家能够尊重公民权利的享有,并有比较充分的渠道容纳公民的利益表达。
(一)静态的社会稳定
分析静态的社会稳定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从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维度上来分析。“党领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主导社会。在这种关系格局下,只要党加强控制,党就能迅速集聚权力。”[1]因此,党、国家、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党完全主导国家,党政之间具有高度的互联性和同构性;国家完全覆盖社会,社会消融在国家之中,二者之间没有缝隙;国家以泛政治化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思想整合和价值整合。第二个维度是从静态型社会稳定的特征上来分析。静态的社会稳定以政治稳定为终极目的,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政治体系对外封闭,社会结构相对僵硬,社会流动性严重不足。静态的社会稳定缺少利益表达机制、政治沟通机制、民意吸纳机制和公共权力的制衡机制,政府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用强力控制或者限制在既定的秩序之内。静态的社会稳定具有专制性、停滞性、封闭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因此,这种稳定是不可持续发展的。第三个维度是从社会心理上来分析。静态的社会稳定是虚假的、麻木的、消极的稳定,与此相适应的的是社会心理处于病态状态,“混”成为流行语,在这种惰性气体的笼罩下,人们睡眼惺忪地看待社会、事业和人生,或身心倦怠、意志消沉,或一切皆为利来,责任与道义放在一边。
(二)动态的社会稳定
我们同样通过以上三个维度来对动态的社会稳定进行解析。第一,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要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2]的要求,党政关系明晰化,党与国家的职能适当分开,党对社会实现政治管理[3];国家从全能主义中解放出来,社会具有独立运作的规则,国家与社会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第二,动态的社会稳定的特征是,社会有表达交流和沟通的空间,政治体系因自身结构和功能的合理配置能适应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并能及时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缓解社会冲突,国家与社会在博弈中各自得到发展。因此,动态的社会稳定具有民主性、开放性、发展性、机制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4]。第三,动态的社会稳定是真实的、平衡的稳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在社会心理上是平稳和健康的。人们有渠道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在民主机制中协调利益关系,因而在社会心理上是开放的、平和的、积极的。
(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稳定观
20世纪 90年代,“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已经成为各级领导者的共识。如今,维护稳定的难度更大。亨廷顿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5]就一般规律而言,现代化意味着不稳定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追赶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构建民族国家、推动经济增长、分享经济成果、扩大政治参与以及应对国际竞争的压力等;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产生大量矛盾的过程。
美国学者派伊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不稳定状态可以概括为六大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贯彻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分配危机。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社会比较稳定。但是,在社会转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过程中,一方面,匀质化的社会基本结构被打破,异质性大大增加,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呈加剧态势;另一方面,按照帕累托定律,当帕累托改进用完后,启用帕累托最优时,的确会造成一部分群体利益受损。因此,社会上也会出现一定的不平衡和不稳定状态,保持稳定就成为当今的主旋律。分析这些不稳定因素,其实大多只是利益表达和博弈形式的问题,很多冲突并非都带有政治性。如果按照静态的稳定观来解决社会矛盾和缓和社会冲突,只能是在平静的海面上掩盖着海下的汹涌澎湃。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很多领导者习惯于在静态的社会稳定框架中来认识社会矛盾和解决社会冲突,对社会冲突有种过度的敏感反应,喜欢刚性稳定的运行机制,总希求以行政手段把一切不稳定的东西消灭在萌芽状态。其实,低度冲突是社会的常态,矛盾始终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社会有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压力体制来控制社会冲突,而不是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诉求表达的渠道和协调社会冲突的机制。多党合作制度能够有效地提供这种渠道和机制,但这种认识恰恰是很多官员所缺乏的。
二、多党合作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功能状态分析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政党制度的解释是:“国家法律规定或实际生活形成的政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特别是政党执掌、参与或影响国家政权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包括与其他政党的相互关系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6]当政党制度牢固地嵌入国家政治制度以后,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表达的渠道和整合的工具,是社会情绪的“调节器”,也是释放社会紧张的“安全阀”。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既承载着扩大政治参与、为利益表达提供渠道、使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在基本价值认同的前提下进行的任务,同时,还要在丛林法则的环境中避免分配危机。
(一)多党合作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价值判断
作为逻辑分析,多党合作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应然状态应该是非常完美的。我们从政党关系的和谐性与政党制度运行机制设置的合理性这两个层面来解析,可以说,多党合作制度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极大的优势。
第一,和谐的政党关系为维护社会稳定奠定了政治基础。在中国特色的政治语境中,对我国政党以及政党功能的理解可以从政治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两方面来展开。一是政治性的价值。中国与西方关于政党在国家权力配置中的安排有着不同的考虑。在我国国家政治架构中,中国共产党处在执政和领导的地位,民主党派处在参政和合作的地位。执政党和参政党目标一致,都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围绕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始终做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执政党和参政党以政治信任为前提,各政党都不会为博弈而博弈,去无端地消耗政治资源,这种政治性价值所带来的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有序进行。二是工具性价值。现代政党,尽管其产生的路径和政党性质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政党来自社会、政党是民众和国家权力之间沟通的桥梁、民众是通过政党来控制和影响政府行为的工具性价值却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越体现其工具性价值,越能对社会稳定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担负着对社会的政治管理,居于管理、分配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的中枢地位。同时,它还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听取各种利益群体的诉求,兼顾各阶层公平,其利益代表面极宽。中国共产党通过基层组织 371.8万个组织网络,实现民意的输入和政策的输出。民主党派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反映和代表了各自所联系群众的具体利益和要求。在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中,共有 17.7万人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共有 1343人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在省、市、县各级人民政协中,共有33.6万人担任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使多党合作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多党合作制度为维护社会有序运行提供了机制保障。要维护社会稳定,民主机制很重要。民主机制就是一种利益表达和磨合的机制,它使每个利益群体都感到有话语权而愿意对差异予以宽容。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使公民直接行使权力来表现“人民主权”。现实的场景必然是不同利益群体选出自己的代表,以便使每个阶层成员都有政治在场感。而这种“在场的政治”能较好地实现利益磨合,调节政治参与的速度,进而维护社会稳定。我国多党合作的运行机制是政治协商机制、参政议政机制、民主监督机制,这种机制设置,恰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实行的政治协商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协商。政治协商内容丰富,既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又有影响群众具体利益的各项决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参政议政机制是科学解决了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结构变迁而引发的复杂社会矛盾的民主机制。参政议政机制不但使国家大事成为各党各派的事,而且有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监督机制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运行中的内在规范机制,实现政党之间相互监督的实质是对权力进行制约。权力与腐败有着不解之缘,腐败是绝对的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掠夺,这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多党合作中的民主监督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防止社会结构扭曲。
(二)多党合作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现实判断
客观地讲,价值判断与现实判断是有一定差异性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也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其原因就是多党合作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
第一,从政党层面上分析。在中国的语境中,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不但拥有充沛的政治资源、广泛的组织网络,还具有先进的价值理念。但是,由于共产党产生于体制之外,政党的使命一开始就定位在拯救国家和民族、解放人民群众的历史方位,“革命党”的思维方式一直缠绕着我们,尤其是党的一些领导干部,他们只看到共产党的政治性价值。再加上中国传统“臣民文化”的影响,更容易产生政党高尚化和神圣化的价值取向,忽视或者根本认识不到政党的工具性价值,看不到在和平年代政党的社会性功能高于政治性功能。萨托利对政党有经典的表述:“政党是表达的渠道。这就是说,政党首先且最主要的是表达的手段。它们是工具,是代理机构,通过表达人民的要求而代表他们。”[7]“到目前为止,我以如下的方式有时是可以互换地说明了政党:(1)代表机构,(2)表达工具。与此相关联的是,它们的主要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代表性功能和表达功能。但是我强调的重点在于后者……政党最好被理解为沟通的工具。”[8]
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与共产党是战略伙伴关系,在维护社会稳定中负有重要职责。但现实是,民主党派的代表性作用不强。社会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中介来吸纳和调适民意,并把大众的需求转变为公共政策,这个中介就是政党。在西方国家,不同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不同的政党来进行表达,的确有“在场政治”的感受,从而使社会矛盾比较容易得到释放。在我国,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然而,如果只靠共产党来充当中介角色,显然在吸纳民意方面存在很多盲区,政党制度的“渠道”、“交流”功能必然要受到限制。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同样承担着利益表达、沟通和回应的中介角色,能够为共产党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使决策更为科学。但是,民主党派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使得这一表达的渠道出现了不畅的现象。一是政党意识薄弱。部分党派成员热衷于仕途,恨“无上天梯”,不敢得罪地方执政党的领导,面对权力是“一半儿支吾一半儿软”,有的豪情万丈地喊出“我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凡是地方党委的决策都想方设法寻找理由作解释,追求的是迁就的一致;有的把加入党派只是作为“联谊交友”的场所,并不关心党派的功能发挥。二是代表性不强。政党代表一定的利益群体参与国家权力,以实现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是,党派组织与自己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体出现互动障碍。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中更多的是以“智力库”的角色出现在大众视野,而不是“利益代表”的中介,各党派所联系的那部分群体遇到问题一般不会要求民主党派来代表他们诉求,社会上对民主党派的利益表达和回应的能力也很疑惑。三是政党监督无力。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由于共产党处在领导和执政的地位,因此,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这是共产党自觉的选择。但是,在现行的政党体制中,参政党对执政党有一定的依附性,加上政党制度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因此,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温软而无力。没有制约的权力是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就有可能走向腐败。腐败对社会稳定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尤其是在长期受“不患寡患不均”思想影响的中国。
第二,从制度层面上分析。由于受宪政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化程度不高,因此,限制了多党合作机制的张力和弹性。衡量一种政党制度的制度化水平有四个指标,即政党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制度化水平高就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扩大体制内主要政党的社会基础,各政党就会有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对政治权威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制约,能够规范组织和程序吸纳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并能缓解参与危机。现实中,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尚有“人治”色彩,政治的透明度和清晰度不高,制度剩余和制度匮乏并存,从而造成了制度空间小于现实需求。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虽然进入了宪法,又有相关文件的颁布,各地还有地方性规定,但是,在机制运行方面还没有形成配套的、完备的规范,具体操作技术粗糙,不注重细节,制度中的“真空”地带不少,因此,制约了多党合作制度社会性价值的发挥。
三、提升多党合作制度社会性价值,发挥其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美国学者阿尔蒙德认为,现代化引起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在于“政治体系的能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脱节”[9]。亨廷顿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政府强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求得最佳平衡,树立政治权威。而在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就在于政府在民主呼声和西方政治榜样的压力下,让政治参与跑到了政治制度化的前面,从而引起了合法性危机等。因此,我们要建设一个把民众与国家权力紧密连接起来的政党体制,使这个体制的每个环节都可以有表达的声音,而且在交流中,任何声音都不会被模糊。
(一)更新观念,突破“革命惯性”的窠臼
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我们执政党的一些干部或多或少都有“革命惯性”的后遗症,他们习惯于看到民众如同浇注模型那样一致,不喜欢听到“风声、雨声、萧萧竹声”。在我国政党体制中,共产党处于核心地位,所以,要开发多党合作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功能,执政党各级干部的观念更新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要提升对“多党合作”社会性价值的认识。只有重视对“多党合作”社会性价值的认识,才能从政党是“表达和沟通”的工具着眼,自觉地扩大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卢梭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文明每前进一步,都是以不平等为代价的。亨廷顿也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并非是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力图致富。从中国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在市场经济促进财富增长的同时,各个阶层在社会资源的获得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平等现象,于是,利益表达很不均衡,如果长期堵塞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执政党除了要学“苏珊大妈”多唱民歌外,还要不怕民众的参与热情,善于引导民众在制度内表达。诉求表达是个体价值的觉醒,是民主发展的必然产物。“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从党的性质和对党的要求上提出的。在实际生活中,“被代表者”往往是缺位的,正是由于党的性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主观努力,这种严重缺位才得以缓解[10],现在,“被代表者群体”自己要表达,我们应当欢迎。
第二,从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性价值着眼,执政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更应该在社会的视野中考量。执政党要以“合法性”为轴心来建设政党之间的和谐关系,要帮助民主党派选好人。有些地方党委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两个偏差,一是选旗帜型人物过于注重其在专业中的地位,孰不知业务精湛并不代表有社会责任和领导能力;二是对所谓的“政治上可靠”缺乏科学考量。执政党不是要以“听话、很顺从”来衡量政治上坚定与否,而是要从国家大局来考量“政治坚定”的问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党派更要以诤友、畏友的角色活跃在政党舞台上。
第三,民主党派的干部要重视“一把头发”在社会中的作用。建国初期,毛泽东针对共产党干部不重视民主党派而提出了“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的精辟观点。现在,民主党派有的“旗帜型人物”只愿意自己成为金光闪闪的“一根头发”,而忽视“一把头发”的基础性作用。如果只关心自己的政治前途,忽视应该承担的政党使命,这是对政党不忠诚的表现,也是对多党合作不负责的表现。所以,民主党派在进行政治交接时要加强政治伦理教育,提升民主党派的联系社会和回应社会的能力,这是提升多党合作制度社会性价值的重要方面。
(二)提升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化水平
从维护社会稳定的需求出发,发展中国家需要一种在平等基础上能够自由协商的机制、在尊重民意基础上能够实行利益协调和磨合的机制、在扩大合法性基础上能够吸纳和同化新兴社会力量的机制、在较高制度化基础上能够按程序办事的机制,而提升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化水平就是必经之路。目前,社会上发生的群体事件大都是在体制外寻求救济的表现,主要原因就是缺少表达渠道。因此,要减少群体事件的发生,提升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化水平意义重大。
第一,政党制度应当是个利益博弈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反映出社会的种种冲突,并在平等对话的框架中实现差异的妥协,达到和而不同。在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中,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和各界别人士在人民政协组织架构中的政治协商,都要体现利益博弈和妥协。通过这样一个可以控制国家权力的表达性的交流体系,表达和沟通在每个环节中自由流通,因此,多党合作制度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透明的,而不是雾里看花似的高度一致。
第二,应该把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与凝聚机制结合起来,各项机制都要有深厚的民意为基础。这是因为,多党合作制度建设的动力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对民主的要求,公民不断的诉求直接促进政党的民主化作风,间接推进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化发展。
第三,从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性价值的视野出发,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化是开拓民主的重要渠道,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历来缺少民主和法制的传统,社会奉行的不是“臣服”就是“反抗”,公民没有制度化参与的途径。这些历史遗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表现出负面的一面,就是公民不习惯按游戏规则办事,不习惯遵守社会契约。
政党制度的制度化不但能够排除参与渠道的堵塞,为利益群体被压抑的紧张气氛提供制度化释放出口,防止对抗情绪积累而引发爆发,而且能够引导人们在制度中表达,使人们学会按照程序来反映诉求,学会妥协并改变零和博弈的心理。例如,美国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经常有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发生,但随着美国政党制度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美国公民在制度化参与中养成了按游戏规则行事的习惯,再加上政党的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发达,各阶层的利益表达渠道多元化,从而使得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另外,从消极应对功能来看,现代化动员使人们患上了“民主饥渴症”,因而迫切需要表达和宣泄情绪。制度化参与在有序地疏导人们不满的同时,也消耗了人们的参与激情,因此,政党制度应该是个释放被封闭的对抗和进攻性情绪的安全阀。
(三)打造现代政治文化,改变传统的诉求思维
在《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之研究》一书中,阿尔蒙德和维巴在揭示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时指出:“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识、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的政治制度。”[11]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制度中内在的要素,它是制度运转的内动力;同时,制度也能型塑一定的文化,它是文化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所以,任何政党的行为、公民的行为都被嵌入在文化之中。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打破了旧社会建立起来的带有旧制度的烙印。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形成的集大权于一身的政治传统和根深蒂固的小农观念以及宗法观念的文化背景中,既有滋生家长制等专制作风的土壤,又有寻找“好官、清官”保护的诉求取向。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政治诉求存在着性善论的政治诉求,认为伦理能够起到法律作用;清官意识的政治诉求,实质是对高高在上的行政权力的崇拜;实用理性的政治诉求,对效用和功利的过度张扬,把程序正义和权力制衡理解为“繁琐”和“低效”[12]。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经济结构水平虽然制约着文化观念的发展,但我们也要以积极的姿态来打造现代政治文化。一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化,使之成为我们的行为导向。在推进过程中,要善于把官方的话语体系转化为学理的话语体系和大众的话语体系,以贴近民众的形式并使人民能够理解和接受。二是要发挥多党合作制度的制度教化功能,以制度为引导,培育公民意识,树立公民精神。
[1]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322.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
[3] 李景治.从政治领导到政治管理[J].中国政治,2009,(1).
[4][9] 吴辉.政党制度与政治稳定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42,51.
[5] 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43.
[6] 中国大百科全书 (政治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43.
[7][8]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6,57.
[10] 王长江.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44.
[11] 罗峰.嵌入、整合与政党权威的重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34.
[12] 俞吾金.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政治诉求[J].政治学,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