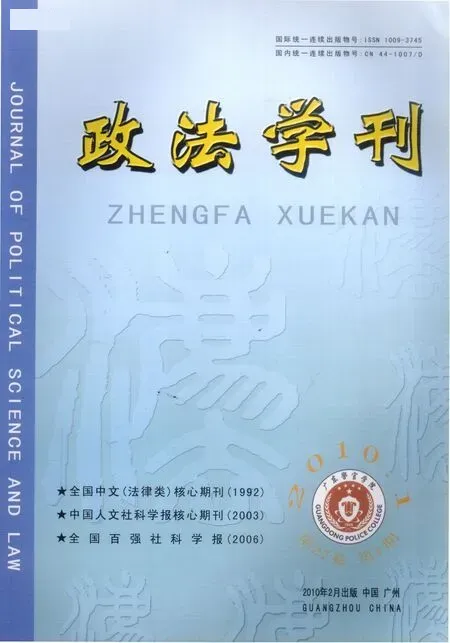现代法理学中“法律权威”问题的困境
——以哈特对奥斯丁的批判为线索
何永红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 400031)
现代法理学中“法律权威”问题的困境
——以哈特对奥斯丁的批判为线索
何永红
(西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重庆 400031)
哈特和奥斯丁之间的学术公案恰当地重启了法律权威的论题。在哈特的批判性审视之下,法律权威的问题陷入了困境:要倡导法律主治,就需要树立法律权威,但到目前为止,现代法理学的各派理论却都无法有效地证明法律是如何拥有权威的。产生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个人自律的道德价值的信奉。
法律权威;哈特;奥斯丁;自律
法律权威已经悄然而又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法律论题中的主流话语。正如夏皮罗所说:“在谈论法律时,很难再想象出比说一定要树立法律权威以规制人们的行为更老套更乏味的话了。”[1]149但是,要描述法律权威的生成机制,或者要在逻辑上证明法律规则或官员何以拥有法律权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有理论家宣称:权威已从我们的世界中消失!这是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阿伦特对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判断。[2]140这个论断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诱惑力,为当代一些理论家所积极响应,也受到其他一些理论家的批判。其中的问题复杂而且抽象,更棘手的是,我们尚不知道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该从何处着手。
二十世纪法哲学领域里有一个经典的文本,即哈特的《法律的概念》,在这本书里面,哈特发起了对现代法理学的奠基人奥斯丁的著名批判,由此引发了持久的论争,此所谓 “哈特和奥斯丁之间的学术公案”。正是这桩学术公案所提供的平台使我们得以恰当地重启法律权威的论题。哈特的批判具有明显的消解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不仅适用于奥斯丁,还适用于其他几种试图解释和证成法律权威的简化论者。在哈特的挑战之下,法律权威的问题陷入了困境:要倡导法律主治,就需要树立法律权威,但到目前为止,现代法理学的各派理论却都无法有效地证明法律是如何拥有权威的。本文旨在清晰地揭示这一困境,并进一步追问它的思想根源。
一、强盗拥有权威吗?
在奥斯丁的学说中,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法律权威来源于强制力。[3]17-41哈特在《法律的概念》里面花了整整三章的篇幅从各个侧面来批判该学说,理由各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 (至少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是将奥斯丁的理论化约为一种与歹徒持枪抢劫的情境相类似的法律模型,他称之为 “强盗情境”。在哈特看来,尽管受害者有充足的理由服从强盗的命令,但 “命令 -制裁”的模式却并没有展示权威的情形。哈特的著述带有浓厚的牛津哲学味儿,注重语词分析,他的论辩直接从概念入手,我们称他的批判为概念上的或本体论上的挑战。在讨论“义务的观念”时,哈特重提强盗情境:A命令 B交出他的钱,并威胁他说如果不遵从就要射杀他。该情境阐明了义务的一般观念,而法律不过是扩大了的强盗情境,所以法律义务就是被强迫服从主权者。B是 “被强迫”(obliged)交出钱的,这是事实,但如果说B“有义务” (have an obligation)或 “有责任”(duty),那么我们就错误地描述了这个情境。如果B侥幸逃脱,然后对他的朋友复述这个情节,他只会说他曾被 A强迫交钱但结果逃掉了没交,而绝不会说他有义务向 A交钱。因此,奥斯丁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 “被强迫”和 “有义务”之间的区分。[4]78-86哈特的结论是,强盗并没有对受害者科予义务,因此他也就不拥有权威,因为在一般的观念中,义务和权威是两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属于一个硬币的不同方面。他对 “强盗情境”的批判性分析不仅适用于奥斯丁的法律模型,还可用来反思当代关于法律权威的一系列重要阐释——尽管哈特本人并不一定致力于此。这正是哈特批判的深远意义所在。哈特的论辩过程和分析效果 (用史密斯的形象比喻来讲),就像剥洋葱一样,从外到里,一层层地剥离,直到接近那个真正的权威内核。可是,剥完后发现什么也没有,空洞无物。除去了那些错误的、不正当的权威观念,但真正的法律权威却依然没有呈现。[5]99
有论者曾指出,一个命令被服从了,或者一个决定被接受了,如果仅仅是因为 X发布了这个命令或者做出了这个决定而没有其他的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X拥有权威。就像说 “我们之所以交税,仅仅是因为法律这样要求”一样,这直接在权威和行动理由之间划上了等号。可是,权威者的命令和行为者的服从之间的相关性从认识论上来讲却是偶然的,因为行为者在选择是否服从之前,可能有更多的因素需要衡量,正是这些因素在根本上决定了行为者的行为,这些因素包括行为者的欲望、目的和动机等等。
此时,强盗的“命令”仅仅是作为引导我渐渐意识到自身义务的诱因而起作用,在其他场合,“命令”的角色完全可以由朋友的忠告或自己的良心来承担。在权威一词较宽泛的意义上,可以说强盗的指示有支配受害者的权威,但那其实只不过意味着受害者应该依照它去行动。但强盗本人其实并不拥有权威,换句话说,受害者承认他的命令并不等于就承认了他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哈特在 “被强迫”和 “义务”之间做出明确区分显然是对的。
二、几种主要权威主张之辩驳
法律权威的理论及其变种复杂多样,很难找到一种明确划分不同法律权威理论的统一标准,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借用史密斯的分类是有益的,他将当下比较得势的权威理论分为结果论,道义论和经验论三种。我们的目的在于证明这三种理论都不能为法律权威提供理由充足的说明。
事实上,最突出的结果论 (consequentialism)正是上文全力批驳过的理论,即用制裁的术语来解释权威和义务。如果说制裁是一种不利后果的话,此处所讨论的就是某种有利结果了。
当代阐释权威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当属拉兹了。他认为,法律所必然拥有的实践权威可以用三个基本命题来理解:依赖性命题 (the dependence thesis):具有权威的指令是建立在其他理由基础之上的,而所谓其他的理由原本是受指令者的一贯行动理由,但是权威指令把它们加以概括并且反映其结果。依赖性命题由正常理由命题(the nor mal justification thesis)来补充:之所以按照权威的指令行事,是因为受指令者更倾向于接受权威者的理由,而不是自己的独立判断,这一命题解释了我们何以会遵从权威。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受指令者不是把权威指令当作一个自己本来就拥有的理由的一个额外因素来考虑的,而是将权威指令直接取代了其他理由,拉兹称之为优先性命题 (the preemptive thesis)。[6]38-68
在拉兹这里,权威之所以受到遵从,是因为行为人“更倾向于接受权威者的理由”,申言之,权威者的理由具有优先性。按照这一理论,能够给出优先性理由的人最典型的莫过于医生了。医生拥有某种专门知识,常常会发布有用的信息,借由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指望一个良善结果的出现。因此,某种专门知识就直接被等同于了权威。这可能是“权威”一词最常见的日常用法了。可是稍加审查便会发现,专门知识与行为者的服从之间同样只存在偶然的联系,就是说,由拥有专门知识的人所提供的建议同样只扮演着“诱因”的角色,它诱发行为者去实现早就潜藏在心中的那些行为原则 (欲望、目的、信念等)。医生建议我停止吸烟,我照做了,但不是纯粹是因为这个建议是拥有专门知识的医生做出的,而是因为这一建议刚和符合我为健康着想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专家的建议和强盗的命令一样,只是引导我渐渐意识到义务的存在,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不是义务本身,因而也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权威。
权威的道义论 (deontological)解释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最为常见的一类是将权威奠基于同意、承诺、契约等观念之上。美国建国时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的建立必须基于人们的同意。当然,这并不是美国人的原创,霍布斯、洛克等政治思想家在各自的学说里都曾以不同形式表达过这类观点,自然状态下的人为了享受和平,都愿意放弃自己的一部分天赋权利而服从法律的指令。
社会契约论因其不符合历史事实经常为人所诟病。[7]209但问题在于,即使我们置这些批评意见于不顾,也很难说基于同意的理论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如前所述,我们的反对理由不是基于事实的,而是基于概念的,它是一个本体论的因而也更具破坏性的挑战。承诺或许是我们按照法律的指令行事的一个充足理由,“我交税是因为我有道德的义务去兑现我的承诺”,但必须再一次指出,遵守法律 (交税)和我的行为原则 (信守承诺)之间只是偶然重合了,在严格的意义上,法律本身并没有给出一个行为理由,因此也不能就此宣称法律拥有权威。第二种对权威的解释并不依赖于同意的观念,而是依赖于感激、互惠、公平竞争义务。[8]186、197、200这种思路强调义务来源于政府和法律施予我们的恩惠 (例如免受暴力的侵害等),作为酬答,我们接受法律的权威。可是,即便感激确实是遵守法律的充分理由,但它本身并不产生权威。
结果论和道义论在解释权威问题上的困境迫使我们寻找另外的途径,一个看起来更审慎更安全的途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人们的确在谈论着权威,并经常把权威归之于各种类型的法律和制度。所以,尽管在理论上证成权威很难,但是可以转而求诸经验 (empirical),研究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人们实际谈论权威和将权威归诸各种事物的方式。
无可否认,“权威”一词的确在日常语言中存在,并在各种场合以不同的方式所使用着,看起来,它似乎并没有像许多理论家所宣称的那样,已经被现代人所遗忘。正是这种语言用法的多样性,增加了我们探讨权威问题的困难,为了能让讨论继续下去——至少就本文的主旨而言,我们不得不在两个重要的概念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即事实权威 (de facto authority)和合法性权威 (de jure authority)的区分。前者是从描述性的角度来讲的,此时说一个人拥有权威仅仅意味着自己的主张能得到它所指向的人的承认或接受,比如说“英国的法律具有权威”,这就只意味着英国的法律在其主权范围内被臣民所接受。在这个层面上对法律权威的特点、产生方式和运行模式进行研究,属于典型的法律科学的范畴。而后一概念则具有规范性的意义,对它的发现、分析和证明的工作应该被称之为法律哲学。
人们同意法律具有权威,这符合事实。但是人们应该同意法律具有权威,就不那么显而易见了。因此,我们的问题必然是:在什么条件下,出于什么原因,法律拥有权威?更准确地说:在什么条件下,一个 (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权威才能存在?
显然,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仅仅诉诸经验是不够的,即仅仅通过举出一系列现实中法律拥有权威的实例是不够的。就像韦伯所说的那样,在一个官僚制的社会中,权威现象如此普遍以致于仅仅瞥见制服,就足以让我们觉得制服下的那人拥有权威因而有权利得到服从。可问题在于,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回答我们为什么应该服从那个穿制服的人。一句话,对 (规范性的)法律权威概念,我们不能靠列出实例来证明其使用得正当。相反,我们必须依靠一种先验的 (a priori)论据来证明,法律权威确实在某些形式的人类共同体中存在。
三、“法律权威”困境的思想根源
对权威的最常见的阐释是将其奠基于强制、协调、同意等概念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简化论者。他们都试图将权威化约成某种其他更可靠更具第一性的规范性渊源:包括避免惩罚,社会协调等,或者是归为那些更主要但无可争议的道德原则,如信守承诺承诺,表达感激等。这倒是很好地解释了人们的行动理由,但却消解了法律权威本身。
所以,法律权威的简化论者陷入了一个困境。它们的解释要么是没有说服力的,因而没有有效解释权威,要么即使有说服力,但最终却消解了权威本身的存在。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困境的深层根源何在?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法律权威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因而需要理论证成的语境。无疑,近来关于权威的理论证明受到了诸种命题的激发,其中最大的或许是康德式的对个人自律价值的信奉。[9]34
1990年,拉兹编辑了一本直接以法律权威为主题的论文集,该集子几乎囊括了现代最有影响的关于该问题的论述,并且拉兹在前言中解释说,这些论文可以理解成是对“哲学无政府主义挑战”的一个回应。[10]1拉兹说,大多数人困惑于一些人居然有权力统治另一些人,而这个困惑其实来源于一个挑战,沃尔夫把这个挑战表达得最为清晰。沃尔夫的核心主张其实比较简单,人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这是道德哲学最基本的假设,用康德术语来说就是,我们道德上的价值和尊严生来就存在于自律这点上。而自律就要求自我立法(self-legislation),就是说,一个人自己在为自己制定法律,并且只服从自己所立之法,就其是自律的存在而言,他没有屈服于他人意志。他也许会做别人命令他做的事,但不是因为他被命令去这么做。而国家和法律相对我们而言就是他律的(heteronomous),它们通过外在的强制力迫使我们遵从它们的指令,但是作为一个自律的存在,我们并没有真正地认同它。尽管某些法律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尊重,但真正说来“所有的权威都同样是不合法的。”[11]12,17
简言之,法律在本质上他律的,而道德和义务却要求自律。其结果必然是,无论义务是否可以以其他方式产生,但法律本身却不能科予义务,因而也就不会享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威。这一论断具有强烈的挑衅意味,但的的确确触及了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任何对法律权威问题的研究,无论是批判还是辩护,都绕不开这一深刻的论断。拉兹编辑的论文集及其本人的著作都可以看成是力图挫败“哲学无政府主义”的一种努力。但不幸的是,这种尝试是无效的,至少站在自律这一立场上是如此。
所以,在信奉自律的框架内,最有效的策略必然是去揭示遵从权威与自我立法之间如何保持一致。但是,以拉兹为首的这些现代理论家们对法律权威问题的证明是不成功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只是在讨论人们服从权威的理由问题。对这一理由提供得越充分,就越容易激起上述的哈特概念论上的挑战。我们这样说,并没有否认事实权威的存在。相反,习惯于服从他人的现象并不是不可想象,很多人就将服从作为自己根本的行为准则。但是习惯性服从的倾向被信奉自律的理论家斥之为愚昧的、可怜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像沃尔夫这些思想家所否认的并不是权威这一种现象,而是“合法性权威” (legit imate authority)的可能性。但一般说来,“权威”一词本身就暗含着“合法性”,所以,“合法性权威”有点自相矛盾的意味。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一点也不惊起阿伦特为何说“权威已从我们这个时代消失”,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是指权威现象已经彻底消失,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如何认识一个已经完全消失的现象?它的意思毋宁是指,我们这个时代,具有合法性的权威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四、结语
其实,在沃尔夫那里,无政府主义绝不是混乱、无秩序的同义词,它只意味着对自律立场的坚守、对哲学演绎 (deduction)方法的推崇,以及对规范意义上的权威无从证明的认定。之所以说它是一种政治哲学,是因为一旦将伦理学上的自律原则贯穿于政制上,结论必然是,只有全体一致的直接民主制才是保持个人自律的唯一方法,而其他不管什么样的代议制政府都是对自律原则的背离。就像沃尔夫自己所指出的那样,认识到这一点可以把我们从以下错觉中解放出来:即以为可以找到一种政治制度,它可以容纳所有具有善意的理性人;其次,它还可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政府无非就是一种利益的安排:扶持社会中某些利益而损害其他利益。
这样,我们也没必要像阿伦特那样悲叹,权威的消失把我们置于一个可悲的处境中。[2]112因为就官员的指令可以得到充分的遵从而言,遵从本身是否反映了真正意义上的权威有那么重要吗?如果权威仅仅只意味着绝对地服从,并进而培育一种普遍的奴性,而权威的消失则意味着奴性的泯灭、独立性的抬升,那可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我们不必为法律权威问题陷入困境而沮丧,因为理论家们可以降低或者进一步澄清自己的目标: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阐释人们遵从官员指令的充分理由,这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理论家们试图用“仅仅因为”的模式来解释法律权威,其结果注定是失败的。
[1]Scott Shapiro.On Hart’sWay Out[A].Jules Coleman.Hart’s Postscript:Essays on the Postscript to The Concept of Law [C].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Hannah 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68.
[3]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 [M].刘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4]H.L.A.哈特:法律的概念 [M].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5]Steven D.Smith.Hart’sOnion:The PeelingAway of Legal Authority[J]. 16 S. Cal. Interdisc.L. J. 97(2006).
[6]约瑟夫·拉兹.自由的道德 [M].孙晓春,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7]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 [M].王笑红,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8]约翰·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 [M].董娇娇,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9]Gerald Dwork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utonom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10]Joseph Raz. Introduction[A].Joseph Raz.Authority[C].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0.
[11]罗伯特·沃尔夫.为无政府主义申辩 [M].毛兴贵,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林 衍
A bstract:Hart’s critique ofAustin properly restarts the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of legal authority.Owing to the critical review of Hart,the issue of legal authority is put into a dilemma.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rule of law,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legal authority,but paradoxically,the modern theories in jurisprudence can not explain where the authority of law comes from.The major cause to this dilemma lies in people’s belief in the moral value of self-discipline.
Key w ords:legal authority;Hart;Austin;self-discipline
The Predicament of Legal Authority in M odern Jurisprudence-Taking Hart’s Critique of Austin as a Clue
He Yong-hong
(School ofAdministrative Law,Southwest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0031,China)
DF08
A
1009-3745(2010)01-0011-05
2010-01-12
何永红 (1981-),男,湖北恩施人,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 2007级博士研究生,重庆市忠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助理,从事法哲学、宪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