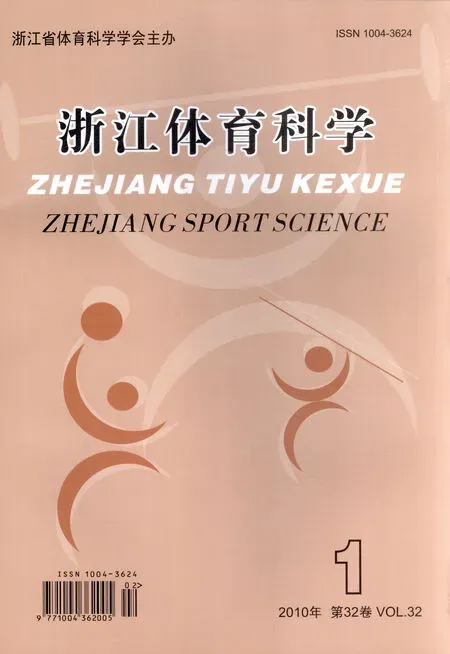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相关研究及评价
潘雪梅,王继帅
(1.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浙江温州325035;2.温州大学体育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课程结构是课程内部各类型、各要素和各成分之间合乎规律的组织形式。课程结构由于受到社会文化的学科分类及逻辑、学习者身心发展规律以及教育条件等制约,并决定教育教学活动的功效,所以历来备受重视[1]。当前我国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正把课程结构的改革作为突破口。课程结构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好分科性和综合性、统一性和选择性、持续性和均衡性这三对矛盾之中[2]。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是体育课程改革的核心部分,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的合理构建是实现学校体育目标的关键,是体育与健康课程顺利实施的依据。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是课程内部各要素、各成分合乎规律的组织形式。课程发展的历史说明,推动课程发展的外在力量只有通过课程结构及其内部矛盾起作用。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是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命脉,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内部的矛盾运动是体育与健康课程发展的动力,只有深入了解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结构,才能正确把握体育与健康课程设计的关键[3]。
由于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理论的滞后给体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带来诸多困难,因此,有必要对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分析,并对此进行简要的评价,指明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研究的薄弱环节和今后的改进方向,以此促进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1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研究的不同观点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是体育与健康课程的重要构成部分,决定着体育教师知识的组合程度,也关系着学生体育素质的培养和人格的健康发展。学者们对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概念表述不一,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也大相径庭。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的概念比较少,界定标准也不够清晰,不能从学科的特质角度给予界定。结构是由内部各要素构成,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也是由内部各要素、各成分合乎规律的组织形式。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构成要素是稳定的、持久的,并且是相互联系的。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不是体育与健康课程各要素的简单拼凑,而是各要素有机的、科学的、合理的组织与建构。
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结构是由学科和活动组成的[4]。另一种观点认为,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是一种课程类型结构[5]。
有学者以体育功能为视角,阐述了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由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五个方面的具体目标及其相应课程内容组成[6]。还有学者从“大体育观”的角度出发,认为体育与健康课程的结构是将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在教师指导或学校组织管理下的一切体育活动,称之为课堂体育、校园体育、生态体育和社区体育[7]。
较之原来的体育课程,现在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单一的传授技术技能的功能发展到培养学生的体育兴趣、发展学生的体能和运动技能、促进学生的身体健康、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功能变化必然引起结构的随之变化。对此有学者将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进行了重新界定,打破了原来只把体育课程局限在体育教学的模式,将其结构进一步扩大,具体包括体育课教学、课外体育活动、课余训练竞赛和社区体育活动[8]。
总之,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是以传承运动技术文化为基点,以体育运动项目为载体,研究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课程类型比例权衡关系、体育运动项目搭配安排、以及运动项目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学习方式等潜因素,并按照预定的一定准则形成相对稳定的课程组织形式。探讨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要素构成,研究各要素的组织方式,能加强课程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协调,更好地发挥各要素的功能。研究体育课堂的有效性问题,不断地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2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的层次关系问题
结构是由要素成分及其相互关联构成相对稳定的系统,这一界定也适合于课程与教学[9]。系统哲学把世界看作一个巨大系统的有机体,是由从微观到宏观、从无机界到人类社会的形形色色的系统组成的层次秩序体系。各个层次等级之间除了共性之外,还有着自身所独具的特性。即一切系统均具有层次性,各层次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高层次的各种大系统或超系统。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是内部各要素、各成分合乎规律并不断融合的组织形式,同样也可分为宏观结构、中观结构、微观结构,它们都是课程结构体系的子系统。
体育与健康课程是一门以传承运动技术文化为目标,关注学生未来发展的课程。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就是以具体的体育运动项目为载体,传递运动技术文化,以各体育运动项目的组合与分配,实现运动技术文化的融合。体育运动项目是文化传递的载体,体育教师、学生、体育课程编制者是文化的传递者,那么,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无疑就是运动技术文化的传递方式和传递形式。运动技术文化具有潜在性,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不仅探讨运动技术文化的形式层面(宏观和中观结构),还研究其实质层面(微观结构)。
2.1 体育与健康课程宏观结构
体育与健康课程宏观结构是一种课程形态结构,是以课程类型为表现形式,主要探讨国家、地方和校本课程的约束性和灵活性问题。对于课程结构的构建来说,最重要的、最根本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如何把这些不同类型的课程有机地组合起来,也就是如何确定不同类型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比例和运作关系[10]。国家、地方和校本课程以何种比例关系更为合理,如何调整和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与国家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是密不可分的。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要“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实施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11]。
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明确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12]”
2003年,《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又提出赋予学校合理而充分的课程自主权,为学校创造性的实施国家课程,因地制宜地开放学校课程,为学生有效选择课程提供保障。
无论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还是校本课程,都是课程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13],在课程设置方案中都占有一定的课时比例,并通过具体的科目、门类落实到学校的教学中去,发挥各自独特的育人功能。当然,三类课程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有机地整合在一起的,相互之间也有彼此增进的关系。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比例关系。从三级课程角度来,国家课程占90%左右,在国家确定的课程之外的10%-12%的课中,校本课程所能占到的也只有5%左右。陈旭远认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所占比例分别为80%、15%、5%[14]。从这个角度分析,“三级管理的课程范围(或称课程形态)应该更确切地称为国定课程、地定课程和校定课程”[15]。
但鉴于当前人们的习惯,以及相关文件中的用语,本文在描述时还采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个概念。其中校本课程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部分,“狭义的校本课程”是指与国定课程、地方课程相对应的校本课程,即国家为学校预留的占总课时5%左右的少部分课程,其目的是发挥学校在课程开放中的自主性;广义的校本课程不仅包括狭义的校本课程,也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化改造后的课程,其目的是适合于本校实际情况和学生的实际需求[16]。
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各自的含义和目的以及我国的国情来看,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应以国家课程为主,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为辅,具体的比例可以随着学段的不同而不同[17]。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程应以国家课程为主,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为辅。随着年级的升高,在高中阶段应加大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比例。
国家课程是政策性的课程形态,主要体现国家的教育意志和指导政策。由于全国的地区差异、学校差异以及学生差异,国家课程所占课时比例应更倾向于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调动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潜力,充分给予学校更大的选择空间,更切合各区域学校的实际情况。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圆锥体一样,三者所占比例逐级增加。因此,国家课程是国家教育政策的反应,要体现一定约束性。学校体育工作者应在遵循国家教育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力度,增加校本课程的比例。
2.2 体育与健康课程中观结构
体育与健康课程中观结构是一种亚形态结构,以体育运动项目为载体,主要探讨体育运动项目与项目之间的关系,各个项目之间的选择与分配问题。体育与健康课程中观结构涉及范围略窄于课程宏观结构,主要处理体育与健康课程类型中各具体的体育运动项目的构成与相互关系,如必修课开设哪些运动项目,田径类项目与球类项目的关系如何。同时体育运动项目也是传递运动技术文化的载体,处理各运动项目的关系以及发挥他们之间的耦合功能,是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解决的重要问题。
体育运动项目是实现体育目的的有效手段,体育目的是人的价值观的表现方式。一个体育运动项目只有在随着文化演进的过程中不断适应社会和人类价值观的转变才会得以延续[18]。如果这个项目将人的价值观与人的健康和兴趣等需求相剥离,那这个运动项目就会从文化演进的历史长河中逃离。铅球、标枪、鞍马、山羊等项目的逃离,正是由于项目的价值观不适合学校体育教学的发展,各运动项目不能很好地体现现代社会价值取向。研究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尤其是探寻课程中观结构的体育运动项目融合以及项目之间的合理分配也成为课程发展的需要。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规定将体育课程分为6个体育运动项目系列和1个系列的健康教育专题,即球类项目、体操类项目、田径类项目、水上或冰雪类项目、民族民间体育类项目、新兴运动项目,并要求学生在高中三年中修满11个必修学分。在调研中发现,在选修的运动项目中,主要侧重于球类项目和田径类项目,很少涉及到水上或冰雪类项目、民族民间体育类项目、新兴运动项目,其中师资力量、场地设施是限制学生选修这些运动项目的主要原因。此外,在不同年级选修的课程内容方面,缺乏其衔接性的考虑,不能根据学生身体素质的差异性进行有针对性地提高。
2.3 体育与健康课程微观结构
美国学者施瓦布专注于课程微观结构的分析,但他进一步研究了学科结构的本质以及学科结构的内在层次性。学科结构就是“规定那门学科所研究的题材和控制其研究方法的一系列外加的概念”[19]。同时他从课程微观结构的角度出发,认为课程内部要素应包括“五个方面的经验”,即学科内容、学习者、社会环境、教师和课程编制(按照施瓦布的顺序)[20]。他对课程结构的有着独到的见解,并已经意识到学科间的关系在课程结构上的意义。而课程结构改变的程度取决于教师、学生和学科知识之间改变程度的相互关系[21]。对此,瑞士学者皮亚杰指出,对深层结构的把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应透过表层结构把握具有转换规则的深层结构[22]。
体育与健康课程微观结构是一种实质结构。主要探讨体育与健康课程内部各要素及之间的关系,探寻体育运动项目渗透的课程价值观念以及各要素(载体)所具备的条件和能力。它包括体育运动项目内容、学生、体育教师、体育教学环境和体育课程编制者等要素。体育与健康课程微观结构是把构成体育与健康课程某一阶段或某一层面作为分析的对象系统,去分析它的结构和相应的功能。这是一个最为具体、最为细致的分析层次[4]。这种分析的水平将最终决定着教学的实施效果。
体育与健康课程微观结构研究的价值在于提高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体育学习成绩,并促进其全面健康发展。此外,通过课程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配合和协调,研究体育课堂的有效性问题,可以更好地提高体育教学质量和水平。
3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的问题
关于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课程结构优化内涵、方式及原则等方面;而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内容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同时也缺少对课程结构优化策略的研究。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是体育与健康课程内部要素的合目的性改造,使其发挥各自功能的基础上,相互协调发展,达到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的整体功能最大化,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改变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象,整体设置课程门类和课程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要,体现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现代教学论认为,良好的学校课程应具有整体性,为了使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课程内容要素和课程范畴应是完整的统一,课程结构优化要体现显性与隐形的统一,静态和动态的统一,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原则研究认为,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遵循目的性、整体性、有序性和针对性四个原则[5]。此外还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明确了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结构优化的基本原则,分别为综合性原则、均衡性原则和选择性原则[23]。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方式研究提出了三课并重的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将体育理论课、实践课和活动课结合起来,从宏观上把握体育教学活动整体及各要素之间内部的关系和功能,充分发挥综合课程的作用,实现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的优化。还有从体育运动项目之间关系方面,阐述了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方式,利用系统整体中各体育运动项目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提供的信息,构建合理的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提高和优化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整体功能和结构。然而,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要求重新认识和确立各种课程类型在学校体系中的价值、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这将有利于体育与健康课程功能的转变和实现。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是由要素成分之间相互关联,形成相对稳定系统的过程。而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一是对要素的选择、组合、添加或缩减,亦或是改善要素本身;二是改变或调整要素之间关联的方式,同样的要素,不同的关联(以及由此关联形成的机制)可以整体地优化这个系统(或体系)。体育与健康课程的优化更多的就是对微观课程领域的优化。因此,体育与健康课程微观结构优化将成为课程领域今后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4 对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研究的简要评价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是体育课程改革的核心部分,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的合理构建是实现学校体育目标的关键,是体育与健康课程顺利实施的依据。其中它体现着体育与健康课程理念和课程设置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正确把握体育与健康课程设计方向的关键。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概念的模糊,给体育课程改革与发展带来了阻力,并使得“淡化运动技能学习”曾一度成了困惑无数一线体育教师的藩篱。运动技能受到强烈的排斥,认为学生体质与健康状况下降的祸根在于运动技能的学习,甚至有“将竞技运动赶出学校”的偏激理论。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且多数学者侧重于课程宏观结构的研究,缺少对体育与健康课程微观结构的研究。多数学者从课程类型、课程功能、课程形态等方面来论述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但研究角度单一,缺乏对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的准确定位。体育教学实践已经证明,只从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要从根本上把握课程结构,就必须从整体上入手,建构一种具有整体性的课程结构观。因此,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阐释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将是一个研究的创新点。其中如何处理好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约束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如何合理分配和选择体育运动项目,如何改善学生的学习方式、提高体育课堂有效性等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的研究甚少,尤其是关于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策略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的内部动力要素是什么?以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优化将是一个新的突破点。体育与健康课程结构的优化可以解释为课程结构的各要素对课程结构的贡献之和,通常来说,课程结构各要素并不是到达它们各自贡献的最大值(或许存在此消彼长的情况),而是,各要素有机地融合一个整体,进而发挥整体的贡献最大值。在融合的过程中,把握体育与健康课程各要素各自贡献值的“度”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1] 黄甫全.现代课程与教学论学程(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467-468.
[2] 裴娣娜.我国学校科学教育的政策与改革思路[EB/OL].http://www.dss.gov.cn,2009-08-07.
[3] 王继帅,樊炳有.中小学体育课程改革相关研究及评价[J].体育学刊,2009,16(1):58-62.
[4] 李艳翎.体育课程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1-66.
[5] 王琪.我国建国以来普通中学体育课程结构的发展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5:7-10.
[6] 季浏.体育与健康课程解析[N].中国教育报,2006-01-13(5):3.
[7] 于文谦,苗治文.中国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新动向[J].体育学刊,2002(3):77-78.
[8] 张瑞林,秦椿林.体育管理学[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3-116.
[9] 张楚廷.教学论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7-70.
[10] 石鸥.结构的力量——《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的理解与实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J].人民教育,1999(7):6.
[12]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J].人民教育,2001(9):6.
[13] 刘家访,余文森,洪明.现代课程论基础教程[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4-67.
[14] 陈旭远.课程与教学论[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12.
[15] 徐玉珍.校本课程开发:概念解读[J].课程·教材·教法,2004(4):25-26.
[16] 周登嵩.学校体育热点50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0-46.
[17] 许洁英.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含义、目的及地位[J].教育研究,2005(8):34-36.
[18] 孙波,李杰凯.论中学体育运动项目的逃离与轻软化趋势[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8(6):11-13.
[19]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美国教育改革[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265.
[20] 帕梅拉·博洛廷·约瑟夫[美],等.课程文化[M].余强,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8:6-7.
[21] 乔治·丁·波斯纳.课程分析[M].仇光鹏,韩苗苗,张现荣,译.赵中建,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99.
[22] 靳莹,周志华.从结构主义走向建构主义的课程观及其启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20):45-48.
[23] 陆作文.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4,21(5):84-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