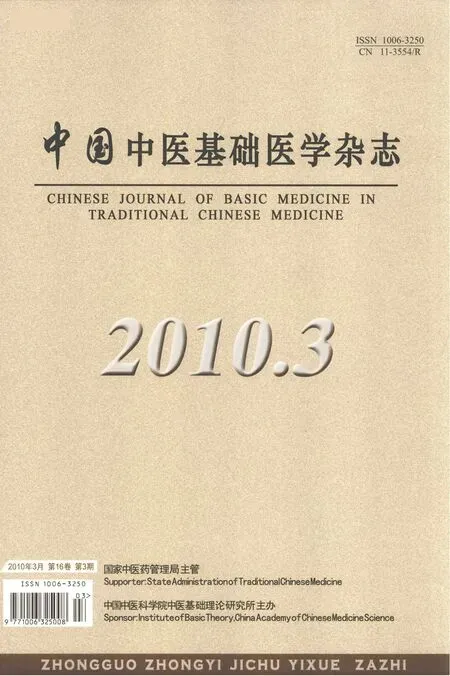建国以来《千金要方》五脏证候总体的研究概况
侍 伟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千金要方》)由唐·孙思邈(541~681年)[1]撰于公元 636~659年间[1,2],全书共 30 卷,分为 232 门,合方论 5300 首。《千金要方》是“孙思邈在整理和提高(唐)以前医学成就的基础上,总结自己毕生的临床经验,写出的一部综合性临床百科全书”[3]。该书内容丰富,有论有方,是一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医方著作,具有很大的临床实用价值。对本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初唐及以前的中医药学发展情况。
本文综述建国以来对《千金要方》五脏证候总体的研究。本文的“五脏证候”以《千金要方》原书明确表达者为准,后人总结者不列入。
本综述引用的文献所使用的《千金要方》版本均为治平三年日本江户医学版影印本或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道藏本,以上版本均经过北宋校正医书局的改校,与孙思邈原书有较大差异。
1 《千金要方》五脏证候总体的研究
1.1 五脏证候总述
李文刚[4]认为,《千金要方》中以五脏五腑为卷名的10卷书,集中体现了以脏腑为纲论杂病的思想。各卷均首先介绍了各脏腑的“脉论”,也就是解剖生理,作为论述病证的理论基础。其次,论各脏腑的虚实病证及五劳、六极病。再次,论与各脏腑有关的杂病,孙思邈又增加了不少病证和条文。这种以脏腑为纲论述杂病的学术思想,对后世研究疾病辨证有深远的影响。
傅芳[5]引何绍奇观点指出,孙思邈继承了《内经》的脏腑学说,在《千金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方法,是脏腑分类辨治的倡导者,相当于今日按系统分类法,对后世深有启发,认为可补张仲景之不逮。
《孙思邈〈千金方〉研究》一书系统整理了《千金方》各脏证候的辨证要点。郭谦亨[6]认为,孙氏承前人之法,突出脏腑辨证的核心作用,以八纲为辨证绳墨,对每一脏分为实热、虚寒两证,并把脏腑俱实、俱虚归为脏病。对如何发现认识疾病及其所伤脏腑的关系,“先诊其候以审之”,也就是从色、脉、症进行了分析、判断。
金芷君[7]认为,《千金要方》形成了一套有脉有论、理法方药具备、比较完整而成熟的以脏腑为核心、以阴阳为大纲、以寒热虚实论证、以脏腑所属表里疾病为具体对象的内科脏腑病证体系。
汪文娟[8]指出:“五脏疾病的调治,继东汉·张仲景之后,对其提纲掣领地辨证用药者,当推孙思邈。《千金方》就五脏虚实的方剂多达788首,约占整个内服方的30%左右。孙氏对五脏病证,是从寒热虚实确定性质,以五脏确定部位,治疗则以‘盛者泻之,虚者补之’、‘处方皆准病根冷热而制之’,为后世脏腑辨证施治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2 “实多热、虚多寒”说
蒋士生[9]认为,“在《千金要方》中实寒、虚热这类证候较为少见。这可能与唐以前医家对寒热的认识有关。实际上亦有一部分实寒和虚热证候,只是当作虚冷和实热归纳罢了。”王景泉[10]认为,“《千金方》论肝之实,多由实热入手;而肝之虚,却偏重虚寒之为证。”
1.3 “脏热腑寒”说
王洪图[11,12]认为,“《千金》中辑录了《集验方》和《删繁方》的论述与方剂。”《千金方》中有关“脏热腑寒”的论述均引自《集验方》和《删繁方》。《集验方》乃南北朝名医姚僧垣(公元449~538年)所撰。《删繁方》的作者是谢士泰,与姚僧垣是同时代的医家。由此可见,在南北朝时期,用“脏热腑寒”去辨证,应该是医学重要流派的辨证方法。《千金方》在有关体窍病的辨治中,体现出了“热应脏、寒应腑”的特点。王氏认为,“由于唐代以后忽略了‘热应脏、寒应腑’,但却继承了该理论指导下的治病方法和方剂,以至于造成了某些误解。如治疗大病后(髓虚)虚烦不得眠,以‘热应脏、寒应腑’来分析,髓虚寒应于腑,故以温胆汤治之,效果显著”。对于今天对温胆汤的解释,王氏认为“皆因脱离了‘寒应腑’之原意而有强解之感”。徐江雁[13]认为,在隋唐时期世人多服食丹石耗阴伤脏而热,在这种特殊背景条件下,产生了脏热腑寒学说。脏热腑寒说是根据当时之临证实践,有别于张仲景伤寒六经辨证的另一种辨证方法,是对《内经》辨证理论切合实际的阐释和丰富。同时徐氏认为脏热腑寒辨证也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并非任何外感、内伤病证皆可用之。
1.4 “五脏极证”说
卓廉士[14]指出:“五脏极证”见于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之十一至卷之二十所论五脏病中。“夫六极者,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应于肝,雷气动于心,谷气感到脾,雨气润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所以窍应于五。五脏邪伤,则六腑生极,故曰五脏六极也”(《卷十一·筋极第四》)。由于“肝应筋,肝与筋合”,故肝气受邪称为“筋极”;“心应脉,脉与心合”,心气受邪为“脉极”;“脾应肉,肉多肌合”,脾受邪气为“肉极”;“肺应气,气与肺合”;肺受邪气谓之“气极”;“肾应骨,骨与肾合”,肾之极证谓为“骨极”;又肾藏精,如精气受邪则为“精极”。病由六腑传入,故又称为“五脏六极”。这是脏腑受邪,内外皆伤,致使脏腑功能出现极度亢奋或极度衰竭的证候。“五脏极证”是邪气留滞五体、迁延不愈,通过经脉及于所系之六腑,进而波及与之相表里的五脏,故影响以该受病脏腑为中心的整个系统。如“筋极”累及肝脏和其所主司的“筋”系统,还及于肝经所循的部位;“骨极”病及于肾和肾所司之骨骼系统,并及于肾经所循的部位,且证情大多重笃。由于反复感受邪气,且时日已久,故临床表现以虚证为多。由于“五脏极证”的证候遍及于脏、腑、经脉,故病势较为弥漫,见症较为复杂。
2 《千金要方》疾病五脏证治通论
2.1 脏腑温病
王永谦[15]认为,《千金要方》中的脏腑温病是脏腑受疫疠感而即发的温疫,如原文指出的“随时受病”,“脏腑受病而生”便说明了这个问题。因为脏腑是生命的根本,无论是外感或内伤诸病,往往累及脏腑,这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感受疫病毒烈之气,可迅速入脏腑而发病,发病急,所以孙思邈称其是“横病”。《千金要方》所论的5种温病,各脏病都具有特殊证候。而且各病皆伴发热,又具有传染性,这就基本指明了脏腑温病的性质和特征。郭谦亨[6]认为,《千金方》首创以脏腑为核心的三焦辨证理论,即上焦主心肺之病,中焦主脾胃之病,下焦主肝肾之病候也。
2.2 五脏虚劳
汪文娟[8]指出,对于五脏虚劳的治疗,孙氏在《千金方》中首先指出,心劳病者,补脾气以益之,脾王则感于心,脾为心子,补脾益心;肝劳病者,补心气以益之,心王则感于肝,心为肝子,补心益肝;脾劳病者,补肺气以益之,肺王则感于脾,肺为脾子,补肺益脾;肺劳病者,补肾气以益之,肾王则感于肺,肾为肺子,补肾益肺;肾劳病者,补肝气以益之,肝王则感于肾,肝为肾子,补肝益肾。具体地讲,就是心虚补脾,肝虚补心,脾虚补肺,肺虚补肾,肾虚补肝。这种壮子益母的治疗观点显然已经突破了单向相生的概念,使单向相生的涵义扩大为母子相互资生。如肝虚寒劳损方中,重用养心气补心血的丹参和川芎,肾劳方中,配伍补肝强筋骨的牛膝、杜仲和五加皮。
2.3 五脏中风
王莉[16]指出,《千金方》多处提及五脏中风的问题。除引述《素问》、《金匮》、《病源》中五脏中风内容外,还在贼风论中论及五脏为厉风所伤。如“治肝虚寒,卒然喑哑不声,踞坐不得,面目青黑,四肢缓弱,遗失便利,厉风所损,桂枝酒主之方。”从上述病证看,五脏为厉风所伤比之《内经》、《金匮》、《病源》所指要明确得多,主要与现代医学所言之脑血管意外(中风)、休克、精神病等发病急骤、病情危重的病证有关。唐宗儒[17]指出,《千金要方》对五脏六腑中风之描述较为详尽:“风中五脏六腑之输,亦为脏腑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王怡、武长春[6]认为,《千金方》以脏腑辨证分析了中风的不同证型,列举了五脏中风的表现。
2.4 心身疾病和精神情志病证
黄健等[18]认为,孙思邈在《黄帝内经》认识的基础上,将中医心身疾病由浅至深划分为4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五劳(志劳、思劳、心劳、忧劳、疲劳);二是六极(气极、血极、筋极、肉极、骨极、精极),是五劳的进一步发展;三是七伤(阴寒、阴痿、里急、精连连而不绝、精少囊下湿、精清、小便苦数临事不卒),实际上是长期过度的精神心理活动和异常的行为因素造成了人体脏腑、阴阳、气血的损伤,是心身疾病的进一步发展;四是七气和十二风,如孙氏指出:“五劳六极,力乏气畜,变成寒热、气疰,发作有时,受邪为病,凡有十二种风。”由于异常精神因素的长期刺激,此类患者已经出现了各种典型的心身疾病症状,如孙氏“十二风”中指出的瘾疹、哮喘、心痛、惊悸、腹胀、吐逆、耳聋、视力下降等。
金芷君[7]认为,《千金要方》还将脏腑与精神情志病证密切相联,如论肝:“肝虚则恐,实则怒,怒而不已亦生忧矣”;论心:“心气虚则悲不已,实则笑不休;心气虚者,其人即畏,合目欲眠……心气盛则梦喜笑及恐畏”,“心伤则苦惊,喜忘善怒”;论脾:“脾气虚则五脏不安,梦饮食不足;脾气盛则梦歌乐”;论肺:“肺主魄,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肺气不足,惕然自惊,或哭或歌或怒”;论肾:“肾藏精,精舍志,盛怒不止则伤志,志伤则善忘,变动为慄,在志为恐”,“肾实也,苦恍惚健忘”。由此可见,五脏情志各有所伤,情志病证多与五脏相关。
2.5 其他
王存芬[19]认为,孙思邈对肺、胃、肾在消渴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认识清楚,定位精确。用羊肺、羊肾、猪肚、猪肾配合药物治疗“消渴”、“胃渴”、“肾消”,达到“同气相求”之效。
刘锐[20]认为,《千金要方》根据扁鹊论腑病水、其根在腑的理论,以腑立名分五腑水,明列证治,实为其特点。并且《千金要方》提出水肿病危象的5种重要体征为五不治:“第一唇黑伤肝,第二缺盆平伤心,第三脐出伤脾,第四背平伤肺,第五足下平满伤肾”,列为医者判断水肿病预后的规律,代相沿用。
乔富渠[6]认为,孙氏指出“病久必归五脏”,列举了五脏痫证的表现。赵璞珊指出,在儿科疾病上,孙思邈着重论述了“痫”、“痉”两病,总的病因认为都是由于“藏气不平”。并可按证候将痫证分为五藏痫、六畜痫。
王怡、武长春[6]认为,《千金方》以五脏主证分类,对贼风侵犯五脏所表现出的症状进行了描述。
3 小结
通过对建国以来《千金要方》五脏证候总体研究文献的总结,可以看出《千金要方》的五脏证候体系基本上是完整的,《千金要方》的“脏腑辨证部分,内容全面系统,体例编排得当,叙述层次分明”,更重要的是五脏证候体系与现代比较有其明显的特点。
现代对《千金要方》五脏证候总体的研究,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千金要方》对脏腑辨证施治体系的发展以及与现代不同的证候理论上,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的来说,建国以来对《千金要方》证候(包括五脏证候)的研究尚缺乏重视,文献较少,在研究深度上仍有明显不足,多数文献只是不加分析地直接引述《千金要方》的原文,缺乏总结和提炼,缺乏与现代证候体系的直接而系统的比较,尤其是从《千金要方》作为中医证候学说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的角度进行系统比较研究者鲜见。
从证候学说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自晋唐至宋金之际,医学界总的来说有重方药轻理法的风气,医家著述偏重于方药的搜集整理,忽视病机理论的研究。但从晋唐时期开始对病的研究已逐渐转为对证的研究,《千金要方》中“既有辨病论治,按病列方,也有在辨病基础上辨证论治,按证列方”,代表了证候学说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所以全面、系统的研究《千金要方》证候体系,在证候学说发展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导师陈小野研究员对本文的指导)
[1] 方春阳.孙思邈生卒考辨[J].浙江中医杂志,2002,9:369-371.
[2] 黄作阵.试述《千金翼方》的几个文献学问题[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18(2):17-19.
[3] 王晓鹤.孙思邈及其代表作《备急千金要方》[J].山西中医,1995,11(3):53-55.
[4] 李文刚,刘宁.浅谈孙思邈对中医杂病论治的贡献[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0(2):132-133.
[5] 傅芳.半世纪来对唐代名医孙思邈的研究[J].中华医史杂志,1983,13(1,纪念孙思邈逝世1300周年专辑):61-65.
[6] 雷自申,赵石麟,张文,等.孙思邈《千金方》研究[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7] 金芷君.《千金要方》内科脏腑病证辨治特点[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22(4):35-38.
[8] 汪文娟.《千金方》五脏病治法初探[J].上海中医药杂志,1991,(8):31-33.
[9] 蒋士生.试论孙思邈对脏腑辨证的贡献[J].湖南中医杂志,1992,(3):14-15.
[10] 王景泉.肝寒证临床管见[J].国医论坛,1996,(5):43-44.
[11] 王洪图.体窍所应及脏热腑寒说[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05,(4):6-8.
[12] 王洪图.脏热腑寒说及温胆汤用法[J].安徽中医临床杂志,2000,12(1):1-2.
[13] 徐江雁.浅析脏热腑寒学说[J].光明中医,2004,(1):17.
[14] 卓廉士.孙思邈“五脏极证”浅析[J].实用中医药杂志,2003,(12):662-663.
[15] 王永谦.试论《千金要方》的脏腑温病[J].陕西中医,1987,(3):126-127.
[16] 王存芬,朱强,田雪峰,等.《千金方》用脏器疗法治疗消渴特色掬萃[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1,7(7):70-71.
[17] 王莉.唐宋“五脏中风”证治特色探析[J].上海中医药杂志,2001,35(9):40-42.
[18] 唐宗儒.《千金》中风治法和制方特色浅议[J].陕西中医,1987,8(3):134-135.
[19] 黄健,郭丽娃.孙思邈中医心身医学思想探微[J].中华中医药杂志,2007,(4):891.
[20] 刘锐.浅谈《千金要方》水肿病的治法[J].陕西中医,1987,(3):1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