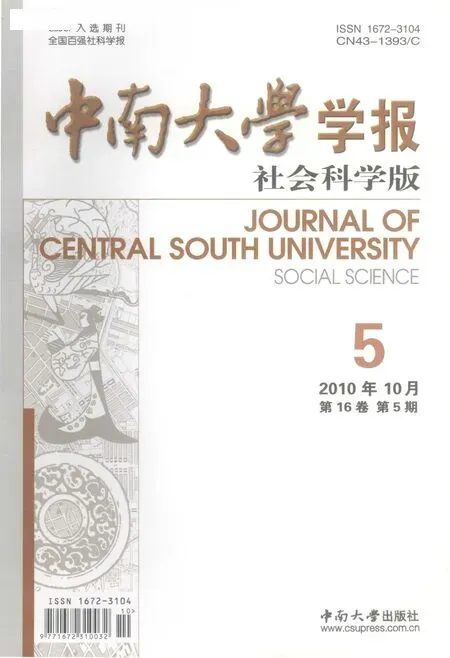《柳毅传》原发生地考辨
肖献军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唐传奇《柳毅传》因文本中多次出现有争议性的地名,致使人们对小说主要发生地有不同看法,综合起来有以下四种:①故事发生在君山;②发生在太湖洞庭东山;③发生地点不确定,但偏重于洞庭东山;④此是小说家所言,本无定处。小说的主要发生地是否具有确定性?如果具有确定性,它究竟又发生在哪里?本文试图通过文本,结合有关历史地理知识,从多角度进行考辨,还原李朝威创作《柳毅传》时小说的原发生地。
一、唐人的小说观与《柳毅传》原发生地的确定性
宋人范致明《岳阳风土记》中说:“《灵姻传》(即《柳毅传》)始言还湘滨,中言将归吴国,固无定处。然则前人因事阙文,后人遂以为实,此亦好事者之过也。”[1](21)鲁迅也曾指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2](70),说明了唐人在创作传奇时开始大量运用虚构手段,这从《柳毅传》可以看出。在唐传奇中,《柳毅传》是运用虚构手段较成功的一篇。但是否真如范致明所说,小说中原发生地是虚构的呢?
事实上,“始有意为小说”还包含有另一层意思,这体现在“始”上,说明了唐人在创作传奇过程中仍然受传统写实手法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强调故事发生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传奇的开头或结尾会有一小段文字,强调传奇来源的真实性,或者是亲身经历或考证,或者是听亲友所说,或强调与小说中主人公的姻亲关系。
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详其事。(白行简《李娃传》)[3](279)
张之友闻之者莫不耸异之,然而张志亦绝矣。稹特与张厚,因征其词。(元稹《莺莺传》)[3](305)
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觌淳于生棼,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李公佐《南柯太守传》)[3](264)
通过这些交代,以强调小说并非凭空虚构,从而为小说中的道德说教增强说服力。《柳毅传》也受到了这种创作观念的影响,因而在文章结尾写道:“至开元末,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谪官东南。经洞庭,……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3](238)
第二,为了强调故事的真实性,作者往往在小说中掺入自己所熟知的家乡名物,或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扯到家乡附近来。《柳毅传》的作者是李朝威,陇西人,约唐肃宗乾元中前后在世,他所作传奇除《柳毅传》外,还有一篇《柳参军传》,“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于长安闲游”。[4](514)华州紧邻京兆府,故事就是以长安为背景展开情节的,这与李朝威是陇西人有一定的关系,以本地人身份写发生在相邻地的故事,更给人以真实的感觉。《柳毅传》原发生地虽然没有在陇西,但却和陇西也有一定关联,龙女牧羊处(泾阳)离陇西就不远,据《元和郡县图志》载:
(泾阳县)本秦旧县。汉属安定郡,惠帝改置池阳县,属左冯翊,故城在今县西北二里,以其地在池水之阳,故曰池阳。后魏废,于今县置咸阳郡,苻秦又置泾阳县。隋文帝罢郡,移泾阳县于咸阳郡,属雍州,即今县是也。[5](27)
唐时,陇西属于渭州,属于陇右道,而泾阳与长安同属京兆府关内道。陇右道和关内道紧邻,而渭州和京兆府之间仅隔岐州和秦州。因此,为了强调传奇的真实性,作者把传奇的次发生地安排在离家乡不远的泾阳。
第三,唐传奇为了强调故事的真实性,多写当朝的故事,具有确定而真实的时间、职官、物产、民情、风俗等。
大历中,陇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进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试于天官。夏六月,至长安,舍于新昌里。……生自此心怀疑恶,猜忌万端,夫妻之间,无聊生矣。……尔后往往暴加捶楚,备诸毒虐,竟讼于公庭而遣之。……又畜一短剑,甚利,顾谓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铁,唯断作罪过头!”大凡生所见妇人,辄加猜忌,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蒋防《霍小玉传》)[3](245−252)
李益,故宰相揆族子,于诗尤所长。贞元末,名与宗人贺相埒。……少痴而忌克,防闲妻妾苛严,世谓妬为“李益疾”。(欧阳修等《新唐书》)[6](5784)
从《霍小玉传》和《新唐书·李益传》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唐传奇中人物、时间、地点、官职、经历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甚至在某些具体的细节上还可以和正史相印证。因而,唐人虽“始有意为小说”,但仍受传统文学特别是史传文学影响较大,除了在情节上虚构成分较大外,作者在其它方面竭力强调真实性。《柳毅传》也是这样,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7](66)与宋元话本相比,唐传奇更体现了“实”的特征。正因为这一特征,至少在作家的头脑中《柳毅传》的原发生地具有确定性和唯一性,不会如《岳阳风土记》中所谓“固无定处”、“前人因事阙文,后人遂以为实,此亦好事者之过也”。[1](21)那么《柳毅传》原发生地究竟在湖湘洞庭还是吴越太湖呢?
二、从文本中地名看《柳毅传》原发生地
《柳毅传》原发生地引起争议,实是由于文本中出现了不少具有争议性的地理名称所致,如“吴” “越”“洞庭” “湘滨”等,如果能够从有关史料中确定李朝威曾游历湖湘洞庭或者太湖,故事原发生地的确定也会变得简单。但从现存资料看作者生平不可考,因而要确定小说的原发生地,须从这些地名所蕴含的文化背景去考察,同时还涉及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推理。
第一,“吴”“楚”之争。
文本中提到:“闻君将还吴,密迩洞庭。或以尺书,寄托侍者,未卜将以为可乎?”[3](230)同时又提到:“毅,大王之乡人也。长于楚,游学于秦。”[3](232)这样直接给人以矛盾的表象,持不同说法者都会持之以为据,但不能详尽其理。要了解小说的原发生地究竟是吴地还是楚地,先看看历史上的吴楚之争。
阖闾九年,吴王阖闾伐楚,经柏举之战,大败楚军,攻入楚都郢。十一年,吴师再次伐楚,楚国迁都于鄀。十九年,阖闾死。此次交锋,吴国打败楚国,前后不过十年,但楚并没有因此灭亡,湖湘洞庭一带仍为楚国范围。战国中期,楚威王败越,占领吴故地,越从此破散。公元前306年,楚灭越,设郡江东。其后,楚东迁都城巨阳、寿春。第二次交锋,越国失败,随着楚都的东迁,吴地成了楚的最坚实的后方。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国。秦统治的时间极短,就给刘邦和项羽给灭了。项羽,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楚国灭亡之后,项氏家族惨遭屠杀,他与项庄、项梁流亡到吴中。不久,项羽反秦成功,建立了“西楚”政权,他本人也以“西楚霸王”自称。吴中地区无疑成了西楚最坚实的大本营了。以致于项羽在楚汉之争失败后说:“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8](336)西楚政权虽仅存四年,然而它以推翻暴秦统治而获得世人的公认,《史记》为之立本纪。汉政权的建立者刘邦为沛人,他和项羽实际上是同乡,秦时同属泗水郡。刘邦虽然建立的是“汉”,但却也以楚人自称,曾说:“(若)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9](2047)楚汉之争,实是楚人内部争夺对全国的统治权,不论是“楚”还是“汉”,吴地都是他们的统治范围,这样楚的概念扩展在长江以南包括吴越的广大地区。
但湖湘洞庭地区在三国时也曾在东吴版图内,地处荆州,分属南郡、长沙郡和衡阳郡,据《三国志》载,东汉建安十九年,孙、刘议定以湘江为界,江东属吴,江西属蜀。因此洞庭成了东吴的前沿阵地,鲁肃便在岳州修建了阅军楼(岳阳楼的前身),训练水军与蜀抗衡。
然而,这里有三点要注意:①湖湘一带归属于吴的地位并不稳妥,这里仍然是吴、蜀和曹魏争夺的地方,不仅鲁肃屯兵巴丘,关羽也屯兵茱萸江(即今澬水,在益阳)。唐时益阳县仍然有关羽濑、甘宁故垒、关羽故垒遗迹存在,因此至少在唐人眼中,这里不能全算作东吴之处。②三国时不存在吴和楚的对立,只存在吴和蜀、魏政权的对立,虽《三国志》中有吴、楚并举的说法,仍然只是沿袭春秋战国时的说法,因而吴楚同时出现在《柳毅传》中,说明传奇的原发生地只能在吴地。③唐代文学作品中如果涉及三国时吴,一般会特别标出,以示和春秋时的吴国相区别。如孟浩然诗“莫辨荆吴地, 唯余水共天”,[3](1634)刘禹锡诗“水乡吴蜀限, 地势东南庳”,[9](3988)李群玉诗“目穷衡巫表, 兴尽荆吴秋”[9](6578)等,皆是如此。而没有特别标明处一般指春秋战国时的吴国,因此,吴、楚同时出现在传中并非矛盾,都是指在太湖附近地区。
文本中还有:“见从者十余人,担囊以随,至其家而辞去。毅因适广陵宝肆,鬻其所得。百未发一,财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为莫如。”[3](236)柳毅把所得宝物拿到广陵去卖,淮右富族羡慕其富贵,都说明其家在淮右附近,也就是吴地,而不可能是湖湘洞庭地区,这也可以证实上面说法。
第二,“洞庭”与“洞庭湖”之别。
“洞庭”一词在《柳毅传》中多次出现,而据《吴郡志》载:“《史记》:三苗国,左洞庭,右彭蠡,裴骃注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无知其极者,名洞庭。’”[10](625)《舆地广记》载:“君山即湘山也,以湘君之所游处,因曰君山。有石穴,与太湖之苞山潜通,故太湖亦有洞庭山。”[11](806)正因为太湖和洞庭湖都可称之为洞庭,且君山和包山都可称之为洞庭山,因而对《柳毅传》原发生地持不同意见者对传中“洞庭”一词有不同理解。
太湖之所以称洞庭,是因为太湖有洞庭山之缘故,以洞庭称太湖,乃是以局部代总体,因而很少有把太湖称为洞庭湖的,只是称作洞庭。唐人似乎很注意“洞庭”和“洞庭湖”的区别,在《全唐诗》中,“洞庭湖”共出现40次,然考其所指,没有一处是指太湖。如钱起《江行》:“千顷水纹细,一拳岚影孤。君山寒树绿,曾过洞庭湖。”[9](2676)元稹《洞庭湖》:“人生除泛海,便到洞庭波。驾浪沉西日,吞空接曙河。虞巡竟安在,轩乐讵曾过。唯有君山下,狂风万古多。”[9](4550)这些均指湖湘洞庭。因而如果在《柳毅传》中出现“洞庭湖”那就可以推出小说原发生地在湖湘地区,但《柳毅传》中,“洞庭”出现了24次,却没有出现一次“洞庭湖”,而在《全唐诗》中,“洞庭”一词,有三分之一左右是指太湖及太湖洞庭东西山。从上面分析可以推论出:《柳毅传》中规避“洞庭湖”似乎在有意表明故事发生地点不是发生在湖湘地区。如果再联系文本中出现的钱塘君,故事发生地在太湖地区就更具有合理性,毕竟,太湖和钱塘江的联系远比洞庭湖和钱塘江的联系紧密。另外文本中还有“闻君将还吴,密迩洞庭”[3](230),能够和吴“密迩”的也只能是太湖,而不可能是湖湘洞庭。
第三,“湘滨”是否只指“湘水之滨”。
文本中提到“仪凤中,有儒生柳毅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3](230)“湘滨”一词于是成了小说原发生地在湖湘地区的铁证。即使主张发生地在太湖的人也认为湘滨是指湘水之滨。“此文在以吴中作为地理背景的同时,掺杂了一点以今湖南为背景的话语,是亦有说。因为两地的洞庭湖在道家的传说中水下是有地道连通的。这样,‘湘滨’一词似乎是作者有意安排所致。”[12](10)这样,实际上又陷入了《岳阳风土记》中的说法。确实,在唐代的地志和正史中,湘是指湖湘地区一带,与湘水关系密切,《全唐诗》中,“湘滨”一词出现三次:“郢路委分竹,湘滨拥去麾”;[9](1059)“江华胜事接湘滨,千里湖山入兴新”;[9](2687)“竹花不给口,憔悴清湘滨”。[9](6573)“湘滨”也无疑是指湘水之滨,但三次毕竟还少,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事实上湘滨是由“湘”和“滨”所构成。滨是水边的意思,那么,吴地与湘有什么关系没有呢? 我们看下面诗:
见说吴王送女时,行宫直到荆溪口。溪上千年送女潮,为感吴王至今有。乃知昔人由志诚,流水无情翻有情。平波忽起二三尺,此上疑与神仙宅。今人犹望荆之湄,长令望者增所思。吴王已殁女不返,潮水无情那有期。溪草何草号帝女,溪竹何竹号湘妃。灵涛旦暮自堪伤,的烁婵娟又争发。客归千里自兹始,览古高歌感行子。不知别后相见期,君意何如此潮水。(皎然《赋得吴王送女潮歌送李判官之河中府》)[9](9261)
据《元和郡县图志》载,荆溪在常州义兴县,从诗中可以看出唐代湘妃的传说在这一带曾流行,溪草、溪竹和帝女、湘妃相联系。不只这首诗,唐诗中还有许多诗句表明“湘”和吴地的联系:
悲歌鬓发白,远赴湘吴春。(杜甫《赠别贺兰铦》)[9](2326)
玉轸朱弦瑟瑟徽,吴娃征调奏湘妃。(白居易《听弹湘妃怨》)[9](4948)
吴歌秋水冷,湘庙夜云空。(温庭筠《芙蓉》)[9](6712)
湘岸荒祠静,吴宫古砌深。(孙鲂《春苔》)[9](10017)
愁中独坐秦城夜,别后几经吴苑春。湘岸风来吹绿绮,海门潮上没青苹。(刘沧《怀江南友人》)[9](6792)
“吴宫”“吴王”“吴苑”与“湘岸”“帝女”“湘妃”“湘庙”同时出现在诗中,而且还多以对句的形式出现,它向我们暗示,二妃的传说不仅只在湖湘一带流传,同时也在吴地流传,既然在太湖诗中能够出现湘岸、湘庙、湘妃,那么“湘滨”一词出现在太湖地区的文学作品中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湘滨”一词虽可解释为“湘水之滨”,但不一定就是湖湘地区的“湘水之滨”,它虽然不是《柳毅传》原发生地在太湖地区的证据,但也绝对不足以成为小说发生地在湖湘地区的铁定依据。
三、从文本中方位词看《柳毅传》原发生地
除文本中地名可作为《柳毅传》原发生地在太湖地区外,还有一些方位名词也可以印证小说原发生地在太湖地区。
第一关于“南”与“东南”的特指。
文本中提到:“毅之表弟薛嘏为京畿令,谪官东南。……嘏常以是事告于人世。”[3](238)由此可推之薛嘏谪官之处即故事的原发生地,但史书中找不到有关薛嘏的记载,因此“东南”具体指哪州已无从考证。但从文化传统和当时实际还是可以推测出其所指大概范围。
春秋战国时期,习惯上把楚国称为“南国”。唐定都长安,但从麟德二年(665年)开始高宗与武后就长期居留在洛阳,除了国家大典之外,很少回到长安,“仪凤中”武则天已长久居住在洛阳。天授二年(691年)正月,正式定都于洛阳,中宗后洛阳一直作为东都存在,湖湘洞庭相对于洛阳来说,只能说是南,而不能说是东南,因而在唐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初盛唐文学作品中,一般把湖湘地区与南相联系在一起:
且酌东篱酒,聊祛南国忧。(张均《九日巴丘登高》)[9](984)
胡为心独尔,惠好在南国。(王琚《奉答燕公》)[9](1061)
夜夜登啸台,南望洞庭渚。(储光羲《田家杂兴八首》之一)[9](1386)
南国久芜漫,我来空郁陶。(陶翰《南楚怀古》)[9](1475)
南过三湘去,巴人此路偏。(刘长卿《赴巴南书情寄故人》)[9](1493)
湘流澹澹空愁予,猿啼啾啾满南楚。(刘长卿《湘中忆归》)[9](1579)
大梁白云起,飘飖来南洲。(李白《留别贾舍人至》)[9](1785)
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湖湘地区与方位词“南”紧密联系在一起。
“东南”本是一个方位词,也在唐诗中作为方位词而使用,然而,“东南”却又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意蕴。《淮南子•天文》中说:“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13](82)东南也就成了靠近大海的地方。《史记》载:“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8](348)三国时吴建都于此,东晋也建都于此,印证了东南有王气之说,这样东南也就成了吴越一带的代称,几乎成了专有地名,这从唐代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
欲厌东南气,翻伤掩鲍车。(李显《幸秦始皇陵》)[9](24)
何事东南客,忘机一钓竿。(刘长卿《过邬三湖上书斋》)[9](1523)
传是东南旧都处,金陵中断碧江深。(孙逖《丹阳行》)[9](1187)
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孟浩然《舟中晓望》)[9](1652)
诗中间的东南,均是指吴越一带。《柳毅传》中薛嘏谪官东南很大可能就是吴越一带,也就是太湖地区,因而可以推之,小说原发生地在太湖地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第二,文本中其它方位名词。
文本中还有:“女遂于襦间解书,再拜以进,东望愁泣,若不自胜。毅深为之戚。”[3](231)“语竟,引别东去,不数十步,回望女与羊,俱亡所见矣。”[3](231)“东望”的方位自然是“洞庭”地区了,“东去”也是去“洞庭”,毫无疑问,湖湘地区是不能说在泾阳之东的,只有太湖地区才能说在泾阳之东。“东望”“东去”虽然不具“东南”那样的文化意蕴,但却比“东南”更能说明小说原发生地在太湖地区。
以方位名词来论证小说原发生地虽然有概念模糊的缺点,但它可以配合文本中地名更好地证明故事的原发生地在太湖。
四、从物产及经济情况看《柳毅传》原发生地
文学作品总会打上原发生地的烙印,每个地区总有其特定的物产,一定的物产又体现了该地区的地域特征,从《柳毅传》文本中的物产,可以断定小说的原发生地。
第一,洞庭橘、社橘与当地生活关系。
文本中有“洞庭之阴,有大橘树焉,乡人谓之社橘。”[3](231)《左传·昭公》载:“社稷五祀,是尊是奉。……后土为社。”[4](1576)称之为“社橘”,可见橘对该地区社会生活意义的重大。那么湖湘地区和太湖地区植橘情况怎样呢?
真柑出洞庭东、西山,柑虽橘类,而其品特高。芳香超胜,为天下第一。浙东、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气标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贵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持久。方结实时,一颗至直百钱,犹是常品,稍大者倍价。并枝叶剪之,饤盘时,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吴郡志》)[10](440)
可频瑜与仲子陵同时作《洞庭献新橘赋》,可赋称:“味能适口,玉果比而全轻,……其价可重,其味可珍,……独专美于当今,及岁时而入贡。”[15](673)仲赋曰:“包之橘柚,至自江湖,岁以为常,知方物之。”[15](673)岳州之洞庭也产橘,但远不及太湖洞庭山所产出名。由此可知白居易之《轻肥》:“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9](4676)韦应物《答郑骑曹青橘绝句》:“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9](1953)均是指太湖洞庭山上的这种特产。太湖洞庭橘,自古以来就为贡品,洞庭山之居民,种植以为生,所以才会有“社橘”。“以其说有橘社,故议者又以为即此洞庭山”[10](116)说法是很有道理。
第二,本文中出现的其它物产。
在《柳毅传》中,还可以见到一些其它物产,这些物产带有一定地域文化特色。下面是从唐代有关文献中辑录的环太湖地区各州物产与洞庭湖地区岳州物产和《柳毅传》文本中出现的物产比照表(表1),从对照中可以判断传奇的原发生地究竟在哪里。
从表1的对照中可以看出,在物产丰富的程度上,太湖地区远远超过了洞庭湖地区,洞庭湖地区的物产很多可以在太湖地区找到,但太湖地区不少物产却是洞庭湖地区所没有的,洞庭湖地区的物产在唐代是相对贫乏的。因此“门户千万,奇草珍木,无所不有”[3](231)、“谛视之,则人间珍宝,毕尽于此”[3](231)、“前列丝竹,后罗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间”[3](239),只适合于太湖地区。
虽《柳毅传》文本中的物产在上表中环太湖地区中也难以找到,但并不意味着环太湖地区没有这种物产。从唐代文献看,《柳毅传》中的这些物产来源于两个途径:①产自东海和南海,而太湖的苏州就与东海相接,因而获取这些物产较易。②这些物产产于域外,如大食、波斯、泥婆罗国等国。《旧唐书》载:“(波斯)出䮫及大驴、师子、白象、珊瑚树高一二尺、琥珀、车渠、玛瑙、火珠、玻瓈、琉璃、无食子、香附子、诃黎勒、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甘露桃。”[16](5312)唐代与这些国家的贸易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陆路,也就是丝绸之路,一是海路。环太湖地区的商业贸易十分繁荣,在唐代就出现了“洞庭商帮”,海上贸易十分繁荣,因而《柳毅传》中出现的一些物产,在唐代环太湖地区是很容易获得的,而在湖湘洞庭地区则不易获得,因而可以推断出传奇原发生地在太湖地区。

表1 太湖地区物产、洞庭湖地区岳州物产与《柳毅传》文本中出现的物产比照表
五、从文化背景看《柳毅传》原发生地
不同地区文化背景的不同,将会影响到该地区的文学作品创作的方方面面。唐代湖湘洞庭地区和太湖地区的文学作品,在呈现出一定共性的同时,又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从这种差异性中可以判断出小说的原发生地。
第一,楚歌与《柳毅传》。
正如前面所说,吴地在历史上受楚的影响很大,同样在文风上也受到了楚文学的影响,李朝威在创作《柳毅传》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上天配合兮,生死有途。此不当妇兮,彼不当夫。腹心辛苦兮,泾水之隅。风霜满鬓兮,雨雪罗襦。赖明公兮引素书,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无时无。(钱塘君)[3](234)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柳毅传》的创作明显受到了楚风的影响。然而湖湘地区的楚歌与吴越地区的楚歌除在形式(句式与语气词)上相似外,在风格和内容上呈现出较大的不同。屈原对湖湘地区特别对洞庭湖一带有深远的影响,因而唐代湖湘地区的楚歌仍然保留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17](434)的特征,这一点可以从唐传奇《湘中怨解》可以看出:
情无垠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郑生)[3](312)
溯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袅绿裾。荷卷卷兮未舒。匪同归兮将焉如!(祀人)[3](312)
从上面的楚歌可以看出,唐代湖湘地区的楚歌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依然保留了较纯的楚辞特色。但吴越地区楚歌却不同,它是楚辞与吴越本土文化融合的结果,因而“记楚地,名楚物”在吴越地区的楚歌中得不到体现,即使是书生柳毅写的诗,也是如此:
碧云悠悠兮,泾水东流。伤美人兮,雨泣花愁。尺书远达兮,以解君忧。哀冤果雪兮,还处其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难久留。欲将辞去兮悲绸缪。(柳毅)[3](235)
这首诗几乎看不到“楚地”“楚物”的痕迹,它与湖湘地区的楚歌是有较大不同的。另外,吴越地区的楚歌受项羽、刘邦建立的西楚和汉政权影响很大,在诗歌风格上变“低徊哀怨”为“慷慨激昂”,下面是项羽和刘邦的两首楚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8](333)
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弓矢,尚安所施!(刘邦)[8](2047)
这些诗歌气势宏大,情感激昂,与湖湘地区楚风表现出很大的不同。《柳毅传》中钱塘君所唱的楚歌也体现了这种风格,书生柳毅的诗虽然是离别前所唱,也较少哀怨悲凄的特色,而洞庭君所唱楚歌更是横绝宇内,其气势可与刘邦、项羽诗歌一比:
大天苍苍兮,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圣兮,薄社依墙。雷霆一发兮,其孰敢当?荷贞人兮信义长,令骨肉兮还故乡。齐言惭愧兮何时忘!(洞庭君)[3](234)
由此可见,湖湘地区与吴越地区楚歌在内容和风格上是有较大不同的,从《柳毅传》所载的几首楚歌看,小说的原发生地应该在太湖地区。
第二,悲、喜剧与《柳毅传》。
某个地区历史文化背景甚至会影响到唐代传奇的情节,湖湘地区在历史上是一个悲剧产生的集中地。
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刘向《列女传》)[18]卷一
(屈原)于是怀石遂自投[沉]汨罗以死。(《史记》)[8](2490)
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史记》)[8](2491)
先有二妃投湘水而死,再有屈原投汨水而死,贾谊的出现加深了这种悲剧意识,因而唐代文学作品中,这种悲剧意识也十分强烈。如前所举小说《湘中怨解》结局就是一个悲剧。中晚唐时,这里还产生了李群玉与二妃的悲剧、巴陵鬼馆诗等,“湘妃”、“斑竹”、“屈原”、“贾谊”等悲剧意象在唐代湖湘文学作品中出现十分频繁。而吴越地区却不同,它是产生爱情喜剧的地方:
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吴地志》)[19](59)
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 。(《三国志》)[20](1260)
范蠡与西施、孙策周瑜与二乔对吴越地区的文化影响十分大,加上唐代吴越地区经济较湖湘地区远为发达,优厚的经济条件也有利于产生爱情喜剧。因而《柳毅传》 “从此以往,永奉欢好,心无纤虑也”,[3](238)爱情以喜剧结局,不是湖湘文化土壤能够酝酿得出的,它必须根植于吴越文化的土壤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唐人的小说观决定了《柳毅传》原发生地具有确定性,同时,从《柳毅传》文本中地名、方位名词、物产及作品内容风格看,故事的原发生地都应该在太湖附近地区,而不可能发生在湖湘的洞庭湖地区,我们不能因为它是小说而否认它的原发生地的确定性。
[1]范致明.岳阳风土记[M].台湾: 成文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五年.
[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鲁迅.鲁迅全集·第十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4]陆楫.古今说海[C]//四库全书·第885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7]史忠义.两组诗学价值的中西比较[J].江西社会科学,2006,(2): 63−72.
[8]司马迁.史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59.
[9]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 中华书局,1960.
[10]范成大.吴郡志[M].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
[11]欧阳忞.舆地广记[M].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
[12]张伟然.柳毅传书之“洞庭”考[J].中国地名,1998,(5): 10.
[13]刘康德.淮南子直解[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4]杜预.春秋左传集解[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15]李昉.文苑英华[M].北京: 中华书局,1966.
[16]刘昫.旧唐书[M].北京: 中华书局,1975.
[17]王应麟.玉海[C]//四库全书·第944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8]刘向.列女传[M].潮阳郑氏用郝氏遗书本校刊.
[19]陆广微.吴地记[C]//四库全书·第587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陈寿.三国志[M].北京: 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