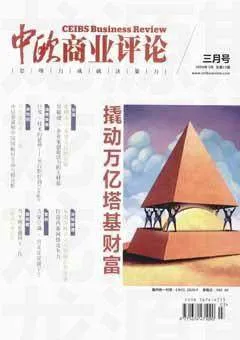企业家创新活力的大释放
对于改革初期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纳为两大类:制度创新活动和创业活动。从逻辑上讲,前一类创新活动和政府采用的变通型制度安排一道,构成了后一类创新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
改革之初,由于政府采用的四项变通型制度安排(见本刊2008年11、12月号本专栏)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中国民间所蕴含的企业家才能被迅速地激发出来,各种创新活动随之涌现,由此形成了中国民营经济的第一次大发展。
改革初期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可以概括为两大类型:制度创新活动和创业活动。从逻辑上讲,前一类创新活动和政府采用的变通型制度安排一道,构成了后一类创新活动得以展开的重要条件。
三大制度创新
尽管各项变通型制度安排打破了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打开了缝隙,然而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还需要一系列支撑性制度,如有关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的制度。在改革初期,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这些制度。比如,当时的宪法和法律只强调“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产权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规范市场关系的法律体系基本是空白,而包括警察、法院等执法机构也只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难以履行社会裁决和规制功能。此外,中国的市场体系本身还不完整,包括资本和土地在内的要素市场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商品市场,虽然银行和金融体系的重建工作在198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但是国有商业银行基本上不给私营企业贷款。
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获得创业所必需的资金要素与技术要素、保证企业家才能的收益不被他人攫取并降低交易成本,中国不同地区的企业家依托当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创造了一系列非正式制度。基于这些制度创新,中国的民营经济以多种形式生长起来。这些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与产权保护有关的制度创新。在私有产权不被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状态下,政府往往成为企业家私人产权的侵犯者。为了跨越改革初期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不同地区的企业家作了多种尝试。
在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地区,企业家依托基层乡镇政府或村集体建立乡镇企业,自己则以管理人员或“承包者”的身份开展创业活动。在浙江省南部的温州和台州地区,企业家先是组成由两个以上家庭企业联合起来的“联户企业”,后来又发展出“挂户企业”(挂靠在乡镇政府或公有企业下面并交纳“管理费”,俗称“戴红帽子”)和“股份合作制企业”,从而获得“公有企业”的地位。有学者在山西省的实地调查还发现,企业家通过与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签订固定分成比例的租赁合同,成为实际上的业主。
第二,与合同执行有关的制度创新。由于缺乏有效的第三方执法的法治体系,民营企业家无法依托法庭的庇护进行交易。因此,他们设法发展各种双边声誉机制和以社会网络或商业网络为基础的多边声誉机制来承担合同执行功能。
例如,企业家们主动建立起互惠性重复交易关系和质押机制等。再如,有的地区由于存在着乡亲间人际联系和信息沟通非常紧密的社会网络。私营企业便依托这一社会网络进行交易。形成本地化的交易网络,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对象的违约风险。浙江温州地区是一个典型的依靠乡亲、宗族关系等社会网络来保证合同执行的例子。有的地方,属于同一行业的企业还自发形成了专业市场,自我维持市场交易秩序。
第三,与资金获取有关的制度创新。在改革初期,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对私营企业不信任和不认可,私营企业无法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资金,因此,企业家们设法建立了各种非正规的金融渠道来满足融资需要。
他们首先建立了各种内源融资渠道,其中温州等地的家庭企业最重要的内源融资渠道是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包括侨属来自海外亲戚的汇款;而苏南的乡镇企业则主要依赖于村集体或基层政府的农业积累。其次,企业家也努力创造各种外源性融资方式,其中一种主要的方式是商业信用,即私营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时,买方延后2~3个月付款,这成为中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普遍商业惯例。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家还“复活”了历史上久已存在的原始借贷形式,如“摇会”或“抬会”等来获取资金。
有了这些制度创新,加上政府采用的变通型制度安排,企业家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便满足了。
市场发现型创业活动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政府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依靠命令方式和人为的价格扭曲进行资源配置,结果导致整个经济存在严重的资源误配问题。由于轻工业发展受到抑制,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改革初期,这一情形为企业家提供了通过重新配置资源来获取利润的潜在机会。产品销售和定价的市场轨形成以后,那些过去发展受到抑制的行业,其产品的短缺性很快通过市场价格信号表现出来,而企业家们则从这些信号中感受到了商机。因此,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着力从事各种生活日用品和商业、餐饮、运输等服务产品的生产,努力在这些紧缺的商品与服务领域打开市场,尽可能地捕捉到市场获利机会。
传统上,苏南地区在面粉加工、丝绸生产和纺织印染等轻工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当地的企业家利用发展社队企业时形成的设备和人力资源,抓住市场机会,进入到了这些自己擅长而又发展相当不足的行业。另外,苏南的企业家还利用靠近上海这个工业中心的地域优势,设法为那些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政策下谋求更多计划外生产的国有企业配套,从而进入到化工、钢铁、冶金和机械等重工业行业。利用这些市场机会,苏南的乡镇企业在改革初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浙江省的私人企业家在开辟和扩大新市场方面表现尤其突出。这个中国东部沿海的省份虽然在自然资源的禀赋方面不占优势,但是,这里的居民对于市场中存在的获利机会似乎存在超乎寻常的敏感性,而且具有非凡的敢冒风险的精神。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府对私人经济的政策放松伊始,浙江的农民便利用其有限的资源,以手工作坊的形式生产各种不起眼然而却是严重短缺的小商品,像纽扣、标签、标牌、小饰品、小玩具等。
温州的桥头镇纽扣市场销售着本地私人企业生产的无数种纽扣。此外,温州柳市镇的低压电器市场、宜山的再生腈纶市场也吸引了国内外的大量购买者。为了在全国范围开拓市场,温州有近14万名的农民采购和推销员分布在全国各地,构成一个庞大的购销网络。在资金得到一定积累之后,企业家们又进入到其他一些依旧短缺的行业,如制鞋、服装、灯具、文具、印刷等。
和温州类似,义乌也是一个资源贫瘠之地,但是,本地农民很早就有摆摊设集和走乡串户经商的传统。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义乌率先建立有形的小商品市场,1 984年该市场的摊位有1 800多家,经过多次改建扩建,到1992年市场摊位已增加到17 000多家,销售收入高达20多亿元。依托该市场,当地的私营企业生产的各种紧缺型商品得以销售到全国各地。
民营企业第一次飞跃
通过企业家的制度创新和创业活动,除了江苏和浙江两省外,广东、山东、四川乃至全国都出现了民营经济大发展的形势。据统计,1981年,雇工人数少于8人的私营企业(即个体企业)仅仅为183万户,到1985年已经增长到11 71万户;从业人员则从1981年的227万人增长到1985年的1 766万人。若按照乡镇企业口径统计,1 981年,全国乡镇企业户数为1 34万户,从业人员为2970万人,到1 985年,户数猛增到1 223万户,从业人员增长到6979万人。
1 98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后,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得到确立,到1989年底,全国私营企业达到1256.1万户,从业人员则达到21 05万人。尽管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调整期,但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有了这支力量,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变得不可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