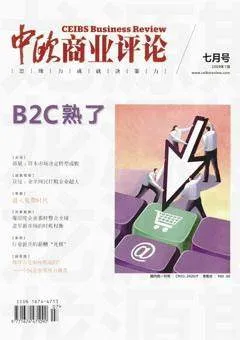学会“议事”
在百余年来的现代化努力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发展方向上的共识。特别是近20年,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效益和公正,已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怎样来落实这种诉求,使其富有成效,将日益倚重具操作性的工具和方法。
在对工具的应用上,欧美人要高明许多,他们面对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会剖析权衡,尽量不蹈前人和同侪的覆辙。他们的历史经验简单说来,是多多应用工具、方法、规制,而不是事事追溯到道德信仰,动辄要求改造人性。其基本出发点,不在于“去人欲”,而是强调使用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依靠程序来规范路径。工具使用若得法,人们的行为大可改善和重塑。在此意义上,规则的正当要比一时一事的合理更能长期奏效。
综观历史,欧洲(及后起的北美)国家之所以能在文明发展中脱颖而出,组织效率是最关键的要素。工业化的技术突破之所以能在西方扎根和兴盛,也是依存于他们的组织效率。
议事规则正是人类组织能够奏效的基石之一。从基础做起,从工具方法乃至行为习惯,一步一个脚印地夯实和提升,发展方能长久。
开会议事是现代人协同、沟通的最主要形式,其中的规范也是决定人际合作成果和集体决策效率的基础。如果会议徒具形式、低效、闲扯,人们就会变得因循守旧、无奈、沮丧,甚至失去彼此的信赖。无效会议虽然是许多组织根深蒂固的积习,却是应该而且能够改变的。建立先进的议事规则就能够提高会议的效率,增强规范运作,促进组织治理,强化诚信环境。
何谓罗伯特议事规则
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准则脱胎于英国的法制演进,经过数百年的锤炼,已经广泛地为各国采纳并应用于各类型的组织,并被证实是有效的。
事实上,我国许多新版组织法规和章程也都遵循了罗伯特议事规则的精神、原则甚至具体的做法,只是没指明其出典而已,如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议事规则已经浸透了现代社团包括公司的运作规则,成了事实上的标准,变成了几乎所有咨询机构和律师行的标准格式母本,久而久之,它已被视为现代组织的“第二天性”了。
罗伯特议事规则既是建立和修改规则的“元规则”,又周延地涵盖了各种操作细节,严密自治,令破坏和贬损规范的行为无法得逞。它有三个特点值得注意:一是约定。规则明示在前,对事不对人;二是突出工具性。凡事不往道德上扯,能用工具解决的,绝不无端拔高和指控;三是中立性,独立于意识形态等价值判断之外。旨在凝聚组织认同,提高运作效率,平衡多元利益,通过文明议事来说服、辩论、妥协,从而达成组织的行动。
为什么现在要推行议事规则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在开会和议事,为什么现在需要引进“外来的”规范?实际上,议事规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经验总结。它的显著成效要在文明和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显现。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和市场化,使议事规则的广泛应用变得刻不容缓。
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我们吃过很多“人治”的亏。不过,大多数对“人治”的批评指向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少针对“我”同他人的交易关系。随着分工精细化和市场交易的扩展,这类关系(如商品买卖、就业聘任、投资合伙及社团参与等各种活动)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怎样约定并信守规则,对民间合作的规模、质量、成本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华人社会的合作关系历来非常稳定,因为传统社会的流动性很低,交易与合作的对象过去被束缚在同一狭窄地域(如村落)。在祖祖辈辈凝结成的长期稳定的信任基础上,合作不出血缘、姻亲、宗亲、同乡的范围。社会记忆在狭小的圈内恒定长久,人们行事不敢轻易违背传统所期许的规范,一旦出格,代价极大。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没有明示的成文规则,人们也都能服膺传承的规矩,不敢稍有逾越。
民国以来的都市化和产业分工,迫使人们逐渐走出了这类“关系圈”。外出谋生、求职或求学,渐增的流动性松弛了固有的信任关系,市场交易关系代之而起,人们的行为模式也随之变化。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施计划经济,人们被安置在工作“单位”里,终身雇用,阻遏了流动性的进一步扩大。在“单位”(和“户籍”)的束缚下,人们终其一生都面对同样的领导、同事、岗位、技能以及彼此的期望,他们的行为和预期在同一个“模子”里凝结而成,生老病死都依附于单位,因此“单位”的惯例或各种“潜规则”在当时是能够奏效的,而无需明定的规则。然而,那时稳定而刚性的关系,无论是以村落还是以单位为依托,在改革开放后都迅速遭到了瓦解。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出现了更多的合作形式。这些合作大多是“短期”的,以交易为基础而不是基于“恒定”甚至人身依附的关系上。频频改换工作,“逐水草而居”,已成了市场化里国民生活的常态。代之而兴起的各类新组织和兴趣团体,要求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迅速形成新的合作和信任。在高度流动的市场里,一个活跃的人隶属于各种团体,参与合作的目的是各取所需,合作失败的后果也只是局部的,食言或失信的惩罚也有限。比如生活在都市,一个人和邻居处得不好,搬到别处照样住;借钱不还,换家银行照样借。以往“关系圈”的约束力也因而大为软化。
既然传统和习俗再也不足以应对不断涌现的新合作关系,为了既省事又快捷地在陌生人间达成合作,就需要有共同遵从的规范,形成彼此间的积极预期,来制约和规范这些新合作关系。在这个关键领域,议事规则作为一个可操作的工具,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用。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与时俱进地操作议事规则,否则将难以有效地推进“公司或组织治理”。
虽然在理念层面,我们对“公司治理”似乎已有了不少共识,可惜不知怎样落实理念,所以实质性的进展并不显著。例如,我国大型企业开会大都按等级来发言,缺乏真实的讨论,有效决议无法形成也很难贯彻。会上没能解决的问题,通常在台底下按潜规则来解决,随意性很大且无从问责。低级的错误因此层出不穷地重复(见辅文:某国企党组会的集体决策剖析)。本质上,人皆有其偏私,但有了规范程序的制约,粗糙荒唐的错误就能少犯。议事规则就是这样一套规范程序,能保障少犯低级错误,不常犯重复的错误;能增进议事的效率和公正,促进组织目标的达成。强调“信”而非偏执于“诚”
在有限度合作中(大多数的市场交易都属此类),人们应强调“信”,而不必偏执于“诚”。“诚”是心和口的一致,“信”则是言和行的一致。一个人心底的想法、动机很难判断,律令也很难对其监控,即使有“诚”,也未必达“信”。例如,一个贷款人由于谋算不彰或时运不济,导致经营失败,还贷发生了问题。此时即便他很有诚意要还贷,信守合约却有困难。对于这种常见现象,银行事先就有预防损失的措施,要求贷款抵押品或第三方担保。因此,在市场合作中,“信”的履行要靠程序规范、风险管控和担保措施,而“有信者”的“诚”是否真实,并不是合作者汲汲追究的关键。
但在我们的传统里,对合作常有泛道德的诉求。如果认为对方人品不好,私德不佳或不够真诚,常会质疑合作的余地和前景,因此不利于现代合作。现代的商业交易多半为有限的合作,品行、脾性、价值观、所属文化、种族、宗教、信仰都是次要的因素,它们和交友或挑女婿是两码事。讨论一项合作事务时,一上来就质疑对方的动机和道德素养而不能用工具性方法来处理,甚或从泛道德的苛求出发,并不能有效地划分人和事,无论是对市场效率还是对现代规范而言,都是很陈旧过时的无效做法(见辅文:关于赈灾活动的一次议事)。
开会议事和团体决策时,“信”具体表现为对议事规则的遵守,体现在合规的议事和决策的程序里。与会者能得到积极语境的鼓励,能够从容不迫地表达是议事规则的核心要求。我们不一定会认同,却应该完整地听取其他人的意见。这样,有了程序的保障,耐心和宽容才能够长久,为人所信服,形成大家牢固和公正的正预期。关键的一点是要把讨论集中在事务的处理上,也就是针对能够解决问题、导致行动的“动议”上,而不要质疑他人的“动机”,否则徒然流于无谓的猜忌和争论。这种程序安排是对人类行为的经验总结,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理念。其一,如前文已述,人的动机很难被观察和被证实;其二,猜疑各自的动机,是对问题解决和创新思路的偏离;其三,退一步讲,自利乃人所共有,容忍对方的自利追求,是寻求妥协与和谐、形成良性的互动、谋求多元组织最大化利益的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