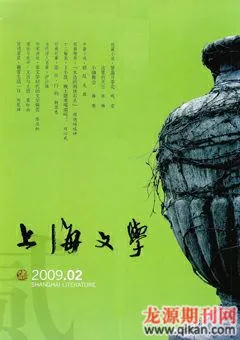“水边的两块石头”
“水边的两块石头”指的是设于街道大拐弯处的“‘崔记’缝补摊。在他们面前,每天来来往往的人数以万计,水一样流淌不休。他们的手艺很好,有做不完的活……”所以叙述便形容为“像水边的两块石头”。这形容不仅是情境的搭档,而且也寓指了生活的乏味和一成不变。故事由此生发,不仅是叙事者的预设,而且也是和阅读期待的共谋。
周而复始,日复一日的生活是这样一种架构:一方面极端的不健全,病态般的单调,而另一方面却又耐久得惊人。生活的折磨不是其中的痛苦或无序,而是其顽固的一成不变。经历了砸小凳子事件,秋媛的离家出走,常态的生活引进了危机,剧烈动荡、刺激、不安和盲目的兴奋。秋媛一次又一次去“想见一个人”,我们也由此聆听一个又一个故事中的故事,但故事后面的括号里分明写着对日常单调生活的不甘和抗争。我们希望在离家出走事件中瞥见另一番生活图像。和所有希望对峙的依然是往日的生活,终于“老崔和秋媛就和平常一样忙碌,在他们面前,来来往往的人从不间断,买菜的,闲逛的,上班的……各式各样路过的人就像水一样流淌。他们安定,稳妥,一成不变,成了水边的两块石头。”这是小说结尾处重复开头时的情境。情境如故,但水边的两块石头不再是形容词而是肯定用语的判断;辛苦依旧,“然而他们不慌不忙安详的样子透露出一个信息——他们生活得很正常。”不清楚这“正常”两字确切含义,不是我们不清楚,而是我们不希望清楚也无法清楚。正常的生活既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疾病,它既是我们每天的必须也是我们每日的不甘,或者正常的生活和异常的病态互为镜像,充斥着滋生和寄生的关联。
火车在小说中很重要,它是动力,是秋媛摆脱“心中没有快乐”生活的可能性。小说中四次写到火车,从她“慢慢地在铁轨上躺下来,感受火车驶过留下的微颤和热气”开始,听觉中的火车、心中的火车、脑子里的火车一直到纸做的火车贯串全篇,伴随着人物的情绪、情节的曲折起伏到故事的结尾。秋媛问:“你坐火车走啊?我每天都听到它的声音,但是从来没坐过火车,想起它,心里就会激动。”火车对秋媛而言,它不只是一个真实的渴望的对象,而是一种对真实的渴望,渴望知道辛苦、乏味的个人生活在碰巧弄得琐碎混乱,单调生活又会成为什么样,渴望知道摆脱的可能性。小说终于让我们明白,一件小事的纠缠随时会激起我RA4MKNxqzKviC67RJVS/UA==们对生活态度和喜怒哀乐的重新分配,而整个叙事成就了单调生活和试图摆脱单调生活的磕磕碰碰。
不只于此,还有那“眼睛”。对叙事而言,视角是出发点,是基本的东西。说到描绘,小说又是观察的艺术,努力接近生活本身应有的“更微妙的成长”(福斯特语)。我们没有必要也无需在这里讨论这方面的“眼睛”。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对象身为情境、局面、公共语言的眼睛在小说中的作用。不长的一个短篇,对眼睛的描写不下十几处,确切地说,这里讲的是观察、被注视的“眼睛”。比如发生在“崔记”缝补摊上的一幕:一位男子出现,“他有霸道的眼神,他的眼神让这些不仅显得合理,更显得惊心动魄”;他来到摊前,“礼节性地看了她一眼”;“下午四点半钟,这位男子来拿缝好的短裤。他显得心事重重,眼睛看着地。”而她呢,“眼睛看着手上的针,耳朵里充满他的脚步声”;“平常的一幕,除了她的内心像闪电一样击过。”而坐在她边上的丈夫,摊主老崔“他不需要抬头,他全身上下都长着眼睛呢”。不同的眼神、不同的看、不同的回眸,还有那不看之看,层次、节奏乃至内心波澜如数登场。还有那贯串全篇的三次“想见一个人”,还有那老崔的悲叹和秋媛的控诉都无不和眼睛有关。有时候,对于眼睛的认识更是超越了视觉的意义。“人家的眼睛看着我们,我的眼睛看着她。”老崔评论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现象。”叙事者甚至补充说,“他把‘现象’两个字咬得重重的。”在诸如这样的句子中,却有着惊愕而透彻的随意,试想,这和晦涩而深奥的拉康名言:“我们只能从某一点去看,但在我们的存在中,我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打量。”又有什么不同。原来,单调的生活也有其并不单纯的一面。从一个更广的背景上说,在一个崇尚快速上网、准点递送、不断创新和增速、时尚隔夜就变、资本四处流动、强调多用途生产的世界上,单一静态的不变之人成为公然的对照之物。“水边的两块石头”既是冥顽不灵,不知今夕为何夕,但其不啻为广大底层、多数小人物的“招牌”。单调乏味的生活,无奈且顽固的坚守,这也许是平淡与冷漠的安慰。从这个意义上说,冠之以“正常的生活”也不为过。一个关于福楼拜晚年的悲哀是这样的,福楼拜一生都在痛斥安定的资产阶级家庭,晚年他看着这样一个家庭却说:“他们过得很真实。”对福楼拜而言这是个可怕的时刻,是对自己主张的一笔勾销。对我们而言,也不失为对日常生活多了一些理解和仁慈。
未来是原封不动、尚未挽回的,但过去则是无法挽回的。唯有“现在”是和“尚未”与“无法”失去联系,它和牵挂与想像没有缘分,僵硬的“石头”唯有在水边才能显示出其顽强的存在,对小说而言,火车是未来的替身,是求变的潜台词,而那无处不在的“眼睛”被注意被感受时已然成为过去。这是“崔记”火车的时间概念,也是一种生存和斗争的哲学。了解一种生活的实情并不是要被迫面对最不幸的事情。面对平淡如水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可以这样安慰自己,正如埃德加在《里尔王》中所发的那番议论,只要我们能够说,“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就不是最糟糕的。”问题在于,当那火车成为脚下纹丝不动的“纸做的火车”时,“糟糕”两字已无法束缚其意义的出路。还有不时纠缠于小说的老崔那多少有些神秘的病,说其是一种“没有快乐”的病,多好,充满着隐喻和意味,但最后把它解读为“忧郁症”,犹如饮料掺水,乏味。
选择《“崔记”火车》,是对叶弥小说创作的选择,而倘如要议论叶弥的小说艺术,此篇并非最佳选择。我注意到一些评论叶弥小说的说法和用词,诸如招魂、非历史性、灵异、寓言乃至童话等等。生涩、扩大化的褒奖,看似明确,细想又是不甚明了的话语经常为人使用,这里的问题不是出在批评而是小说。经常有这样的书写,大家都似乎感觉到其好,但妙在那里又似乎都在云里雾里,“说不清,理还乱”,叶弥的小说也是其中一例。这也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经常说的,“小说应该毁掉确切性”,“全部小说都不过是长长的疑问。”叙事对叶弥意味着,我们在想像中对世界做了什么,以及这个世界如何布满了我们的偏爱和诠释。但叙事也意味着语言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注定会在语言的牢笼中谋求生存,随时都会落入语言布下的陷阱,也可能因文字的疾患而步入“病态”。小说中,当那个男子问秋媛,她丈夫得的是什么病,“不知是关心她还是关心她的男人”,秋媛说:“没有快乐。”叙事者进一步告诉我们,“这句话没头没脑的,但是这位男子注视着秋媛,自认为听懂了。他不想表示出听懂的样子,他是个本分的男人,只有不了解他的人才会被他的外表迷惑。”
这里,听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自认为读懂了其实是没读懂,不想表示出读懂的其实是读懂了其无以言表的东西。书写者和阅读者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千万不要被外表所迷惑。
2008年12月6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