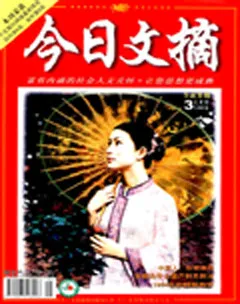犟人谈迁
“钝感力”被日本作家渡边淳一提出来,翻译成中文后,现在是个时髦名词,为人津津乐道。但其实,我们古代就有不少“钝感力”的事例,明末清初写《国榷》的遗民历史学家谈迁,大概可算一位吧。
谈迁这人,天资不高,至少从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标准来说,他的禀赋确实差了点。他自称“下笔痴重”,没有倚马可待的捷才,也就是说思维有点“钝”。这不是谦虚话,因为有个叫王介人的朋友说过他多次,但他就是快不起来。
谈迁的记性也不好,有时听到一件事,高兴得“击节称快”,刚好没有纸墨在身边,没有及时记录下来,过几天就根本记不起来了。这样的记忆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几乎是致命的,不过这也养成了谈迁的一个好习惯:听到什么有意思的,立即用笔记下来。
谈迁的家里很穷,这其实也不适合做历史学家,这不是歧视,而是实情。写史需要博览群书,在古代,没有公共图书馆,也没有网吧可上,收集史料全凭自己藏书,或者朋友之间互通有无。谈迁一介穷书生,没有达官贵人的朋友,家里只有十亩薄地,买不起珍本、善本,也没有人肯借给他。谈迁就想了个笨办法:抄。当时杭嘉湖一带学风很盛,涌现了许多私人藏书家。谈迁就到这些人家里打工,帮主人做一些抄抄写写的活,作为交换,晚上可以看主人的藏书并抄下来。这种方式,当时叫做“佣书”。
天启二年到三年,他在嘉兴的一个藏书家家里住了两年,白天做工,晚上抄书。天启五年“客风林徐氏”,天启六年‘客同邑徐氏”,甚至他父亲死的时候,他也在嘉兴“佣书”,竟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就这么靠着“佣书”,谈迁在五年间搜集了一百多种明代史籍。
读书人都有点迂,谈迁则是特别的迂。他在当时就有好几个绰号,一个叫“木强人”,大概是说他反应迟钝,脾气倔强吧。一个是“汉阴丈人”,这个典故出自《庄子》,说汉阴有一老人,挖了一条通向水井的隧道,抱着个坛子装水浇灌。后人用“汉阴丈人”指那些事倍功半、费力不讨好的人,这用在谈迁身上挺合适。还有一个是“愚公徙山”,把谈迁比作以一己之力欲移动太行、王屋两山的北山愚公。
南明弘光年间,当朝宰相高弘图很赏识谈迁的才学品德,一再要推荐他做中书舍人,这对于贫困交加的谈迁可以说是雪中送炭,但谈迁拒绝了:“以贫骨一具,弟安之耳。”我天生的穷命,只要有口安稳饭吃就行了。话说到这份上,高弘国只能是“默然而退”。谈迁并非不想脱贫致富,只是他觉得一做了官,每天陷入繁琐的事务堆中,就无法写史书了,所以一再坚辞。这在世人看来,自然是标准的“愚公”行为了。但谈迁身上有着一种异乎常人的品质,那就是超强的毅力。
顺治四年,有个小偷潜入谈迁家中,大概见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顺手牵羊把谈迁的书稿《国榷》偷走了。26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这对谈迁来说,简直是比死还难受。鼠标一点就可以拷贝一次的现代人也许永远理解不了这种打击之巨大。
差不多同时,大学者钱谦益的绛云楼失火,烧毁了钱谦益正在撰写中的250卷《明史》稿,钱谦益受此打击,一蹶不振,从此潜心佛典,不再从事明史的研究。绝顶聪明的钱谦益,无法容忍把做了十几年的事再重做一遍,而死心眼的谈迁却更无法容忍一件事开始了却没有结果。他做出了近乎疯狂的决定:重写!于是,已54岁的谈迁重新背着雨伞、包袱、纸笔、干粮,又一次开始了他借书、抄书、编书的历程。这样的毅力已经不是“坚强”两字所能形容的了。
为了掌握崇祯皇帝临死前的第一手材料,谈迁不惜奔波数百里去找为崇祯守陵的宦官。这一天,他从北京出发,先是步行,累得实在走不动了,只得打了个的叫了头骡子。第二天,为了省几个钱,又开始步行。找到崇祯在昌平县银泉山的思陵后,向守陵人详细询问了崇祯临死时的细节,记下后,又步行到昌平县城。休息一晚,又步行了整整一天,才到北京的寓所。
一个61岁的老人,三天步行数百里,只为了解一段史料。在这样的坚强下,又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郑伟佳荐自《报刊精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