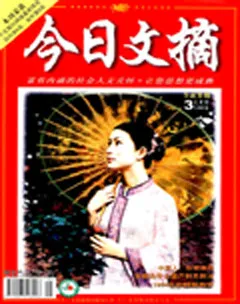黄永玉:这个老头很有趣
斜戴的贝雷帽和烟斗,永远是黄永玉的标志。
大师、名士、绅士……这些尊号戴在他头上总像小一号的帽子。这个86岁的老头依然时尚,比我们更先生。
他是一个活得最像自己的老头。有时小孩、有时慈悲,有时狡猾,有时泪流满面……
很难让人将黄永玉与86岁高龄联系在一起,他精力旺盛,思维敏捷、语言幽默,脾气也不减当年。
有爱心的黄永玉
生于湘西的黄永玉,少年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在福建、江西一带过着流浪的生活,靠着自学的绘画和木刻,在战乱中求生存。那时半个中国的人几乎都在流亡路上,江湖潦倒、前途未知,倒是给一个少年人的奇遇打出了草稿。
在泉州,他在一座寺庙游玩摘玉兰花时遇到他最尊敬的丰子恺的老师李叔同。在江西,黄永玉遇到画三毛的张乐平。在宣传队,蒋经国和蒋方良喊他的外号“蛮牛”。在杭州,他遇到了久仰的大师林风眠。在香港,他遇到了写杂文的知交聂绀弩。他在香港《大公报》用木刻记录新闻,在长城公司写电影剧本,拍过《小城之春》的费穆就趴在他的剧本底稿上死去,上面还留着咳出的血迹。上世纪50年代初他听了表叔沈从文和朋友的劝告,热血沸腾地回到北京,在大雅宝胡同的邻居,正好是李可染、李苦禅、董希文诸先生。文革中,造反学生的皮带抽在背上,他心里数着数,二百四十下,却也把它当奇遇一场。
身处的逆境多了,奇遇也如平常。86岁黄永玉,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北京东部的乡村一隅,有他的“万荷堂”,在意大利翡冷翠,他与达·芬奇相守于山上石屋;在香港,他有“山之半居”;回凤凰,则有“夺翠楼”和“玉氏山房”。每一处住所,自然又是一段段奇缘。这个人,他怎么可以穿过这样繁复的时空而保存有孩子般的心神!
黄老头捏着烟斗自己答:“有爱心,恐怕是要紧的”。
勤奋的黄永玉
黄永玉很勤奋,屋里常挂着几幅未画完的画。哪怕接受采访时,如果有调整拍摄器材、换磁带、打灯光的间隙,他都会跑去画几笔。
一次,采访进行到中午,大家暂停去吃饭,一个小时后回来,大家傻了眼,客厅里又多了一幅画,是一幅蓝色的荷花,那是用上午一幅画中剩余的蓝色颜料画的。黄永玉的五弟说:“这半个钟头,他用剩余的颜料又挣了128万。”因为,按市价,黄永玉的画4万元一平尺。
黄永玉说:“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日子好了,也不懒。我的画怎样我不管,反正我天天都在画。”
黄永玉现在只做两样事情。一是读书,没一天不读书;二是工作,没有长时间不画画。一时高兴就画画,画完就悔,赶紧画第二幅填补后悔;不停地后悔,不停地画画。
问他看什么书?他说:“我一辈子不停地看书,看书的毛病就是记不得。学问家看书,但是他们家里的书不多。我问钱钟书:你的书呢?他说书在图书馆。我看马克思《资本论》,从来不记得,但是陈寅恪读了都能记住。我们画画的人读书是读感觉,都读了。你说哪件事我知道,画画不是大学问家,显示书本的学问干什么?因为读了书,所以画画会用感觉鉴别,我们是在书本上滚过来的。”
黄永玉最喜画荷花,大概有八千多张,画了这么多年的莲花,它们的形态与精神已经烂熟于心,即使睡觉的时候也有“十万狂花入梦寐”。为此他还专门刻了一个图章,叫“荷花八千”。据说,他小时候,外婆家附近有个荷塘。他一淘气犯事,外婆要找他算账的时候,黄永玉就把一个高高的洗澡盆滚入荷塘,跳到里面躲起。“小时候个儿不高,看着荷花像房顶那么高,呆久了,青蛙都过来了。水蛇什么,能够仔细地看到它了。于是发现荷花底下的那种变化,不是我们所看到的那种一根一根这么清清爽爽。有很多的苔、草,那种光的反映、色彩的关系,丰富多了,我开始画荷花。”
“惹不起”的黄永玉
提起黄永玉,人们肯定会联想到沈从文。世上能让黄永玉佩服的人没有几个,但沈从文无疑排在首位。多年来,他提得最多,而且语气最为恭敬的只有他表叔沈从文。但沈从文也曾让他“失望”过。
黄永玉少年时曾在福建德化的一家小瓷器作坊里做小工。有一次,老板破天荒给一块钱让他去理发,他花了三角钱理了发,剩余的七角,买了本沈从文的《昆明冬景》。结果,黄永玉十分懊恼:“我可真火了。我是冲着沈从文三个字去买的。钻进阁楼上又看了半天,仍然是一点意思也不懂。我怎么可以一点也不懂呢?就这么七角钱?你还是我表叔,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呢?七角钱,你知不知道我这七角钱要派多少用场?知不知道我日子多不好过?我可怜的七角钱……”
许多年后,黄永玉拥有一个小小的书库,收集了沈从文几乎全部的著作,明白了表叔书中说过的话。
但同为湘西人,性格方面,黄永玉与其表叔沈从文截然不同。他说自己表叔的性格“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他年轻时,则是靠“拳头打天下”挺过来的。他的性格让不少人都畏他三分。
早在抗战时期,他才十六七岁就在街头以剪影为抗战捐飞机,虽然剪一个影才5毛钱,但是,没有这一点手艺活,连5毛钱也挣不到。
1948年,黄永玉的作品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在上海的一次展览中展出。一对年轻的夫妇买下了黄永玉的部分作品,男的叫黄苗子,是国民党财政部的要人,女的叫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永玉一直没有收到稿费,他在好友王琦的陪同下,去南京郁风家上门“收账”,后来两人竟成了好朋友。
2004年夏天,乡亲们对黄永玉说,沱江上游有人开了一家化工厂,污染了水。黄永玉一听,叉起腰:“怎么能这样呢?好,我带几个人去‘搞’他们一下。”居然把人家的办公室给砸了。黄永玉说:“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快的。要告诉他们这样是不行的。”他说,爱护自然要像讲卫生一样自觉。
懂享受的黄永玉
没有人比黄永玉更喜欢造房子和买房子的了。至今为止,记录在案的就有五处:凤凰两处——夺翠楼和玉氏山房;北京一处——万荷堂;香港一处——山之半居;意大利一处——无数山楼。
这些住宅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规模,都各具特色,很有讲究,且耗资巨大。很多人都认为他这样做无非是有钱了之后显阔罢了,而他却说“这大概也是一种玩法。其实建筑也是艺术。盖房子,盖什么样的房子,和画一幅画花费的心血一样多。房子的形式又比画大得多,我可以容纳许多朋友到我的作品中来,不仅是一个人的开心,它是很多人的开心。”的确,他所设计和建造的豪宅都几乎成为了文人墨客欣然向往的地方。见过黄永玉私宅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既懂艺术,又懂享受的人。
回龙阁、夺翠楼这个地方,原来都有点历史的底蕴,后来败落,曾经做猪栏养过猪。但见识过翡冷翠和塞纳河黄昏的黄永玉,最知道凤凰的美在哪里。当他看到沱江边新式的“洋房”一栋栋盖起来,非常着急,就在当地的电视台上,连续7天讲解了保护古建筑风格的意义。
但人家未必听他的,只有用事实来说活。黄永玉在县城的沙湾一带,买下一块宽3米、长27米的坡地,建造了如今在当地很有名气的夺翠楼。“夺翠”是凤凰话。一个粗俗并不诗意的话,比如说吃的东西吃得好,就说很“夺翠”,今天你的衣服很“夺翠”。夺翠楼建成后,成为当地的一处独特的风景,也成为当地人的骄傲。在夺翠楼的影响下,政府部门重新对沱江两岸的建筑进行规划,古城凤凰渐渐恢复了它往日的风貌。
喜鹊坡上的玉氏山房是黄永玉先生在凤凰修建的第二座房子。
“不随地吐痰,不乱丢烟头”、“字画陈设,请勿触摸”。在黄永玉的家里很多地方可以看到贴在墙上的各种告示,大多诙谐幽默,却不乏警示的力度。这些告示就充当了双重角色,第一它们是黄永玉的作品,我们可以像欣赏他的画一样欣赏它们;第二它们是黄永玉家中的行为规范,作为客人都要遵守。有言在先好办事,谁要是不规不矩恼了先生,说不定会泼以冷水、欢送出门。
黄永玉写告示是有悠久历史的,他4岁的时候在自己新房的墙上用毛笔题上了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写的时候很是神气、非常得意,也拿到了他的第一次“稿费”——屁股上挨了几巴掌。至今这几个字仍留在他凤凰家中的木板墙上。
有趣的黄永玉
“你们看我现在心态挺好,健康快乐,其实原因在于……”当所有人都以为老爷子会说出什么养生经时,黄永玉吐出两个字:“受苦。”他的文章中引用过一句话:有些事可以宽容,但不可以原谅。“我要是没吃过那么多苦,怎么能有这么大爱心呢?但是恶人恶事却永远不能原谅,而应该狠狠地记住。”
黄永玉喜欢看书,据说到了每晚不看便睡不着觉的地步。就在获“奥林匹克艺术奖”的前一天晚上,黄永玉住在酒店里到凌晨4点还没睡着,大家以为他因得知获奖而激动难耐,他却轻轻来一句:“乱讲!我带错了眼镜,到酒店一看没镜片了,看不成书才睡不着的!”他最反感的就是被问到做某件事有什么意义:“人生不要去找意义,过日子平平常常,有的有意思,有的没意思,不是什么都有特别的意义。我就是普通人,什么伟大的意义、深刻的意义,世上压根不存在。”
被他称为“大厅”的屋子约有70平米,杂乱无章地堆着各种器玩,从不知哪个朝代的夜壶到几人合围的大树桩,无所不有。他也是在这里作画,“不要把画画弄得那么神秘,有些人说画画必须要听贝多芬、肖邦才能画得好,哪里有这个事。你想好了,还要贝多芬干吗?……有时我就穿裤衩打赤膊,不是电影里反映的神气活现的样子。”
他爱养鹦鹉,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玉氏山房,处处闻啼鸟。他的画作,常常是在巨大的摇滚音乐夹杂着鸟鸣狗吠中完成的。他家的鹦鹉,常常会讽刺地说“老板,你好”,过年又说“恭喜发财”,有时还讲英语。关于鹦鹉的故事,他有时一口气可以说上好几个,最好笑的是这样一个:有人丢了一只鹦鹉,很焦急,怕鹦鹉把他曾花了时间教给它的东西说出来,左思右想后,决定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人的政治观点与丢失的鹦鹉完全不同。
黄永玉亦喜欢作对联。这几年,家乡旅游旺起来了,他作了一堆对联。如“水秀山清风景好,红男绿女送钱来”。又如,“大嫂沿河开餐馆,幺妹满街卖姜糖”。这些描述荡漾着凤凰新的风俗及情趣。玉氏山房“黄永玉艺术工作室”的大门旁,一副“展出百般手艺,招惹各路财神”对联,把黄老头儿干活攒钱之心不遮不掩,痛痛快快地告之世人……■
(陈嘉薇荐自《三峡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