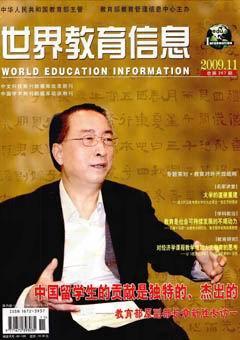大学的道德重建
编者按:大学的存在到底是为什么?大学的价值是否能用金钱来衡量?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怎样把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素质教育放在首位?校长和教师在大学道德建设中应如何发挥表率作用?2009年8月26日,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校长史蒂文·施瓦茨(Steven Schwartz)教授在其学校年度演讲中,结合自己多年担任大学领导人的实践经验,对上述引人深思且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做了独到的分析和回答。麦考瑞大学是澳大利亚一所国际知名的大学,与我国清华、复旦等高校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也是中国赴澳留学生十分青睐的学府之一。施瓦茨教授曾任澳大利亚梅铎大学校长、英国布内尔大学校长等职,自2006年2月起任现职,曾多次访问中国。文章由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建民推荐、郝青青翻译、祝敏申审校,经施瓦茨校长授权在本刊发表。我们相信,施瓦茨校长的演讲对正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高等院校的道德建设和科学发展亦有重要启发意义。
麦考瑞大学的校园很大,人们有时会迷路。因此,我们在校园里的重要地点都设立了指示地图,以方便学校的来访者。一天,我发现其中的一块指示地图被涂鸦给“美化”了一下,在写着“你在此处”的指示箭头下面,有人写下了“但是为什么?”的字样。正如他所问,我在此处到底为什么?
我们为何在此?更确切地说,大学到底是为何而存在?我将尝试回答这一问题。为确保不被误解,我想先表明一下自己的主要观点。大学曾经有明确的道德教化目的,但多年以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道德教育方向。为了实现我们真正的目标,我要突出强调的观点是:大学需要道德重建。有鉴于此,我想谈谈自己那段已经有些模糊的童年时光,以此作为演讲的开始。
我五岁的时候,全家都生活在纽约。当时,我家隔壁的一个小女孩患了脊髓灰质炎,也即通常所称的“小儿麻痹症”。恐慌很快在邻里之间蔓延。孩子们都注射了丙种球蛋白,但这只能暂时提高身体的免疫力。那时候虽然是夏天,但家长们都想尽办法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公园和公共游泳池,一些家长甚至不让孩子到户外玩耍。在那个夏天,我的父母把全家从城里搬到了乡下,因为他们认为乡下干净的空气可以提供保护、避免感染。在我全家离开纽约期间,隔壁的那个女孩渡过了几周依靠人工呼吸机的日子。当她回家时,她的大腿被装上了托架。她活了下来,虽然变成了残障人士。然而,其他患者却没有她那么幸运。
那一年,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死于小儿麻痹症,其中超过一半是儿童。这种悲剧每年夏天都会重演。虽然人们可以在小儿麻痹症不流行的秋天回到正常生活,但恐惧却年复一年。
两年后,一些令人振奋的事情发生了。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一位默默无闻的年轻大学研究员,发明了小儿麻痹症疫苗。最初的实验结果看起来充满希望,但疫苗从实验到正式应用推广,还需要大规模的研究来确保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为此,孩子们被号召参加一个全国范围的双盲实验[1],我的父母毫不犹豫地为我报了名。我父母的行为不是个例,当时总计有两百万小学生挽起了袖子,作为“抗击小儿麻痹症先锋”而闻名于世[2]。我还记得接种疫苗时,学校大厅里长长的队伍和用来鼓励孩子们勇敢一些的红色棒棒糖。对我来说,棒棒糖可能就是为了不哭。整个实验是成功的,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这是好消息,而坏消息是,我当时在控制组,我接种的注射液中只有盐水,和那些实际上没有参加实验的孩子一样,我不得不重复所有过程。
毫无意外,索尔克因此而出名了。他是新移民的孩子,是家庭中第一个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所以,千万别说给更多的人提供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有什么不好。没人知道有多少像索尔克这样的人被埋没着,等待被发现。
尽管索尔克出名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富有。因为索尔克和他所在的私立匹兹堡大学开放了疫苗资源,允许任何想要制造疫苗的厂商生产。道德的驱使令索尔克的工作变得简单。大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发现和传播知识并使之服务于社会。赚钱曾经不是它们的目标。
现在,让我们从那个年代快速推进到现在,看看今天的世界。今天,家长还会热心地让自己的孩子参加那样的实验吗?我希望如此,但我恐怕要伤心地说:“答案是否定的。”现在,许多家长拒绝让他们的孩子接种已被实验证明可靠的疫苗,更不要说是让孩子参加疫苗实验。当然,这并不是说当年我的父母天真。他们知道临床实验的风险,但仍相信大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相信科研人员告诉他们的实验利大于弊。这种信任,现在看来已经不复存在。现在的家长强烈地质疑科学和科学家们,尤其不信任那些抱有商业目的的药品公司、研究员和大学。
让我们直面他们的意图。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澳洲媒体一直都在突出报导默克公司(Merck Sharp & Dohme,MSD)官司的进程。默克公司负责研发了一种强力关节炎镇痛药。30万澳洲患者曾使用过这种药物,但该药物在被指出可引发中风和心脏病(尤其是对于那些高剂量使用者)之后退出了市场。尽管对于药物是否会引发并发症,以及对并发症的赔偿都取决于法庭的裁决,但在这个复杂的故事里,鲜为人知的是著名大学科研人员在最初批准药品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首先,药品公司的员工撰写研究文章来赞美该药品的优点。接着,公司的代表接洽知名的药物研究员,并邀请他们在文章上署名。知名研究员被告知,就算是总统和首相都有代笔人,为什么科学家不可以有呢?很多知名的科学家同意这个观点。结果,这些研究文章出自公司员工之手,但却由知名研究员署名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上。值得重视的是,我说的不是那些为非著名大学工作的二线研究人员。小人物无法为药物销售造势。就像网球,你不用找亚军帮忙,它靠的是冠军。
那些把自己具名为作者的科学家,包括一些世界上最知名的科学家,他们为世界上最有声望的大学工作。你震惊吗?不要震惊。这是惯例,非常普遍地存在于日常实践中。对于那些同意署名的科学家,他们可以收到药品公司的旅游资金。这些资金允许科学家出现在目前那些讨论研究成果(那些并非他们真正参与的)的会议中,这些会议大多是在夏威夷、巴黎或者里约热内卢召开,而从来不会是在克里夫兰、利兹或者达伯召开。不过,这些刺激没有太多必要。发表论文才是大学科学家职业领域的核心,一些科学家答应在文章上署名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在他们的简历上再多加一篇论文。显然,我们生活的时代已经离索尔克的时代远去了。
大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已经从根本上被改变了。知识的发现和传播已经被欲望所取代。试问,今天的大学还有可能出让有价值的疫苗吗?这似乎太困难了。事实上,政府鼓励大学走向反面,禁锢我们的发现,并将专利知识资本化。
曾经有一所知名大学花费了巨额的律师费,希望在法庭上赢得一种有效药品的所有权。结果大学败诉并支付了巨额的诉讼费。这所大学会为它上法庭而感到遗憾么?并不一定。就如一名高层管理者解释的那样,如果诉讼成功了,大学将会从中获益数百万。
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反对专利权、资本主义,或者是变得富有。我同意有“银幕女妖”之称的梅·韦斯特(Mae West)的话:“我富有过,我贫穷过,但是我相信对于我的孩子,富有比贫穷好。”对大学而言,通过知识产权来挖掘商业价值并不是什么不合法的事情,而且只有老天知道大学是多么需要钱。奥斯卡·王尔德曾说过,他可以抵御任何事,除了诱惑。作为大学校长,我有时也感到,我可以抵御任何诱惑,除了钱。
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商业交易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商业交易有可能与传统的学术价值不相容。我可以举例说明。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3]发现,98%的由药品公司赞助的研究论文是在阐述药物的有效性,而只有79%的非商业赞助的研究报告是正面的。当科研人员的实验结果取决于是谁来出经费的时候,人们不再相信医学专家的宣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已经引用了医学和科学的例子,因为这是我的专业背景。但不是科研人员的也不要沾沾自喜,因为科研人员不是唯一需要在伦理道德上被监控的群体。那些不负责任的金融家引发了金融危机,其痛苦波及了全世界的家庭。而这些金融家就包括一些毕业于世界顶级大学的人。英国国会的“报销门”,这个耸人听闻的事件涉及到国会议员使用纳税人基金报销色情读物以及家俱、私人城堡和护城河的维护费用,而卷入该事件的人就毕业于英国最著名的大学。
我想,这个有城堡和护城河的人最好能被曝光出来。因为当愤怒的纳税人想要报复他的时候,他只需要拉起吊桥,然后看着每个人掉到护城河里。这无法不让人变得愤世嫉俗。因为每个人都在做的事不一定都是对的。就如同美国喜剧女演员莉莉·汤姆琳(Lily Tomlin)所说,麻烦总是伴随着卑鄙的竞争,就算你赢了,你仍然是卑鄙小人。而相对于站出来曝光,大学只能保持沉默。这是因为它们不再是道德榜样,出于极端的实用目的,它们已经放弃了成为道德榜样。
澳大利亚联邦今年的预算案明确了这一观点,即大学的目的“应该是增长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你是不是喜欢“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个调调呢?今晚在座的各位有谁能够定义一个“以无知为基础”的经济?
预算报告把大学进一步描述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高等教育上投资越多,回报给每个人的财富越多。澳大利亚前首席科学家罗宾·巴特哈姆(Robin Batterham)在他的报告《改变的机会》中可没有这种“低调言论”。他提出了更令人惊讶的观点。在他看来,投资高等教育可以获得巨额回报,因为大学是“促进发展和创造财富的发动机”[4]。作为大学校长,我很希望自己能相信他的言论,但是我不得不遗憾地说:“他的观点太过夸张。”
大学经费投入的多少和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以瑞士为例,这是一个富裕、高增长、高投资的国家,但它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低于波兰。法国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它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低于发展中国家智利。巴西,世界十大经济大国之一,经济已经发展到非常强大的地步,但对大学的投资仍低于任何一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印度也是如此。香港在过去50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高增长,但其发展成果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是基于大学研究。
尽管言论和现实之间存在差异,但是许多大学还是非常乐意接受把大学的目的定位为助催经济发展。它们夸耀,比起那些没有学历的人,它们的毕业生可以挣更多的钱,而且使学生相信大学是使他们走向人生一劳永逸的起点站。
一些人试图用金钱来证明大学的价值。上帝是仁慈的,他派遣经济学家来帮助大学。例如,查尔斯特大学宣称它已经为地区增长总值贡献了2.64亿美元[5]。詹姆斯·库克大学估算它对汤斯维尔和凯恩斯的经济价值是4.45亿美元。我们是否可以说,詹姆斯·库克大学比查尔斯特大学优秀两倍?
这些并不严谨的研究以及很多类似的研究,都再一次地印证了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Marshall Sahlin)的名言:现实虽然是个可以旅游的好地方,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要生活在那里。
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说大学不应该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它们当然有助于经济发展。就如同莎士比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样。游客每年在“埃文河上的斯特拉斯福镇”的食宿上花费数百万英镑,更不用说花费多少钱购买有《哈姆雷特》台词的咖啡杯[6]。这些消费涉及设计和印刷莎士比亚的戏剧、销售他的十四行诗以及演出他的作品。仅在全球剧场演出幕间休息所销售的葡萄酒就创收数百万英镑。问题是,莎士比亚的价值应该不仅仅是创收。再一次,如我引用王尔德的话,请原谅我一再地重复,我们知道每个东西的价钱,但不是价值。
我们澳大利亚应该为昆士兰研发的子宫颈癌疫苗日后可赚钱而感到骄傲么?澳大利亚的另一项发明——仿生耳(bionic ear),它的重要性难道只是因为可以为国民生产总值作贡献吗?
最近出版的《麦考瑞大学笔会原住民文学选集》看来不能被列入给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带来贡献的名单里。这是否说明文集就没有价值了呢?歌剧院、国家美术馆、州立图书馆都对经济发展有贡献,但这不是它们存在的原因。并不是所有东西的价值都要通过几元几分来体现。就如前牛津大学校长所言,当大学的目的被简单地解释成赚钱,大学的工作就被贬低和削弱了。
教育是或者应该是一个道德培育的载体。作为一个大学的领导者,应该超越数百年前的理念。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帮助人们树立“为了生活,而不仅是活着”的理念。
我不是一个令人失望的老天真。我知道很多学生,事实上是绝大部分学生,他们来上大学就是因为大学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一份好工作。这并没有错,一份满意的工作构成了圆满人生的一部分。但是,即便是工作,也不单单只是关于挣钱,工作也有道德价值。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曾说:“人劳碌所得的最大奖赏,不是获得,而是经历。”[7]
在最经典的论述中,教育从来不只是为了获得工作技能,它曾经的真正目的是塑造品质,以便毕业生可以在社会上扮演有益于大众的角色。就如同柏拉图所说:“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好的教育,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教育塑造好人,并使好人成为表率。”
早期的大学贯彻这一信条并且通常通过反复灌输宗教箴言来培养学生素质。欧洲最早的大学建立于800年前,全都是以基督教为契机建立的,包括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在内,当时都是在教皇的教谕之下运作。教育的意义是为了塑造学生的品质这一理念持续了将近700年。直到19世纪,几乎所有的大学仍旧明白它们的任务。
红衣主教纽曼于1854年写道,教师是传教士和布道者。[8]和牧师一样,大学教师在纽曼那个年代不得不独身。对于在座听众中我的同事们来说,你们可能会对这一观点感到担忧。我想你们大可放心,我所说的大学道德重建并不包括要求大学教师独身。
19世纪美国的大学,如哈佛、耶鲁,都有其道德目标,在教堂参加礼拜是必须的;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学习一门道德哲学,并且所有的学生都要切实遵守行为守则。哈佛大学的行为守则包含不少于40页的规章制度。这种严格的带有强制性的规章是为了反复灌输并强调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以便学生逐渐养成优秀的品质。
澳大利亚的大学则不同。不像早期的美国和英国大学那样,不是私立就是拥有独立的信托基金。澳大利亚早期的大学是公立的,根据议会通过的法律建立,并且每年得到政府的财政拨款。它们的建立是有意与宗教分离的。因为我们首批大学建立时,正是科学逐步兴起,宗教被启蒙思想,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所挑战的时候。此外,澳大利亚城市扩张,移民涌入,也使得人们从更广泛的视角来审视大学。
一些大学乐于接纳新移民。悉尼大学的创始人温特沃斯(W.C. Wentworth)就是很好的榜样。他把该校确立为兼容并包的机构,就如同“无论是基督徒、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抑或是其他异教徒,泉水谁都可以享用”。他的确是高瞻远瞩,他的观点也或多或少说明了过时的、基于宗教道德的教育已经不可能实行了。在一个多元社会,基于一种宗教的课程框架是行不通的。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的大学从来没有放弃塑造品行的目标。并没有哪个大学站出来说:“就这样吧,我们现在不再从事培养品行的营生,从现在开始,捞钱才是关键。”澳大利亚的大学仍旧主张塑造品行,不仅要言传身教,更要耳濡目染。这个观点主张通过为学生树立那些有品行的追求真理的学者的榜样,促使他们努力追赶榜样。
追随苏格拉底的观念,澳大利亚的大学希望良好的知识可以自然地引导人们向善。
但是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开始,即便是这样的非宗教的教育途径也变得令人怀疑。越南战争和市民权利运动引发了美国校园骚乱,并进一步蔓延到欧洲,最后还波及澳大利亚。其结果是,不只是学生,而且大学教给们也渐渐觉得探求真理是无用的。当时极端的想法是,探求真实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者嘲笑西方取得的成就和大学已经渐渐沉没在道德相对论的泥沼中。所有的观点都可以被兼顾,而各种信条可以有对有错。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对和错,真和假,而这些只能对少数人的观点起到约束效果。
道德相对论使大学无法判断,它们甚至不能决定学生到底应该学什么学科。
现在,学生可以在数百门科目中选择他们的课程,而这些科目没有重要与非重要之分。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大学在教授学生,但是并不能教授学生智慧。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在1867年就任圣·安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校长的演讲中说:“大学本身并不仅仅造就纯熟的律师、物理学家或工程师,而是培养有能力、有教养的人”[9]。米尔是对的。
在麦考瑞大学,我们已经决定尝试,是否在当今的教学机构里除了教授职业技能,还能培养完整意义的“人”。我们以建立一个道德共同体为开端。虽然我们没有重新引进哈佛40页的行为守则,但是我们有需要师生共同遵守的准则。教师遵守准则是关键,因为我们不能期待当教师自身做不到品行端正时,学生还能尊重伦理道德。
我们的基本道德准则是:师生互相尊重,举止恭谦,并履行责任。我们建立了一系列面向管理层的行为守则,并作为雇佣合同的一部分。这些都是受到《诺兰报告》(Nolan Report)中关于公共生活标准的启发。每一位管理人员都必须同意做到正直、客观、有责任感、公开和诚实。同时,我们也要求我们的学者树立好榜样,按时上课,及时把作业反馈给学生,并公正地阅卷评分;我们要求我们的学者在他们的领域保持活跃,确保他们的教学资料能与时俱进,并确定他们能运用最有效的教学方法来教导学生。此外,我们每年都会对每位学者进行评估。
从学校层面来说,麦考瑞大学也在谋求建立道德规范。
我们严格履行如下政策,包括杜绝虚假研究、懒惰、种族排斥、性贿赂等现象。我们谨慎地对待处理利益冲突、剽窃以及商业机构的贿赂行为。我们管理我们的奖学金和资金,给予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而不仅是那些以高分进入大学、可以提高我们大学排名的学生。
制定所有政策的初衷是为了确保麦考瑞大学是合乎道德规范的机构,并能够为我们的学生树立榜样。此外,我们也没有忽略我们的课程设计。尽管我们不会回到那个教授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信条的年代,但我们确实希望,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可以成为米尔所期望的有教养的人。
在麦考瑞大学,我们相信一所大学的教育应该塑造有教养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了解世界,了解他们所处的空间,他们可以正确地说和写,他们知道诗歌,他们能欣赏交响乐。
我们的教务长萨克斯(Sachs)教授,把我们的新课程框架归纳为三个“P”,即人(People)、行星(Planet)和参与(Participation)。我校所有学生,不论他们选择了什么课,都要求学习有关“人”的科目(使他们能够触及艺术及人文学科)和关于行星的学科(使他们明白什么是科学)。但这对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希望学生们可以回归到教育原初的目的,并且塑造品行;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可以升华到特尔斐神谕中“了解你自己”的境界。我们如何才能做到这些呢?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三个“P”中的第三个——Participation列入我们的课程中。
麦考瑞大学的所有学生,无论他们读什么专业,都要参与一个校外社区项目,有些甚至是澳大利亚之外的的项目。
我们的合作者包括澳大利亚国际志愿者组织。我们要求我们的学生去帮助指导伤残儿童,教成年人读书,建立社区基础设施,在避难所和监狱见习。我们希望他们有何收获呢?毕竟,在监狱工作不能帮助学生学习物理,指导伤残儿童不能告诉学生会计学的平衡表,在避难所工作对于学习民事侵权法也没有多大帮助。
即便如此,我相信这些经历将教会我们的学生一些很重要的事情。这些经验将会给他们机会培养自信,并在逆境中磨砺自己。这些经验将会让他们有机会体验团队合作,或让他们成为团队领导者。学生将学会与不同背景的人沟通,学习如何统筹时间,如何向目标努力。他们将学会信任、诚实和公平。最重要的是,他们的经验将会培养他们顾及他人的意识,而这正是建立所有道德规范的基础。麦考瑞大学正在重塑道德。
我们正在实施新课程框架,它不是立足于发展课程自身的优秀,而是立足于发展学生的心智。我们理解会有反对意见,曾经有家长告诉我,高等教育就应该为职前做准备,而不是什么志愿活动——那些学生可以晚点参加,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但是,如果家长对整个塑造品行的主张都有意见,试问他们如何能够判断正确与错误?
这些观点似乎很容易被推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想我们的目标是值得去努力的。麦考瑞大学正在努力使教育回归本源。我希望事实可以证明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
注释:
[1] 双盲试验是指在试验过程中,测验者与被测验者都不知道被测者所属的组别(实验组或对照组),分析者在分析资料时,通常也不知道正在分析的资料属于哪一组——译者注。
[2] 参见网站http://www.polio.pitt.edu/中的例子。
[3] 参见Mildred K. Cho and Lisa A. Bero,The Quality of Drug Studies Published in Symposium Proceedings,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1996(5):485-489,http://www.annals.org/cgi/content/abstract/124/5/485.
[4] 参见Robin Batterham,The Chance to Change. Canberra:2000,cited in Geoffrey Boulton & Colin Lucas,What Are Universities for?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2008:6,http://h29.it.helsinki.fi/?page=1.
[5] 参见http://news.csu.edu.au/director/latestnews.
[6] 莎士比亚的故乡——译者注。
[7] 参见Alexander Meiklejohn,cited in Anthony Kronman,Educations End: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Caravan Books,2007:39.
[8] 参见John Henry Newman.,The Idea of a University(1854),http://www.higher-ed.org/resources/newman-university.htm.
[9] 参见John Stuart Mill ,Inaugural Address,http://digital.library.cornell.edu.
责任编辑 熊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