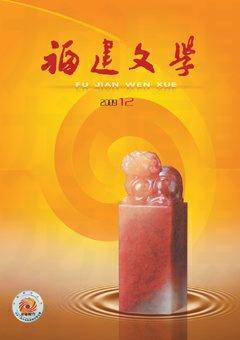小玉姑娘
肖久恩
我每次回老家,总能看到小玉。小玉依然穿着一身穿了多年却整洁素净的旧衣裳;依然禁不住村里老少寻她开心的逗笑;依然会不时地伸出那握块棉巾、长年蜷缩在袖套里的残疾的手,将嘴角流下的涎水迅速地擦去。
据村里经事的老人说:半个世纪前,小玉出生在邻县陈氏官宦之家,曾经的陈家,家族显赫、人丁兴旺。转眼,小玉三个玉树临风、健康俊朗的哥哥,也各自成家立业,事业、生活都顺风顺水;幺女小玉也已长成一个亭亭玉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父母、兄嫂对她更是宠爱有加,一心想给她找个门当户对的婆家。没料,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年,陈家吃了一场哑巴大官司,几个兄弟也相继受到牵连,家道因此败落;祸不单行的是,同年,待字闺中的小玉,竟然患上流脑,陈家虽顷其所有给她救治,结果还是晚了,以致留下了半身不遂、吐字不清、张嘴流涎水的后遗症。
小玉先后嫁了两个丈夫。因了自己的疾病,面目依然清秀的小玉姑娘,嫁到离城不远的乡下。前夫自幼丧失双亲,在村里吃百家饭长大,故取名“村水”。村水生性懦弱,身材矮小,但对小玉嘘寒问暖、百依百顺。平日里,两人你耕田来我洗衣,小日子倒也过得清贫自在。隔了几年,小玉生下一个胖女孩,小玉姑娘也就成了小玉妈妈,她还给女儿起了个乡下人不明所以的名“一脉(mo,默)”。白天,人们总能看到小玉端坐在门前的小竹椅上,把小一脉稳稳当当地抱着,少有走动——她说,她生怕,自己那残疾的腿脚,走路一颠一颤,会摔着女儿;她还成天戴个自制的围嘴口罩,直到一脉断奶,她说,她生怕,喂奶的时候,自己嘴角不经意流下的涎水滴到女儿的小脸上,会吓着她。一家三口,更加甜蜜和谐了。
转眼,十六个年头过去了,在那年初秋的一个清晨,一脉跟着父亲上山采红菇,在深山里,父女俩遭遇了踩中猎人布下的虎剪的野公猪,野猪一见了人,就咆哮着冲过来,正忙着将吓得瑟瑟发抖的女儿藏进身边空树洞的父亲,躲闪不及,被野猪重重地顶了一下下腹部,带着女儿强忍伤痛回到家后,没几天,父亲就去世了。从此,一脉远离了这个村庄,再也没回来过。她写信给母亲说,这美丽绵延的青山上有可恨的魔鬼,是那魔鬼夺去了自己亲爱的父亲的性命,她再也看不得那留给自己惨痛记忆的群山,她要到一个没山的地方,一颗破碎的心,才能安宁;小玉失去了丈夫,还多了一份对身在异乡的女儿遥远的牵挂。那段日子,小玉妈妈,苍老了许多。
不知怎么的,在我懂事的时候,小玉搬到了我们村,独自过了一段清冷寂寞的日子。后来,经好心人撮合,一个来我村打磨石头的山东男人同意到她家落户,成了她现在的丈夫,村里人都称他“小山东”。
小山东五官端正、老实本分,言语很少却热情、不吝气力,经常帮邻里做点力所能及的活,对小玉更是爱惜有加:平时在家,升火烧饭,尽量不让小玉沾手;打磨石头的钱分文上交,还隔三岔五到邻里八乡打点短工,赚点钱贴补家用;出门做事前,给小玉备好腊肉、蘑菇干、辣椒酱、豆豉、榨菜,还得找足几天的青菜,洗净,挂在灶头的吊钩上。渐渐的,小玉快乐起来,成天呵呵地笑,偶尔也串串门,和邻里拉拉呱;遇到村里人的红白喜事,她也会热心走来帮忙;谁家媳妇生孩子,她怀揣几个自家母鸡生的土鸡蛋,欣喜地前来恭贺;最忙的是她丈夫快回家的日子,一大早,小玉就要到村里的小店,买好一瓶丈夫爱喝的山东高粱,还要在我们村那条只有短短几华里、直通村里水口的路上,一颠一颤折腾几个小时后,静静地站在水口的桥上,等她丈夫归来。
或许,还有一点残缺、模糊的潜意识在感召她吧,小玉出奇的爱进她出生的县城。我们村离那县城二十多华里,坐班车很近,走路倒很远。在那条通往县城的国道上,如果你看到一个男人拉着一辆坐个女人的三轮小板车,一路上走走停停,还说说笑笑,没准就是小山东又拉着小玉要进城或出城了。起初,别人都笑小玉:怎么班车也舍不得乘,要烦累老公用板车拉着你啊?小玉说:才不是呐,是我爱人要拉我呢。一听她口口声声说“我爱人”,大家都会笑晕——“一个乡里巴人,还‘爱人长、爱人短的,怎么说得出口哟……嘻嘻……小玉羞羞……”小玉听了,倒是无动于衷,“爱人”依旧。渐渐的,这便成了路上最独特的风景。
有一次,一对胸前还佩着“新娘”、“新郎”红绸标的新婚小夫妻,刚下班车,在路上走着走着,先前是相互指骂、推推搡搡,后面竟然大打出手,新郎飞起一脚直想把新娘往死里踹,新娘不甘示弱,在路边拣起一块砖头正要往新郎头上拍去,正巧看到小山东拉着小玉在她们面前路过,小夫妻间的一场升级版的架,戛然而止——男人收起了拳头、女人蹲在地上嘤嘤地哭诉:你这没良心的,别人四五十岁了,还对自己的老婆那么好,看也给你看可惜了啊……
如今,小玉已做外婆了,但我想,在小山东心中,她依然是他心爱的小玉姑娘。
责任编辑 贾秀莉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