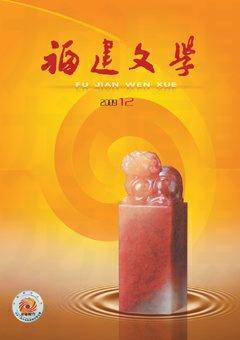七婆的金子
胡向群
孤身过日的七婆没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
闽西一带的客家妇女,名字一般都很简单,常在姓氏后面加个阿招阿娣阿娘阿妹的。七婆原名是阿什么,已无人知晓,七婆这个名字是因丈夫排名老七而叫顺的,客家话中对兄弟间排最小的小弟称作“满”,老七就叫七满了,血缘上与她比较亲的也有人叫她“七满叔婆”。
七婆矮小,头发全白,尖嘴瘪腮,长年换穿着几身洗得发白的对襟蓝布褂子,配几条大裤腿的交头裤。不论乡间人家流行什么穿戴,她这几套从不改换。
七婆是全公社罕见的双料烈属:丈夫,红军烈士;儿子,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成了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八百多位八闽儿女之一。所以,她在我们那个土楼里享受着最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她家门上挂有一块“光荣人家”的红牌子,逢年过节,大队、公社就会有人来给她送年画、送抚恤金。
七婆住在一间用谷仓改成的睡间里。那间谷仓与客家地区几乎所有的谷仓一样,有一个半米多高的门槛。这么高的门槛,七婆不知为什么从来没考虑过把它改低,以利于进出。因为她房间的门槛如此之高,使得土楼里面的小孩对于她房间的了解一直被隔在了这半米多高的阻挡之外。有人背后说:七婆的门槛高,是防贼用的,黑咕隆咚的房间里藏有金子!又有人说,当年生产队的社员都下地干活了,曾有人看见七婆把一包金光闪闪的东西拿出来晒,自己就坐在旁边守着,不让人靠近。
七婆有金子,对于辛苦一年才得到一两百元分红的生产队社员来说,干瘪的七婆因此好像一身都闪着金光。
我开始会叫她七婆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尖尖的嘴巴像个脱杆很久的干茄子,上面有一条条刀刻般的皱纹,整个脸部的皮肤干瘪得像一条老苦瓜;吃东西像是兔子吃草一般,不见嚼,只见闷咽。牙都没了,她常年只吃稀饭,不吃干饭。命运坎坷的七婆从不生病,只是眼有老疾,怕光,出泪,听说是哭坏的。老人每餐能吃三碗稀饭,还为生产队养着一头水牛。每天她都戴着一顶竹壳斗笠,专注地盯着在田埂上吃草的水牛,那头水牛看似老实,其实挺狡猾,吃草时两只大眼睛总是咕噜咕噜地四下乱转,只要七婆稍一走神,它就会迅速伸出长长的舌头“刷”地卷过一大把禾苗,然后沙沙沙地猛嚼。别人看见了,就会高叫:“牛吃禾了——七婆。”
七婆听见,赶紧用力拉几下牛鼻绳,骂几句:“笨畜,饿死你了?”
骂了,打着手障遮着怕光的眼睛,找到远处的人,咧着干巴的嘴笑着:“死笨畜,一下没看见,就让它偷吃了,好在你叫我。”嘿嘿地干笑几声。不论什么时辰,也总是问人家吃饭了没有,以此表示着感谢。
然后,就要翻起胸前客家妇女特有的蓝布胸襟,擦擦眼睛。她的眼睛老出泪,整天湿漉漉的。
骂归骂,她从不打牛,对那牛,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
有金子的七婆,一直笼罩在一层金色的光环中,在整个公社备受尊敬。七婆尽管有“金子”,却好像并不见得她有多高兴。有时也会看见七婆对着天空中的星星凝神地望着,嘴里还自言自语。
我对七婆的印象总是停留在她的几个充满感情的举动中:逢年过节,总要捧着香对着苍天小声念几句谁也听不懂的祈语,念完后在大门口的青石柱缝里插上几柱,然后再到村口曲九树上同样插上几根。大人们说,这是七婆在为丈夫和儿子引路,希望他们也能回家过节不致迷路。不管生活多么艰苦,她总是倾尽所有买来一桶桶的煤油,在厨房里点着一盏长明灯,灯前供奉着观音菩萨的神像。老人们说,七婆在解放前丈夫死后就住在一座观音庙里吃斋念佛。“文革”初期,庙就被砸了,她只好回家。经是不再念了,神和斋却是继续保留着。她很会养鸡,却只卖不吃,逢年过节要三牲敬神。这可难不住戒杀的七婆,她嘴里念叨着:“你吃人谷,就被人屠。超生转世,不做牲畜……”念完洒上几滴老泪,然后为鸡们放上一小串鞭炮,再叫人拿到楼外看不见的地方去下刀。
除了本村,知道七婆的人并不多,她从未出远门,也从来不去十几里外的大队看电影。据说,朝鲜停战后一次军队慰问团为了慰问这位烈士母亲,带着发电机和放映机,翻山越岭,到村里专场放了一场反映抗美援朝的影片。七婆坐在最优越的位置上第一次看电影。电影开场了:大炮在怒吼,机枪在扫射,弹雨和履带撞碾着战士母亲的心。烈火和鲜血模糊了七婆的双眼,她被惨烈的战场惊得目瞪口呆,眼泪如断线的珠子般滴湿了厚厚的蓝布褂子,她当场痛哭失声。七婆把故事片当成真的了。
第二天,人们发现七婆的眼睛红红的,肿得老大。她说是上火害火眼了,别人却知道是她昨晚看电影哭的。
七婆从此再也不看任何电影了,她对别人说是自己听不懂电影上的人说的“官”话。
命运残忍地安排七婆将没有丈夫和儿女的陪伴照顾,她要独自度过自己的一生。接连失去亲人的痛苦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趋于平静。当我们懂得叫她七婆时,好像已经看不出七婆的不幸纪录了,她的言行和生活起居与我们自己的祖母们,没什么不同。
村里非常偏僻,直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还未通车、通电。为了通车,全村人集资出工开路。七婆无力,不能出工,便捐了几担米谷。这时,邻村一位回乡探亲的老华侨突然中风而卒,亲人们措手不及,找不到合适的寿材,听说七婆有一付上好的棺木,派人来劝说七婆先让给他们。七婆收了棺材钱,却把卖棺材的钱全部捐给了村里用来开路。这笔钱刚好用在了路上的一座小石桥上。桥修好后,桥墩上刻了“七婆桥”几个字。
这时的七婆已八十开外,脑子还清醒,腿脚却僵硬得没法越过那半米高的睡间门槛了。她的眼睛也很花了,几乎看不见,她只好睡在了底层的一个角间里,三餐由土楼里的同族帮忙着。
七婆那间藏有金子的睡间从此被紧紧的锁了起来。
七婆是五保户,有公社的时候,生活由生产队保证,后来,生产队解散了,便由政府的民政部门关照着。
村旁有一条小河,常年流淌着清澈见底的溪水,这终年流淌的溪水平时只用来灌溉农田、洗洗衣服洗洗菜,也没觉得还有什么用处,村民眼界开了,大家感到应该利用得天独厚的水利资源建一个小水电站,为村里供电。一算下来,要几万块钱。还是大家摊派出钱。按家庭人头,多的多出,少的少出。村里干部找到半瞎的七婆,要她出名以双料烈属的名义向政府打报告,请求提供资助。
七婆问:“听说电灯不用油也能亮,点起来也没烟,有这好东西?做起来大家要出多少钱?”
村干部说:“七婆,您就别出钱了,我们已经打了报告,您出个名就行了,您那名就值很多钱。”
“哦,我出名就行?没出点钱,总不太好。”
七婆边念叨着边按了一个手印给村干部。
“您放心,七婆,电站建好了,我们不会忘记给您装灯的,也不会忘了给您观音菩萨装长明灯。”
干部走了。七婆一天天的等着那不用油的灯亮起,却一直不见动静。灯没等亮,却等来了一个收废品兼收古董文物的“货郎”。他在楼里收东西,听说七婆还藏有“金子”,便眼睛一亮,口气很和蔼地问:“七婆,听说你老人家藏有几件宝物,能不能拿出来看看,这些东西你留着用处不大,要是能换些钱,你老人家买些油盐咸淡什么的也方便些。给我看看行吗?”
七婆动心了,她想把金子换成钱,捐给村里装那不用添油能亮的灯。便从腰里取出从不离身的一串钥匙,叫来探望他的娘家表弟和几个人到楼上开了锁,拿出了那包金子。
听说七婆取金子了,全楼的男女老少都挤过来,瞪大眼睛来看七婆的金子。“货郎”打开一层又一层的布包,先取出几封信件和证书什么的,最后才抖出一包沉甸甸的东西。大家一看,是几枚金光闪闪的军功章,那贩子先是眼睛的瞳孔放大了,接着整个脸部的肌肉在痉挛,脸上冒出一层细汗。可他把“金功章”拿在手里掂了掂,放在嘴里咬了咬,又在一块随身带来的黑黑的石块上划了划,大失所望:“嗨,七婆,你这些‘金功章不是金的,它是铜的。不值什么钱!”
“铜的?不会吧?”大家都不信。
“是铜的!不信你们可以拿到银行去检验一下,这试金石一划就知道了,我要骗你们,天打五雷轰,骗七婆这样的烈属,那是要坐牢的。”
“原来是铜的,那就不值钱了。”
“真是铜的,就不值了。”村里那些看热闹的人,拿过金质奖章,在手里掂了掂,感到分量也确实不大够,也就信了“货郎”的话。
七婆原来并没有什么金子!只是几个奖章而已。
楼里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颇为自己将这些铜奖章信以为金子几十年而感到失落,这些“金子”为七婆的晚年增添的光彩和期望也立时暗淡了许多。
七婆也有些失望,但她还是要回了那些奖章:“铜的吗?都说是金的,挺金亮的呀,政府部队上的人给我带回来的,我儿子的东西,几十年了,你不要,我还要藏起来。”
“货郎”拍了拍手,擦了擦汗,脸上舒展了许多,有气无力地收拾起家伙,显然他是想走了。
七婆要回那包东西,小心地把里面的东西仔细地叠好,又一件件地装回包里,“货郎”眼睛突然又亮了,盯住那包里的一个发黑的牛皮纸信封,转身又放下了家伙担子:“慢,慢,七婆,那是什么,我看看。”
他抽出一个破旧的信封,那是七婆当红军的丈夫给她寄来的唯一一封信。抽出这个信封,“货郎”眼都直了:那是苏区实寄封啊!还贴有用粗糙的草纸印刷的“邮票”,这可真是价值连城的文物!“货郎”声音都颤了:
“七婆,这几个旧信封你没用吧,当旧报纸卖给我吧,我拿一个东西跟你换也行。给你一个电饭煲换要吧?水电站建起来,你做饭把米放下去,电饭锅就自动会煮熟饭,那东西可好了,大冬天你也不愁会吃冷饭!”
“有这样的好东西?那不是像‘田螺姑娘一样了。”七婆差点同意了。
“慢着,我看看。”旁边那个来探望七婆的娘家退休表弟看出名堂了,他要过信封,左看右看:“表姐,这信封是哪来的?好像是表姐夫寄给你的?”
“是呀,他当红军,说是一年就回,记得是走的第三个月,给我寄了这封信,说是从江西寄来的,我不识字,叫人念了就留了起来,想等他回来怕有用。没想到,他只给我留了这封信,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位娘家表弟见过世面,知道这东西可能非常宝贵,坚决不换了。“货郎”加价又加价。“货郎”越起价,七婆表弟越发不卖了。“货郎”缠了半天,人家就是不卖,他只好低着头走了,走到村口的曲九树边还唉声叹气地直拍大腿:“没风水,没风水!不该发。唉,厚有财缘,薄有财份!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刚好碰上一个冤家对头丧门星呢?”
这“货郎”蹲在曲九树下,抽了半盒烟都还没走,直到天快黑了,才一步三回头出村了,听说过几天还想再来。
表弟怕他再回来被骗走了,便把信封带到山外,把发现苏区实寄封的消息向政府文物部门打了一个报告。政府来了人,带了信封,见了七婆,说这一个信封可真值了大钱了,三两金子也不值这个信封!政府里的人把信封要走了,给七婆写了收据和证明。
不久,村里的干部接到上级的通知,说是七婆捐出的信封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为了奖励捐献珍贵革命文物的七婆,除了给她一笔奖金外,对于村里建水电站的投资,全部由政府出资。
水电站在七婆珍藏的那个信封换来的“金子”的驱动下,正式动工了。
动工那天,人们扶着七婆来到电站工地,把一把剪刀放到她手里,让她摸索着剪断了开工彩绸。
七婆眼睛看不清工地上的东西,只耳闻有从未听过的轰隆隆的机器在周围不停地响着。
“那机器的叫声比牛牯还大。”七婆回来对人这样说。
责任编辑 练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