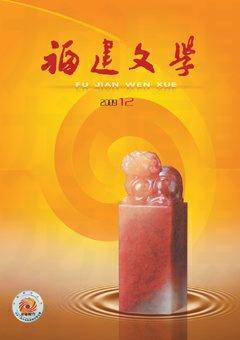人或神(外一篇)
李集彬
那是一个春日的早晨,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我不知道这样的时候,是否更有利于一种思绪的进入?当我经过一座装潢得金碧辉煌的乡村寺庙的时候,我突然记起,它以前是一座碾米厂。
这座碾米厂,在一篇写我四姨夫的文章里我曾经提及过。我的四姨夫,一个退伍老兵,曾经是这座碾米厂里的工人。
关于那篇文章,以及这座乡村碾米厂的事,写过我也把它忘记了。生活就像潮水一波波涌来,后面的细节很快覆盖、淹没了前面的细节,我们往往很快遗忘生活里发生的一些事。最近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健忘:一个很熟悉的人,突然就忘记他的名字,让我有点恐慌:不知有一天,我是否会忘记自己?
像往常一样,从寺庙那边经过,我突然记起它曾经是一座碾米厂。那样鲜明,突如其来,猝不及防。每天我都要从那里经过,为什么偏偏这时候记起?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这样的天气,或许某种情境,或者什么隐蔽的暗示。
从我记事时起,那座碾米厂一直存在。
那时候,它没这么漂亮,也没这么安静,安静得出奇,让人觉得诡秘。那时候它一直灰扑扑的,机器的吼声振聋发聩。现在突然安静下来了,反而让人觉得空落落的很不习惯。
那座碾米厂,原本就是一座乡村寺庙。“破四旧”的时候,一个崇拜人类力量的时代,人们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活生生的人身上,是无需什么神灵的,便把佛像从寺庙里拆除,也从人们心灵里撤离。在那热火朝天、如火如荼的年代里,乡村寺庙改建成碾米厂,外壳依然保存,内容彻底改变,粗笨坚硬的机器代替了神秘莫测的佛像。在神灵崇拜根深蒂固的历史背景里,人类迫切需要建立自信。
这是一个平凡的村庄。它的所有建筑形式、人们生活,以及一阵阵吹拂过山间里的风,都与其他村庄无异。唯一值得夸耀的是,很久以前这里曾经建立过一个临时县衙。当地的一些地名,诸如“官厅”、“衙口”,似乎可以印证它的存在。我也曾经反复提及过,目的还是为了强调它的存在。然而村庄历史上,不曾出现过哪怕一个能让方史学家津津乐道的人物。这座村庄的那一段光辉岁月,仿佛一道光芒在历史深处闪烁一下,复归于沉寂。现在,它甚至比其他村庄还来得普通。
在我的童年,以及更早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锄头、犁铧、耙这一类原始的农具,依然是人们手中的主要劳动工具。人们用镰刀收割了庄稼之后用碓臼加工粮食,那是多么沉重的劳作啊。我也曾经深受其累,透彻肺腑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一直怀疑一些文人关于劳动的抒写,以为他们未事稼穑不知其累,他们只是旁观者,轻易对一种劳动评头论足,那也太奢侈了。
在这默默无闻的乡村里,后来出现了几台笨重的碾米的机器,以及那种叫碾米厂的乡村里唯一的所谓工厂。与过去比,这无疑是一种巨大进步,甚至可以说,代表了整个村庄最先进的物质文明。我不知如何描写这种粗笨的机器:一团乌黑庞大无比的钢铁构件,吃油如喝水一般豪迈,几台机器一齐启动,吼声震天,几乎欲把屋顶震塌了。灰尘雪花一般纷纷扬扬,一个人在里面停留半小时,出来时胡须眉毛全白了。一种机器,似乎要以这种强有力的形式强调它的存在,以及它的无坚不摧。人们似乎也被这种神秘的力量震撼了,对它充满敬畏,一时忘记了神灵的存在。
在我童年记忆里,这里充满神秘,除了大人不让我们轻易进去之外,还有其他原因:那种半裸的机器,仿佛一个妖艳的女人,媚惑背后充满杀机,即便和它整日相处的工人,稍一疏忽也难逃厄运。曾经就有一个工人,一只手臂被卷进转盘里,整个人甩出很远,哀号之声响彻村庄,让人不寒而栗。
在人们眼里,机器的巨大力量,以及隐秘的杀伤力,让它变得诡秘,就连那些操纵机器的人,也变得神秘起来了。
后来,碓臼逐渐不用,仅仅用来捣猪食。整个村庄的人们加工粮食都到这里来,碾米往往需要排队。这样的状况下,碾米厂工人手中,便仿佛有了一种无形的权力。
尤其那个掌控着碾米厂的头头,一个秃了顶,整天戴着一顶旧军帽的老头,似乎也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时常负着手、昂着头在碾米厂里走来走去,吆喝工人干活。在他眼里,除了大队干部,无一例外必须奉行他所制定的规则,仿佛他便是这里的帝王了。
由于四姨夫也是里面的工人,他们歇息的时候,我便有机会进入这样的殿堂。那时候,他们往往正准备吃饭,粗大的瓷碗里装着咸粥,上面飘着一层油,很让人眼馋。
更多的时候,我只能呆在外面,凝望屋顶飘过的一阵阵青烟;或者到碾米厂后面的那个水池旁边去,看水从一根管子里进去,从另一根管子里出来。那时候我一直搞不明白:一台机器为什么要像人一样喝水,是不是干活久了也会口渴?这种疑问挥之不去,直到我进入更远的中学,课堂上,物理老师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后来,我离开村庄。再后来,碾米厂解散了,盘给村里一个农民。
当物质不再神秘,心中那个神撤离,心灵空虚下来了。在沉重、枯燥的劳作之余,心灵的空虚需要一种东西来填补,村里寺庙恢复了——现在的乡村寺庙,更多作为民俗传扬的载体,找到合适的存在形式,自身也获得更好的发展。人们把它重新装修起来,变得金碧辉煌了。
至于为什么,我会在这样的早晨,在这样的晨风细雨中,突然想起那么遥远的事?大概童年里,无数这样的早晨,这样的雨天,我呆在家里无法出去,只好伏在窗口对着远处田野、近处寺庙凝望——它离我家很近,这样的情景唤起我的记忆,或者墙壁的某一块石头上面,留有我童年刻写的印记,这时候提醒我它的存在。
一棵在时光里消逝的桃树
什么都会消失,比如我们人,一拨拨来一拨拨去,像赶集一样吵吵嚷嚷,然后散去,留给后人淡薄的记忆。
和人一般,树也一样,比如那一棵桃树。
一棵树总要跟一个人联系在一起,尤其一棵能结果子的树,总要跟一个人息息相关。这个人或者是你,或者是他。乡村里有一种说法:这棵树是谁的树。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我家老宅里的那一棵桃树,我们总说,那是祖父的树。
祖父是我所认识的我们家族里辈分最高的那个人,再往上去,我就一无所知了。比如祖母在的时候,讲起我的太祖父,我就一脸茫然了。
祖父的形象在我记忆里犹如一张发黄的老照片,被岁月磨洗得淡薄而模糊。有时,我竭力想从记忆深处打捞起他的形象,然而往往徒劳,一片模糊不清,依稀记得的只是他有一个光滑的前额,像父亲一样秃了顶——我们家族里的男人,上了年纪大多这样。他的形象和我苍老的父亲有些相像,只是祖父多了一支拐,祖父年老的时候拄拐的,这一点我印象很深。
祖父是一个多情的人。他和祖母一辈子相依相伴,一前一后走路,连拌嘴也是轻声细语——这一点在我们村庄里广为流传,以致祖母垂垂老矣的时候每每回忆起祖父仍充满温情地怀念。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夫妻感情方面留给我最美好的印象。我一直不理解:为何物质越来越丰富,人与人之间感情越来越淡薄?这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拨弄不清的谜团。也许物质与感情是此消彼长的两个方面,永远无法并肩前进,犹如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祖父一辈子除了教过一阵子私塾之外毫无建树,就连居住的房屋也是祖上遗留下来的老宅。难怪母亲一直抱怨嫁给我父亲时家里一穷二白,祖父能给父亲的确实无多。
然而后来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对祖父的看法。
据说祖父年轻的时候试图告别祖母到南洋去谋生。那时候,许多闽南人无以为生,一些人仗着年轻力壮,告别家人,漂洋过海到南洋去,企图凭此趟开一条生路。然而祖父到达厦门码头,买好船票,就要上船了,想起撇在家里他的媳妇——我的祖母,割舍不下,又折身回家。村里到南洋去的人有几个确实发了财,后来风风光光地回来了。不知道这件事会不会成为祖父心底的一个遗憾?然而从祖母后来深情的回忆中不难看出,他们后来的日子更加温情。
那个多情的人一直喜欢种树。
我家房屋周围有祖父栽种的七棵龙眼树——那是他留给后人唯一值钱的东西了。除了我们至今受益的那七棵龙眼树,还有一棵,就是记忆中老宅里的那棵桃树。
李渔《闲情偶寄》里说到桃花:“其色极娇,酷似美人之面,亦所谓‘桃腮、‘桃靥者。”那该是怀着浪漫幻想的。祖父是当时村庄里不多的识字人之一——前面提过,他教过私塾。我想,他一定喜欢看书,只是不知是否读过李渔的书?他在一个苍老的院子里种下一棵桃树,是否也因怀着浪漫的幻想,向往娇艳的桃花?这些问题无从考证。然而我们从此受益。当然,受益的不是我,而是比我年长的兄长。在我童年的时候,那棵桃树已经很老,老到开不出一朵新鲜的桃花,寥寥结着几个干瘪的桃子,在那业已废弃的老宅里寂寞苍老,以至后来父亲不得不下令把它锯倒。
虽然我没有享用过祖父亲手从桃树上打下的桃子,然而凭借兄长们后来的记忆,我能想象出当年的情景。
那是一棵高大的桃树,从来不曾见过那么高大的一棵桃树:树冠覆盖半个院子,树梢高出屋脊许多。粗壮苍老的树干,春天里,枝头上生出许多嫩芽,伸展成一片片狭长新鲜的叶子,然后,开出满树娇美的桃花,结出无数绒绒的嫩桃。
那样的时候,兄长们围在树下——那时候他们还是孩子,仰着脸,望着桃子一天天长大,直到绒毛褪净,一颗颗新鲜光洁。父亲的管束是很严格的,他们不敢自作主张往树上去,于是兴冲冲跑进厢房,去告诉他们的祖父。
或者是上午,或者是下午,祖父出来了,拄着拐杖,站到树下去,验证桃子确实熟透了,接过不知从哪一个孩子手里递过来的竹竿,伸往树上去,抖抖索索打那桃子:一下,两下,三下……桃子一颗颗跌撞着掉落下来。兄长们围上去抢,抓到一个,来不及拭去尘土,迫不及待塞到嘴边,就要咬起来。祖父厉声喝止。于是,他们很不情愿地翻开小手,把抓到手里的桃子一一记牢,到厨房里去,把桃子交给祖母。
祖母把桃子一颗颗洗净,放进早已预备好的黑陶罐里,撒把盐,把陶罐捧起来,上下甩动几次,放在那里;大概过了一个时辰,盐水把桃子浸透了,再倒进一个白瓷盘里。兄长们已等得够久了,围上去认领属于自己的桃子,放到嘴里咬起来。过了盐的桃子干净、香甜、可口。那大概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了。
我能想象当时祖父的表情:欣喜,心疼,内疚——他能给他的孙儿们的只有这些了。
不知怎么,虽然没有亲自经历过,然而这样的情景,我的印象比兄长们还要深刻?也许我很像我的祖父,沉默而多情。也许是兄长们的讲述,那种温情的生活使我沉迷,我喜欢上桃树,喜欢上桃子。后来我也种一棵桃树,不像祖父的桃树那样高大,然而一样开鲜艳的桃花,一样结鲜美的桃子。我一样喜欢把桃子摘下来浸盐水。也许那种咸甜的香味,早已沁入我的心灵深处。
一棵在时光的河流里消逝的桃树。不曾想到,那淡薄的记忆,能给我这么深刻的影响。
责任编辑 贾秀莉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