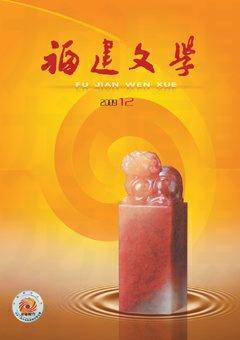圆混混,活泼泼
康启昌
1988年8月,在我接到退休的人事命令时,老伴把叶芝的一首诗念给我听,声音低沉,含情脉脉:“当你老了,白发苍苍,睡意朦胧,/在炉前打盹,请取下这本诗篇……”我感激他给我叶芝似的挚爱。是这样,他曾爱我以“欢乐而迷人的青春”,如今更爱我以“日益凋谢的脸”,爱我一颗“朝圣者的心”。但我说,我虽“白发苍苍”,却没有“睡意朦胧”,没有“在炉前打盹”,没有“佝偻着,在灼热的炉栅边”。我还说,你也是。于是,飘零的黄叶重返枝头。我们相约各写一篇同题散文《趁我还不老》,以示我们在花朝已过杜鹃春老之时,犹有刁顽的童心。上个世纪末,我那篇《趁我还不老》被吴欢章、沙似鹏选入他们主编的《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改名为《不老歌》。那是“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的写意,是说“在密密星群里”,我们的爱没有赧颜。说白了,老而不服老。什么时候感到自己老了呢?是我送走了老伴,揣着一粒温热的白骨,离开埋葬他的墓地的时候。这是我第二次失去他,这一次是永远。心被掏空了,头重脚轻。往日轻捷的步履,骤然蹒跚。丁香花惨白的花穗雪一样冰冷着我的肌肤,嫩绿的街柳 晃着秋天衰老的晕黄。累了,实在太累。踩在泥泞里的双脚,每走一步都要瘫倒。老了!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大自然的意志,不可违抗。该走的必然要走,该来的也不能不来。我的一个学生刚满55岁,多好的年龄,不该走的,他也走啦!我还怕什么坏日子吗?
蛰伏一个夏天,门窗紧闭,息交绝游。把自己囚禁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精神牢笼里,就像一只瘸腿的老狼,终日蹲在一个石洞草窝里等待末日。不愿对视明镜里的霜雪,怕见亲友怜悯的目光。秋天,参加大学生的一次活动,走出家门,恍若隔世。秋容不娇,强烈的阳光逼我双眼。想到此时此刻银杏树下的故人,独自长眠在无尽的黑夜,心中的凄然仍是难抑难禁。与大学生对垒,用氢气球打排球,我木木地僵在阵地上,一个球毛都没有摸着。一个大学生问我:“您老多大岁数?”分明是鲁迅看见了祥林嫂。“你看?”“有八十岁了吧?”她说出了别人不肯直言的皇帝的新装。我挤出一个笑脸,点头称是。可是,我才65啊!老娘九十有二,还能登太原街的过街天桥。我65岁就躺倒待毙,任凭时间的铁蹄无情地踏过我苍白的头顶?这不应该是我。福克纳用他的小说《野棕榈》感动了我:主人公的爱人因流产死亡,他却要在监狱里服刑十年。他想自杀,有人给他带来一粒毒药,但是他却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认为唯一能延长他所爱的女人的生命的办法便是把她保存在记忆之中。她不在了,那一半的记忆也不在了。如果我也不在,那么所有的记忆都将不在。于是在悲伤和虚无之间他选择了悲伤。我曾经是保尔·柯察金的追随者,是牛虻的崇拜者。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即使不为别的,为了我那一半记忆,我也必须站起来,必须走出去。即使老了,也不能老死洞穴。我为什么不能化做一阵狂风,扶 直上去追赶失去的勇气和信心?小寒那天,小北风哑着喉咙,挡在街口。我去市场给老娘买茧蛹,揣着老女儿一颗耿耿不变的孝心,迎着声音喑哑的北风。本是轻车熟路,街市依旧充盈生机,空气注满了料峭的新鲜。可是我不再是我,老了!孱弱的筋骨,耐不住白雪覆冰。横过马路,在距离汽车很远的地方像一个几十斤重的面袋子被摔到马路上。完了,屋漏偏遇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左腕尺骨骨折,疼得我忘记了命运的乖舛。吊着一只残臂,40天,再也不敢上街。不光摔断了手腕,还摔掉了行走的自信。一只手陪老娘玩牌,完全是装腔作势,哄老娘宽心。一次次被衰老打败,一次次被“孝”字武装以刚强。我对女儿说,我之所以能够爬起来,皆因老娘在。家有高堂,儿不敢言老道病。还有,一颗冥顽的虚荣心也在蠢蠢欲动,给它一口气,它就不想抛弃历史的嘱托。还有,老伴留给我的期望还在前方招 。那期望是刻在我们约定的三生石上的。我没有权利退出,没有理由背叛。我要孤注一掷,以我仅有的一切赌我更老的明天。在我吊着一只没用的左臂,用我不辞辛苦任劳任怨的右手给老娘做饭的日子,我擦干老泪,背起两个人的行囊,又一次上路了。
老了吗?老了!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哲学命题,而是最普通不过的自然现象。说到底人不过是一种物质,一种高级的复杂的有机的无机的混合物质。世界上,宇宙里,至今还没有一种物质长生不老。关键是这种物质有思想有感情。精神上的物质,是任何别的物质不具备的。那就让我最后一次放纵我的岁老弥坚的虚荣,让我理智地面对西天虽不灿烂却也不失光明的晚景吧!我从整理一年来的稿件信件记忆开始,重操旧业,捡拾青春的翰迹墨汁,撰写《文学与爱情》。正如邓荫柯先生的评论:“文学与爱情是她生命的双面神。”我的文学的花仔曾在爱的土壤里发芽,在没有爱的日子里枯萎,在重新获得爱的时候,它复活,成长,茁壮。现在我用什么灌溉它,滋润它,让它重放往日的光艳?饥渴的路上,我把手伸进了饱满沉重的行囊。啊,没有一件微小的携带不是爱的见证。太多的贮藏,足够的积累将我变成爱的富婆。我不仅是爱的消费者,更是爱的创造者。我要创造一个新的太阳。黄昏的野径上,是我一个人踽踽独行吗?不,心中有伴,我不孤独。午夜的星辰只照耀我孤单的身影吗?不,我笔下有人,灵犀相通的情感跨越生死沟通阴阳,在我破碎的稿纸上机敏地捕捉灵感。我迷失了退避的路。我让朋友的掌声引领西西弗斯不断地向上推动大石。不知疲倦,不知今夕何夕,不顾岁月的残忍,不顾老之冷漠无情,我呼唤没有远逝的春梦,呼唤没有青春做伴的新的活法。
所幸没有老年痴呆,读书的兴趣犹如年少。陆放翁诗云:“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其实那年的放翁仅仅43岁。离老还差十万八千里。我43岁也有白发入侵,但我把它染黑了,把心染绿了。“路漫漫其修远”,43岁,我正年轻。放翁夜读,在青色荏苒的灯影里找到了童年的欢欣。我73岁夜读,在白炽如昼的灯光下,展卷漫游,开释我少年的青春烂漫。我读梭罗的《瓦尔登湖》。我承认我对《瓦尔登湖》的喜爱远不如某些人那样极端。但是我收获的思想却是我自己没有想到的。我敬仰梭罗,不是因为他对保护环境的超前认识,而是他能够独立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我读米兰·昆德拉在接受以色列国际文学大奖时在耶路撒冷所做的讲演《智慧是什么》,如逢圣教,如饮圣露。我拍案惊奇,连说妙不可言。读一遍,我看到一点热闹,想再看看;读两遍,热闹没了,只觉得高山隐隐,海洋深深;第三遍,看到一副崭新的图画,听到一种从来没有听到的声音;第四遍读它,我说,嗟乎!没有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亏了!早年读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佩服他对生命价值的大胆颠覆,现在读他讲演,才知道他将彻底颠覆我想都不敢想的文明法度。我在手头没有新书的时候,发现了我曾百读不厌的《少年维特的烦恼》。捧持之,把玩之,爱不释手。放到枕边,灯下再度,不禁又一次泪雨滂沱。这是不是哈罗德·布鲁姆说的“经典性”就是“陌生性”?始知经典著作的生成,自有其不可动 的内在生命逻辑,它是读者心灵的筛子筛选出来的。在我心灵的筛子上,《维特》是歌德之最,《浮士德》也要排在它的后面。它的审美活动不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运作,而是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写到这,我想起二十年前读过的裴多菲的散文《第九封信》。我曾经像崇拜歌德一样崇拜裴多菲,喜欢他散文作品中海一样的激情,赞佩他感情风暴刮起的英雄交响,但我不喜欢他的刻薄,尤其是对歌德的贬责。他在1847年7月6日从拜叶写给朋友的信中,用嘲讽的语言评论歌德:“我不喜欢他,厌恶他;好像我厌恶奶油拌山药这种食品一样。歌德的头脑是用钻石制造的,他的心是用天然石灰石制造的……”又说:“歌德的心的制造材料不是别的,是一种令人讨厌的材料,一种潮湿的松软的材料(天然石灰石是松软、潮湿的吗?——笔者)。特别是在塑造维特这样一个傻瓜时,歌德用的材料又干又硬……”太刻薄太偏激了!维特不是傻瓜,歌德用的材料也不干硬。你裴多菲描写自己的爱情,也曾傻瓜似的“松软”“潮湿”。你在《第五封信》中说:“再见吧,亲爱的朋友!如果这是我写给你的最后的一封信,那么就请你转告世界上理智清醒的人们:是爱情的失望和爱情的疯狂毁灭了裴多菲·山陀尔!”当然,裴多菲并不是因为这句“傻话”才在我心中缩水贬值的。
老年读书排除功利,破除迷信。也不写什么读书笔记了。高兴,摘几段收在电脑的精品栏里,以助记忆;不高兴,看完拉到。不管谁是名人,谁是名著,信手在书的空白处涂鸦。天头地脑,随便乱画,胡批滥侃。反正是自己的书,产权自授。小时候读书,都是借的,岂敢?有时对某些权威,也敢信口雌黄,“说大人则藐之”。比如,方才对裴多菲,又如,我对叔本华的《说女人》也颇有微词;对某大师的某观点也曾表示不敢苟同。读迟子建小说,爱其底层小人物的活泛,“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读王充闾的《人生几度秋凉》,我心说:充闾,你该向诺贝尔奖冲刺了。到医院看病,坐在候诊室里读小外孙的《红猫蓝兔》,护士小姐三次叫号,我愣是没有听见。心想,怪不得孩子们哭着喊着要这份圣诞厚礼。兴之所至,在赴日本旅游之前,天天读日语,还把老朋友请家来伴读。老朋友夸我记性好,东京口音,我一高兴,读出了满眼樱花的上野,读出了鲁迅郭沫若郁达夫。
不知晨昏,不觉饥渴。宋代学者尤袤曾有这样感受:“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读之以当朋友……”所以“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如有所启,或有所悟,那真是“数点梅花天地心”了。
端坐在电脑前敲字,累了,关机看书。所以,看书是休息,休息就不端坐。或偃或仰,或半躺斜坐,怎么得劲怎么着。“野渡无人舟自横”,老了,没人管了!最喜欢的姿势是钻进被窝,裸着两臂。不管我面东还是面西,我的小黄猫总是在我胸前呼呼噜噜。一只手握书,另一只手在小猫的脑皮上脊背上轻轻地抚摸摩挲,小猫幸福地眯起双眼,我快乐地高声朗读:“……如果男人自身终于被减轻了负担,被解脱了责任的约束,被消除了一切性交能力的忧虑,这也是值得高兴的理由……”君特·格拉斯,真有你的!在你的世纪里书写诺贝尔科学的未来,讶得我跑进了月球。不过,克隆了人,把男人解放了,是不是男人们都愿意?小猫呼噜噜说,愿意。我的小猫是男性的,至今还没有同女性幽会过。
我不是什么楚狂人,但“一生好入名山游”,如果尚有千八百的人民币看守存折,其余的银子都想去国际旅游局报到。几年前,我的旅游野心是“走到我不能走到的时间,走到我不能走到的地点”。现在看来,时间已经迫近,空间却还遥远。“八千里路云和月”应该是功名尘土的旅行者的襟怀。当然,还可以问问自己的膝盖,“尚可饭否?”不能登高,可屡平地。不能涉水,可以荡舟。不能打猴拳,可以试试太极。量力而行,随遇而安。把“九天揽月”的梦留给年轻人去做,自己的残梦则由自己去圆。2007年7月,我刚从日本回来,就迫不及待地还想出去,圆梦,体力显然没有恢复,左腿肌肉拉伤,还没有痊愈,但我的老来疯犯病了,不走不行。哪座青山不埋白骨,何况我的女儿无论如何也能把我的骨灰装进我的宝瓶里。届时,我举着鲜艳的黄手帕,寻找另一只蓝色的宝瓶,我们在天上漫游。我们彻底除去脖子上昂贵的虚荣,彻底摘掉腕上时间的浮躁,回归没有遮拦的永恒。这样的结局不好吗?求之不得吧!于是,任性的老太婆在重庆发大水的时候,让女儿陪我西行。一车人,我的年龄最高。皓发童心,笑看罂粟花红透的美丽。
我们从成都下飞机换乘大巴,溯岷江而上,一路颠簸,领略李白的“蜀道难”。李白惊呼“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我晃晃不失韵律:“我远道而来,目的是‘闻子规啼夜月”,主题是蜀道不难。我赞美这条蜿蜒蛇行拐弯抹角通达青天的柏油公路,赞美大巴司机高超的驾驶技术,赞美人们改造自然的大胸襟大手笔。夜宿阿坝州的茂县,惨了。从汽车下来,想看一眼子规啼月的夜空,只觉得一种神秘的幽蓝托着一瓣橘黄的弦月向我压来,我和女儿同时领教高山反应的强烈。女儿头晕,手持钥匙,蹲在地上,不敢起来开门。我则急于呕吐,不敢走动。两人共用一桶氧气,你推我让,早把李白置之脑后了。但我心踏实,我觉得这种反应并非我老年人的偏得,铁岭那位新科女大学生,也在忍受头痛欲裂的煎熬。年轻人登高,也没上保险。勉强起身,买一条藏式的羊毛披肩,一,抵御高山寒气,二,纪念海拔3100。离开茂陵,海拔徐降,一车人谈笑又风生。我再望窗外的峻岭又想起了“危乎高哉”,但到达九寨沟的最高景区——长海,我却主动放弃了“丫”字形山左边的高峰之旅。时值细雨牛毛,方才蓝色的天影,忽如一口铁灰色的大锅笼罩了“丫”儿,隐蔽在太阳身后的“丫”峰,以傲慢的缄默封闭了没有门窗的神秘。王安石在《褒禅山记》里说,如果具备了条件,却中途放弃,这是没有出息的表现,但是如果你尽力了,即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妥了,我有征马不前的论据了。挟泰山越北海,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能负千斤,我绝不背八百,能负九十九,不必逞能凑一百。三十年前,有人见一落水儿童,他自知自己的水性不佳,却去舍己救人。为此获得罗圣教式的英雄、烈士。宣传那人的光荣事迹时,我什么都不想说,也不敢说。我认为,他在添乱。我主张六十岁以前的人要信仰儒家的“有为”,甚至可以“知其不可而为之”,即使不达目的体验一下过程也很美好嘛(但不会水,千万别胡来,那是有规律不可巧取儿戏的)!但六十以后的老人则应该学点道家的“无为”,“贵乎一点灵明,圆混混,活泼泼,无心无而为,时止时行,以辅万物之自然”。不要为了打败一个破风车,卖老命,死而后已。“无为者,天道也;有为者,人道也。无为同天,有为同人。”无为是顺应自然,不妄为。天让你筋短骨脆,你偏要九天揽月五洋捉憋,这就是逆天行事。所以当我见到了九寨沟来自天上的孔雀蓝色的“海”水,赏玩了九个藏族村落的高山湖泊群,我说余愿足矣,余梦圆矣!知足者常乐,没有谁还能怂恿我这野心勃勃的三千丈白发再去长海查挂钩去攀4457米的高峰。这就是我老年登山的体会。王羲之于俯仰之间触景兴怀,我不能稍逊;但像他那样“临文嗟悼”,“悲夫”死生,我大概不能,也不想。就是说,不想再跟自己较劲,老了!学一点老子的灵明,“圆混混,活泼泼……”,处处顺应自然,不妄为,不胡闹,自在逍遥,挺好!
责任编辑 贾秀莉 林 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