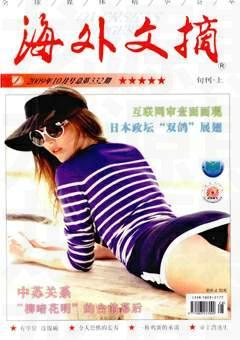绝食的海鳗
宇 捷
女兽医伊丽莎白·诺兰对一条海鳗的绝食行为感到迷惑不解,而后来所揭示的缘由令她既诧异又深有感触。
绝食
一条绿色的、还未成年的海鳗不久前来到了新英格兰水族馆。它原来的主人是外州某酒吧的一位调酒师。在过去的几年里,这条绿海鳗居住在那家酒吧旁的一个水柜里,但由于它继续生长,原来的“家”对它来说已显得颇为狭小。
在野生环境中,绿海鳗生活在温暖海域的多礁石海岸和珊瑚礁区域。它们属于独居鱼类,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隐藏在裂隙或洞穴中,夜晚出来捕食鱼类、虾类、蟹类或头足海洋生物。据我所知,这条绿海鳗并不是个胆怯的家伙。它在那些吧客们心中一直是个受人喜爱的观赏物。
在绿海鳗刚刚到达水族馆时,作为一种防疫措施,工作人员在展厅的后墙处沿墙设置了一个大型水柜,让它单独待在里面。如果经过一段时期的观察,认为它是健康的,能适应新环境中的生活,再考虑把它放养在别处。
这条绿海鳗进入水柜后,像鳗鱼惯常的生活方式那样,成天躲在水柜里的岩石丛中,既不游出来,也不进食。这种行为对于某些换了新环境的鱼类来说,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它始终藏在隐蔽处,不肯浮上水面吃东西。
由于海鳗来到这里才几天,我们对它的进食习性知之甚少。考虑到它的体长已经几乎1米,相当于成年海鳗一半的长度,因此进食应当有相当的平衡性。要使水生动物能够健康生存,水的质量和营养十分关键。一些强壮的海鳗能够好多天不进食,但是在较长期的绝食期间,它们的健康会受到损害。
于是,水族馆的工作人员开始用各种方法来引诱这条海鳗进食。他们不但将各种不同的食物加工成各种形状或添加各种料味喂它,而且尝试用细鳞胡瓜鱼、鲱鱼的碎块、整只的虾或一片片鱿鱼,甚至活的诱饵给它吃,但是,这条海鳗对于这些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工作人员还对水柜里的水质多次进行检测,以确定各种数据是否符合海鳗的生活条件。他们还将水柜遮盖起来,并调低灯光的亮度以减少对海鳗的干扰。有人调侃:“这是为了模仿绿海鳗以前在酒吧的昏暗氛围。”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全然徒劳,绿海鳗继续着它的绝食行为。
到了第三个星期的周末,水族馆内的人们更加关注绿海鳗的命运。我也一直在思忖这个问题:这条海鳗不吃东西是否因为生了病呢?我们讨论了可选择的诊断方案,包括验血、寄生虫检查…… 此外,用进食管强行喂食的方案也被提了出来。
身体检查
水族馆的几名工作人员设法将海鳗用网子兜住,放进了一个溶解了麻醉粉末、装满水的大桶之中,并加上盖子,水中还放入了一块能释放气泡的石块,使海鳗在受检期间有足够的氧气。随着海鳗呼吸频率的减缓,镇静作用显现,它的身体开始有点侧翻。
过了几分钟,绿海鳗彻底安静下来。我们将它捞出水面,捧在手中,它已不会挣扎。我着手对海鳗做全身检查,试图寻找有病的迹象。它的淡绿色皮肤上生有一层薄薄的、此类海洋生物通常都会有的粘液。在海鳗长长的背鳍和尾部都没有看到受伤或不正常的痕迹,它的腹部也没有显现肿胀或其他问题,它的腮是正常的深红色,吻部和牙齿看上去都不错。作为检查鱼类的常规程序,我收集了腮部的一小块样本以及它的排泄物,并刮下一点粘液,分别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也没有发现任何寄生虫。我又从它尾部的血管里抽了一点血样,结果显示是在正常值范围内,没有任何疾病的症状。
在收集完诊断标本后,我们将一根细细的橡皮管通过海鳗的嘴巴插入到它的胃部,注射了一些鱼肉糊。我们觉得那天至少给它补充了一些营养。过后,我们将它放回到水柜里,并在鱼鳃上喷撒了一些盐水以解除镇静作用。几分钟后,海鳗开始游动。不久,它又游回到岩石堆中藏了起来。
当我坐在那里思考这条海鳗的行为时,我回忆起孩提时代对鱼类这种生物的印象。我最早对鱼类的接触可能是品尝肉联加工厂制作的鱼肉香肠;到了小学期间,则是与哥哥去小溪涉水捕捉小小的米诺鱼;在少年时代跟随父亲钓鱼时,一旦钓到8厘米以上的“大鱼”,我就会自豪地用照相机拍摄下来作为留念。小学5年级时,我在学校组织的游园会上赢得了一小缸金鱼,这激起了我对鱼类极大的兴趣。我时常长时间地注视着小金鱼在玻璃缸中畅游。
后来,我上了一所兽医学校,但从未料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鱼类医生”。在第4年快毕业时,我有机会跟随新英格兰水族馆的兽医主任实习。我被水族馆日常工作所面临的挑战和范围涉及广泛的水生动物医学所吸引。这一领域人类相对知之甚少,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少奥秘。于是,我在毕业后就来到了水族馆工作。
3个星期过去了,这条海鳗仍然拒绝进食。它会饿死吗?我们固然可以用喂食管给它输送营养,可这能维持多长时间呢?大家都被这一情况难住了。最终,有一位管理人员提出,与原来那位赠送绿海鳗的酒吧调酒师联系,征询他的意见,或许他能够提供一些怎样让海鳗进食的线索。于是,我们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在听了我们关于海鳗绝食的讲述之后,那位调酒师并没有立刻在电话中给予我们任何建议,但他同意不久就到水族馆来一次。
与人类的亲情
一天上午,我正在水族馆的展示厅巡视,一位高个子、肩膀宽阔的男子走了进来,他就是那位酒吧调酒师。只见他显露出疑惑的神态,径直走到绿海鳗栖息的水柜前,然后静静地站在那里,注视着水下的动静。
不多时,在水柜一角,岩石堆底部的空隙处,一个小脑袋探了出来,是绿海鳗现身了。它犹豫了一会儿,探测着周围的情况,然后缓缓地从躲藏处钻出。只见它小心翼翼地游到酒吧调酒师面前,停在那里,用它那双圆圆的、没有眼睑的眼睛,渴望地盯着他。
随后,令我诧异的是,绿海鳗开始以一种滑动而悄然的节律前后波浪形地摆动它的身体,而眼睛仍一直保持着与调酒师的对视。酒吧调酒师此时扬起嘴角,露出欣慰的神情,他面容中的疑虑顿时消失,老朋友又相聚了。
我记不得酒吧调酒师那天所说的爱抚话语,只记得他手里拿着一块块鱼片和小虾喂给海鳗吃的情景。我忘不了他那天脸上所显露出的亲情神态,而这种表情是在海鳗从隐藏处游向他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从那天起,海鳗再也没有拒绝过进食。
[编译自美国《路标》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