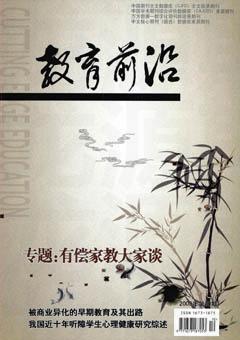译者的屈从性
买尔旦江 练丽娟
对翻译的研究势必涉及原作者与意者的关系问题,几千年来无论是西方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还是中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都向我们揭示了以下基本事实:翻译必然是译者将原作者用源语的符号系统构成的文体(原作)转换到的语符号系统(译作)的语言转换活动,是对原文的复制;译者的使命无疑是对原作的的正确理解与最佳传达本文从作者,原作,原作文本类型出发,探讨翻译行为时派生的,译者是屈从于原作的。
在译文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无论译文以何种面孔呈现在语文化中,其立足点是用源语构成的文本——原作。原作文本中的各种因素才是制约译者的主要因素。下面,我们看看原作中各因素是如何限制译者,使全部翻译行为始终具有了派生性。
作者真的死了吗
译者的首要的任务是将一种语言符号所表达的信息准确无误地运用另一种语言符号表达出来。毫无疑问,这种语际转换行为的起始点是作者用源语创作而成的原作中的语言符号。而面对原作时,译者首先要充当读者理解原文,再用目的语的言说方式将原作展现在目的语中。古今中外几千年的翻译活动中,译者总是规矩行事,不敢“越雷池半步”。
然而到了20世纪,这种观点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以海德格尔(Heidegger)和伽达默尔(Gadamer)为代表的现代释义学派全盘否定了原作的存在。之后,解构主义鼻祖德里达也否认了结构派提出的原作先结构,从而影响了无所谓原著的观点。无所谓原著,也就无所谓作者。随着(Barthes)的《作者之死》一书的出版,以往作者及原作的神圣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巴赫指出“作者不一定拥有原作,是语言,而不是作者在进行创作。”(笔译者)令人费解的是,难道作者不是通过语言进行创作的吗?更有甚者,他将作者和原作比作是父亲与儿子——父亲自然先于儿子来到世上,等到儿子出生,成了独立个体,便不再屈从于父亲了。这种观点是在牵强。我们不妨试想一下,父亲在养育儿子,促使其成人的过程中,必定向其灌输了自己的思想。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儿子必然受父亲的影响,至少,父亲与儿子是具有统一基因的。稍作分析,巴赫的“作者已死”的观点实在缺乏科学依据。诚然,作者既然是原作的第一创作者,其作品必然是他思想灵魂通过语言符号的艺术性再现。作者的“声音”始终存在于作品中,他还“活着”。
原作对译者的限制
纵观古今中外译界,原作的神圣地位从未受到扼杀。从而,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译者在实现自己的创造性的时候,总是受到原文这个客观存在的文本限制。如果将写作比成自由舞蹈,翻译就是译者戴着镣铐跳舞。不可否认,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但离开原作的无限制的译者创造性是不存在的,毕竟,主体的每一项功能都离不开客体赋予的“价值扩展空间”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认为,人沿着合理的方向,运用合理的手段,在可能的范围内有效地改造外部世界,从而实现自己的意志,就是主体性这种“人的本性”的实现,由此可知,翻译毕竟只是翻译,译者的创造性也至多是再创作的过程。这个“再”字已清楚地说明译者不肯能像作者那样尽自己能力进行创造。原文文本应是任何类型的翻译行为的出发点,译者应尊重原文文本这个客观事实,以它为客观依据和衡量译文的准绳。诚然,原文始终都在限制着译者的行为。
文本类型对译者的限制
翻译策略的选择取决于文本的类型。文本类型在翻译过程中不断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并使其不不屈从。
然而,根据文本类型选择翻译策略并非易事,因为在一种文本类型中可能会出现其他文本类型。根据赖斯的观点,文本的功能应基于文本的重心(gravity),即:内容、形式、呼吁。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文本是只包含一种类型的文本,大多数文本都是同时包含上述三种类型,并且基于文本预期目的而倾向于某一种类型。译者应考虑到文本的类型,文本的各语言要素以及文本产生影响的非语言要素,采用适合该文本类型的翻译策略。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约,不断斟酌不定,屈从于原文文本类型。
翻译行为自发生的那一刻起就具有了派生性,这种派生性决定了译者的角色是从属的,屈从的。其行为的本质是基于原文的再创造。
如上文所述,任何类型的翻译行为都以原作为出发点,是基于忠实于原作的再创造。显然,译者本人也是步步屈从于原作的。好的译作是译者合理地发挥自身屈从性和创造性之间张力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