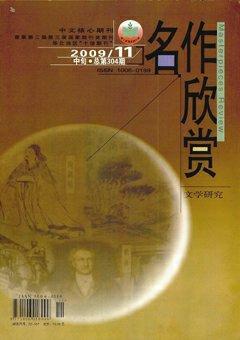深沉素朴的生命之歌
何 英
关键词:朴素意象 生命流注 本色世相
摘 要: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解读了《鸭窠围的夜》一文的魅力:首先是灌注在朴素意象中的生命感、湘西情,其次是以视听结合的笔法去呈现活色生香的本色世界。
《鸭窠围的夜》是沈从文的散文名篇,是其著名散文集《湘行散记》的第三篇。1934年初,为探母病,在离乡十余年后沈从文重返故乡,他乘船由常德沿沅水溯流而上,一路上随时向新婚的妻子张兆和报告旅途见闻,这些家书即是《湘行散记》的雏形,《鸭窠围的夜》就是在1934年1月16日晚间那封信的基础上改定的。它写隆冬时节的一场雪后,作者随船夜泊鸭窠围,于此从黄昏到午夜的所历所感。
朴素意象中的“生命流注”
风雪,无边的寒气,冷硬脏湿的棉被,瘦弱的孩子,打盹的母亲,无声的名片,摇曳的灯光,熊熊的火光,歌声,划拳声,嘱托声,羊叫声,锣鼓声……《鸭窠围的夜》以大量原生态的生活意象来呈现水上人的生活状态。这些朴素而生动的意象不仅体现出沈从文对湘西水手生活的熟悉,更寄寓着他对这些同乡们命运际遇的深刻理解。
文中数次提到小羊的叫声,作者说那“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这叫声让我“仿佛触着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看明白了这世界上一点东西,心里软和得很”。作者为什么会忧郁?他触着的、看明白的又是什么?小羊“固执而且柔和的叫声”让作者由被命运主宰的羊想到眼前这些安于天命的人——他们都是自然之子,活得质朴、率真,却又被动、艰辛,他们因缺乏对自身际遇和命运的自觉而让沈从文忧郁满怀——这忧郁缘于他对湘西无以言喻的爱。
文中写到临街的铺子里烤火者的情形时,特别地提到神龛下的名片,还说:“除了这些名片,那屋子里是不是还有比它更引人注意的东西呢?锯子,小捞兜,香烟大画片,装干栗子的口袋,……提起这些问题时使人心中很激动。”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何其平凡,作者为什么在提起它们时竟然会很激动?
《湘行散记》中的第五篇是《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写水手牛保的故事。牛保因与吊脚楼上的多情女子缠绵,一再延误启程时间,使同伴由催促而至辱骂,这让“我”对牛保充满了好奇。机缘凑巧,牛保回船时从“我”船边经过,“我”冒昧地招呼他,他竟笑着举起满满当当的棕衣口袋要请我吃核桃,且告诉“我”从吊脚楼得来的那口袋里还有栗子、干鱼等许多好吃的。为感谢牛保赠以核桃,“我”回馈他四个烟台大苹果。没想到牛保拿着那四个苹果飞奔而去,又上了吊脚楼,导致他的同伴那天骂哑了嗓子……这似乎可以作为“装干栗子的口袋”之美丽动人的一个小注脚,在沈从文看来,锯子、小捞兜、香烟大画片……无不与牛保们的多情故事相关联吧?
至于名片,亦引人遐想,那些红白名片上那“许多动人的名衔,军队上的连副,上士,一等兵,商号中的管事,当地的团总,保正,催租吏……”在沈从文看来,每一个名衔后面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些人各用一种不同的生活,来到这个地方,且同样的来到这些屋子里,坐在火边或靠近床边,逗留过若干时间。”这些名片让他感受到相识的不相识的各色湘西人的气息,且不能自已地去揣想他们后来的命运:“这些人离开此地后,在另一世界里还是继续活下去,但除了同自己的生活圈子中人发生关系以外,与一同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却仿佛便毫无关系可言了。”十几年前,沈从文之所以毅然离开湘西,独自北上求学,不就是为了“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语出《从文自传》)吗?虽然他为此历尽艰辛,受尽磨难,但也因之更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他的生命因“与一同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建立起更深广的联系而变得厚重丰富。虽然这时的沈从文已深切地意识到他的这些同乡们与世界、与变化着的时代的隔膜,但他并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之进行道德批判,也没有带着优越感去表达所谓的“同情”。那个听着吊脚楼上的声音终于按捺不住跑上岸去的临船水手,让沈从文想到了十五年前的自己,当年他年轻鲜活的生命也曾同样被禁锢在枯燥的漫漫长夜中,所以,他说:“我懂得那个忽然独自跑上岸去的人,为什么上去的理由!” “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
沈从文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唯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
怀着让“彼此生命流注”的热望,沈从文投身于写作;怀着对湘西无以言喻的爱,沈从文写下了《湘行散记》与《湘西》。在《湘西·题记》中他曾写道:“去乡约十五年,去年回到沅陵住了约四个月,社会新陈代谢,人事今昔情形不同已很多。然而另外又似乎有些情形还是一成不变。我心想:这些人被历史习惯所范围、所形成的一切,若写它出来,当不是一种徒劳。……大家对于地方坏处缺少真正认识,对于地方好处更不会有何热烈爱好。……所以当我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明乎此,我们就会懂得沈从文的对湘西社会的观察、思考与写作寄寓着何其深刻的理解、何其美好的期盼。
《鸭窠围的夜》展现了水上人生活的艰辛、悲苦,亦呈现出他们因真率、执著而凸显出的美丽与强悍,他们身上闪耀着即便被压抑、被摧残亦不磨灭的人性光辉。水手与吊脚楼上的妇人在那不无畸形的形式中追求着真挚缠绵的情与爱,而午夜时分水面上展开的那渔人与鱼的搏战,“已在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将在接连而来的每个夜晚依然继续存在。”这里渔人与鱼的搏战很像水手们与水的搏击。沈从文曾在《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文中这样描绘那些收入微薄的水手:“掌舵的八分钱一天,拦头的一角三分一天,小伙计一分二厘一天。在这个数目下,不问天气如何,这些人莫不皆得从天明起始到天黑为止,做他应分做的事情。遇应当下水时,便即刻跳下水中去。遇应当到滩石上爬行时,也毫不推辞即刻前去。在能用力气时,这些人就毫不吝惜力气打发了每个日子。”然而,当他们“人老了,或大六月发痧下痢,躺在空船里或太阳下死掉了,一生也就完事了。这条河中至少有十万个这样过日子的人”。这些水手与渔人的顽强坚韧让人肃然起敬,然而他们生命的卑微、命运的叵测,他们人生中每天都在上演着的这近乎原始人与自然抗争的酷烈之剧,怎能不让人起无言的哀戚?怎能不让人切盼变革?!
聪耳明目中的“本色世相”
《鸭窠围的夜》一文的成功,固然在于沈从文对湘西的深情,对那个世界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理解,而尤在于其高超的文字表现力,在其独特的生命与美学观念烛照下形成的文章笔法。
文章开篇从交代时令天气与泊船过程到描绘河岸上的景致,井然有序而富于质感,让人过目难忘——船只泊定后已是黄昏,天冷得“便是空气,也像快要冻结的样子”,两岸壁立的高山这时只剩余一抹深黑,最让人惊奇的是当地的建筑奇观——那离水三十丈上下像挂在半空中的吊脚楼。这吊脚楼,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长年与流水斗争的水手,寄身船中枯闷成疾的旅行者,以及其他过路人”,有了落脚之处。“这些人的疲劳与寂寞是从这些房子中可以一律解除的”。船只泊定后水手忙着做饭,饭后或躲进又冷又湿的硬棉被里去休息,或上岸去烤火谈天、赴吊脚楼上的幽会。午夜时分,水面上上演了一场“水中的鱼和水面的渔人生存的搏战”,那仿佛是一场“原始人与自然战争的情景”。作为风俗文化型作家,沈从文最善于描绘“境中之人”,在梦境中被美妙声音托起来上山去采虎耳草的翠翠,在橘园里时而捕蜻蜓、拾蝉蜕,时而光脚爬上树与人比赛摘橘子的夭夭(《长河》),抱着小丈夫听祖父说“女学生”的萧萧(《萧萧》),都让人过目难忘。而《鸭窠围的夜》中的“水上人”,乃是被水上的船与岸上的吊脚楼共同塑造成的。文章半写景物,半叙人事,全篇在人与自然契合的背景上动人地展现了这一方水上人“也是眼泪也是笑”的苦乐人生。
沈从文喜绘“境中之人”,似乎是缘于他的人与自然合一的文化理想,而他之善绘“境中之人”则缘于他从小就痴迷于人生这本大书,他说:“我永不厌倦的是‘看一切。”夜宿鸭窠围,由于始终栖身于小船之上,所以他“眼前”的景象其实十分有限。那何以《鸭窠围的夜》又触目即是画面,时时带给我们如身临其境般的真切?这恐怕要归功于沈从文那双灵异的耳朵了,他曾说:“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泼剌的微声,全因到耳时分量的不同,我记得那么清清楚楚。”那么此时,当夜色模糊了视线,耳之聪就更突出了:
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暗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只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
另外一处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声音。
羊还固执的鸣着。远处不知什么地方有锣鼓声音……
邻近一只大船上,水手们已静静的睡下了,只剩余一个人吸着烟,且时时刻刻把烟管敲着船舷。也像听着吊脚楼的声音,为那点声音所激动,引起种种联想,忽然按捺自己不住了,只听到他轻轻的骂着野话,擦了支自来火,点上一段废缆,跳上岸往吊脚楼那里去了。
这里的声音是“实在”的,但由之引出的场景却往往是想象中的:
我估计那些灯光同声音所在处,不是木筏上的头在取乐,就是水手们小商人在喝酒。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戴了水手特别为从常德府捎带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
禳土酬神还愿巫师的锣鼓。声音所在处必有火燎与九品蜡照耀争辉。炫目火光下必有头包红布的老巫师独立作旋风舞……(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当年因逃学而受责罚时沈从文就常常不由自主地去回忆见到的各种事情,“想象恰如生了一对翅膀,凭经验飞到各种动人事物上去。”这里由声音唤起的“想象”也无不出自过往的经验,故似幻而实真。沈从文以其慧心、聪耳、明目遣生花之妙笔,勾连今昔,让人不以耳听为虚,不疑眼见之实。
《鸭窠围的夜》带给我们的真切感不但缘于沈从文丰富的湘西生活阅历,而且缘于他立足于呈现“本色世相”的写作理念。前文已指出《鸭窠围的夜》以大量原生态的生活意象来呈现水上人的生活状态这一写作特色,并通过对文中部分意象的分析阐释了沈从文寄寓在其中的思想与情感。这里所谓的“立足于呈现‘本色世相”既与此密切相关,又有关乎沈从文美学思想的更深的内涵。
沈从文说:“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这段表白有助于我们理解沈从文与他的文学世界的关系,在他看来,艺术家不应该为俗常的社会价值所局限,而必须尊重世界的本相,按照万事万物本原的生命逻辑去呈现其存在状态。
所以,《鸭窠围的夜》虽写于左翼文学盛行的上世纪30年代,但在此文中我们丝毫看不到流行的阶级观念。沈从文也不以精英作家的启蒙立场自居,他总是怀着好奇去贴近世界,去捕捉每一个动人的表情,去倾听每个人心灵的律动。他为了听到那个按捺不住自己终于去了吊脚楼的邻船水手回船的声音,半夜还不肯睡去;他对那个唱曲时故意戴着水手捎来的镀金戒指理着鬓角的女子,非但没有嘲笑,还说那是“多动人的一幅图画!”
沈从文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两句话很耐人寻味。“照我思索”,能理解“我”,好像理所当然。那何以“照我思索”,就可认识“人”呢?怎样的思索才可“认识‘人”呢?唯有立足于“本色世相”,立足于呈现“人”自身的生命逻辑吧?如此“思索”,让沈从文创造出一个素朴而庄严的文学世界。
张新颖先生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家是以某种理论装备或价值预设去面对外在世界的,与之相比,沈从文的特别之处乃是:“沈从文的‘看,突出的并不是‘看的个人和‘看的有色眼镜,而是直接‘看到的现象。”我们不能完全否认那些运用理论与价值预设的写作的价值,但沈从文这种直接让人看到“现象”,立足于“本色世相”的写作无疑充满了魅力,因为就如同我们在《鸭窠围的夜》一文中领略到的——那是一个真正活色生香的世界。
作者简介:何英,文学硕士,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抽象的抒情》,范桥、吴子慧、小飞编《沈从文散文》第3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2] 沈从文《从文自传·女难》,范桥、吴子慧、小飞编《沈从文散文》第2集。
[3] 沈从文《从文自传·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范桥、吴子慧、小飞编《沈从文散文》第2集。
[4] 张新颖《沈从文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责任编辑: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