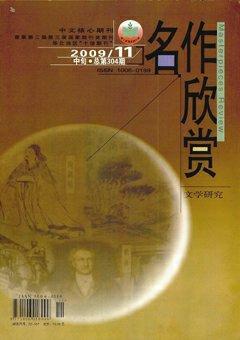略论黄仲则诗歌中的矛盾心态及其解脱之道
关键词:黄仲则 诗歌 出处两难 解脱之道
摘 要:清代诗人黄仲则,生平屡遭挫折,唯有借助诗歌宣泄心灵的矛盾心态,并借助诗歌,找寻解脱重负的方式。研究此种心态,对研究作家的心态史或心灵史很有启迪意义,对考察清中叶文人尤其是不第文人的命运、创作也有借鉴意义。
黄仲则(1749—1783),名景仁,字汉镛,一字仲则,清代著名诗人,“毗陵(常州)七子”之一。其诗不乏激昂慷慨、意气蓬勃、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也有游山历水、俊逸爽发、挟带金石之声的壮兴,更多叹贫嗟苦、啼饥号寒、抒发穷愁愤慨的心声。其间,出处两难的矛盾心态,交织纠缠,成为其诗情感序列中的重要主题。
一、黄诗充溢着出处两难的矛盾心态
黄仲则现存诗歌近1200首,诗中的情感丰富多彩,尤为鲜明的是他抨击是非颠倒的现实,悲慨自己怀才不遇的命运的怨愤之情,与怨愤之情共生的便是纠结他一生的出处两难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我们从三个方面略作分析:
首先,从时间跨度来讲,这种心态贯穿其创作始终。其《两当轩集》收录的第一首诗《初春》①,其内心矛盾已可见端倪,“未觉毡炉暖,旋怀柑酒新。”此诗题下注“癸未年起”,这一年,黄仲则十五岁。江南初春,小小少年竟连毡炉也不觉其暖,是气候的异常,也是其心态的异常。此年,黄仲则始专攻诗,而《初春》一诗,隐隐中注定其与世界的不相谐和。看似无意,终成必然。稍后的《舟中咏怀》云“长歌阙已再,倾耳谁与应?殊悲生事薄,聊觉野情胜”,已明显表达出诗人对现实生存的无奈无力、对自然野趣的钟情,其内心的挣扎跃然纸上。这种矛盾心态,至其晚年,始终未曾消歇。《除夕述怀》作于1781年,距其生命终了只有两年,黄仲则慨叹“俯仰既无藉,出处弥自惭”。同作于此年春的《恼花篇时寓法源寺》,黄仲则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出处之难:“无人之境讵可得,徒使冰炭交心胸。”而1782年,其留存的诗歌寥寥无几,1783年夏,他已溘然长逝。实际上,作于1781年的诗歌,几乎可以看成其生命的最后悲唱了。显然,从其作诗伊始,至其生命结束,出处两难的矛盾心态始终挥之不去。
其次,从其境遇来看,其一生多逆境,使其始终在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中难以自拔。于他而言,逆境时时有之。有亲人的陆续离去之痛:童年丧父、少年失去祖父母、兄长,他经历的是灰色的童年、阴暗的少年;有勉力养家之难:其《自叙》云“家益贫,出为负米游”并非虚语,其挚友洪亮吉云“君为诸生,家甚贫”②可资证明;有疾病缠身之苦,“一身零落已自怜,况复疾来相缠”,身体病痛,日蚀其壮心;更具毁灭性的打击是才名早著却屡试不中。家庭小环境的苦难尚可慢慢承担,来自社会大环境的打压以他一己之力实在难以消解。生命中的如斯挫折,使他在诗歌中屡屡表达出处两难的困惑:“风波一失万里长,落落行藏谁共商”(《狄港舟次遇徐逊斋太守罢官归滇南》)、“大陆浮沉且未休,吾侪身世将安托”(《偕稚存望洪泽湖有感》)。
最后,从写作意图来看,不论是他的内心独白,还是与友朋交游酬唱之作,他的出处两难之情,均显露无遗。其《言怀》一诗云“可知战胜浑难事,一任浮生付浊醪”,显见其在出处两难中,无可奈何,故作洒脱。如果说内心独白似有强自安慰之嫌的话,那么,与友朋交游酬唱之作中反复提及自己的矛盾心态,无疑是在寻求一种情感的支持。无论是 “才命古难一,行藏我欲迷”(《寄丽亭》)、“风波一失万里长,落落行藏谁共商”之类诗歌中向前辈仇丽亭、徐逊斋悲慨身世,希望获得指点;还是“商略身世事,百法欠帖妥”(《余伯扶少云昆仲施大雪帆消寒夜集分赋》)、“行藏聊自点,歌哭向谁真”(《得吴竹桥书促北行留别程端立》)之类朋辈间的倾诉,意在宣泄内心压抑,都可以看出,出处之难的情感是黄诗中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个基本主题不光体现在其诗词中,甚至体现在其画作中,其《蒲团看剑图》直可视为其出处两难心态的高度浓缩,其友左辅、赵怀玉分别为之作了《题黄秀才〈蒲团看剑图〉》《金缕曲·黄仲则〈蒲团按剑图〉》等诗词,亦可视为此图的解说词,这其实也是黄仲则的矛盾心态在朋辈间激起的共鸣与回应。左辅体察其处境之悲,“雄心岂向湖海尽,欲摄天地归蒲团”③,赵怀玉引黄仲则为同道,真诚安慰中不乏无奈,“真空毕竟何时了,误平生,输他柔骨,工于媚鳌。放下屠刀原作佛,吾辈行藏难料。便一任,路旁鬼笑。”④两首诗词皆因《蒲团看剑图》引发,“蒲团”象征出世,“看剑”象征入世,出处之难,即两人所言“此意沉吟恨难剖”、“触起心头千古恨”之“恨”,正在于“行藏难料”。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出处之难的普遍意义。
二、出处之难的心态缘由
黄诗中充溢着出处两难的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态的产生之因,首先是源于黄仲则用世之志破灭,处世艰难。黄仲则生在一个典型的文人家庭(其祖父是县学训导,其父亲为生员)之中,此种家庭保证了经济上从事学术文化的可能性,在文化上也保证了他从小能够受到正规的教育,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也是意图以功名入仕。黄仲则也有过对武功的向往,《少年行》中“男儿作健向沙场,自爱登台不望乡”可见其为国效力、驰骋沙场的豪情壮志。《写怀示友人》中“宝马不恋粟,男儿重横行”传达出男儿应当纵横沙场的豪迈气概。其颇为自诩的《虞忠肃祠》更以对英雄的追慕来倾吐自己建立武功的热情。虞忠肃指挥采石一役而致大捷,南宋江山得以安稳。黄仲则称誉其为“肃爽须眉一代雄”,于中寄托了自身渴望待机建功的宏图伟志。
然而,其自身终究无缘沙场,黄仲则只有走读书之路,考取功名以兴家旺族。且无论是其文人家庭,还是其自身禀赋(“年八九岁,试使为制举文,援笔立就”⑤),条件均极有利,而其科举之途迈出的第一步,也颇为顺利,十六岁时,“吾乡应童子试者三千人,君出即冠其军”⑥。然而,造化弄人,举人之试,却是其一生不曾迈过的关口。其一生四应江宁乡试,一应省试,三应顺天乡试,均铩羽而归。而此种遭遇,正是其时文士的普遍经历。以乾隆九年为例,江南乡试(合安徽、江苏两省)分上下江取中,此科(甲子科)应中额共114名⑦,而赶考者则在两万名左右。可以说,乡试几乎成为科举全程中最不易登进的一级。黄仲则的遭遇,正是当时士人在仕进之路上艰难跋涉的缩影。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毗陵七子”中,洪亮吉、赵怀玉、杨伦等都是三十五左右方中举,才子尚且如此,资质不如他们的士人,中举之难可想而知,从开蒙读书至一举及第,岂止十年寒窗苦。
其次,用世难,出世更难。读书应试,必须要有相当的经济支撑,士子们往往要一面应试,一面负起养家之责,艰难困苦,可以想见。功名可以不要,家庭的责任却不能轻抛。可是,封建社会提供给文人的出路实在少之又少。达时兼济天下不难,穷则独善其身却非易事,所谓“排遣中年易,支持八口难”,“毗陵七子”中赵怀玉高吟的“人生痛饮余莫顾,明日拍浮任何游”⑧的洒脱注定是酒客狂言。
现实如斯沉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太过遥远,“齐家”远比“修身”更为现实,也更为艰难,面临“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的窘境,理想肯定要搁置一边。且治国之责,下层文人无由承担,而一旦不能进入国家权力的纽带中,“平天下”俨然成为空幻之词甚至是对文人的嘲弄之词。范仲淹所说的“进退之忧”只是对谪官而言,他们曾进入权力中心,居庙堂而忧黎民是其职责所系,滑落边缘,也不忘忧思朝政;而对普通文人,“进退之忧” 显然有别于此,进之忧,在于前途不明,读书求仕并不必然成功;退之忧,在于养家之责难卸,养家之道难寻,“学贾非所长,学剑非所喜,学农昧菽粟,学律恶鞭棰。”⑨此忧,正是其时不第文人的普遍性焦虑。
再次,出处之难,是黄仲则对时代的敏锐洞察。黄仲则生于乾隆时期,梁启超论及此际云“时方以科举笼罩天下,学者自宜十九从兹途出”,认为此际“俗既俭朴,事畜易周,而寒士素惯淡泊,故得与世无竞,而终其身于学”,“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⑩,无疑,梁启超的数语勾勒乾嘉学风,传神中却不乏理想色彩。盛世的局面,所造宏观形势,政治、经济、文化等确会极一时之盛,但是,施之个体境遇,仍是千差万别。即以“毗陵七子”而言,不忧贫的前提须家境殷实,七子中孙星衍庶几近之,游幕他乡的黄仲则、洪亮吉等则时见抒忧之作。而黄仲则出处两难的矛盾心态产生,不仅是忧贫所致,更是对时代认知的敏感所致。“科举笼罩天下”,无人可以幸免。侥幸科举入世,也难有伸才之机。黄仲则曾有过“谁于笼鹤采丰标”的期望,而在京城,见识了各色高级官僚之后,他写下了名作《圈虎行》,写照了才人的命运,即令凶猛如老虎,一旦被豢养、被调教,也终于“似张虎威实媚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用世其实只是成为“笼中鹤”、“圈中虎”而已。出世难消养家之忧,入世又有失去人格尊严之虞。黄仲则洞悉了时代,却无力超越,使他内心反复挣扎。
三、出处之难的解脱之道
黄仲则的诗歌中,提供摆脱焦虑的方法主要是借助诗歌展开幻想,以仙境、幽境冲淡现实的困扰:
(一)仙境与追寻之念。现实中,士子为求取功名,游学他乡,孤身一人,心念的是家庭的温馨;蹉跎岁月,渴盼的是生命的长久,藉此,可以理解黄仲则“乘槎未许到星阙,采药何年傍祖洲”(《后观潮行》)的疑虑中潜藏的希望。“乘槎”可至天庭,晋张华《博物志》及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均有记载。“祖洲”则传说有“不死之草”,正可医治诗人心头生命如寄的忧恐。诗人还曾幻想,“径欲身骑二龙去,御气直到扶桑东。”兴发弃尘世而遨游太空的想望虽高远,而神想之诞幻,与身游之征实相倚而生,诗人不得不清醒地面对现实:仙境可慕而不可攀。但是,诗人反复地传达着自己的追慕之心,“终当粗毕向平心,来向云中抱云住。”诗人出世之心非常强烈,甘愿舍弃人间生活,与“黄山白猿”相从,“黄山白猿千年物,出没无时不知穴。……山空日暮无可托,我欲拾橡来相从。”(《重游齐云山》)人世间已让其感到了无趣味。追随“千年白猿”,清楚透露其对仙境的追慕。
诗人对于仙境的追寻,从积极意义上来理解,可以看成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而从消极意义上来体味,不难看出其对人世的厌弃和逃避。在看到黄仲则逃避生活的构想时,我们确实应当秉持“同情的理解”。实际上,在艰难的生活中,诗人还能有这样看似天真的想象,已是非常令人抱以敬意了。
总之,仰慕仙道、充满玄思的诗人,每登临山水,往往或生羽化登仙之想,或思及美丽的神话故事而凄然感怀。因为摆脱尘世之累的意识,潜藏在那些诗人的心头,遇到一定的契机,就会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黄仲则正以其诗歌透露了自身强烈的出世之想。
(二)幽境与隐居之情。仕隐观念一直影响着古代文人对于人生的抉择,黄仲则也在出处之间苦苦徘徊。诗人内心深处有着“宝刀不念桑,男儿重横行”的雄迈追求,洪亮吉云:“先生长身伉爽,读书击剑有古侠士风。”{11}可是,严酷的生活终究日渐消磨侵蚀着其激情,其诗也愈显对于生活的退缩。壮怀消退,取而代之即是“自笑出门无远志,五湖三亩是归人”(《舟中咏怀》)的归隐之心。黄仲则极想在山林之中、“人境”之外“幽处”,他对世外桃源充满向往:“千载桃花源,想象遗民宅。自崖讵能从,问津信何益?”而桃源已杳,斯境难寻,只有在人间苦度,在内心追随。神仙难以做得,那就退而求其次,做做樵夫,或者渔夫:
一衣与一食,千里悬相招。吁嗟劳人亦已劳,何日归作西峰樵!(《道中偶成》)
出郭病躯愁直视,登高短发愧旁观。升沉不用君平卜,已办秋江一钓竿。(《杂感四首》之一)
当然,樵夫、渔夫都只是黄仲则对于隐居生活的设想,他在进退之间徘徊犹豫:“湖吞全楚尽,天压百蛮低。才命古难一,行藏我欲迷。”(《寄丽亭》)出处两难让他甚至否定自己的生活,觉得人生一场“百年羁旅夜,生事太无聊”(《康王庙夜宿》)。
审视黄仲则的矛盾心态,可以发现,仙境、幽境,其实都不是他直面的纯粹的客观世界,而是其想象中的心灵停泊之所。壮志难宣泄,是山水容纳了诗人郁闷的心灵。其山水之诗,正是其心境的曲折反映。其诗歌构建的心灵世界,具化出其出世与入世的矛盾纠缠。“毗陵七子”之赵怀玉与孙星衍絮谈,也时有“流传自有名山在,出处宁为世网婴”{12}的类似慨叹。出世难,入世亦难,正是其时不第文人普遍性的遭遇。
总之,黄仲则作为性灵派中代表乾嘉诗风的一位,其“诗有真性情”,代表了“下层失意知识分子的感情”。其出处两难的心境,借助诗歌得到了充分宣泄,研究此种心境在诗歌中的表现及其解脱方式,对研究作家的心态史或心灵史很有启迪意义,对考察清中叶文人尤其是不第文人的命运、创作也有借鉴意义。清代盛世文人心灵悸动的轨迹并不一致,貌似平稳的时代潮流下其实已经暗流涌动。而在清中叶以后,士人的社会地位普遍回落,经济上相对日益贫困化后,寒士诗人群体不断兴起,黄仲则等部分乾隆时期任天率性的寒士诗人遭际及其表露出处两难心境的诗歌,正是暗流涌动的第一波,正是“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的先知先觉之声。
本文系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KYY08051)“毗陵(常州)七子的交游诗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蓝士英,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
① 黄景仁.两当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以下未注明的黄仲则诗歌皆出自本书.
②⑤⑥⑨ 黄树,陈弼,章谷等.黄仲则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③⑧{12} 赵怀玉.亦有生斋集诗[M].嘉庆间刻本.
④ 左辅.念宛斋诗集[M]. 光绪石印本.
⑦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⑩ 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11} 洪亮吉.玉尘集[M].光绪十六年粟香室刻本.
(责任编辑:古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