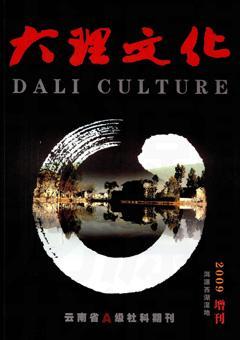前世的西湖
杨友泉
没有约定,说来就来了。
从浮桥进入小船,船是常见的小木船,用柳树做的,柳木经泡。泡久了、晒久了的柳木透出一种耐看的黑,黑中带着白、带着灰,透着一种深沉的坚硬。
和柳木的黑呼应着的还有水,早晨的阳光是斜照的,秋天微凉的空气,很清新,阳光透过空气渗入水里,水就是黑的。微微簇着浪的水,拍打着船舷,我的手里也拿着桨,也一下一下地划着,湖里的水不时被船桨溅起,—片、—块,或者—绺,像一朵朵白花,一条条银链。我想,这些白花银链,是黑水突然离开巨大的母体,发出的灿然一笑。
不一会,小船穿过两座小石桥,绕过一个村落,到了村子的另一面。这时视野更开阔了,村子里鸡鸣狗吠,黑瓦绿树,时不时还飘起一绺炊烟,这样的村子有好几个,布陈在湖中央。村与村时而首尾相连,时而遥不可期,时而叠在一起、抱成一堆。这些住在岛上的村子,常常就由一道汊港把它隔开。
真正有隔世之感的,是到了西湖南面。那时,世中人,完全脱离了现世的一丝一亳的羁绊。
小船依依呀呀的,仍然不惊风,不簇浪,静默着,就进入了一个梦境。好像进入这样一块处子样纯净的时空,必得用静默、用听得见一颗针坠地的沉静,才能进入,才能听得见、听得清、听得明,才晓得,自己是不期而至的,寻找百年后,就在这蓦然间,闯进了属于心统属的那块领地。
这样的梦境、这样的时空,必得有伟大的事物隔绝着,必得有超乎意志的坚贞护卫着。
这个伟大的事物就是西湖西面的苍山云弄峰,高拔过天的身姿,以万夫莫挡之势,挡住西面任何一个侵入者;另一位超乎意志的坚贞护卫者,就是西湖南面的覆钟山,他的身姿虽然没有云弄峰高拔过天,但却挺拔傲然,以陡峭悬壁,肃然而大跨度地站在南面,没有哪一位轻易过得了这个关隘。
千万年的固守之后,蓄就了这一泓处子般宁静的水。
船桨划动着,水声依呀着,这依呀声,像在哼唱一首远古的歌,使这里的时空更加宁静。我往水里看了看,我看到一条又一条水痕,把什么弄皱了。我停住了手里的桨,往远处的水中一看,这是倒映在水中的覆钟山,小船一到,静穆在水中的覆钟山,开始颤抖,开始变形、扭曲——是啊,每一点的响动,对于这片处子般的静穆,都是惊心动魄的,都会留下这样那样的遗憾,尽管我们乘的小船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小船没有发动机,所以也没有留下油污,但是,我们的惊扰,让这泰然安坐千万年的覆钟山,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丝不安呢?
水似乎更黑了,当然,这种黑不是受污染过的那种黑,是水中的矿物使然。果然,在船慢下来时,就能看清深水里的水草,水草各式各样,最有形状的是水中形似宝塔的那种,茎节分明,主茎直立,遍布湖中。这种长势像塔的水草,在湖底密密麻麻分布着,像高山上的雪杉,起起伏伏,波澜壮阔,像看一桢水底地图。光影在茎叶间晃过,可以看到停在叶脉上的一个虫趸,或躲在叶边隐匿的一条小鱼。在这个充满光影和幻觉的水底,存在着一个可以幻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条小船的到来,每一把木桨的划动,都在它们的世界里注^新的空气,带给它们新鲜和刺激。当然,也可能带给他们纷扰。
小船划了近两个小时,渐渐对西湖有了更切近的了解,水中泊着的不仅仅是六村七岛,还有一个个小洲,洲上驻着一株株老树,由于已近中秋,叶片大多凋零,但枝干仍然曲虬粗壮,看上去如蹲似坐,像一个老人在那里张望着什么,又像在那里静自沉思,一坐百年。
除了长着老树的小洲外,还有长着芦苇的、长着青草的,甚至还有长着青菜和稻子的小洲。
小船在无数个小洲间穿插、出没,明明眼前没有出路了,绕过这个长着芦苇和水草的小洲,一条水道却赫然出现在眼前,泄着一道白光,不禁让人胸中为之一颤,这巧夺天工、天造地设的奇迹,就这般不惊不疾地潜伏着、埋藏着。
在我们的小船经过这条泄着白光的水道时,却发现在水道的右边有一个小洲,两块篮球场那么大,上面的地是用来耕种的,土是黑土,一看就知道这种土质种庄稼是上好的。这块地大概是两家人的,地被窄窄的地埂分成了四、五块,上面有两块簸箕大的小白菜,几个大人在上面劳作着,两个小孩在地边的树下玩着什么。边上泊着两条小木船,看样子他们就是乘这两条小木船到这个小洲上来的。
他们穿着白族人常穿的服装,戴着白族人常戴的头巾,抬头看了看我们,笑了一下,又低下头去开墒培土,好像和别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我却觉得有太多的不同。于是,我扶着被垒得高过墒地很多的护堤,摇了摇,小洲上的墒地真的竟摇晃起来,和我坐在一条船里的人说,你在整哪样!我这才发现,小洲没有摇,菜地也没有摇,是小船在摇。这位当地人告诉我,你扶着的护堤,是从湖底捞起来的淤泥砌成的,里面有水草,干了后的淤泥特别结实。过了这个季节,湖里的水位会上涨,那时这些护堤就起作用了,土里的干草就会紧紧抓住泥巴,护住这块菜地。
这时,我们的小船穿过一个村庄,村里的房屋离水道不远,因而很容易就能看到,房屋是常见的瓦房。我一直在想,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真是一个奇迹。
同船的一位当地人间我,你看出这些房子有没有异处。我看了一会,果然看到有一两间房屋开裂,要倾颓的样子。我以为在潮湿的地方建盖的房屋,柱梁容易被水气腐蚀。我的这个观点说出后遭到了他的否定,他说,这里的房屋有一部分是歪的,特别是盖在岛边的房子,一年后,房子就开始倾斜,一个人一辈子要盖三次房子。
我再看岛边房子时,正的的确不多,正的大都是新盖的。这些瓦房在六个岛上,是一个令人景仰的景观,让人们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更多的好奇,这是让人们对西湖产生向往的又一个原因。
这些黛黑的屋脊和灰色的土墙,被或深或浅的竹林和树木掩映着;让三三两两或在垂钓,或在劳作,或在划船打鱼的人有一个温暖的居所,它已经成了西湖又一道令人瞩目的景观,可是它同时却是如此的虚弱,那样的娇贵。另一位当地人又说,住在岛上的人家,往往一辈子要盖三次房,住在岛边沿的,盖好的房子一年后就会倾斜,十年后,墙体就会开裂。
吃过饭后,还想着岛民住房,我心里还有一个结,还想到岛上,了解一些岛民的生活。
这次我们没有乘船,而是走过两个栽着高大荷叶的池塘,上了一条通往由北向南的栈道。这条水中栈道看来已建成多年,黑中带白的质地,坚硬牢固。这条四、五百米的栈道把我们送到岛上,上到岛上才知道我们来的不是时候,这是下午两点来钟,岛民们都到田地里收割水稻了,几户人家的院子里,晒着黄灿灿的水稻,只有老人在一边看护打盹。
巷子里不时看到一个个沼气池,这些沼气池依墙而建,我问同行的一个当地朋友,其他地方的沼气池是在地下的,这里的沼气池盖得咋这样高?这位朋友说,以前的沼气池是建在地下,但温度低,温度低产出的沼气少,一个月要换一次稻草牛粪,换得勤不算,沼气还不够用。把沼气池建得高一些,温度就能提高。即使西湖涨水,把地面淹了,也淹不到它,是一举两得。
提到牛粪,我想起了洱源奶牛有名,又问,岛上是不是也养?
咋不养呢?不养他们一辈子咋盖得了三次房。奶牛的粪用来制沼气,你们跟我来。边说边带我们到了沼气站。
他说,一个三口之家,每月交来一吨牛粪,就能换到公司一个月的沼气供应,够他们一家煮饭炒菜用。
能够使用清洁能源当然好,难怪很难看到岛上袅袅的炊烟。
他指了指铁栅门里卧着的几个蓝色的大罐子,说这几个大罐子可以供一百二十多户人家用。他又说,在别的岛,开始建出售沼气基地,卖给当地跑营运的车辆。我们这个地方坡坎少,汽车烧下来一年能节约一万来块。把烧油车改造成烧气车,改造费也不高,六千多块就能改好。
这时,我们来到湖边,准备乘船返回。湖边两条船里有两位妇人洗白菜,白菜茎白叶肥,不一会就洗了半船。我对那位朋友说,这里的菜长得好。那位朋友说,是不错。前几年岛民爱用尿素,尿素好是好,可菜地被水一淹,尿素就跑到水里,这两年引进了一种缓释肥,埋在菜根上,菜根需要了,它就释放,不需要了,它就不溶解。即使菜地被水淹了,它也不溶解,不释放,始终能保持水体的清洁。
我居住在下关,我知道大多数下关人都在饮用洱海水,西湖是洱海的源头之一,西湖对于洱海的重要性,对每个下关人的重要性,我想已不必多说,我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只有在心里默默地感谢上游的人们,他们所做出的努力,所付出的艰辛,我们要始终牢记,心怀感恩。
在返回的船上,我回过头去望了望小村,我知道我不能走进其中的某一户人家了,心中稍感遗憾,但是,我知道的也许也不算少了。千百年来,六村七岛的人们能在一片片奇特的土地上生存繁衍,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船上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房子在不成了,就掀了重盖,重盖的位置还是原来的位置,重盖的地基还是原来的地基,他们的一辈子就是这样,盖了拆,拆了又盖,盖了再拆,仿佛在和命运中的某种神秘力量在对抗,彼消此长,彼长此消,坚守着属于自己的那个轮回。
这多像一个远古的童话,一个关于人自身的寓言。